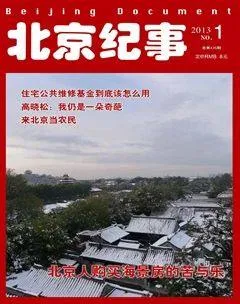年的“37分貝”
曹磊

?90年代初廠甸廟會手提燈籠的小姑娘
住平房大雜院那會兒,聽街坊講過一個笑話……很久以前,胡同里住著一位傻子。年三十夜里,家家戶戶剁餡包餃子。傻子過的是有今沒明的日子,拿不出買面、買肉的錢,聽見前后左右全都“梆梆梆”“梆梆梆”,剁得來勁,他也把家里的菜刀、案板找出來,鉚足了勁,“梆梆梆”“梆梆梆”地干剁,為的是湊個熱鬧,爭口氣,讓大伙聽聽,自己日子不比別人差,過年也包餃子了。
包餃子是中國人過年的保留節目,捎帶手,還得預備幾樣好吃、耐放,能下酒,也能下飯的年菜。三毛五分錢一斤的高級帶魚,收拾干凈,用剪子鉸成段,拿作料腌透了。蜂窩煤爐子的風門徹底打開,爐蓋、爐圈全都摘掉,火燒得旺旺的,坐上油鍋,把帶魚放進去“呲啦、呲啦”炸。肉厚的中段炸到半熟,留著年歇那幾天燉著吃,做紅燒帶魚;肉少的頭尾炸到全熟,吃的時候重新回回鍋,徹底炸酥、炸透,撒點花椒鹽,就是下酒的好菜。
子曾經曰過,一羊是趕,倆羊也是放。大過年的,費勁巴拉預備一鍋熱油,炸帶魚是炸,炸別的也是炸,索性那就多炸幾樣。有肥有瘦的后臀尖,細細剁成餡,摻上豆腐泥、饅頭渣,拿醬油、蔥花什么的調調味,“呲啦、呲啦”下鍋炸,炸葷丸子;水靈靈的胡蘿卜,細細擦成絲,用面糊調了,擱點香菜末、五香粉,也是“呲啦、呲啦”下鍋炸,炸素丸子。這么個裉節上,饞嘴的小孩必定人手一雙筷子,守著爐子吃“鍋挑兒”。幾個孩子你爭我搶,很快就亂了次序,生出不大不小的矛盾:“該我吃了,你剛才吃了!……沒吃,剛才是他吃的!……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吃了!……沒吃,沒吃,就是沒吃!……嗯,媽,他欺負人!”
“梆梆梆”的剁餡聲,“呲啦、呲啦”的熱油聲,“咕嘟、咕嘟”的燉肉聲,“噼里啪啦”剝花生、嗑瓜子的聲音,再加上孩子們的歡鬧,大人們的寒暄,電視機里的喜氣洋洋……如此種種,混合著魚香、肉香、茶水香、煙酒香,從每家每戶的窗戶里飄散出來,彌漫在大街小巷,悄悄發生著化學反應,滋潤著街面上的每個人。“噼——啪”……化學反應的過程中偶爾發出兩聲脆響,那是淘氣的小孩兜里揣著小鞭兒,邊走邊放。
街上的行人面帶喜色,多數都沒空著手。男女老少、新衣新帽、連說帶笑,手里提摟著點心匣子的,那不用問,準是串門走親戚的一家子。單喯一人,自行車上馱著整袋的米、整桶的油、整箱水果之類大件年貨的,十有八九,則是單位剛發完東西,正往家倒騰呢。東西的花色和數量直接影響著他們跟別人打招呼的態度。單位效益好的這位,東西發得多,自行車前后全裝滿了,騎都沒法騎,只能慢慢推著往家走,滿頭大汗、氣喘吁吁,精神方面卻是相當地煥發,相當地昂揚,前后左右瞎尋摸,就盼著能碰見個把熟人,好跟人家顯擺、顯擺,發自內心地吆喝一句:“哦,您好、您好,過年好!……是是是,我們單位今兒發東西啦!”
您聽聽,這句話連標點符號都算上,個頂個從嘴里說出來,全都帶著水音。哪怕張嘴的時候沒留神,喝了一口西北風,咳嗽兩下,那都跟放二踢腳似的……“廳——嘡”,全是雙響。要是單位的效益不好,發的東西數量少,花色品種還不多,那這位走在大街上,都不好意思拿正眼瞧人,甭管走到哪兒,全都蔫頭耷拉腦,屬黃花魚的——溜邊。
北京首次實行禁放是在1994年,之后雖然又經歷過“禁改限”的十來年,大街上、胡同里卻很少再能聽到孩子們連跑帶鬧,放鞭炮的聲音。隨同鞭炮聲一起消失的還有挨家挨戶過年殺雞的動靜。
30多年以前,市面上沒有加工好的白條雞,商店、市場賣的都是活雞,售貨員不管宰,想吃雞只能自己動手。二十七殺公雞,雞跟“吉”同音,老北京人為了圖個吉利,討個好彩頭,年夜飯的餐桌上必須要有一只整雞。每到小年前后,街坊鄰居們就要陸陸續續地買雞、殺雞。殺雞的人搬個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兩個膝蓋夾住雞身子,左手薅住雞脖子后邊的羽毛,使勁往后一拽,再用右手把雞喉嚨部位的毛差不多揪干凈,然后抄起菜刀狠狠一抹,大公雞、老母雞拖著長音,白眼一翻……“呃、呃、呃”,發出最后幾聲哀鳴,奔西方極樂世界去了。這也算是那個時代北京過年特有的一種聲音。
過年殺雞這一刀,考驗的是技術,更是膽量,碰上膽小、手軟的“二把刀”,不光人難受,雞也跟著遭罪。記得住大雜院那會兒,界壁新搬來了小公母倆,爺們兒是在機關上班的小干部,媳婦是小學老師。兩口子全是知識分子,心靈本來就很脆弱,結婚前跟著父母當甩手掌柜,過年?等吃現成的,結婚以后,頭回頂門立戶過日子,想自己動手還真沒那個膽子。
殺雞的計劃今推明、明推后,一直拖到臘月二十八,小干部實在繃不住勁了,下班回家時,車把上掛了只大公雞,少說得有六七斤。小公母倆手里攥著菜刀,你推我讓。折騰到最后,新媳婦眼睛一楞楞,猛地把刀往爺們兒手里一塞,還在口頭上給予了適當鼓勵:“你去!趕緊的!就這么點事,你是不是個男人!?”

?燃放煙花
小干部讓媳婦一擠對,街坊鄰居再一起哄架秧子,當時血灌頂梁,一股男子漢大丈夫的豪情壯志涌上心頭。手里緊握切菜刀,顫顫巍巍、哆哆嗦嗦,嘴里好像還小聲叨咕了兩句勵志口號,左手摁住大公雞,右手掄圓了,咬牙閉眼,照著雞脖子,“當”就是一刀。原本想給自己和雞都來個痛快,一刀把腦袋剁下去,然而終究還是賊人膽虛,菜刀撒著狠掄到一半,手上的勁就先泄了,刀的軌跡也跟著拐了彎,“當”的一下,正好剁在雞大腿上。大公雞腿上一疼,慘叫一聲,也是個急勁,噌、噌、噌,連躥帶飛可就上了房了。站在房坡上,蜷著受傷的那條腿,金雞獨立,伸著脖子、瞪著眼,沖著小干部,“哦哦哦”,打了個鳴,意思好像是說:“小樣,想要我的命!姥姥!”
打完這個鳴,大公雞撲棱兩下翅膀,翻過房脊,就跑沒影了。小公母倆和看熱鬧的閑人站在院里,苶呆呆發愣,仰頭瞧了老半天,最后還是街坊大爺有深沉,最先回過味來,急赤白臉喊了一嗓子:“雞跑啦,追去呀!”大伙這才反應過來,稀里胡嚕、稀里胡嚕,手忙腳亂往外追。至于說這只雞最后到底是讓別人撿洋落給燉了,還是真的自由了,那就是我們胡同的千古之謎了。
編輯 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