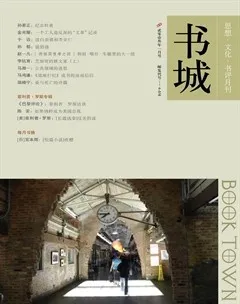憂端齊終南
張憲光
一
從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至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不停來往于長安、奉先、靈武、鳳翔、鄜州間,隨著仕途的起落,奔波于關隴大地,寫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哀江頭》《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三川觀水漲二十韻》等一系列全用入聲韻的詩作。這段時間里,第一件驚天大事是爆發了安史之亂,整個帝國從錦繡繁華的頂端跌落塵埃,秩序崩潰,兩京失陷,君臣流徙。在路途流轉中,詩人打開了視聽器官,詞自己“生成”了,詩自己長出來了,聲音自己被聽到了,時間的斷片與抽泣的詞語邂逅了,構成了杜詩獨特的景觀。
第一首這樣生成的詩,是《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以下簡作《赴奉先》),與此前的漫游之作有根本不同。杜甫早年漫游期間,或尋訪親友,或探訪古跡,或登高遠眺,結識了李邕、李白、高適、岑參、張玠、宋之悌、鄭潛曜等名流宦隱,開拓胸襟,激發詩性,沐浴于盛唐氣象中,總體上是輕松愉悅的。仰望泰岳,登兗州城樓,游龍門奉先寺,登慈恩寺塔,南下吳越,東游齊趙,這一系列漫長的游歷是官宦子弟將來進入官僚階層必備的教養,是主動認知自然山川、風土人情、人際交往的行為。在這一準備的過程中,道路聯通著未來,初步展示出一個人的氣度、志向、才情,莫不彰顯著一個年輕詩人的自信與自負。《赴奉先》的出現,則意味著這些準備基本上失敗了。
一首古詩的詩行從右到左排列,一首現代詩從上到下排列,但詩的地基并不在詩的結尾處,而是在開端處。就古典詩歌來說,第一個韻腳往往是第一塊基石,只有地基堅實了,上面的建筑物才有可能堅固而雄偉,才有可能是不朽的,否則的話就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快傾塌。《赴奉先》開頭寫道: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杜陵有布衣”,發端的一句,多么普通的一行詩,就像一個講故事的人在說某地有某人一樣,而且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的走向。然后第一個韻腳出現了:“老大意轉拙。”這顯然是一個被時間煎迫的詩人,“老大”二字暴露了長年的迂闊與不切實際,第一個韻腳“拙”則成為人生的一個縮寫。杜甫謀生拙,謀官拙,最“拙”的竟然是“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第二個入韻字“契”(xiè)則強化并解釋了“拙”,使得杜甫的人生根基變得不穩固了。他所秉持的“竊比稷與契”理想與現狀之間巨大的落差,構成了這首憤怒之詩的地基。《說文解字》云:“拙,不巧也。”注云:“不能為技巧也。從手,出聲。”這位詩人和漫游者,是語言的大師,他缺少的是謀生的技巧,而不是用筆操作語詞的技巧。他的手注定要發出最偉大的聲音,他知道這點,因此對自己的能力、技藝非常自信,甚至到了狂的地步。年輕時,他就很狂放,至壯猶然。正史說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又說他“性褊躁”,大概都和自負太高有關。當他“放蕩齊趙間”,瞻望泰岳,何等雄闊的氣魄與胸襟:“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劉辰翁評后一句:“五字雄蓋一世。”浦起龍評曰:“越境連綿,蒼峰不斷,寫岳只‘青未了’三字,勝人千百矣。”并非虛譽。這是杜甫存世較早的一首詩,他一開始就要“看入”泰山的內部,“看入”造化的內部,看見那不可見的全景。“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不是又隱隱有著“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回聲嗎?再看他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那志向,是不是也會讓人側目而視?《奉寄河南韋尹丈人》:“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毫不客氣地以揚雄、曹植、孔融、郭璞、阮籍自比,“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一句則把自己的命運跟孔子相提并論,這不是狂是什么?《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延續了這種自我認知:“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也是自比為王粲、杜密,與當代權貴汝陽王李琎套近乎。這一系列在旁人看來不切實際的自我認知,也是“拙”字的內涵,透露的恰恰是自負。
二
古典詩歌中,除了《離騷》,還沒有一首詩充滿了這么多的自我辯駁,不停地在自責與自我辯護之間盤曲地尋找語言的道路: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
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
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
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
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
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
沉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絕。
這一年,詩人四十四歲了,多年尋求仕進,謀得河西尉的微職,不拜,改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也與自我期待有著巨大落差。“居然成濩落”精準表明他的心境。“濩落”即瓠落、廓落,引申為淪落失意;“契闊”,即辛勞,“甘契闊”聽上去是認命了,實際上是“不甘”,于是有下面的“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也就是說,只要沒有蓋棺論定,“稷契之志,至死方已”。這是一轉。整天為百姓蒼生憂勞,被同學取笑,依然“浩歌彌激烈”。這是二轉。“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是三轉,“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是四轉。這后面兩轉,是說:君臣之義不能廢,所以不能隱逸終老;廊廟之材雖多,微如葵藿的我不會改變向陽的本性。但是“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后面又是一大轉,似乎把前面的“此志常覬豁”給推翻了。關于“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兩句,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認為詩人在諷刺那些螻蟻一樣只求自保的小人,另一種則認為是詩人的自比,后說義長。螻蟻與大鯨的體形、目標相差很大,做個“自求其穴”的螻蟻是小人物的常見選擇,可是詩人不一樣,總想做偃蹇滄海、搏擊風浪的鯨鯢,這才是“兀兀遂至今”的原因。明智的人,既可以欽佩詩人志存高遠,也可以鄙薄詩人志大才疏,不切實際,可是杜甫不管那一套,他就是有點軸,有點認死理,有點倔強,窮愁困苦中依然“憂黎元”,依然“腸內熱”,為此弄得老婆孩子吃不上飯。可是他真的“忍為塵埃沒”嗎?“忍”,乃不忍之意,他做不到像巢父、許由那樣一心一意隱居避世,保持自己不仕的獨立性,只能通過飲酒、放歌來“破愁絕”。這種傻勁,正是詩人打動后人的地方。
三
這一氣呵成的三十二句,自剖心跡,愁腸百轉,似黃河的九十九道彎,繞來繞去,還是歸入那憂愁的大海。這三十二句對應的是詩題中的“詠懷”二字,一反阮籍詠懷詩的內斂、朦朧與悲哀,反復陳說,迸發出“浩歌彌激烈”的激情。它是杜甫貫穿一生的價值觀,也是這首長詩的堅實地基。接下來,他開始寫從長安到奉先縣(今陜西蒲城縣)的迢迢長路了。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
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關于杜甫此行的路線圖,仇兆鰲《杜詩詳注》引朱鶴齡注謂:“自京赴奉先,從萬年縣渡浐水,東至昭應縣,去京六十里。又從昭應渡涇渭,北至奉先縣,去京二百四十里。”詩人一路經過的地方不少,卻將筆墨放在了兩段,這第一段就是夜過驪山。路就是這樣神奇,你不知道它會在什么時間把你帶向何方,會遇見怎樣的景象。詩人與驪山的相遇,是偶然還是必然?他不一定非得在那個時間出現在那個地點,但是他在那個霜嚴風急的夜晚出現在了那里,而這幾乎是一個歷史性的節點。這一年十月庚寅,唐玄宗到華清宮過冬,十一月甲子安史之亂就爆發了,杜甫恰好在大亂之前經過驪山。“嵽嵲”(dié niè)是山高貌,御榻就在那高高的驪山上,而詩人則是獨自走在山谷里。老杜不僅是一位地理學家,每到一處,便記下當地的山川風物,也是一位氣象學家,不會輕易放過那些風云雷電雨霧。“蚩尤”二字,近來注家多解為霧,是有道理的。班固認為“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圣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霿”乃昏昧不明之意,唐玄宗寵信外戚,使得君臣相蒙,正與黃霧蔽塞的天象相應。杜甫當然不是讖緯家,很少在詩中提及,也不太相信那一套解釋系統,但是他對這一套知識系統并不陌生。
杜甫是道路與詩歌的雙重探索者,二者之間有著必然的互文性。而且這條道路冥冥中有種預言性質,預示了他后來攜家帶口、踽踽道路的宿命,“高岡”“中夜”“崖谷”這些詞語將在秦州、同谷、夔州詩中一再出現,連“霜橙壓香橘”這樣的字眼也在夔州的生活中占據了重要地位。除了驪山,他還著重寫了官渡渡口的景象:
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群冰從西下,極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
行李相攀援,川廣不可越。
我們是不是看見了像崆峒山一樣高的冰凌?是不是聽見了橋梁那窸窸窣窣、吱吱作響的聲音?“崒兀”“窸窣”都是很形象、逼真的詞語。“崒兀”又作崒屼、崔嵬,山勢高峻的樣子,借來形容冰凌堆積得很高,幾乎可以使天柱折斷。這幾乎可以視為唐朝政治危機的一種隱喻,此時安史之亂尚未爆發,他只是隱隱覺察到某種危險的東西正在逼近。杜甫沒有料到的是他后來將遠赴隴右,所經歷的山川的高峻險惡遠遠超過了這一次。
四
詩句的盤曲綿延,恰如道路的盤曲綿延;艱難道路的展開,仿佛詩境的展開。在兩處關于道路的描寫之間,夾雜著關于華清宮帝王君臣奢華生活的想象:
瑤池氣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
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圣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栗。
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
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
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
私人遭際與國家政治在驪山這個具有象征性的地方相遇了。這個時刻,可以說是盛唐最后的輝煌時刻,叛亂的火山已經在開始噴發它的巖漿。這二十四句的鋪排,描寫了君臣在華清宮洗浴的場景,表明了杜甫對于皇帝寵信外戚的批判。杜甫是個比較純粹的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對于國家以及人的純粹性非常嚴苛,一直在用那一套思想儀器診斷朝廷的病癥,并在詩里發牢騷。《兵車行》中說:“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這是對君主窮兵黷武的指責。《麗人行》云:“后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則是對楊氏家族的指斥。這是那個時代最高亢的聲音,可是似乎從來沒有被同時代的人聽到,因為它們在時代的躁狂癥里被忽略了,被其他噪聲掩蓋了。一個詩人的聲音,只有等時代的塵埃落定、喧囂散盡的時候才顯現出那聲音的高度、清晰性和持久性。這樣憤激的高音,在今人看來或許并無多少新意,卻顯現出那個時代最清醒、深刻的洞察力,帶著一種不祥的預言性。
杜甫所擁有的一個高亢、憤激的聲音便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詩人很清楚,“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是因為處境不同者的情感是無法共享的,落實到詩人身上,便是自身的悲劇往往獲得的是隔代的回應,在遙遠的未來獲得共鳴。他不能不寫下自身的遭際,來作為那個時代的呈堂證供: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
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
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
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
這個無能的父親,恰如無數個無能的父親一樣,內心充滿了自責:“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他固然還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發聲,但是幼子的死亡迫使他放棄了高調,沉入歷史的低音區里—無論號啕,還是嗚咽,都是低音,如果沒有被詩人寫下來,便不會被聽見。真正的苦難,永遠是藏在心靈深處的、具體的個人的體驗,不是歷史文本籠統的敘述、客觀的概括所能替代的,歷史省略的地方是心靈最幽深的處所,詩帶領我們抵達那里,聽見那些微弱的呻吟與嗚咽,并隨著時間延展愈發清晰。
作為那個時代的批評者,杜甫以對自身的反省與自責來開始這首詩,因為或許正是自身的迂闊造成了詩歌結尾處才暴露的“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的結果—死亡,那令詩人陌生的難聞的氣味,似乎第一次出現在他的詩里,并將在《悲陳陶》等詩中不斷地蔓延開來。但一位偉大的詩人,不會沉溺或停縮于私人得失,也不會止步于自憐。杜甫正是如此,即便處于絕望中,依然“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悲痛不僅僅源于自身,也源于推己及人,推及那看不見的浩大的人群(他們將在后來的詩里頻頻現身),于是“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那巨大的峰頂聳然出現了—那是一首詩的峰頂,也是時代悲哀的峰頂。《麗人行》《兵車行》等詩指涉時事,體現的是一個士人的公議,《赴奉先》不然,它的質疑與憤怒源自幼子餓死的切身之痛,具有私人性,它動搖了杜甫的立身之本,甚至預示了他后來遠離長安的離心運動。
五
詩人的用韻,具有自傳性。布羅茨基說:“一個詩人的傳記是在他的元音和咝音中,在他的格律、韻腳和隱喻中。”杜甫早期的漫游及歌行之作,《麗人行》《上韋左相二十韻》《驄馬行》《醉歌行》《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等詩都是平聲韻,《兵車行》等詩平仄韻交錯,但入聲韻較少。隨著道路的延展,入聲韻成了主基調。這些詩主要作于安史之亂爆發初期(755年至757年之間),后來流離巴蜀,亦有入聲韻佳作,但不如上述諸詩影響大。言為心聲,情聲相應,豈偶然哉!
“韻腳”這個字眼很有魅力,押韻字仿佛就是詩句的腳,沿著一定的節奏規律帶領詩歌向前運動。韻腳既是運動軌跡,也是運動的組織者,也是情感的承擔者。著名的《分四聲法》歌訣云:“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這是對自古以來延循的聲情關系的簡要概括。王易《詞曲史》也有相似觀點:“韻與文情關系至切,平韻和暢,上去韻纏綿,入韻迫切,此四聲之別也。”平和、正大、昂揚、莊嚴之情態,比較適合平聲韻,而纏綿、憤激、迫切之情適合用仄聲韻。杜甫任職宮廷之詩,若“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游絲”“云近蓬萊常好色,雪殘鳷鵲亦多時”等句,雍容高華,偉麗正大,非平聲韻不可。而踽踽道路,心憂如焚,切迫而不能言者,入聲韻便是一種需要。
作為情感與智慧的建筑,詩是聲音和文字共同營建的立體物。從聲音的角度說,《赴奉先》給人強烈的阻滯不暢感。它通篇以細微級的韻字為主,五十個韻字分別屬于《切韻》的九個入聲韻部,以薛部(拙契熱烈絕裂轍折雪)、屑部(訣缺穴筋結咽屑)、末部(活奪豁掇葛渴闊)字最多,錯雜使用月、沒、質、物等韻。有人說入聲為聲韻之骨,對杜甫的古體長詩來說,尤為確當。入聲的特點,是發音短促急迫,氣流突然被阻斷或未完全阻斷,音被吞吃掉,形成戛然而止、突然收束的效果。杜甫的這些入聲韻的長詩,整飭的句式一直重復著短促的韻尾,造成阻滯不暢之感。更有甚者,《赴奉先》中有不少五連仄的句式,則將那種扭曲不暢的情感推發到極致。比如“竊比稷與契”一句,據《切韻匯校》等書復原的韻部,“竊”為入聲屑韻,“比”為入聲質韻,“稷”為入聲職韻,“與”為上聲語韻,“契”為入聲屑韻,一句中有一個上聲字、四個入聲字,而且“竊”“契”為內韻,讀起來自然要不停地收束,造成頓挫的效果。再如“指直不得結”,除了“指”是上聲字,其他四字為入聲,“直”為入聲職韻,“得”為入聲德韻,“不”為入聲物韻(《切韻》未收),“結”為屑韻,讀起來非常不順暢。此外“物性固難奪”“路有凍死骨”“老大意轉拙”“盡在衛霍室”都是五連仄,一句中常有兩個入聲字,強化了那種急促的聲息。除了尾韻,也使用了大量的句內入聲韻,不同詩句中同一入聲韻部的字在不同的部位強化著那種急促的聲息。比如入聲質韻,韻腳使用了室、質、橘、卒、出五個字,其他詩句非韻腳的位置又用了實、一、失、日、疾、律、崒等同韻字,造成一種同韻相應的效果。再加上臨韻同押,這首詩簡直變成了入聲字的合唱。在非韻腳的位置,作者也使用了大量同韻字。如“杜陵有布衣”的“布”字,屬去聲十一暮,下文反復使用了暮、慕、渡、路、露、顧、故、固、濩、誤,簡直比韻腳還要響亮,仿佛用一把悶錘一次次敲擊著道路之鼓。當然,如果通篇都是入聲,那么詩便像一輛輪子摧折的馬車,無法繼續聲音的旅程。詩人一方面按照慣例在奇數句使用平聲來補救,同時也使用了一些洪亮級的平聲庚部、蒸部字來補救。如“杜陵有布衣”的“陵”,用一個長鼻音補救了下句中的五連仄。這樣的鼻音,平仄兼用,如成、傾、送、凍、崢嶸、纓、終、澒洞等,試圖保持音韻長短的平衡。
詩的阻滯不暢,也體現在詞語的選擇上。漢語是表意文字,杜甫又擅長用字形來抒情,簡直把它變成了一次關于雙聲疊韻詞、偏旁相同的聯綿詞、字形繁復之詞的展覽。比如:濩落、契闊、葵藿、螻蟻、溟渤、崢嶸、嵽嵲、蹴踏、膠葛、筐篚、涇渭、崒兀、崆峒、枝撐、窸窣、澒洞等。
顧隨《稼軒詞說》論字形云:“曰形者,借字體以輔義,是故寫茂密郁積,則用畫繁字,寫疏朗明凈,則用畫簡字。一則使人見之,如見林木之蓊郁與夫巖岫之杳冥也。一則使人見之,如見風清與夫沙明水凈也。”
老杜眼中所見、耳中所聞、心中所感,多與山、水、足、木等偏旁字有關,必須借助這些筆畫繁復、飽和度極高的聯綿詞來抒發那種繁密而孤獨的感受,仿佛在用聯綿詞編織一部不斷休止的語言法典。
《赴奉先》兩次寫到了山,一次是驪山,前文已經分析過了,第二次則在末尾:“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憂端齊終南”是五個平聲字,“澒洞不可掇”是五個仄聲字;平聲肯定了憂愁的闊大,仄聲則強化了詩人的無奈。憂愁如山,向上延伸,如終南山一樣高聳、綿亙在大地上;但它是“無形之象”,混混莽莽,寥無涯際,無法拾掇或者抹去。
西人有言,道路為一切開出道路,道路本身蘊含著要言說的一切內容。甚至可以說,詩人是道路的工具,道路在使用著詩人把自身呈現。道路的特點,就是具有切身性,即便走同一條路,體驗的差異也很大。每個行走在道路上的人,對于道路的感受與表達能力也不一樣的,一個詩人與道路的相遇,其本質就是被所遭遇之人、之物、之事震動,并經受、接受、改造這一震動,順從語言/詞語的要求,成為語言的被使用者。《赴奉先》是一段偉大旅程的開端,從這里開始,他還要遠赴秦州,奔走巴蜀。閱讀杜詩,便是跟隨杜甫行走在華夏大地上,看他如何以自己的雙腳丈量大地的廣度,如何以詞語拓展著詩歌世界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