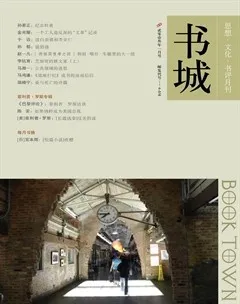說方言的胡適與講國語的胡適
段懷清
胡適不是他的時代首倡國語之人,但在推動和普及國語方面,卻有著顯著貢獻。比一般倡導國語者走得更遠的是,胡適還將國語與文學關聯或捆綁在一起,或者說將現代國語與現代文學關聯在一起,首倡“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并有《國語文學史》一書行世,這在他的時代,亦具有顯而易見的先進性及開創性。
有意思的是,在關于《國語文學史》一書的一篇演講中,胡適談到了自己當初著手撰寫這部特別的類型文學史的一些情況:
在此時研究中國的文學史,是很有趣的。因為這是一篇未完的文章,很需要我們去研究,去盡我們的工夫,因為有許多材料都等著我們來發現,這好像是科學家預備要發明一種科學一樣的有趣。……白話的文學,中國的智識階級向來不重視它,所以有許多重要的材料都被埋沒了。
上面這段文字,有幾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其一是在胡適當時看來,中國的文學史研究,是“一篇未完的文章”,亦就是尚未終結,還有不少需要發展或可以推進的空間余地。這一點,無疑是從一個學者的視角來看的;其二是把文學史的研究,與科學家的研究相提并論,顯示出胡適對于文學研究的一種個人的、現代的立場與態度,尤其是在研究的思想與方法上,具有明顯的現代意識—在人文與科學兩者之間的對話會通方面,胡適恐怕也是他那個時代的學人中倡導有力、踐行亦有力者。他的《文學改良芻議》這一里程碑式的論文,既在一個具有留學生的科學研究背景的《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亦在更具有思想啟蒙和人文導向的《新青年》上發表,似乎已經足以揭示出這一點;其三是文學史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于廟堂的、貴族的文學,而是拓展甚至專注于民間的、平民的文學,就其語言形式而言,亦就是白話文學,而這種文學,胡適有時候亦會與國語文學替換通用。
白話與國語,是胡適文學改良運動期間所使用的兩個重要術語或關鍵詞,分別關聯著白話文學與國語文學這兩個重要概念。在胡適的學術話語體系中,白話文學與國語文學當然存在著交集或重疊,但又有著不同的側重甚至指向,分別服務于胡適文學及文化改良思想中不同階段的目標或訴求。有時候,白話文學與國語文學是兩個并行的概念,有時候它們又是相互銜接但又分屬于不同階段的兩種類型的文學。這兩個概念中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或者時代性,并因為這種政治性或時代性,而與之前的或者同時代其他類型的文學或語言區別開來。
胡適的文學改良思想是從嘗試白話入詩發端的,但在國語文學這里,其文學思想又有了一個明顯調整。如果說之前所提倡的白話文學,更多關注的是文學作者個人的表達與讀者的接受,或者說兩者之間通過文學文本而實現對話交流的能效性,那么國語文學似乎轉而將文學教育以及文學需要實現的社會責任或民族國家共同體建構等更為宏大的關切與追求,納入了視野或結構之中—在這里,白話與國語既有交集,顯然亦有差別。
但無論白話或者國語,在胡適這里都不是無源之水或無本之木。九年的家鄉教育以及后來六年的滬上求學,讓胡適的方言能力和經驗,從績溪方言擴展到了上海方言。而上海當時(1904-1910)正在推行的新式學堂和學校教育,又使現代學校教育的共同知識、共同體驗、共同文化、共同價值乃至共同信仰的“共同性”或“普適性”,在胡適早年的學習成長記憶中牢牢地扎下根來。亦就是說,說方言的胡適與講共同語的胡適,在上海六年的求學期間,有了一個時間及空間上的對接與轉換,胡適也逐漸從一個習慣于說方言的少年,轉換到一個逐漸習慣于講國語的青年學生,直至后來倡導并推動白話新詩以及白話文學運動—這個時期的胡適,顯然已經成了一個時代、國家層面的言說者了。如果觀察到了這一點,對于胡適白話文學思想以及國語文學思想的產生,應該亦會有進一步的認識,那就是胡適的上述思想,并非是在單純的思想或理論語境中產生的,而是與他自己說方言的生活經驗和講國語的語言經驗密不可分的。這種經驗與思想及理論的結合,或者從切身的實際的方言、國語經驗,再到抽象的白話文學與國語文學的理論倡導,中間的“過程”,恰恰反映出胡適的思想理論,與現實生活及實際經驗之間積極互動、融合的過程。
不過,即便如此,如果有機會聽到胡適晚年的講話錄音,一定會從他所講的國語中,聽出一絲半縷的方言腔調,其中既有滬語的聲音痕跡,似乎仍有著績溪話甚至四川話的味道。方言與國語,在胡適這里通過這種方式,形成了一種聲音與內容的融合。那里面既有著個人及時代的色彩、氣息與積淀,也有著理想、追求以及孜孜以求的踐履篤行所留下來的深刻印記。
說方言的胡適:績溪話與上海話
眾所周知,胡適生長在一個學校教育尚未充分普及、方言依然盛行的時代。方言與文言,是人們開展交際、相互對話的主要語言形式。前者應用于日常生活形態下的彼此對話,后者應用于借助于書寫文本的相互交流。而方言與文言,事實上亦是確定人們的地域及知識文化身份,同時又區隔甚至阻礙人們彼此之間開展交流活動的“語言障礙”。在口頭語以及書面語兩個層面的交互影響作用之下,人及社會事實上亦被分隔成交流受限的個體、小眾或者階層。這一點,在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祝福》《社戲》等小說文本中,均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書寫表現。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安徽績溪上莊,幾乎仍然是一個對外封閉的村莊。這里所謂封閉,一方面是就地理環境而言,另一方面則是指晚清以來的“西學東漸”的“潮流”甚至“流風余韻”,基本上都未波及這里—盡管績溪或上莊有不少人在外地經商做買賣,但從胡適《四十自述》中有關自己早年的家鄉教育一節來看,基本上未涉及當時在外面世界,尤其是他后來前往的上海業已出現的一些新式教育。對此,后來胡適常引述宋代楊萬里的《桂源鋪》一詩,來描述一種受到阻隔束縛的自由自在: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
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這里的“萬山”與“溪水”,既是一對矛盾,又彼此成全。萬山的原地不動與永遠堅守,既攔得溪水“日夜喧”,又成就了溪水擺脫攔阻封鎖之后的“堂堂出前村”的“解放”與“自由”。或許胡適從這里,也很早就體會到了某些跟方言與國語有所交集的個人經驗。
《四十自述》“在上海”一章,描述了胡適自己一九○四年從家鄉績溪上莊初到上海之時的語言遭遇。這種語言遭遇一方面體現在知識語言方面,另一方面體現在日常會話方面。胡適所舉的例子,都跟學校有關。在這兩個例子之前,胡適還提到了自己第一次見到新式學堂的師生時的個人境況: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著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因為我不懂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階》,算學班上用《筆算數學》。
相對于上海話,胡適所熟悉的績溪話或者上莊話,顯然就成了他鄉下人身份的一種體現或證明。與這種鄉下人身份相關的,不僅是他的上莊方言,還有他在上莊所接受的“經學”教育和訓練—與文明書局所出版的《蒙學讀本》以及《華英初階》《筆算數學》等教材相比,胡適接受過的那些知識與教育,似乎跟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口里所說的方言一道,共同建構出了一個梅溪學堂小學生眼里的“鄉下人”形象。只是在當時,胡適顯然還沒有意識和能力,將方言、知識以及個人身份這些要素結合起來,進行整體性的思考。
這里不妨再稍微提一下胡適上文中所提到的三種新式教科書,即《蒙學讀本》《華英初階》和《筆算數學》。
《華英初階》《華英進階》,一至五集,由謝洪賚將英國人為印度人編寫的課本,翻譯成中文,配課文單字漢語釋義,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蒙學讀本》,俞復等編,全書共七冊。光緒二十八年(1902)春交文瀾書局印刷發行,后因文瀾書局印刷不甚清晰,俞復等人收回版權,集資組織文明書局,重行印刷,并配置圖畫。對于這種教科書,曾有人評價“寫畫都好,文字簡潔而有趣,那時能有此種出品,實在是難得”。
相較之下,《筆算數學》這類西方科學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在時間上要略微晚一些。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廷欽定學堂章程頒布,此亦為中國規定現代學制之始。上海文明書局,即遵章編輯教科書一套。定名“蒙學科學全書”,包括經訓修身、文法、中國歷史、西洋歷史、東洋歷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珠算、心算、筆算等十九種二十二冊。文明書局之外,此時商務印書館亦組織編輯初小、高小所用教科書,并邀請三位日本人協助編輯。
上述三種教科書,不僅是晚清以來“西學東漸”以及“洋務運動”的產物及見證,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在教科書編纂領域所取得的最初進步。無論是教科書定名為“蒙學科學全書”,還是編輯出版之“文明書局”以及“商務印書館”,都反映出晚清中國在知識、教育、文明諸方面所發生的巨大而深刻的改變。
上述教科書亦恰恰是清末民初的中國,通過學校教育重建“國語”和“國文”之新知識或現代知識基礎所進行的嘗試。對于這些,初來滬上的胡適,顯然是渾然不知的。實際上,遠在皖南大山之中的少年胡適,對于大山之外的現實與時代之中的那個“中國”,幾乎是一無所知的。這種知識上的缺失,恰恰是與胡適此間對于“國語”的缺失同步的。
至于胡適初到滬上在知識及語言上所遭遇到的兩個例子,亦都與梅溪學堂有關。梅溪學堂,也是他初到上海之后進入的第一所新式學堂: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分班的標準是國文程度。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卻可以畢業。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別情形。
這里所提到的梅溪學堂的課程開設情況,尤其是國文、英文和算學三門功課在學校教學、考核乃至畢業審查時的地位,比較典型地反映出胡適所謂“過渡時代”本土知識與外來的西學知識的存在處境,及所享有的知識地位與權力。寬泛意義上講,胡適這里所謂國語和國文,在當時正在初步出現全球民族國家語言的時代結構中,不過是一種新的“方言”,而以算學為代表的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及知識語言,以及以英文為代表的一種新的強勢民族國家語言,正在影響并塑造二十世紀學校教育中的語言形態和語言認知。梅溪學堂給胡適留下的印象是,在這里國文依然受到重視,甚至超過了算學和英文。
胡適的這種觀察和發現,還從另一個角度得以體現。這在《四十自述》中也有描述:
這樣過了六個星期。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機會來了。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里面還有人站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里面有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隨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我那時已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了,等他講完之后,我拿著書,走到他的桌邊,低聲對他說:這個“傳曰”是《易經》的《系辭傳》,不是《左傳》。先生臉紅了,說:“儂讀過《易經》?”我說讀過。他又問:“阿曾讀過別樣經書?”我說讀過《詩經》《禮記》。他問我做過文章沒有,我說沒有做過。他說:“我出個題目,撥儂做做試試看。”他出了“孝悌說”三個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交給先生看。他看了對我說,“儂跟我來”。我卷了書包,跟他下樓走到前廳。前廳上東面是頭班,西面是二班。沈先生到二班課堂上,對教員顧先生說了一些話,顧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
這段敘述,讀過《四十自述》者應該都留有印象。其中有人會關注當時新式學堂里學生知識水平、知識結構所存在著的巨大差異,亦有人會對其中所提到的沈先生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的靈活而自由的教育培養印象深刻。同樣地,應該也會有人對早年胡適在鄉下所接受的經史教育訓練的“扎實”底子表示欽佩。在這些之外,極有可能忽略當時胡適在梅溪學堂上學期間所面臨的語言環境:胡適當時是借助于上海方言在課堂上聽課學習的。上面兩個例子,恰恰反映出正在生成的新的“國語”或“國文”,怎樣成了只懂績溪或上莊方言及“舊國文”的胡適的“攔路虎”。第一個例子說明,算學及英文兩科,正在成為新式學堂里的學生們的新國文知識,而對于這一部分新國文知識及教育訓練,胡適之前完全是空白—他的國文知識,完全建構在家鄉九年的“經學”教育及知識基礎之上。第二個例子又恰恰反映出,在當時的新式學堂里,胡適原來所掌握的那種舊國文,并非全然無用。這也反映出了當時的教育及知識環境,仍均處于“過渡”時期。
胡適說自己當初在梅溪學堂,“已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為了證明這一點,二十余年之后,胡適還特意模仿上海話,“復述”了當初與沈先生之間的那場有關“傳曰”的對話。當然這段對話對于胡適來說,并非要刻意展示當時課堂教學所使用的授課語言,但他對沈先生當初話語的“復述”,卻客觀上反映出了那個時候在上海的新式學堂里,課堂教學的方言化色彩以及國語尚未真正普及使用的現實。
講國語的胡適:上海的最后幾年
一九二○年四月,民國教育部召集各省“有志研究國語的人”,在北京辦了一個國語講習所。胡適應邀在這個講習所也講演了十幾次。講習所結束之際,刻印了一份同學錄,胡適又應邀為此寫了一篇序。這便是《〈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一文的來歷。胡適的這篇序文,先是發表在一九二○年八月七日、八日的上海《時事新報》上,標題就是《〈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后來該文又以《國語標準與國語》為題,發表于由蔣夢麟主編的《新教育》第三卷第一期上。另在一九二○年《奉賢教育匯刊》第六期上,亦轉載過《〈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推測應該是從《時事新報》上摘錄轉載的。
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胡適提到了自己所講、所用“國語”的來歷:
我的國語,大半是在上海學校里學的,一小半是白話小說教我的。還有一小部分,是在上海戲園里聽得來的。
上面這段文字,胡適將自己的“國語”習得,在時間上和教育上完全歸因于早年在滬的經歷,其中既包含了學校教育這一部分,也有從白話小說閱讀中的學習,甚至還包括從“戲園里聽得來的”。如果說胡適的國語還包括通過“看白話小說”而獲得,那么從時間上來說,早在來滬之前的家鄉教育九年之中,胡適就閱讀了不少白話小說,所以胡適對于“國語”的接觸與閱讀體驗,應該說在家鄉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只是胡適似乎不這么認為,原因并不復雜,在胡適此處語境中,這里所提到的看白話小說,極有可能并不僅限于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至于在上海戲園里聽得來的,究竟哪一種戲,能夠對“國語”學習產生益處,推測應該是指京戲吧。
只是在上面三部分或者三種途徑所習得的“國語”,究竟是怎樣一種國語,而這種國語在戲園里聽得的“聲音”,與白話小說看到的故事敘述,以及在學校里學習到的幾乎全新的知識,看起來似乎分別對應了這種“國語”的知識、文法修辭以及發音發聲。不過,應該說這也只能是胡適所說的那種“國語”的基礎或開端。
相較之下,在十年之后的《四十自述》中,胡適對于自己“國語”的習得及修養來歷,另有一番描述:
我們現在看見上海各學校都用國語講授,決不能想象二十年前的上海還完全是上海話的世界,各學校全用上海話教書。學生全得學上海話。中國公學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授的學校。學校里的學生,四川、湖南、河南、廣東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說“普通話”,教員也用“普通話”。江浙的教員,如宋耀如、王仙華、沈翔云諸先生,在講堂上也都得勉強說官話。我初入學時,只會說徽州話和上海話;但在學校不久也就會說“普通話”了。我的同學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話清楚干凈,我最愛學它,所以我說的普通話最近于四川話。
上面這段回憶性敘述,不僅有助于今天的人了解二十世紀初期上海學校里的教學語言及生活語言的一般情況,而且對于了解“國語”在上海學校的興起及普及,亦有一定幫助。
在《〈中國公學校史〉序》一文中,胡適再次提到了“普通話”、中國公學以及自己早年在滬習得“國語”的情況:
我是丙午年夏間考進中國公學的,在校兩年多,在中國新公學又留一年。我現在回想當日公學的精神,有最可紀念的幾點:
第一,中國公學可算是全國人的公共學校。學校在上海,而校中的學生以四川湖南河南廣東的人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差不多全有。學生說的話是普通話,講堂上用的話也是普通話。我當時只能說上海話與徽州話。在校一年多,便說四川話了。二十年來,上海成為各省學生求學之地,這風氣不能不說是中國公學開出來的。
上面這段文字,內容上與《四十自述》里的描述大體一致,但其中特別提到了中國公學為“全國人的公共學校”這一認識觀點。在胡適的邏輯里,普通話或者國語的應用及推廣普及,顯然是與當時中國公學“全國人的公共學校”這一特點或者屬性密不可分的。當然,來自全國各省各地的學生在一起共同學習以及相互交流,確實是為普通話的興起及普及提供了基礎與平臺,但胡適對于這種與現代知識、現代思想以及現代價值、現代信仰密切相關的“普通話”的認識,顯然又并不僅限于可供不同地區的人之間對話交流,同時還強調了這種普通話的“革命性”與“時代進步性”的面向,在他看來,中國公學是“革命運動的機關”,“在學校成立之時,一切組織多含有試行民主政治之意”。
從說方言的胡適,到講國語的胡適,在胡適的自我回憶和敘述中,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但是,這一過程在時間上又有著明顯的先后銜接。從說方言到講國語,胡適初步完成了自己從一個“地方性”的自我處境或狀態,到全國性甚至世界性的自我處境與狀態的調整轉變,這也為他接下來參加赴美留學考試以及在美國的七年留學,提供了“語言”上的支撐。至于胡適在留美時期圍繞著文言、白話之爭甚至國語文學等命題所開展的學術上、思想上的觀察與思考,這一切與他上海時期的方言與國語體驗既有著顯而易見的關聯,又是在另一個層面對于方言、文言、白話及國語的更進一步的研究與提倡了。
胡適在上海的國語體驗中,已經將“白話”—無論是方言還是普通話—實際地與智識階級結合在一起了。亦就是說,在中國公學尤其是中國新公學時期,當時在校之人—無論是學生抑或是教師—都是在用普通話進行交流,而這種普通話所包含的現代性、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科學性、革命性以及進步性等,都是與這種共通語言的使用者的知識生活、思想生活乃至革命生活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