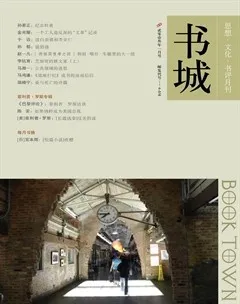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四時之外》:超越的存在與藝術
重木
從《詩經·曹風·蜉蝣》中“朝菌不知晦朔”的微小蜉蝣,到“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不安,中國的古人們不斷地意識到他們的生命和存在,可能只是不斷流逝的時間之河中轉瞬即逝的匆匆一瞥,因此抵抗不斷的消逝以及存在的崩潰就成為他們念茲在茲的創造與想象的動力。“詩是關于人生困境以及怎樣從這困境解脫的詠嘆”,除此之外的其他藝術形式也往往承擔著相似的功能,即作為寄托、創造和展現古人永無止境地對抗存在焦慮的存在形式,它們不僅僅是工具,而且是關于存在本身的顯現。朱良志在《四時之外》(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中,便通過對傳統中國藝術的研究與探索,重現作為古人存在意識以及形式的藝術作品中的深邃與超越。
在《四時之外》中,作者認為中國藝術的靈魂正是清代畫家惲格(號南田)所謂的“其意象在六合之表,榮落在四時之外”。“四時之外”不僅暗示了中國傳統藝術的來龍去脈,也直指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即時間。而恰恰是對于時間的敏感,導致古人對于自身的存在產生了最為清晰與親密的感知。從這一不斷流逝的時間中,他們所窺探到的存在真相便是,人類個體的有死性以及萬事萬物的榮枯循環。古人發現,時空作為人類存在的先驗條件,一方面為其提供了存在的基本框架,但同時也限制和界定了人類的存在形式,在《四時之外》的作者看來:“在時空二者之間,重視超越的中國藝術更注意時間性因素。”因此中國思想也大都展現出“時空結合、以時統空”的傳統,而如何突破這一時間性對于存在的限制,以及為其所賦予的特定且秩序化的形式,便成為中國藝術不斷探究和希望破解的難題。
古人對于時間性的關注,與他們對于歷史的感知和思考息息有關。中國古人早早地就意識到,自己生活于一種不斷變化的歷史進程之中,這一基礎性的心理時間結構或許從先秦諸子思考“何謂美好的生活”或是“如何重建和諧的天下”時便已經深藏其中。先秦諸子雖然思想各異,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想象或預設曾經存在著一個完滿的時代,上古三代的黃金時期成為整個時間啟動的源頭,而也恰恰是因為三代的沒落才導致時間開始流動,而在它奔流的方向中潛藏著衰敗。古人意識到自己只不過是這一不斷變化的時間之流中的滄海一粟,面對其洶涌往往除了興嘆,別無他法……或許正是為了抵抗這一無能為力感以及試圖重新構建黃金時代,古人便想要成為“控制時間的‘英雄’”,似乎只有如此,才能掙脫不斷被形式化與知識化的歷史之流,發現或是創造另一種新的存在—時間形式。
朱良志在《四時之外》中認為在中國古代藝術家心中,實際存在三種不同的對于歷史的認知:一是“在時間流動中出現的歷史事實本身,這是歷史現象”;二是“被書寫的歷史……具有知識屬性,多受權威控制”;三是“作為‘真性’的歷史,它既不同于被書寫的歷史,又不同于具體的歷史現象,而是人在體驗中發現的、依生命邏輯展開的存在本身”。前兩種歷史都存在于時間之中,前者始終是混亂雜多的現象,后者則是形式化的知識,這兩者最終不僅無法對抗時間的侵蝕,而且因其企圖對時間的知識性切割、認知和書寫而僵化了時間,從而導致其無時間性;唯有第三種“歷史”,它與生命與存在共同生成,不斷地流動、變化與創造,是一種“生命時間”,與存在緊密相連,而與知識和權威無關。這樣的“歷史”被古人看作是“生命真性”,它“不是隱藏在歷史背后的普遍規律,而是人樸素本真的存在狀態”。
因此,“四時之外”指的便是“超越時間和歷史”,不作時史,僅僅依賴于“個體生命感覺”,好似一尾透網金鱗,從時間、歷史、知識、欲望等密密織就的羅網中脫出,到生命的海洋中自由游弋。在這樣一顆凈明心體(或曰“古意”)中,存在不再受困于時間,身體雖然依舊會在其中不斷地衰敗,但生命卻已經獲得了絕對的自由,“與天為徒”,而這才是存在本來的、真性的面目。因此我們才會發現為什么在中國藝術觀念中,不斷地出現關于“相”“真”與“幻”的討論,“幻”與“真”的關系都被置于時間之中,是從“榮枯過眼、倏忽萬變的角度來理解的”。對于那些無法在時間流逝中自我持存的東西,它們都是“幻”而非“真”,諸多向我們顯現的“相”不過是暫時的、因緣際會的幻覺,因此只有“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人的身體、形象以及其所擁有的一切物質與榮譽,最終也不過是注定會毀滅的“諸相”,因此對其的沉湎只會造成不斷的痛苦和焦慮,唯有穿透這些被時間所束縛的諸相,發現存在于這一切雜多之后的“真性”,生命才能真正變得靈活生動。
因此,“文人藝術所推崇的創造方式,不是再現或表現,而是‘示現’”,它是“兩面歷史鏡”:“一面照出如幻的人生,映現出歷史書寫(第二種歷史)的喧囂和魅惑;一面照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本相,那種洞穿歷史現象、脫略知識書寫的第三種歷史的本色。”對于古人而言,虛幻的“諸相”背后存在著一種頑璞的真性,它不僅是存在的本質,也是生命解脫之道。而藝術的位置正在于此,它具有“示現”的能力,以及對生命真性的直觀。
區別于形式化與規范性的“知識時間”,存在的真性,即“生命時間”,有著自身的節奏,它是“天之時”,體現著天地本然的節奏(“天趣”),因此不需要人的巧心經營。“人作”在藝術創作中屬于下層,只有“宛自天開”才是上品。這一中國藝術創造綱領恰恰體現了對于“生命時間”的追求,而非一種矯飾,因為“人”的知識及其能力始終是有限的、短暫且困于具體時間段中,因此只不過是暫時的“相”,是“幻”,脫離了生命時間的整全性,而只有把這一時間段(瞬間)置于“天”(永恒)之中,其才能獲得生機,否則只是僵死的形式。因此,“瞬間永恒”這一于知識中的悖論在此被完美融合,如莊子所謂的“齊物”,無論是瞬間還是永恒都只不過是知識性的認知建構,實則二者都不過是時間性的展現,“它不是一種認識方式,而是對人樸素本真存在狀態的描述”。
就如《四時之外》中所指出的,自唐宋以來的藝林中人所追求的永恒,實則是非時間的,而總是在“四時之外”徘徊,它也不是一種由外在賦予因此能夠被規定和形式化的,而是“在當下即成心靈體驗中實現的”,今生今世的此時此刻就是永恒,它是一種“永恒感”,而非庸俗所理解的對于物質的永遠占有或是精神的不朽。對于中國藝術的精神追求而言,它不執不迷,由此才得自在,才能夠不斷地接續,生生才是可能的。朱良志在《四時之外》中通過對諸多藝術意境的考察來重現古人于藝術中的追求,如“杖藜行歌”“一朝風月下”與“茶熟香溫時”,它是一種存在方式、一種此刻的永恒感。因此,唐宋以來的文人藝術創造的核心精神被總結為“以簡易的方式,超越變易的表相,表現不易的生命真性”,其目的依舊在于超越時間的秩序化束縛,而能夠在“四時之外”開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存在。
中國古代藝術雖然同樣注重各類技巧以及擁有一套完整且復雜的知識系統,但其根本精神或目的則始終脫離了對于特定時間點或時間段中存在的描摹,而往往是關切著在所有時間中的生命本身,穿過所有時間,才能抵抗時間之“短”“暫”,以及由此產生的“老”“幻”和“壞”的身體感受。這是關于生命存在的根本問題的追問,“目對脆弱易變的人生,到藝術中尋找底定的力量;深處污穢生存環境,欲在藝術中覓得清凈之所;為喧囂世相包圍,欲到藝術中營造一方寧靜天地;為種種‘大敘事’所眩惑的人,要在當下直接感悟中,重新獲得生命平衡”……對于古人而言,這是關于自身存在最真實的問題,即使于當下,它也依舊咄咄逼人,因為“知識時間”在現代社會已經徹底宰制著人的生活、生命與存在,“真性”成為虛無縹緲的幻覺,可計量、可被知識化,成為判斷生命重量與價值的總綱領,“生命時間”徹底啞然,時間依舊流逝但卻不再穿過生命,它變成了荒漠。
《四時之外》通過探索古代中國藝術的精神、風格與其對于存在之“真性”的示現而企圖重新激活這一漸漸被遺忘的古老感知和心靈能力,對于處在當下世界的我們而言或許尤為珍貴。作為一種始終處于不斷流動、生成和差異化的生命(living),“知識時間”自始至終都企圖通過對其的形式化和客體化而實現對其的管控,不斷涌出的生命之流被切割成一段段可以計量的單位而能夠在商品與生命的市場中被交換與流通,存在不再是生生不息,而成了僵死的物。就如朱良志在《四時之外》中所說的,“中國藝術家所在意的,是人們不明白時間的實質,心被表象世界掠去,被知識的敘述掠去,脫離了時間的本義,脫離了生生的邏輯,從而成了時間的奴隸”,而作為中國藝術的超然時間之思所渴望發現的“匝地清風”,是否還能夠重新激活生命的動力,在此時此刻突破浮游的困局,則依舊有待我們不斷地去省思、感知與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