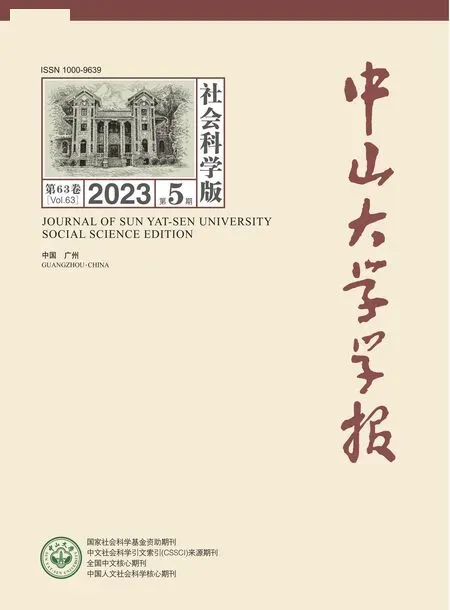文明對話視域中的人文科學(xué)研究*
——對漢學(xué)主義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的反思和批判
金惠敏
人文科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究竟有什么區(qū)別?貌似經(jīng)過著名學(xué)者巴赫金的著名界定之后,在理論上已經(jīng)不成其為問題了:自然科學(xué)處理的是無言的客體,研究者與其研究對象是一種主客體關(guān)系,而人文科學(xué)面對的是文本,是另一主體的言說和話語,因而人文科學(xué)在本質(zhì)上就是主體間性的對話。簡明言之,前一種關(guān)系屬于認(rèn)識論范疇,而后者則可歸于對話論。認(rèn)識論性質(zhì)的自然科學(xué)追求對象本身的真實,其評價標(biāo)準(zhǔn)是符合論,符合者為真,不符者為偽,即是說,自然科學(xué)研究存在真?zhèn)沃郑欢鴮υ捳撔再|(zhì)的人文科學(xué),雖然其研究也有科學(xué)性的要求,即深入地貼近和知曉對象,但主要目的則在于對話:不是反映,而是反應(yīng)、回應(yīng);不是“解釋”、改造、控制、整合“對象”,而是“理解”、尊重、包容、和合(和而不同)“他者”①巴赫金認(rèn)同狄爾泰以“解釋”和“理解”辨識自然科學(xué)和人文科學(xué)之方法論異同,并進(jìn)而明確地分別賦其以“獨(dú)白”和“對話”的性質(zhì),他說:“在進(jìn)行解釋時,僅僅存在一個意識,一個主體;在進(jìn)行理解時,則存在兩個意識,兩個主體。對客體不可能有對話關(guān)系,因而解釋已失去對話元素(除了形式—修辭學(xué)上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總是具有對話性。”轉(zhuǎn)引自[俄]博古斯拉夫·祖爾科撰,周啟超譯:《巴赫金觀點系統(tǒng)中的人文科學(xué)》,《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16年第4期。相關(guān)論述亦可參見[俄]巴赫金:《人文科學(xué)方法論》,錢中文主編,白春仁等譯:《巴赫金全集》第4 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9頁。,這一他者永遠(yuǎn)保有自身之存在,不是那種作為自我之投射的對象,因而精準(zhǔn)言之,如此的對話便不再是胡塞爾“主體間性”意義上的對話,而是筆者所謂的以“個體間性”為基礎(chǔ)的“間在對話”。
如果說巴赫金對人文科學(xué)的特性之強(qiáng)調(diào)和凸顯,用之于一種文化傳統(tǒng)內(nèi)部的研究,例如中國學(xué)者對自身文化之歷史的研究,對于其當(dāng)代社會的研究,對于一般性理論的研究,尚待進(jìn)一步的推敲和厘定(對此歐美文化研究和批判解釋學(xué)有不少發(fā)人深省的論辯①See Hans-Herbert K?gler,“A Critical Hermeneutics of Agency: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in Hermeneutic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ed.by Babette Babich,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9 [2017],pp.63-88.,但我們不太能夠接受其對內(nèi)部異質(zhì)問題的聲張),那么對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人文科學(xué)研究,進(jìn)而言之,對于如今文明互鑒、文化對話視域下的人文科學(xué)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參考價值。
對話理論如今被廣泛地使用于當(dāng)代國內(nèi)外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乃至當(dāng)代社會的一切領(lǐng)域,其廣泛和普及程度幾乎取代了該詞原有的基本含義,而成為一種通用通行的新廢話,所以研究對話本身或者運(yùn)用已有的對話理論,都可能被鄙夷為一種老生常談,一種無的放矢的空談或廢話,即便往好處說,對話亦不過是處在一種被熟視無睹的狀態(tài)。我們需要喚醒學(xué)界的對話意識,但其前提工作不是重復(fù)而是更新已有的對話理論,即對話如果不是間在的,不是個體間性的,那么它就仍然未能跳出反映論的領(lǐng)地:純粹話語層面的對話,即建立在主體間性之上的對話,例如在哈貝馬斯那里,終究不過是一個所謂的“理性”之獨(dú)白,甚至霸權(quán)。不假定個體的存在,就不會有反應(yīng)性的對話,和而不同的對話,這即是說,對話中一定含有不可付諸對話的元素。對話必須同時是反對話的,且因此而得以保持和繼續(xù)。
本文擬從間在對話論的角度,對在國內(nèi)外爭辯已有時日的“漢學(xué)主義”及其所依托的后現(xiàn)代主義進(jìn)行反思和批判。其最終目的是在當(dāng)今文明互鑒、文化對話總體語境中,在國內(nèi)“新文科”建設(shè)的時代吁求中,將間在對話論引進(jìn)人文科學(xué)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異質(zhì)研究(即對其他文明文化的研究,如西方漢學(xué)、中國的外國研究等),以達(dá)成一個從反映論模式向?qū)υ捳撃J降霓D(zhuǎn)換。
一、漢學(xué)主義的一個錯誤假定:意識形態(tài)與客觀知識的對立
“漢學(xué)主義”是對國外漢學(xué)之根本“錯誤”傾向的一種批判。表面看來,這種批判似乎證據(jù)確鑿、真理在握、義正詞嚴(yán),但仔細(xì)閱讀下來,則會發(fā)現(xiàn)這種批判本身還是有待進(jìn)一步批判的。筆者的觀點是:“漢學(xué)主義”之批判的武器是源起于法國實證主義的機(jī)械反映論,以自然科學(xué)為其典范,但當(dāng)被轉(zhuǎn)用于人文科學(xué)時,尤其是具有對話性質(zhì)的異質(zhì)研究時,便顯出其僭越、因而無能和無效來。不消提起,任何理論都有其適用的邊界,因為理論是視角性的,一方面是洞見,一方面是盲視。
學(xué)界關(guān)于“漢學(xué)主義”的討論已然熙熙攘攘,也有論爭文章的匯集②[美]顧明棟、周憲主編:《“漢學(xué)主義”論爭集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7年。和專書的申述③[美]顧明棟著,張強(qiáng)等譯:《漢學(xué)主義:東方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年。,因此本文就不擬從頭說起、不厭其詳了,而是單刀直入,在其肯綮處下功夫。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好在所遺漏者均在行內(nèi)讀者掌握之中。閑言少敘,讓我們即刻轉(zhuǎn)入正題!
“漢學(xué)主義”的命名者和闡述者發(fā)現(xiàn)西方漢學(xué)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漢學(xué)主義”,他們甚至要在西方漢學(xué)與“漢學(xué)主義”之間畫上等號。如周寧所稱,“廣義的漢學(xué)與其說是一門學(xué)問或知識體系,不如說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他不是說漢學(xué)中存在著“漢學(xué)主義”的因素,這樣說興許還有部分的道理,而是相反,決絕地堅持“漢學(xué)包容在漢學(xué)主義中”,此言下之意乃是說,漢學(xué)不過是“漢學(xué)主義”這一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傳教士”或傳聲筒,它沒有什么“知識”的屬性,而只有意識形態(tài)的毒性。或可承認(rèn)漢學(xué)的知識性和學(xué)科性,但周寧則警告我們必須認(rèn)清,這一學(xué)科只是在權(quán)力的支配下生產(chǎn)那種為權(quán)力服務(wù)的知識和話語。知識與權(quán)力狼狽為奸,相互確證、慫恿和強(qiáng)化。西方漢學(xué)本質(zhì)上都是漢學(xué)主義,從早期階段直到改換了其名稱的“中國研究”,莫不如此,始終如此,即完全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對中國歷史和現(xiàn)實的意識形態(tài)虛構(gòu)和想象④周寧:《漢學(xué)或“漢學(xué)主義”》,《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2004年第1期。。顯然,周寧對漢學(xué)是本質(zhì)否定(質(zhì))和全盤否定(量)的。
顧明棟試圖與周寧的極端主義拉開距離,他先后給出“漢學(xué)主義”的五種①[美]顧明棟:《什么是漢學(xué)主義?——探索中國知識生產(chǎn)的新范式》,《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2011年第3期。和八種②[美]顧明棟:《“漢學(xué)主義”引發(fā)的理論之爭——兼與張西平先生商榷》,《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2016年第1期。描述或定義,以盡可能包括和包容各種不同的言說,顯示了其作為學(xué)者的客觀謹(jǐn)慎、綜合以及溫和。但實際的效果是,他最終仍舊未能說服我們相信他真的提供了一種新版本的“漢學(xué)主義”。
顧明棟對“漢學(xué)主義”的基本理解依然停留在周寧的判斷和批判上:“從整體上看,它作為一個知識系統(tǒng),建立在西方為中心的種種觀點、概念、理論、方法和范式構(gòu)成的總體基礎(chǔ)之上。其理論核心是以認(rèn)識論和方法論的殖民化與自我殖民化為中心的一種隱性意識形態(tài)。”③[美]顧明棟:《什么是漢學(xué)主義?——探索中國知識生產(chǎn)的新范式》,《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2011年第3期。西方漢學(xué),無論其美化抑或是丑化中國,讓顧明棟憂慮的是,它們都不能達(dá)到“對中國及其文化的客觀認(rèn)識與再現(xiàn)”④[美]顧明棟:《什么是漢學(xué)主義?——探索中國知識生產(chǎn)的新范式》,《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2011年第3期。。通過對“漢學(xué)主義”的批判,顧明棟所要達(dá)到的目的是“盡量遠(yuǎn)離任何形式的歧視、偏見、主觀性和政治干擾”,以便“盡可能客觀公正地生產(chǎn)中國知識”⑤[美]顧明棟:《“漢學(xué)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再辨析——走向自覺反思、盡可能客觀公正的知識生產(chǎn)》,《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2015 年第4期。。但既然“漢學(xué)主義”的核心是永遠(yuǎn)無法擺脫的、或隱或顯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控制和“干擾”,既然如其言之鑿鑿“一切知識都是構(gòu)建的敘事,而構(gòu)建者都有意無意地受制于某種意識形態(tài)”⑥[美]顧明棟:《“漢學(xué)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再辨析——走向自覺反思、盡可能客觀公正的知識生產(chǎn)》,《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2015 年第4期。,那么完全符合中國本來面目的知識也就不可能如其所愿地生產(chǎn)出來。對顧明棟而言,遠(yuǎn)離“偏見”云云、盡可能“客觀”等,也就是只能作為一種主觀努力而非實際的后果了。于是,當(dāng)其宣稱“漢學(xué)主義不是漢學(xué),而是異化了的漢學(xué)研究”⑦[美]顧明棟:《“漢學(xué)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再辨析——走向自覺反思、盡可能客觀公正的知識生產(chǎn)》,《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2015 年第4期。時,他無非告訴我們,非“漢學(xué)主義”的“漢學(xué)”實際上并不存在,而實際存在的漢學(xué)就只是“異化了的漢學(xué)研究”。純凈的、非異化或非對象化的、如其本然的中國和中國知識是可望不可即的,是本質(zhì)上無法接近或得到的。由此而言,顧明棟便不得不返回周寧的論斷:漢學(xué)不能不是“漢學(xué)主義”,同樣,“漢學(xué)主義”不能不是漢學(xué)研究的主導(dǎo)性質(zhì)。
要走出這樣的理論窘境,就必須拋棄其中隱藏的康德式的本體與現(xiàn)象之間的二元對立認(rèn)識論模式。可惜,顧明棟對此沒有清醒的意識,因而也從不予承認(rèn)。他執(zhí)意將意識形態(tài)主控的漢學(xué)研究與追求客觀知識的漢學(xué)研究一概稱作“漢學(xué)主義”,用“漢學(xué)主義”反對“漢學(xué)主義”,從而取得對“漢學(xué)主義”的克服和超越⑧對于這種用同一個術(shù)語來表達(dá)相反的意指,估計多數(shù)人讀者會感到不知所云。這里是戲仿顧明棟的用詞(非)邏輯,以凸顯其問題所在。,但無論是哪種“漢學(xué)主義”都無例外地假定了一個客觀知識與主觀闡釋之間或者說客體與主體之間的二元對立以為前提,前者是遮蔽了真實的世界,后者則是要對被遮蔽的真實世界進(jìn)行去蔽,其念茲在茲的一直是“客觀”(對象性)“知識”。那么,什么是“知識”呢?我們都知道,世界本身不是知識,事實不是知識,對世界或事實的認(rèn)識才是知識,而認(rèn)識是有主體的,知識作為此認(rèn)識的結(jié)果也同樣是有主體的,通俗言之,不存在離開人(個體和群體)而漂泊無依的知識⑨關(guān)于“知識”的性質(zhì),學(xué)界基本的共識是,將其作為“意識與事實之間的一種關(guān)系”(Keith Hossack,The Metaphysics of Knowled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7),因而單純的認(rèn)識主體(意識、意識個體)與事實都不能稱其為“知識”。凡“知識”必為與“知者(knower)”相關(guān)聯(lián)的知識,“與水和黃金不同,知識總是隸屬于某個人”,隸屬于“某一活生生的主體(some living subject)”,易言之,“沒有可以不與任何主體相捆綁而自由晃動的知識”(See Jennifer Nagel,Knowledg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2-3)。在我們看來,一切知識都是經(jīng)由解釋學(xué)而來的知識,是含有主體性和個體性的知識。人只能在主體客體之間的“解釋學(xué)循環(huán)”中獲得“間在知識”。如此得到的知識既非純粹主體性的,亦非純客體性的,而是中間性的,是巴赫金所謂的“事件”。。因此,只要我們是在認(rèn)識論的框架內(nèi)談?wù)撝R,或者說,只要我們是談及知識自身,那就一定難逃主客體二元對立模式,一定無法求取什么絕對客觀的知識。對此,海德格爾的基礎(chǔ)本體論和伽達(dá)默爾得其真?zhèn)鞯恼軐W(xué)解釋學(xué)做有經(jīng)典性的論證,茲不贅述。
隨手再拈一例,雖其新意無多,然在國內(nèi)讀書界較之周寧、顧明棟的“漢學(xué)主義”則受眾更廣,這就是文史專家葛兆光的“漢學(xué)外學(xué)”說。盡管其與海外漢學(xué)界過從甚密,知之甚深并多有推介,但在知識論、方法論這類原則性的層面上并不對他們的成果表示認(rèn)同,甚至并不視之為同行、同道,其態(tài)度是懷疑的和批判的:“我們應(yīng)該注意,外國的中國學(xué)雖然稱作‘中國學(xué)’,但它本質(zhì)上還是‘外國學(xué)’,所以我老是說,所謂‘中國學(xué)’首先是‘外國學(xué)’。因其問題意識、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國的、當(dāng)時的學(xué)術(shù)脈絡(luò)、政治背景、觀察立場密切相關(guān)。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應(yīng)該把‘中國學(xué)’還原到它自己的語境里去,把它看成該國的學(xué)術(shù)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個部分,不要以為他們和我們研究的是一回事。”①葛兆光、盛韻:《海外中國學(xué)本質(zhì)上是“外國學(xué)”》,《文匯報》2008年10月5日,第6版。轉(zhuǎn)換為周寧和顧明棟的語言,葛兆光等于在說,由于所秉持的意識形態(tài)不同,“他們和我們研究的”即彼此的研究對象都不再是“一回事”了。更明白地說,雖然都在研究“中國”,都在進(jìn)行以“中國”為名的課題研究,但海外漢學(xué)家研究的不過是“外國學(xué)”,而我們中國人研究的則是“中國學(xué)”。這里一個“外”字便將海外漢學(xué)的研究價值擊得粉碎。他們的研究與中國“事實”無關(guān),套用尼采的話,他們的研究沒有“事實”,只有“闡釋”,他們費(fèi)力所得的無非是其意識形態(tài)先行置放進(jìn)去的前見和偏見。有此根本性的否定,即便此外加之以多少具體的肯定,也將是無濟(jì)于“事”/“是”了。
二、不能一以貫之的“漢學(xué)主義”理論
對“漢學(xué)主義”的批判,將海外中國學(xué)打入另冊,其潛臺詞已顯然是否定了所有的異域研究,包括例如在中國進(jìn)行的外國文學(xué)研究、外國哲學(xué)研究、外國歷史研究,等等,因為這些毫無疑問也都?xì)w屬于中國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與外國本身無關(guān)。擴(kuò)大言之,這潛臺詞進(jìn)而還是對一切人文學(xué)科以及社會科學(xué)的否定,因為它們無不受到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盡管這影響是深淺程度不一,但亦足以模糊和扭曲研究對象的真實面目。再擴(kuò)大言之,這將最終導(dǎo)致對于漢學(xué)批判者、詰難者、否定者例如周寧、顧明棟、葛兆光等人本身之批判、詰難和否定的取消,因為他們無法證明自己對漢學(xué)的觀察、研究和褒貶就一定能夠免疫于意識形態(tài)的感染而與其他人有什么質(zhì)的不同。借用佛家觀點,“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經(jīng)》),也即是說,當(dāng)我們視一切皆空、無物而永駐時,那么對空的一切思考和討論也將淪為一種空或色(現(xiàn)象)了。所謂“受、想、行、識,亦復(fù)如是”(《心經(jīng)》)者,蓋此之謂歟②談錫永指出:“佛家謂諸法自性空之理。此中所謂諸法,既包括所認(rèn)識的客觀事物現(xiàn)象,亦包括能認(rèn)識的主觀思想。知前者自性空,即斷‘人我’的執(zhí)著;知后者自性亦空,即斷‘法我’的執(zhí)著。”(談錫永主編:《佛學(xué)經(jīng)論導(dǎo)讀:〈金剛經(jīng)〉〈心經(jīng)〉》,北京:中國書店,2009年,第166頁)據(jù)此可知,色為現(xiàn)象,空為對色在觀念上的否定。。笛卡爾看法與此不同,他認(rèn)為,我們可以懷疑一切,但絕不能懷疑我們正在懷疑這一事實,即一定存在著一個思維的理性或主體,否則連我們的懷疑也將被懷疑掉了。
周、顧、葛三位都是學(xué)貫中西的當(dāng)代大儒,他們絕不會天真到要取消一切乃至自我取消的地步,或者說:他們既接受一切事實都是闡釋、敘述、建構(gòu),在這一點上他們追慕、仰仗的是后結(jié)構(gòu)主義或后現(xiàn)代理論,同時又承認(rèn)還是有一個事實在那兒存在著,承認(rèn)有世界本身的非我性存在,這是唯物主義的反映論或科學(xué)精神。關(guān)于后一方面,例如,葛兆光尋思,我們總不至于面對殷墟遺址而稱其不過是一個“敘述”吧?!他坦承:“說實在話,我并不認(rèn)同后現(xiàn)代史學(xué)對真實存在的‘過去’和書寫出來的‘歷史’的漠視和瓦解。”他堅信夏商周不是“外星人”的作品,堅信“歷史不可能是文學(xué)式的‘散文’”,這因而也就是堅信歷史自身乃赤裸的歷史的存在及其影響③參見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增訂版),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9年,第93—95頁。。同葛兆光一樣,顧明棟也是既要批判“漢學(xué)主義”對真實中國的遮蔽和發(fā)明,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對國際漢學(xué)同行們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視而不見①實際上,顧明棟絕非用“漢學(xué)主義”將國外漢學(xué)研究一筆勾銷,他曾真誠地稱贊過一些漢學(xué)家的成就:“高本漢、葛蘭言、馬伯樂等杰出的漢學(xué)家以其全新的研究方法對漢學(xué)作出了令人稱羨的貢獻(xiàn)”([美]顧明棟:《漢學(xué)研究的知性無意識》,《北京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13年第3期)。,于是便顧不得邏輯上同一律的要求而魯莽地賦予“漢學(xué)主義”以相互矛盾的多重含義。這就像用“好”來表示“壞”的意思,用詞上經(jīng)濟(jì)則經(jīng)濟(jì)矣,但最終使得讀者無法辨別其“好”究竟是真“好”、還是假“好”而真“壞”,失去了學(xué)術(shù)表達(dá)的嚴(yán)謹(jǐn)性。當(dāng)然,日常生活中的活用或文學(xué)性的修辭則另當(dāng)別論。
周寧對漢學(xué)因其為“漢學(xué)主義”即西方意識形態(tài)所充斥和挾裹而采取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從他2004年發(fā)表第一篇系統(tǒng)討伐“漢學(xué)主義”的論文,至2011年將此文摘要性濃縮后再次發(fā)表②周寧:《“漢學(xué)主義”:反思漢學(xué)的知識合法性》,《跨文化對話》2011年第2期。,這態(tài)度沒有絲毫改變,但匪夷所思的是,周寧長期以海外中國形象學(xué)為研究課題,廣義地說,是對海外漢學(xué)的研究,倘使這個漢學(xué)一無是處,那還有什么必要“為伊消得人憔悴”呢?!而如果說中國形象在漢學(xué)家的彩筆下還能顯示出其在我們自我鏡像中從未出現(xiàn)過的別樣異貌,對我們更清晰、更準(zhǔn)確、更全面地認(rèn)識自己有所參照,那么這樣的漢學(xué)就不會一無是處,就不能趕盡殺絕。因此,能夠發(fā)現(xiàn),在不專門談?wù)摗皾h學(xué)主義”的別處,周寧則是悄然回到了一個學(xué)者當(dāng)有的理性和客觀。例如,他也承認(rèn)“西方文化自身的開放與包容性以及自我反思與批判的活力”,這基本上就是對“漢學(xué)主義”所寄生的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某種承認(rèn),甚至禮贊了。再者,他更是反過來指出,對這一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后殖民主義批判“在那些后殖民或后半殖民的社會文化中,卻可能為偏狹的文化保守主義與狂熱的民族主義所利用,成為排斥與敵視西方甚至現(xiàn)代文明的武器”③周寧、周云龍:《必要的張力——周寧教授訪談錄 》,《社會科學(xué)論壇》2015年第1期。。可以讀此為“夫子自道”,有自況、自省和自警的意味。但這與他對“漢學(xué)主義”花崗巖般堅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是有矛盾的、不相協(xié)調(diào)的,所幸他找到一個時興好詞,“必要的張力”,具體說,是后殖民主義與全球主義之間的張力,然而,問題在于這種“張力”是如何將矛盾著的二者連接起來,可惜他未能予其以一個清晰的回答。“張力(tension)”不是“斷裂(break)”,而是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力量彼此有異,但又相互拉扯、難解難分的關(guān)系:其義一方面在“異”,一方面在“合”,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稱之為“張力”。因而,對于周寧來說,使用“張力”一語,就必須對其蘊(yùn)含的兩方面內(nèi)容都有說明,但由于其“異”顯而易見,那么人們迫切需要知道的便是其“合”了,即怎樣“合異”,怎樣“和(而)不同”。我們當(dāng)然不會反對民族立場與世界意識以及它們之間的協(xié)和、共生,恰恰相反,我們十分推崇世界主義的理念,筆者多次借用“星叢”一語來表達(dá)對“世界主義”的理解,但若是不能圓滿地表接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那么周寧對待“漢學(xué)主義”的偏激姿態(tài)似乎就只能被目之以“為賦新論強(qiáng)標(biāo)異”之類的寫作策略罷了,算不得多么嚴(yán)肅、堂正,讀者也只好姑妄聽之了。
三、視角或意識形態(tài)是研究者作為具體個體無法擺脫的自身存在
對于“漢學(xué)主義”論辯,通過以上的重述和分析,其實錯誤的既不是漢學(xué)研究乃至其中的“漢學(xué)主義”,當(dāng)然也不是如周、顧、葛等人通過對漢學(xué)研究的“漢學(xué)主義”定性和批判而要求的回到中國本身,只要論辯的雙方能夠各退一步,即承認(rèn)任何研究都是視角性的、文化性的、意識形態(tài)性的,即使那種聲稱最客觀的研究也都存在著不為其執(zhí)行者所清醒地意識到的“前見”和“前結(jié)構(gòu)”的影響,此其一也。再者,我們要涉及一個更復(fù)雜的問題,即如果說有意無意的“漢學(xué)主義”或者“前見”和“前結(jié)構(gòu)”是一種主觀主義,那么要求對事物進(jìn)行如其本然的再現(xiàn)則是一種客觀主義。“客觀”怎么可能淪為“主義”呢?誠然,強(qiáng)調(diào)研究的客觀性表面上是為了規(guī)避任何類型的先入之見或局外闡釋,而實際上對于研究對象來說,此要求亦不外乎一種先入之見或局外闡釋,一種視角或“主義”,這是因為:其前提是假定研究對象作為物自體般的存在,而這個物自體卻是一種純粹理性的推論。
什么是物?康德的物自體是物本身嗎?應(yīng)該不是。所謂“物”乃是物的存在和存在方式,也就是物的出顯/現(xiàn)象,此“出顯/現(xiàn)象”不能只是理解為物的形式,依此則仿佛物還擁有離開其形式的內(nèi)容即物本身;非也,物之所以被分解為內(nèi)容和形式,或者本質(zhì)與現(xiàn)象,不是因為其有一個獨(dú)立的自身存在、而后再發(fā)展出一個現(xiàn)象性的存在,它就是一個渾然一體的存在,但不幸的是,理性錯誤地以為其所看見者為現(xiàn)象,看不見者為本質(zhì)。看不見,那是主體的認(rèn)識局限,不是物這方面的自設(shè)防線。對于物來說,真相和假象的區(qū)別唯在于其本質(zhì)與現(xiàn)象之間是常規(guī)性或非常規(guī)性之連接,但無論怎樣,在主體眼中的本質(zhì)與現(xiàn)象于物本身則是連接不二的。
這說的是自然界的事物。作為人文科學(xué)研究對象的人類活動,除了要服從這一般性的規(guī)律而外,其通常所謂的“形式”和“現(xiàn)象”同時還意味著與研究者之間所構(gòu)成的一種關(guān)系,與其說我們生活在“傳統(tǒng)”之中,毋寧說我們生活在對“傳統(tǒng)”的解釋和選擇之中,甚至也可以說,我們生活在我們自己的觀念中或一個意義交織的世界。人類活動的歷史是由理念所指導(dǎo)的物質(zhì)實踐史,歷史本來就包含了理念,也包含了其當(dāng)代賡續(xù)者對此歷史及其理念的理解和闡釋。歷史永遠(yuǎn)是帶著對于歷史的虛無主義而展開自身的,當(dāng)有人稱“所有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時,其意即包含了“當(dāng)代”對“古代”的取與舍,即使所謂“取”也不是照搬,而是抽取,將可取用者抽離其具體歷史語境而移用于當(dāng)代語境,是“古為今用”。因此,不僅是自然科學(xué)不能將研究對象區(qū)分為本質(zhì)與現(xiàn)象,人文科學(xué)更加不能想象一個不帶理念、闡釋和抉擇的純粹本然的歷史。如同“漢學(xué)主義”之作為一種主觀主義,在對“漢學(xué)主義”的批判和否棄中對返回事實本身的要求也同樣是假客觀之名的另一種主觀主義。
在任何研究中,視角和“主義”都是我們?nèi)祟悷o法擺脫的宿命。在自然科學(xué)中,它們表現(xiàn)為解題方式、實驗工具和條件,如物理學(xué)家海森伯的測不準(zhǔn)原理所揭示的。在人文科學(xué)中,潛入研究過程和方法論、從而妨礙其研究對象之呈現(xiàn)的還有話語、裝置(dispositif)、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習(xí)俗等等。顧明棟注意到“漢學(xué)主義”之作為“知性無意識”“學(xué)術(shù)無意識”“政治無意識”①參見[美]顧明棟著,張強(qiáng)等譯:《漢學(xué)主義: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 年,第六、七章。等貌似悖論的現(xiàn)象或規(guī)律,在我們看來,這也是注意到了視角的先天性,它不是可以隨便甩掉的:它不再是從外部被嵌入的異物,而是早已內(nèi)化為研究主體的結(jié)構(gòu)和存在。因而,可以進(jìn)一步斷言,視角是存在性的,為人類的生命所本有:視角是人類的存在方式。俗謂“人是理性的動物”即含有理性歸屬于人之存在的意味,這也就是說,理性展開于人的存在之中,理性是人的存在方式。不消說,我們討論的視角無非理性的一個別名。
顧明棟敏感于漢學(xué)“無意識”,目光如炬,將無處不在、無時不有而我們卻習(xí)以為常的“漢學(xué)主義”弊端和丑態(tài)暴露出來,這無論對于海外漢學(xué)家抑或國內(nèi)同行都是一種有益的提醒,幫助我們在研究工作中擺脫單一視角的局限,而趨向于多視角和交互視角。不過,遺憾的是,顧明棟(也包括周寧、葛兆光,還有其他許多學(xué)者)卻沒有意識到,其本人對研究客觀性的要求即一種客觀主義也同樣是一種視角,一種視角形式的生命沖動。亞里士多德在其《詩學(xué)》里早已說過,再現(xiàn)(mimēsis,representation)、求真、求知乃人類之天性,自孩童起便有表現(xiàn),在這一點上,哲學(xué)家和普通人無異②安東尼·肯尼(Anthony Kenny)爵士的亞里士多德《詩學(xué)》新譯本將其中的關(guān)鍵術(shù)語“mimēsis(摹仿)”翻譯為更貼近亞里士多德褒義的“representation(再現(xiàn))”,而非在柏拉圖那里帶有貶義色彩的“imitation(摹仿)”,也不采用懶漢做法的音譯“mimesis”。參見Anthony Kenny,“ Introduction” ,in Aristotle,Poetics,trans.by Anthony Kenn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注:“Introduction”未編頁碼。。接著這一思路,海德格爾順利將認(rèn)識論納入存在論,例如將康德變成其本人的一個副本。
因此,在主張客觀再現(xiàn)的顧明棟等學(xué)者那里,也同樣存在著“主義無意識”或“視角無意識”。但這不是我們要批評顧明棟們的地方,因為沒有人能夠完全做到客觀、無立場、無視點,不用說,這也包括我們自己。我們也不擬揭露他們對自己的先在“視角”毫無自覺、而對他人的“視角”是無限放大,仿佛他們已經(jīng)掌握了上帝視角,而其他人則只有“習(xí)見”“俗見”“偏見”等。我們不在視角之有無、多寡、大小上糾結(jié),我們只是為其惋惜:當(dāng)他們了解到視角無意識而根深蒂固時便在理論上止步不前了。他們未能意識到這是人的“此在”性質(zhì)使然,人的局限性使然,因而也未能看到我們與研究對象的關(guān)系不只是意識對意識、理性對理性、話語對話語的純認(rèn)識論關(guān)系,而是兩個及以上個體之間的存在論關(guān)系。對此,無論胡塞爾的“主體間性”抑或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都僅僅說對了一半;其完整的含義只能用“個體間性”來表達(dá),因為所謂“個體”既意味著它的獨(dú)一無二性,又表示此個體與彼個體之間既同一又有差異的關(guān)系,一個個體的存在是以另一個個體的存在為前提的,更簡單明了地說,沒有社會,便沒有個體,二者區(qū)別而在,就像沒有他者,便沒有自我一樣,因為任何個體或自我都必須通過與外部世界的聯(lián)系和互動而建構(gòu)其身份。
既然將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定位于“個體間性”的存在論關(guān)系而非胡塞爾“主體間性”的認(rèn)識論關(guān)系,那么對于這樣的研究就不能再以認(rèn)識論的標(biāo)準(zhǔn)來要求,而必須轉(zhuǎn)變?yōu)橐源嬖谡撘曋8鶕?jù)認(rèn)識論的要求,研究的最佳境界是達(dá)到主體與客體的完美契合,主體得到客體的全部真相,最終目的當(dāng)然是對于客體世界的控制和利用。而根據(jù)存在論的標(biāo)準(zhǔn),主體不是面對一個死的、物質(zhì)性的、不言語的客體,而是面對一個活的、精神性的、擁有自己話語的對象,這一主體嚴(yán)格說不能再以“客體”相稱,而當(dāng)以“主體”這一稱謂相禮敬了,根據(jù)巴赫金的說法,如本文伊始所概述,這是人文科學(xué)之區(qū)別于自然科學(xué)的基本特點:如果說在自然科學(xué)中,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是認(rèn)識論的主客體關(guān)系,那么在人文科學(xué)這里,研究者面對的是文本,是一個言說主體,因而其與研究對象便構(gòu)成了一種新型的關(guān)系,即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一種對話性的關(guān)系。
知曉了人文科學(xué)的“個體性間性”對話特征,漢學(xué)主義之將漢學(xué)研究原罪化、污名化的問題所在便昭然若揭了:漢學(xué)主義執(zhí)迷于“反映論”的思維模式不能自拔,沒有自覺到包括漢學(xué)在內(nèi)的人文科學(xué),其根本特點不是正確地反映,而是深切地反映,以實證主義的標(biāo)準(zhǔn)苛責(zé)人文科學(xué)的準(zhǔn)確性,這無異于緣木求魚①例如,在文本接受或文化傳播過程中,常常發(fā)生的“誤讀”“挪用”“變異”等現(xiàn)象唯有放在“間在對話”的框架中才能獲得其合法性、正當(dāng)性和積極的意義。。人文科學(xué)是人的科學(xué),是活生生的個體在研究活生生的個體,他們有理智,也有情感,而情感是不可拿理智來分解的,更不可以實用性相要求②當(dāng)代法國哲學(xué)家米歇爾·塞爾甚至發(fā)誓說:“我寧愿死在一個只談理性的時代到來之前。”他道出其中的緣由:“一個無時無處不為理性所霸占的生活是無法讓人生活下去的。”他悲觀地看到,只談“正確性(rightness)”的精密科學(xué)將毀滅一切無法驗之為“正確”的東西,包括格言、俗語、信仰、神話、詩歌、悲劇等等;它們一無“是”處,且亦一無“用”處,“不能生產(chǎn)任何東西,不能治病,也不能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發(fā)展”,那就更無存在之必要了。(See Michel Serres,“Literature and the Exact Sciences”,SubStance,1989,vol.18,no.2,pp.3-34)。
四、 反映論的變體:后現(xiàn)代主義和新實在論
看來,一個貌似稀松平常的對話論,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和掌握的。“漢學(xué)主義”的批判者沒有,其所倚重的后現(xiàn)代主義或后結(jié)構(gòu)主義,在“漢學(xué)主義”所經(jīng)歷的失敗中,其實也暴露出它們未曾窺入對話理論的堂奧:如果真的是抓住了對話的要義,那它們就不會效法康德之在本體與現(xiàn)象之間劃出一條理性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宣稱符號永遠(yuǎn)不可企及實在的世界,其所謂“文本之外無一物”(非唯德里達(dá)如是說,此為后結(jié)構(gòu)主義之基本原理),即是說,任何意指無論如何延異、漂流都始終不能越出文本的限制,用尼采的話說①杰姆遜借用尼采的一段話作為其一本書的題記,這段話包含了“語言的牢籠”一語(See Fredric Jameson,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ifc),但查閱德語尼采全集版原文,實則為“語言的束縛(sprachlichen Zwange)”(參見:Friedrich Nietzsche,Nachgelassene Fragmente,1885-1887,KSA 12,hrsg.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München:DTV,S.193)。,語言是思想打不破的牢籠,因為語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
德國新實在論哲學(xué)家馬庫斯·加布里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康德陰魂:“后現(xiàn)代主義不過是形而上學(xué)的又一個變體。”②[德]馬庫斯·加布里爾著,王熙、張振華譯:《為什么世界不存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2年,第3,6,1,12,77,75頁。雖然康德證實了現(xiàn)象及其規(guī)律的合理有效,相反,后現(xiàn)代主義者否認(rèn)符號和話語的真實指涉,但他們的共同前提則是對一個物自體的假定,而且,若是言及物自體,康德的現(xiàn)象也是無涉、無份的,其規(guī)律也是有限的。康德的現(xiàn)象就是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話語和符號,借助它們事物得以成為現(xiàn)象,然卻不是與本體相關(guān)的現(xiàn)象。
新實在論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批判算是鞭辟入里,不過,這也并不是說新實在論因此就真正抓住了對話論的精髓,因為雖然其認(rèn)定了“對于事實的思考與被思考的事實一樣,都有充分理由被視為是存在的”③[德]馬庫斯·加布里爾著,王熙、張振華譯:《為什么世界不存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2年,第3,6,1,12,77,75頁。,尤其是將建構(gòu)主義認(rèn)為虛妄的觀念、話語、視點和感受一概視為真實的存在,似乎終于打通了康德及其后現(xiàn)代繼承人在本體與現(xiàn)象之間所設(shè)置的隔閡,然而,對于二者究竟具有怎樣的關(guān)系,它尚未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說。設(shè)若其真是打通了本體與現(xiàn)象的阻塞,那么它就不會放言:“一切都存在,除了:世界。”④[德]馬庫斯·加布里爾著,王熙、張振華譯:《為什么世界不存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2年,第3,6,1,12,77,75頁。它界定“世界”為至大無外、包容萬有的“整體”,因為這樣的世界無處立足、存在:“一切存在的東西都存在于某處——即使只存在于我們的想象中。”⑤[德]馬庫斯·加布里爾著,王熙、張振華譯:《為什么世界不存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2年,第3,6,1,12,77,75頁。而反過來說,假使世界能夠存在于某處,那它就只是某一具體之物,無法包羅他物、包羅萬象。再者,如果允許“世界存在于我們的思維中”,那么“我們的思維便無法出現(xiàn)在世界之中”,“否則就會存在一個處在我們的思維以及‘世界’(在思維內(nèi)容的意義上)之外的世界了”⑥[德]馬庫斯·加布里爾著,王熙、張振華譯:《為什么世界不存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2年,第3,6,1,12,77,75頁。,這就像“畫了一切的畫家無法在作畫時將自己畫進(jìn)畫中。畫中的畫家不可能與作畫的畫家完全同一”⑦[德]馬庫斯·加布里爾著,王熙、張振華譯:《為什么世界不存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22年,第3,6,1,12,77,75頁。。而如果說世界之外仍有某物(思維或思維主體)存在,那么世界便不成其為“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的世界了:它將變成某物,眾多事物中的一物。
要之,加布里爾在“世界”和“存在”之間楔入看似無法解除的矛盾和悖論:其一,肯定具體的存在,就不能肯定超越性的世界;其二,世界若在思維之中,則思維必定在世界之外。這顯然沒有克服其所批判的康德和建構(gòu)主義的本體與現(xiàn)象、主體與客體的二元論,缺乏對話性思維:它未能看到被設(shè)定為包容萬物的世界只是意味著萬物之間的聯(lián)系以及對此聯(lián)系的想象,未能看到這樣的聯(lián)系是眾多個別事物包括個人之間對話的產(chǎn)物:只有想象一個超越你我他或萬物的“整體”/“世界”,彼此之間的聯(lián)系才能建立起來,對話才能啟動。若是封閉于自我的狹小世界里,而不去想象一個更闊大的世界,那么對話根本無從形成,只能是各守本位、自說自話、老死不相往來。絕對的差異不能導(dǎo)向?qū)υ挘挥嘘P(guān)系中的差異才能形成對話。
從反映論與對話論之相區(qū)別的角度觀察,新實在論其實仍然是一種反映論,它設(shè)定了主客體之間不可移除的二元對立和彼此外位。若是沒有這種主客體二元對立和彼此外位,我們在思維世界時,有什么不可能將世界和執(zhí)行思維世界的主體一起包括進(jìn)世界呢?!不放棄主客體二元對立模式,即便一時能夠?qū)⒂^念、話語、視點和感受均視為真實存在,即便相信我們能夠認(rèn)識到自在的事實,那也不能堅持多久,它們終歸是要被作為不能反映事物真實的主觀幻象的。
新實在論運(yùn)用在文化問題上,就是文化多元主義或文化相對主義,文化之間彼此不通、各是其是、各美其美、相望無“事”①文化多元主義的基礎(chǔ)是文化相對主義,而文化相對主義就是堅持“每一種文化都是自足的、自治的、獨(dú)立的但同時又是平等的”,即是說,“每一種文化都在自己的背景下才有意義”,因而對于不同的文化,“你要做的只是了解它的背景,然后弄明白人們正在做什么,為什么這么做”。文化只可以尊重、了解乃至深描,但決不能從外在介入、干預(yù)。應(yīng)該承認(rèn):“文化和價值既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某個特定的種族、宗教群體或社會階層所固有的。它們可以通過政治和司法采取行動,通過經(jīng)濟(jì)和社會改革,通過開明政治領(lǐng)袖的努力以及通過學(xué)校、教會和大眾媒體的教育而發(fā)生轉(zhuǎn)型。”是的,文化是發(fā)展的、變化的,中國古人早有“移風(fēng)易俗”一說,但推動文化發(fā)展和變化的力量只能是處身這一文化內(nèi)部的人民及其真實的需求和愿望。或許“有益的外部影響”也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外因必須通過內(nèi)因而發(fā)揮作用,否則便會“在政治上不正確”。(參見[美]勞倫斯·哈里森著,王樂洋譯:《多元文化主義的終結(jié)》,北京:新華出版社,2017 年,第3—12頁)但隨著當(dāng)今國際流動性的加劇,從而形成文化全球村,也就是說,當(dāng)代人既生活在其世居的文化圈,也經(jīng)常出入于其他文化圈,準(zhǔn)確說,當(dāng)代人生活在一個“文化的交互空間”,即“第三空間”,一種文化間性或一種新的文化便出現(xiàn)了。這種新文化不單獨(dú)屬于任何一方,但同時又是屬于進(jìn)入其間的所有人,屬于所有仍然自有其文化圈的人。這就是筆者所謂的“文化星叢共同體”(參見金惠敏:《文化自信與星叢共同體》,《哲學(xué)研究》2017 年第4 期)。加布里爾的新實在論,因其否認(rèn)“總域”即“世界”的存在,就不能夠闡釋和迎接這一新的文化空間的到來。其實,只要加布里爾將其“總域”理解為無處不在的關(guān)系,那么“世界”便不會不“存在”。。這一傾向在其“意義場”論中表現(xiàn)得更加清晰:由于不存在無所不包的意義場,“無數(shù)的意義場并不聚合為一個總體”,意義場各在其在、各守其位,彼此之間不可能建立“世界性”聯(lián)系;而如果有人堅持人類終究還是能夠“觀察并創(chuàng)造”諸多“意義場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那么此關(guān)聯(lián)也“總是只能位于一個新的意義場中”②[德]馬庫斯·加布里爾著,王熙、張振華譯:《為什么世界不存在》,第197—198,198頁。。這就是說,人類只能龜縮在自己的意義場內(nèi),“意義可謂是我們的宿命”,“我們無法擺脫意義”③[德]馬庫斯·加布里爾著,王熙、張振華譯:《為什么世界不存在》,第197—198,198頁。,因而即便我們能夠想象異域和異質(zhì),但也是寸步不移于我們自身的意義場,結(jié)果,他者的意義要么不能進(jìn)入我們的意義場,要么被我們自我化、內(nèi)部化,也就是轉(zhuǎn)化、消化和消逝了,即一切非我將歸于自我。或許可以認(rèn)為這是一個新的意義場,不再是那一舊我,但我們是在一個老的意義場內(nèi)迎入他人的新的意義場,后者被拆解和整合進(jìn)我們的意義場,我的主體地位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是得以加強(qiáng),且是加強(qiáng)了一個具體而個別的意義場,此時再行辨認(rèn)意義場之新舊已經(jīng)沒有意義。這就是我們的意義宿命,即我們永遠(yuǎn)是在個人狹小的自我圈子里打轉(zhuǎn)。顯然,加布里爾的“意義場”論與“漢學(xué)主義”發(fā)明者和批判者的盲目排外、自我中心如出一轍。其實,即使沒有意義場論,只要株守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反映論模式,文化(意義場)之間的對話便不會發(fā)生。反映論堵絕了在兩個文本、或主體、或文化域之間的對話論。試想,在一個文明/文化對話時代,哪一種文明/文化可以立身于自我的主體性而判定其他文明/文化為“不正確”呢?文明互鑒、文化交流需要對話論,而非反映論:對話論導(dǎo)向“和”而不同、多元共存,反映論帶來唯我獨(dú)“是”、唯我獨(dú)尊。反映論雖然古老,但它在西方現(xiàn)代性的改造和利用中,如果不是國際霸權(quán)主義的思想淵源,至少也是扮演“幫兇”的角色④嚴(yán)格說來,反映論并不代表(西方)哲學(xué)史的一個特殊時期(一般認(rèn)為此前的哲學(xué)是本體論),也不能與任何一種政治經(jīng)濟(jì)主張或行為相捆綁,但是由于認(rèn)識論的要義是對主體性的確認(rèn)和強(qiáng)化,而此主體性在“現(xiàn)代史”和“世界史”的形成過程中又表現(xiàn)為對自然、客體、他者的征服和控制,于是認(rèn)識論就與帝國主義、霸權(quán)主義內(nèi)在地勾連起來。道理很簡單:認(rèn)識論只承認(rèn)一種真理,即“正確的”真理,認(rèn)為世界問題只有一種答案,即“正確的”答案;且這種被奉為“正確的”東西只是為西方人所擁有。其實,在任何一種社會歷史語境,認(rèn)識論都無法避免唯我論的趨向或偏向,這是由認(rèn)識論自身的性質(zhì)所決定的。要根本上解決認(rèn)識論的問題,就必須進(jìn)行一場哲學(xué)范式的轉(zhuǎn)換,在筆者,就是向著對話論的轉(zhuǎn)換。參見金惠敏:《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對西方哲學(xué)發(fā)展史的一個后現(xiàn)代性考察》,《陜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05年第1期。。
余 論
漢學(xué)主義,以及其以之為支撐的后現(xiàn)代主義,還有試圖克服后現(xiàn)代主義之話語建構(gòu)性的新實在論,其一個共同點是守持主客體二元對立之思維模式,而主客體二元對立思維即是一種認(rèn)識論思維。如果說這三者之間有什么不同的話,那么可以認(rèn)為:漢學(xué)主義是天真而樂觀的反映論,它相信有不帶意識形態(tài)前見和客觀而純粹的知識;后現(xiàn)代主義是清醒而悲觀的反映論,它不相信有任何能夠反映客觀現(xiàn)實的符號,一切都是文本和話語。新實在論稍微復(fù)雜一些,但終究難逃反映論的思維方式:它欲將存在和人類對存在的感受、認(rèn)識和想象一并歸作真實的存在,而不承認(rèn)那個不可寄身于具體存在的總體性存在即所謂的“世界”,它堅稱如此的“世界”“不存在”,這好像是從主客體二元論回到了存在一元論,一舉取消了反映論,但實際上它不過是將過去所謂的“主觀”變成了其所謂的“客觀”(1),然后又在“主觀”之中剔除可超越于自身存在的即關(guān)于“世界”的想象(2)。進(jìn)而言之,如果將人類的所有存在算作一方,將總體性的“世界”算作一方,則可以看出,新實在論之憂心所在乃是總體的“世界”無法表征具體的“存在”,而這不正是后現(xiàn)代主義所發(fā)現(xiàn)/發(fā)明的那個語言學(xué)的“再現(xiàn)危機(jī)”嗎?新實在論之拒絕“世界”就如同后現(xiàn)代主義之拒絕“語言”,因而它們都不能實現(xiàn)我們期待的那種再現(xiàn)功能。顯然,新實在論最終仍跌倒在認(rèn)識論面前。
漢學(xué)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以及新實在論只有徹底拋棄其實證主義的反映論而轉(zhuǎn)向間在對話論,才能克服其自身的理論矛盾,才能正確地看待人文科學(xué)之不同于自然科學(xué)的特殊性:它本質(zhì)上是對話,是反應(yīng),而非反映,不是說對話中不存在反映,而是反映歸屬于反應(yīng),歸屬于對話。馬克思早就告訴我們,關(guān)鍵的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解釋”是對世界的認(rèn)識,而“改變”則是人類與世界之間的、以行動所主導(dǎo)的關(guān)系。對話既包含認(rèn)識,又同時落實于行動,因為我們既是精神性存在,也是物質(zhì)性存在,我們是身心一體的存在。遺憾的是,漢學(xué)主義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將人類僅僅作為精神性存在,符號性存在,新實在論將精神性存在和物質(zhì)性存在一并作為“實在”,但仍留下一個無法歸入“實在”的“世界”,這一“世界”如果不是人類全部精神“世界”的話,那也是人類精神存在的一個重要特征,因為只有精神才能想象一個超越其自身存在的“世界”。新實在論對“世界”的排斥就是對精神職能的懷疑,這也是對認(rèn)識論的懷疑,而對認(rèn)識論的不信任則源自于認(rèn)識論本身:認(rèn)識論分裂了主客體,由此在主客體之間,它只能選擇二選其一,即要么是符合,要么是背離。新實在論最終還是回到了它所反對的后現(xiàn)代主義。以筆者之愚見,新實在論最好不要宣稱“世界不存在”,而應(yīng)該說“一切存在皆為世界”,任何試圖超越“世界”的努力都是“世界”本身的合理延伸。
“漢學(xué)主義”論爭已有時日,似乎高潮已過,但學(xué)界對它背后的哲學(xué)支撐及其與文明互鑒和對話之時代大趨勢的脫節(jié)尚未給予充分而有效的揭示。此乃筆者不憚“好辯”之名、爰成拙文的初衷。予豈好辯哉?“情”不得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