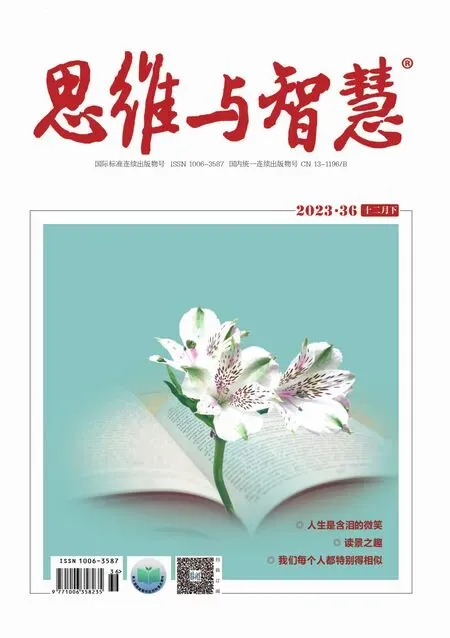錢鐘書生命中的楊絳
◎ 林 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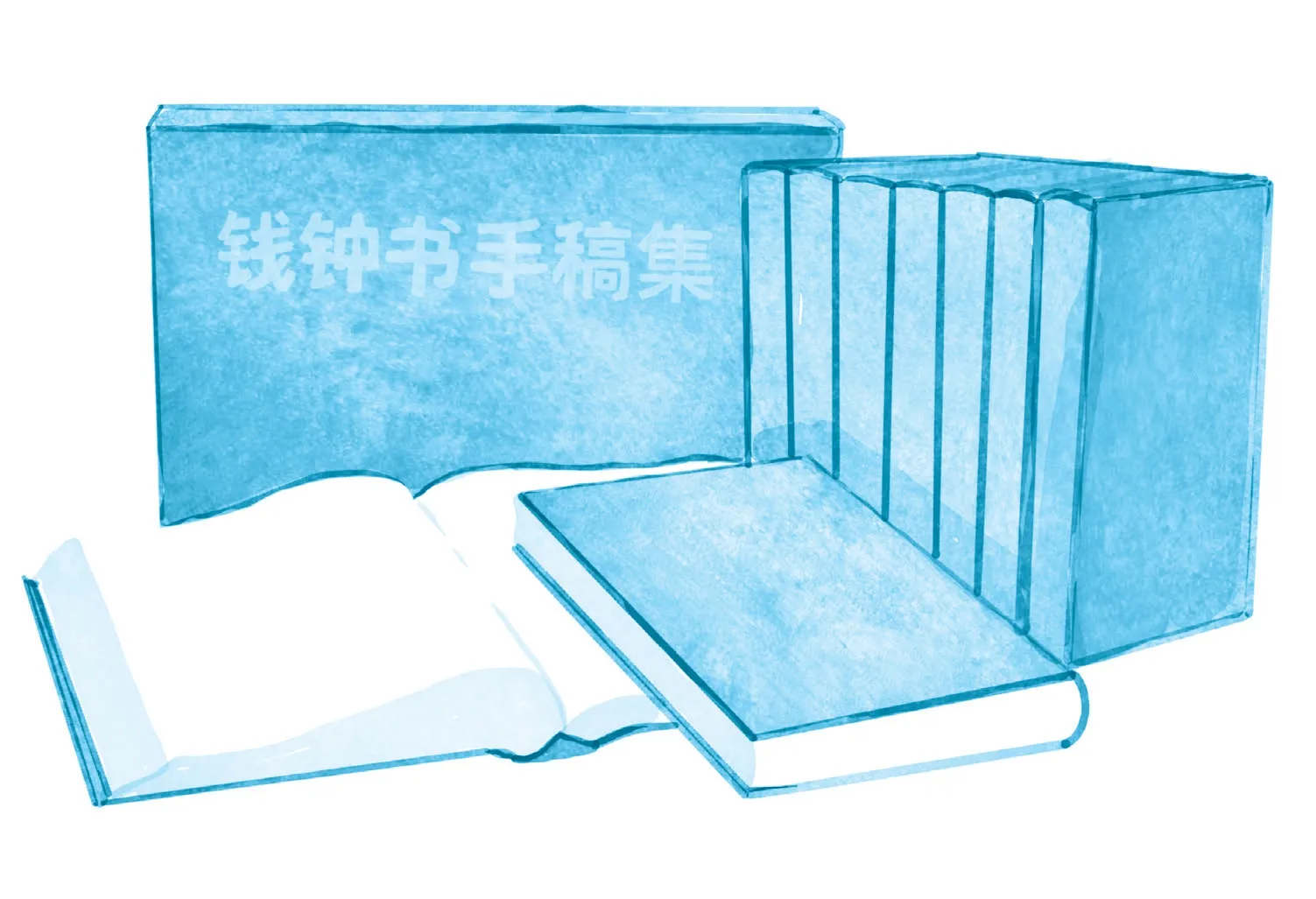
錢鐘書與楊絳在彼此眼中是什么樣的呢?楊絳是錢鐘書口中“最才的女”,錢鐘書是楊絳眼中拙手笨腳的“書呆子”。楊絳明白錢鐘書的不諳世故,但她更愿意保護他的天真,她為自己設定的角色是“最賢的妻”。
2003 年7 月,楊絳晚年寫的回憶錄《我們仨》出版。錢鐘書再次進入大眾視野,讀者們得以看到他的日常生活,以及他與楊絳的愛情傳奇。如今,《我們仨》出版20 周年,錢鐘書和楊絳這對學術伉儷,兩人一生長河一般的往事,已經成為一種精神性的象征。他們生活中相濡以沫,精神層面也是棋逢對手。
錢鐘書在1946 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人·獸·鬼》的樣書上寫道:“贈予楊季康,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這就是錢鐘書眼中的楊絳。
楊絳曾在自己的書中寫道:“我做過各種工作:大學教授、中學校長兼高中三年級的英語教師,為闊小姐補習功課,還是喜劇、散文及短篇小說作者等等。但每項工作都是暫時的,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我一生是錢鐘書生命中的楊絳。”
1998 年錢鐘書去世后,楊絳說,她還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她“應盡的責任”。這責任,就是整理錢鐘書的學術遺物--幾麻袋的手稿和中外文筆記。她找出大量筆記,經反復整理,分出三類:涵蓋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的外文筆記,與日記混在一起的中文筆記、讀書心得。這些成了《容安館札記》,178 冊的外文筆記,20卷的《錢鐘書手稿集》。
錢鐘書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是筆記式的。錢鐘書的筆記也隨著他不斷搬遷。從在英國牛津大學讀書時開始,錢鐘書的筆記不斷從國外搬遷至國內,從上海到北京,從一個宿舍到另一個宿舍,在鐵箱、木箱、紙箱,以至于麻袋、枕套里出出進進,幾經折磨。他盡情地讀書,勤謹地記筆記。有部分筆記本已字跡模糊,紙張破損。楊絳回憶:“鐘書每天總愛翻閱一兩冊中文或外文筆記,常把精彩的片段讀給我聽。我曾想為他補裰破舊筆記,他卻阻止了我。他說:‘有些都沒用了。’哪些沒用了呢?對誰都沒用了嗎?”
在楊絳生命最后一程,對她來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整理錢鐘書生前的讀書筆記和手稿,包括中文筆記、英文筆記和日札。錢鐘書認為這些東西“沒用了”,但楊絳不這么看,她覺得這些是他一生積累的知識,對其他學者做研究是有用處的,而保存手稿最好的方式是整理出版。
錢鐘書的手稿裝了幾大麻袋、7 萬多張,多數是字跡已模糊的散頁和紙片。楊絳戴鏡逐頁辨認,再仔細剪貼、分類和梳理,最后交到商務印書館影印。日復一日,她不慌不忙地,一個人在書桌前做著這些浩繁的工作,邊整理邊交付出版。2015 年年底,《錢鐘書手稿集》終于全部出齊。
百歲老人,在靈魂上和錢鐘書息息相通。1997 年、1998年兩年間楊絳失去了生命中兩個最親的人--女兒和丈夫,孤身一人怎么面對人世和死亡?她的精神世界里,錢鐘書和女兒錢媛都還在。她似乎成了錢鐘書生命的一種延伸。“夜聞風雨聲,耳始聾。《我們仨》改定題目,選定段落。”《我們仨》書稿快要完成的2002 年8 月19 日那天,楊絳在大事記里寫了這樣一句。
2003 年7 月,《我們仨》由三聯書店出版了,它是楊絳晚年最動人的作品,用平實的語言講述這個單純溫馨的學者家庭。“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為有我們仨。我們仨失散了,家就沒有了。剩下我一個,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窮的羈旅倦客;顧望徘徊,能不感嘆‘人生如夢’‘如夢幻泡影’?但是,盡管這么說,我卻覺得我這一生并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是我們仨。”
2016 年5 月,105 歲的楊絳辭世,“我們仨”團聚了。楊絳生前已經將他們家中所藏的珍貴文物字畫,全部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其他藏書和手稿等物,也得歸其所。
(曉潼摘自《遼寧日報》2023 年8 月2 日/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