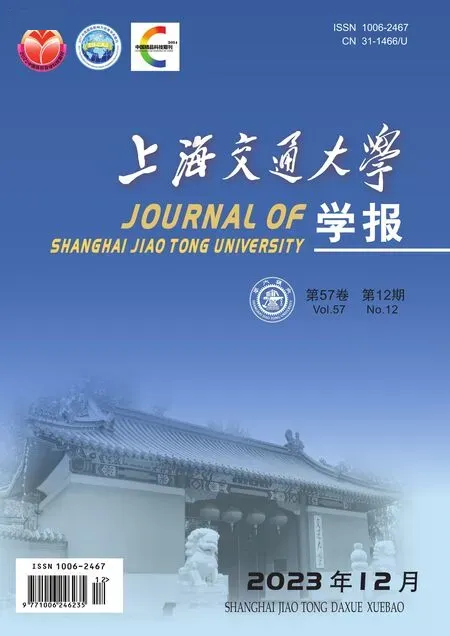雙線平行頂管上跨地鐵盾構隧道施工環境影響實測分析
應宏偉, 姚 言, 王奎華, 張昌桔
(1. 浙江大學 濱海和城市巖土工程研究中心, 杭州 310058; 2. 河海大學 巖土力學與堤壩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南京 210024; 3. 杭州市市政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杭州 310014)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人口的增長,城市化進程對空間與資源的有效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下空間的開發逐漸成為城市規劃的重要方向.頂管施工技術是繼盾構施工技術之后發展起來的一種非開挖隧道施工技術,常用于各種地下管線、通道的建設.目前頂管法隧道的施工環境越來越復雜,頂管施工不可避免地會對周圍建(構)筑物產生影響,因此研究頂管施工對諸如地表沉降、隧道變形等周圍環境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在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研究中,有理論解析法、數值模擬法、經驗公式法、模型試驗法等方法.而對于經驗公式的研究,又以Peck[1]于1969年提出的基于實測數據的地表橫向沉降預測公式最具影響力.Peck公式是基于有限地區實測資料提出的經驗公式,在我國各地應用時需考慮其適用性及其沉降槽寬度系數i、土體損失率η等參數的選取.國內外學者[2-4]提出了很多理論方法計算i與η,由于這些計算方法最終還是取決于其他相關參數經驗值的選取,所以直接基于實測數據通過Peck公式反分析得到沉降槽寬度參數和土體損失率應用更為廣泛,使用更加簡便.
國內有不少學者收集了我國各地隧道施工引起地表沉降實測數據,通過反分析得到相關參數,為Peck公式在我國各地的適用性提供了豐富的參考依據.韓煊等[5]通過對30多組不同工法及開挖方式隧道實測數據的分析,肯定了Peck在我國的適用性;吳昌勝等[6]收集并分析了各地區盾構隧道施工引起的土體損失率和沉降槽寬度參數,完善了我國各地Peck公式經驗參數的取值;馬克栓[7]、丁智等[8]基于多線平行隧道的實測數據,得到了相關參數的經驗值,進一步肯定了Peck公式在多線隧道中的適用性.
在新建隧道上穿對下方既有隧道影響實測與模型試驗研究方面.朱蕾等[9]基于上海地鐵13號線上穿地鐵4號線施工期隧道變形監測數據,指出既有隧道的隆起具有滯后性且縱向變形曲線近似成正態分布.黃德中等[10]采用離心模型試驗與現場實測結合的方法,指出新建盾構施工對既有隧道的影響主要在兩隧道交點左右兩倍盾構直徑范圍內.
在隧道施工引起的環境影響實測研究中,學者們多將目光聚焦于盾構隧道,而頂管隧道施工雖與盾構施工有諸多相似之處,但在頂進、注漿方式等方面還是有較大差異,因此對于盾構隧道的研究結論可參考而不能照搬.在頂管施工環境影響的理論與數值研究中,以黃宏偉等[11]、魏綱等[12]為代表的學者們常將頂管施工中的作用概括為土體損失等位移作用以及正面附加推力、管壁摩擦力、注漿壓力等荷載作用分別加以研究.在頂管施工環境影響的地表實測研究中,周順華等[13]對單線頂管實測地表沉降進行了分析,魏綱等[14]對雙線平行頂管實測沉降進行了分析.
可見頂管施工引起的環境影響,特別是頂管穿越引起下方隧道隆沉的研究較少.本文以杭州砂質粉土地層中某大直徑雙線平行電力頂管隧道為研究對象,整理了頂管從上方穿越地鐵隧道過程中地表沉降、地鐵道面隆沉的實測數據,詳盡分析了地表橫向沉降分布、地表沉降隨時間的發展、下方地鐵隧道隆沉發展變化的規律.
1 工程概況
1.1 場地環境及工程地質條件
案例為城市高壓線路上改下工程,里程總長度2 044.4 m,雙線頂管長約285 m,埋深約4.14 m,管節內徑3 500 mm,外徑4 140 mm,壁厚320 mm,單節長度2.5 m,采用泥水平衡頂管機施工.頂管從北至南由8號井推至9號井,西線頂管先行施工.
頂管上穿杭州地鐵1號線盾構隧道,穿越角度為71°,頂管與地鐵盾構隧道的平面位置關系如圖1(a)所示.盾構隧道埋深約10.28 m,管片內徑5 500 mm,外徑6 200 mm,壁厚350 mm.為了減少頂管穿越對地鐵的影響,控制地鐵設施的受力與變形,地鐵隧道上方采用全方位高壓噴射(MJS)工法進行水泥土加固,加固深度為地表以下2.0 m到盾構隧道拱頂上方 1.0 m, 加固區平面圖和剖面圖如圖1所示.

圖1 頂管上跨地鐵盾構隧道與MJS工法樁加固區的平面圖和剖面圖(m)Fig.1 Plan view and sectional view of pipe jacking crossing over subway shield tunnel and reinforcement area of MJS method (m)
施工場地第四紀覆蓋層厚度約為70 m,其上部為河口相地層,系錢塘江口近、現代沖海積沉積的粉砂性土地層.施工場地地面高程6.5 m左右,各土層物理力學參數如表1所示.表中:h為隧道軸線埋深;w為含水量;a1-2為壓縮系數;ES1-2為壓縮模量;c為黏聚力;φ為內摩擦角;kh為水平滲透系數;kv為垂直滲透系數.本工程地鐵區間隧道位于④-1、④-2砂質粉土層,電力頂管隧道主要穿越②-2砂質粉土層,剖面圖如圖2所示.

表1 土層物理力學參數Tab.1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oils

圖2 電力頂管隧道剖面圖(m)Fig.2 Profile of the power pipe jacking (m)
1.2 監測點位布設
為了監測雙線頂管施工過程產生的地表沉降,沿頂管軸線方向進行地表沉降監測點的布設.頂管斷面j的地表沉降監測點布置情況如圖3所示.圖中:DBC表示地表沉降監測斷面.沿頂管軸線在穿越地鐵區域共布置7個監測斷面,監測平面圖如圖4所示.同時為了監測頂管穿越期間地鐵道面隆沉,沿地鐵方向布置2×23個監測斷面如圖5所示.圖中:DM表示地鐵盾構隧道監測斷面.

圖3 地表沉降監測斷面Fig.3 Monitoring section of surface settlement

圖4 地表沉降監測平面圖Fig.4 Plan of surface settlement monitoring

圖5 地鐵隧道監測斷面布置平面圖Fig.5 Layout plan of subway tunnel monitoring section
2 頂管施工實測結果分析
2.1 地表橫向沉降規律
頂管穿越地鐵盾構隧道區間典型沉降監測斷面DBC-1不同施工階段的地表橫向沉降監測曲線如圖6所示.圖中:坐標原點位置與x軸方向如圖3所示,坐標原點位于雙線頂管中軸線與地面的交點;S為地表豎向位移,負值表示沉降、正值表示隆起,下同.本文地表橫向沉降曲線圖坐標系均與圖3保持一致,不再贅述.

圖6 監測斷面DBC-1各施工階段地表沉降Fig.6 Surface settlement of monitoring section DBC-1 in each construction stage
以圖6所示斷面DBC-1為例進行分析,西線頂管穿過地表監測區域后,地表沉降槽發展為明顯的“V”形,最大沉降量發生在西線頂管軸線上方地表處,占該處最終沉降量的52.7%.西線貫通后,沉降槽保持“V”形,變形基本穩定,軸線上方地面沉降值相對穿越DBC-1斷面時僅有少量增長,增量占最終沉降量的9%.當東線頂管貫通后,地表沉降槽由“V”形變為不對稱的“W”形,后行頂管軸線上方沉降大于先行頂管.
頂管施工時需要克服開挖面的土壓力、刀盤的切削阻力、頂管機外殼和襯砌與土體之間的摩擦力等阻力,這些力的反作用于周圍土體使其經歷了擠壓、剪切等復雜的應力路徑并產生附加荷載.頂管通過后,頂管機與襯砌間的管徑差形成建筑間隙,土體向建筑間隙內移動,引起土體松動卸荷.在上述附加荷載與卸荷作用反復擾動下,頂管周圍加固土體力學性質降低,文獻[15]中采用室內模型試驗驗證了先行隧道對周圍土體擾動的現象.因此在經過先行頂管穿越期間對周圍土體的擾動后,后行頂管施工將引起更大的土體損失,造成更大的沉降量.
從圖6中還可發現,東線頂管頂進時,除了在自身軸線上方產生較大的沉降增量外,在西線頂管上方也產生了較大的沉降增量.原因有:① 如前文所述,東線頂管施工也對周圍土體產生了擾動,造成先行頂管四周土體強度降低;② 后行頂管施工過程中產生的力學效應傳遞到先行頂管襯砌上,使其產生位移和變形,造成先行頂管周圍土體發生應力重分布.因此在東線后行頂管的二次擾動下,西線先行頂管地層損失增大,最終使地表沉降量增加[16].由二次擾動引起的西線頂管上方的沉降增量占最終沉降量的38.3%.由此可見,近距離雙線平行頂管的開挖頂進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既要考慮先行頂管對周圍土體的擾動,也要考慮后行頂管對先行頂管的二次擾動.
2.2 地鐵盾構隧道豎向位移規律
以頂管頂進到影響區域為時間零點,對下方地鐵區間的道面累計豎向位移進行統計分析.如圖7所示.圖中:Stnl為地鐵隧道豎向位移,正值表示上浮,負值表示下沉;Ltnl為地鐵隧道里程.西線頂管在里程513 m左右處穿越,東線頂管在里程522 m左右處穿越.

圖7 頂管不同施工階段地鐵隧道縱向豎向位移Fig.7 Settlement of subway tunnel at different construction stages of pipe jacking
當西線頂管穿越完成后(7月31日),如圖7中黑色虛線所示,地鐵隧道豎向位移曲線表現為“W”形,以兩穿越點中線為對稱軸呈現較為明顯的對稱性,豎向位移在數值不大,上浮最大值約為1.70 mm,占最大上浮量的72%;西線穿越完成至西線貫通(8月3日)期間,地鐵隧道持續上浮達到最大值2.36 mm,曲線形狀基本保持不變,相對于剛穿越完成時,上浮增量為0.66 mm,占最大上浮量的28%.盾構隧道在西線頂管穿越完成后持續上浮直至貫通結束,說明頂管施工過程中管節周圍持續的注漿壓力等因素對下方盾構隧道上浮有一定影響,造成了上浮的滯后.
東線頂進期間地鐵隧道上行線的豎向位移規律與西線頂進期間類似.在東線頂管貫通后(8月24日),曲線峰值對應里程附近隧道繼續發生持續上浮,在9月2日達到上浮的最大值,約為3.5 mm.
從圖7所示的地鐵隧道豎向位移曲線來看,頂管頂進引起的沉降與上浮數值不大,但是影響范圍約為穿越點兩側4~6倍頂管管徑,遠大于文獻 [9-10] 中提到的影響范圍.
3 Peck沉降預測公式的適用性
3.1 單線頂管
目前工程界對單線頂管施工由土體損失引起的橫向地面沉降計算方法主要采用Peck提出的地面沉降橫向分布估算公式[1]:
(1)
(2)
式中:Smax為隧道軸線上方最大地面沉降;R為隧道半徑;i=Kh[2],K為地面沉降槽寬度參數.
在東線頂管穿越前,可以將西線頂管當做單線頂管加以研究.通過式(1)對西線先行頂管貫通后斷面DBC-1的地表沉降曲線進行擬合,得到曲線如圖8所示,其余斷面的擬合參數如表2所示.擬合曲線表明Peck公式可以較好預測單線頂管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西線頂管貫通沉降達到基本穩定后,各斷面K范圍在0.63~0.90之間,平均值為0.79,η范圍在1.22~1.93%,平均值為1.60%.

表2 單線頂管Peck法橫向地面沉降擬合參數Tab.2 Transverse surface settlement fitting parameters of Peck formula of single-line pipe jacking

圖8 單線頂管斷面DBC-1橫向地面沉降Fig.8 Transverse surface settlement of single-line pipe jacking in section DBC-1
3.2 雙線頂管
對于雙線平行隧道的地面橫向沉降預測,常采用將兩條單線隧道地面沉降橫向分布公式疊加的方法[7],并將重點放在先行、后行隧道的沉降槽寬度和土體損失率的選取上.
(3)

通過雙線隧道沉降預測式(3)對雙線頂管斷面DBC-1的地表橫向沉降實測數據進行擬合,結果如圖9所示,其余各斷面的沉降槽寬度及土體損失率參數如表3所示.表中:K1、K2分別為先后行頂管的地面沉降槽寬度參數;ηavg為先后行頂管的平均土體損失率.

表3 雙線頂管地表沉降曲線擬合參數Tab.3 Fitting parameters of the transverse surface settlement curve of Peck formula of double-line pipe jacking

圖9 雙線頂管斷面DBC-1橫向地表沉降Fig.9 Transverse surface settlement of double-line pipe jacking in section DBC-1
從圖9可以發現,式(3)可以較好地預測雙線頂管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曲線.案例中的雙線平行頂管,先行頂管的沉降槽寬度參數K平均值為0.74,大于后行頂管的0.58,是后行頂管的1.28倍;后行頂管土體損失率平均值為3.11%,是先行頂管的1.29倍.
4 地表沉降的時間效應
4.1 地表沉降時間曲線特征
圖10、圖11所示為7個監測斷面頂管軸線上方地表沉降隨時間t的變化曲線.

圖10 西線頂管上方地表沉降隨時間變化Fig.10 Time-dependent surface settlements above the pipe jacking of the western line

圖11 東線頂管軸線上方沉降測點沉降隨時間變化Fig.11 Time-dependent surface settlements above the pipe jacking of the eastern line
由圖可見,無論是西線頂管還是東線頂管,在頂管接近沉降監測斷面及其后的穿越期間,絕大部分測點觀測到較為劇烈的沉降;而在東線頂管接近沉降監測斷面及其穿越期間,可以在西線頂管軸線上方各沉降點觀測到輕微隆起,且這7個點的隆起特征較為一致,觀測到的隆起發生時間主要在穿越開始前一天,此時頂管已頂進66環,推測頂管頂進至接近監測斷面時可能發生隆起.
在圖10中,可明顯發現后行頂管對于先行頂管二次擾動的影響.在先行頂管穿越完成后,先行頂管軸線上方沉降發展若干天后保持穩定甚至有輕微的回彈,但自東線頂管開始頂進以后,先行頂管軸線上方沉降速率明顯增大,在穿越完成后的若干天后沉降發展穩定且基本保持不變直至監測結束.
4.2 考慮時間效應的地表沉降預測
由地表沉降的時間曲線(圖10、圖11)可知,頂管軸線上方沉降觀測點的沉降規律具有明顯的時間效應.根據地表沉降的時間曲線特征,可以看到其發展趨勢與軟黏土地基地面堆載引起的地面沉降發展趨勢有相似之處[17],這里借鑒采用指數曲線擬合法對頂管引起的地表沉降時間曲線進行擬合:
Smax(t)=Smax0+α[1-e-β(t-t0)]
(4)
式中:Smax(t)為頂管穿越當前斷面后軸線上方任意時刻t的地表豎向位移;Smax0為頂管穿越當前監測斷面后t0時刻的瞬時豎向位移;α為反映最終豎向位移的參數;β為反映豎向位移發展快慢的無量綱參數.
對西線、東線頂管頂進期間上方實測沉降曲線進行擬合,同時將參數α、β標注在各曲線附近,分別如圖12、圖13所示.結合圖10、圖11,西線頂管穿越完成后至東線頂管頂進前,其軸線上方測點先產生較小的瞬時沉降,隨后的沉降發展規律符合指數

圖12 西線頂管上方地面沉降發展預測值與實測值對比Fig.12 Comparison of predicted and measured values of surface settlement development over pipe-jacking of western line

圖13 東線頂管上方地面沉降發展預測值與實測值的對比Fig.13 Comparison of predicted and measured values of surface settlement development over pipe-jacking of eastern line
曲線的發展規律;東線頂管穿越完成后,其軸線上方測點將產生較大的瞬時沉降,之后的沉降發展曲線也比較符合指數曲線發展規律.對于參數α,東線頂管大于西線頂管,說明對于具有時間效應的曲線段,后行頂管軸線上方產生更大的最終沉降;對于參數β,東、西線頂管較為接近,說明兩頂管軸線上方地表在發生瞬時沉降后的沉降發展速率和形式較為接近.
由于案例所在場地⑤-1淤泥質黏土層埋深33.8 m,距離盾構隧道與頂管較遠,所以不考慮該土層對地表沉降的影響.MJS工法以水泥為固化劑對原狀土進行加固,通過水泥的水化、凝固作用填充原狀土孔隙,改善原狀土結構,以提高其強度與抗滲性能.已有研究表明[18],經水泥土加固后,砂質土的滲透系數可以降低兩個數量級以上.案例中MJS加固區域如圖1所示,可見頂管穿越全程在加固土中進行.由此推測粉砂土地層中頂管施工引起地面沉降呈現時間效應的原因為,頂管頂進前現場采用MJS工法對地鐵隧道上方的土體進行了加固,使之形成了具有較高強度和較低滲透性的水泥土,頂管施工產生的超靜孔隙水壓力消散較慢,在頂管頂進后一段時間內,頂管軸線上方將持續產生沉降后再趨于穩定.
5 結論
通過對杭州砂質粉土地層中大直徑雙線平行電力頂管上穿已有地鐵盾構隧道過程中地表沉降、隧道內道面隆沉的實測數據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 單線頂管橫向地表沉降曲線為“V”形,雙線頂管橫向地表沉降曲線為不對稱“W”形,且后行頂管軸線上方沉降大于先行頂管,平行雙線頂管施工存在交叉影響.
(2) Peck公式在頂管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曲線預測中適用性較好.本案例對于單線頂管,沉降槽寬度參數K取0.79,土體損失率η取1.6%;對于雙線頂管,先行、后行頂管的沉降槽寬度參數K分別取0.74和0.58,前者是后者的1.28倍;先行、后行頂管土體損失率η分別為2.41%和3.11% ,后者是前者的1.29倍.
(3) 頂管上跨使地鐵隧道產生“W”形沉降曲線,頂管穿越完成后隧道持續上浮至最大值,存在一定的滯后性,頂管貫通暫停施工后隧道產生一定回落.平行頂管上跨施工對下方地鐵盾構隧道的影響范圍約為4~6倍頂管管徑.
(4) 頂管穿越監測斷面后產生瞬時地面沉降,且后行頂管的影響大于先行頂管.考慮MJS工法樁加固將降低原狀粉砂土的滲透系數,可采用指數函數描述頂管穿越引起地面瞬時沉降后的沉降隨時間繼續發展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