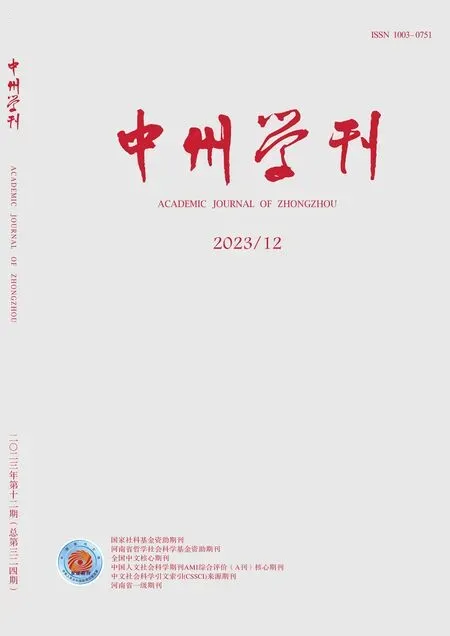通情達理: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的精神邏輯
郭衛華
“情”和“理”均為人性,二者在人的精神生命中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成為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對情理關系進行文明設計,成為中西方精神文明之異的重要標識:西方文明形成以理為本的情理二分傳統,中國則側重以情為本的情理融通,即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并形成了與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在Kant哲學,理性至上而神圣;在中國傳統,理性只是工具,人的生存、生活、生命才是至上和神圣(它的前提又是整個自然界的生存),從而人的情感才是根本或至上。”[1]113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情”與“理”融通的中國化表達就是“通情達理”。“通情達理”既是中國人價值世界的生活化表達,也是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的精神凝結,并蘊含著深厚的倫理意境。
一、“情”據“理”而“通”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情”被賦予情實、情境、情緒、情欲、情感等多種內涵。“情”在被賦予多種含義的基礎上,還被提升到哲學本體的高度,成為“天—命—性—情—道—教”中的一環。同時,在這一本體論的邏輯中雖無“理”字,但在“天—命—性—情—道—教”本體建構中,由“天道”向“人道”的落實,無不彰顯著情理融通的文明智慧。
從人性發生學的角度看,“情”的初義為人性接物而感通生成欲望、情緒、好惡等自然之情,并在道德哲學中凝煉為兩種含義:反映人的生物性需求的自然情欲以及物我感通中自然而然產生的好惡之情的情感義。“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禮記·樂記》)在人性論角度,無論是自然情欲還是好惡之情,都具有自然必然性,都屬于人性,因此情欲與情感同源并具有相通性。當然,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的文化設計中,二者的地位和文化功能又截然不同。自然情欲成為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規約的對象,好惡之情經由理性提升而成為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的精神動力。
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首先肯定滿足人的自然情欲的客觀合理性,并把自然情欲的滿足作為人的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即使儒家極為重視“大體”對“小體”的超越、弘揚“舍生取義”的道德精神,但在普遍意義上,仍始終堅持適當滿足人的自然情欲需求是其他一切價值的基本前提,如宋明理學高揚“存天理,滅人欲”,反對的也只是過度的人欲,并不否認滿足自然情欲的客觀必要性,甚至認為滿足人的合理欲望本身內含于“天理”之中。道家更是從天道自然的哲學高度重視對人的自然之情的滿足,乃至產生了對中華文明影響深遠的“貴生”思想。佛教在中國化過程中受肯定自然之情價值取向的影響,其佛法中“不殺生”“普渡眾生”的理念也得到凸顯。但是,人作為擁有意志自由的生命存在,在追求自然情欲的滿足時,與物相感應,又產生好惡之情。“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悅而后行,待行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2]在這里,人的自然欲望雖然有客觀必然性,但在滿足自然欲望需求的過程中又會產生主體意志自由滲透其中的好惡之情。“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榮辱》)好惡之情因與物感通而產生,具有自然性,但因交織著自由意志的好惡之情,其已不同于本然的天然之性,而具有了人化的特征。于是,“性”接物感通產生的自然之情雖然具有客觀必然性,但是在物我感通中如何滿足自然情欲便具有了善惡意義,好惡之情也隨之處于善惡的臨界點:好惡之情如果得到道德理性的引導就會成為揚善抑惡的精神動力,反之則會激發惡,“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圣人”[3]。
于是,好惡之情因與自然情欲相通而具有自然必然性,不可否認,不可抹殺;同時,因其交織了意志自由,又成為“自然人”走向“道德人”的基礎和邏輯前提,正所謂“禮因人情”。那么,好惡之情如何由自然之“情”升華成為具有倫理普遍意義的道德之“情”?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訴諸“通”的哲學智慧。“通”是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內涵具有豐富性和開放性。“總體上講,‘通’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有超過一百余種訓詁方式,大體可歸納為十一個方面:1.達、至;2.行;3.順、暢;4.共、同、舉;5.開;6.連;7.深;8.知可;9.道;10.卷;11.輒。按其內容可歸為‘變通’‘會通’‘貫通’‘感通’四個層次。可見其內涵之豐富,外延之廣泛。‘通’不僅是一個哲學觀念,也是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論原則,同時代表一種高明的精神境界。”[4]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正是基于“通”的哲學方法,化“通”的理性智慧為“通情”的倫理道德智慧:在“天—命—性—情—道—教”的本體建構中,“情”上通“天—命—性”而具有了客觀必然性和神圣性,下通“道—教”的理性引導而取得了人化的形式,并交織著人的意志自由。由此,自然之情與“道—教”(道德理性)相關聯后,“情感”與“情欲”相區別開來,情欲因其生物性而成為道德哲學的規約對象,“情感”因交織著意志自由經道德理性引導而成為道德哲學發揮倫理教化功能的精神動力。
有待進一步論證的是:“情感”和“道—教”如何關聯?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的文化邏輯就是通過人倫秩序之“理”(“禮”)對血緣親情進行文化塑造,賦予血緣親情以倫理本性成為“通情”的起點,“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當然,基于“天—命—性—情—道—教”本體意義上的精神自由之追求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抱負來看,血緣親情雖然具有直接性和絕對性,但是“情”的普遍形態如果僅僅囿于血緣親情,就仍有其局限性和道德風險。“儒家在血親主義架構中陷入的上述倫理悖論,構成了它內在固有的一個最根本最致命的深度悖論……說它最致命,則是因為始終高調地以弘揚倫理道德為己任的儒家思潮,恰恰在這個悖論中違背了‘不可坑人害人’的正義底線(亦即孔子自己倡導的‘志仁無惡’的道德標準),居然公開贊美那些為了維系血緣親情而不惜坑人害人的道德邪惡行為。”[5]由此,如何突破血緣親情的局限性,使千千萬萬囿于家庭的私情貫通為具有倫理普遍意義上的“情”?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基于物我、人我、天人之間的一體關聯,訴諸推己及人的情意感通,通過發揮忠恕之道的理性能力,以己之情推擴至家人、國人、天下人之情。通過“盡己之理”與“推己之情”等“通”的哲學智慧,個體通過發揮自身主體性自由使“己”之“情”在倫之“理”的秩序安排中與他人之“情”相通,乃至與天地相通,于是,“情”便具有了倫理普遍性。“以我自愛之心而為愛人之理,我與人同乎其情,則又同乎其道也。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由此思之,則吾之與人相酬酢者,即人人各得之理,是即斯人大共之情,為道之所見端者也。”[6]與他人之“情”相通相合后,個體便能從一己偏私的陷逆中挺拔出來,使彼此間在身、家、國、天下的倫理秩序中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最終打破物我、人我、天人之間的彼此隔絕,通過自身道德之行與他人之好惡、情義相通相合,進而在彼此的情意感通中達至心靈順暢而無礙的精神自由之境界。
總之,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基于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有機統一,“通情”在己之好惡與他人好惡的理性溝通中,形成共同的倫理準則和道德規范,即情通則理得,以精神的方式凝結為“天理”或“天道”。由此,“情”也從自然之情的封閉性據“理”而“通”,從而獲得開放性,自然之情進而升華為具有倫理普遍性的情。關于中國這一情理智慧,孟子以“經驗變先驗”(李澤厚語)的方式,通過“不忍人之心”的情感體驗進行了“通情”表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丑上》)
二、“理”由“情”而“達”
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關于“情”的本體意義建構中,“情”雖然被上升到天道的高度,但在人類實際的道德生活中,“通情”最終的文明歸宿是“達理”,因為“通情”只是為個別性通向普遍性提供了現實根據,“通情”本身還無法形成普遍有效的倫理法則和道德原則,“通情”還需走向“達理”,從而獲得精神哲學意義。
在文字學意義上,“通”和“達”可以互訓互證,如《說文》辵部:“通,達也。從辵,甬聲。”但從通情達理的道德哲學意義上看,“通”和“達”又有相區別的一面:“通情”更重于過程,側重于言說人與物的感通、人與人的情意感通,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當下性;而“達”更側重結果,在道德哲學意義上體現為個體應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社會應達到的至善,具有開放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如老莊所講的“虛”、佛學講的“空”和理學家所求的“廓然大公”,都是主張破除一己私欲和主觀任意性,以開放的心態和超越現實世界的意義追求,求得無私至善之通達。因此,“達理”既是一種道德修養方法,又是一種倫理抱負,同時也是一種精神境界。當然,基于“通情”與“達理”的內在關系,“理”無“情”則不達。
第一,從道德的角度看,“達理”展現為個體的德性修養。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既有物質之維,也有精神之維。對于區別于動物的人的本質屬性而言,精神之維在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中更具根本意義。因此,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的人性前提雖然奠基于人的自然之“情”,肯定自然情欲的滿足對于人之生命存在的基礎性作用,但是其關注點為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精神生活需求。因此,“達理”的首要道德目標便是“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轉化。這種轉化既關乎作為理性凝結的倫理準則的引導,又關乎個體內在情感世界的價值追求。從現實的形態看,“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轉化是在道德實踐中完成的。而道德實踐的發生既出于“我應該做”的道德認知,也出于“我想做”的道德意愿。“我應該做”主要展現為理性的自覺意識,而“我想做”則融合了意志和情感。具體而言,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視域中,“自然人”向“道德人”轉變的核心要點就是自然之情(也即好惡之情)經由理性的引導、教化升華為涵容理性和意志的道德情感,如儒家的“仁”、道家的“慈”和佛家的“慈悲”都是“情”與“理”互融又互滲。在這種轉化中,個體超越自然情欲和主觀任意性的束縛,呈現出以善為目的的與他人、社會、天地的倫理互動的自我開放中,由此成就了“自然人”向“道德人”的轉化。“道德人”與“自然人”的根本區別就是:前者擁有了理性、意志、情感相互融攝而形成的道德品格,并在反復的道德實踐和道德修為中化為人的第二天性,習慣成自然,并彰顯出人之所以為人的高貴。如儒家所言的“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在這里,“見”展現的是對人倫之理的理性自覺,“自然”包含著情感(愛親之情和惻隱之心)的體驗和感受,凸顯出情感由知到行的直接性,所以這里的“知”不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知識和認知,而是融合理性、情感和意志的道德行為,在“知孝”“知悌”“知惻隱”的道德實踐中,人就超越了動物性而成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的“道德人”。
第二,從倫理的角度看,“達理”體現為追求人倫和諧的倫理能力。在道德哲學意義上,“達理”不僅體現為道德上的理性認知,還包含著付諸道德行為的實踐智慧。對于“倫理優先”的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而言,“達理”價值目標便是“人倫本于天倫”的倫理和諧。那么,如何實現倫理和諧?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源于中國血緣文化,是與中國傳統社會由家及國、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相適應的倫理精神。由此,在實現倫理和諧的這一價值追求中,“達理”展現為一種以倫之理涵育的道德之情為內在精神動力,并在踐行倫理準則的反復磨煉中形成的倫理能力。這種倫理能力基于人的類本性。人作為類的生命存在,其意志自由的發揮主要體現在如何處理與外在世界的關系上。盡管人的意志自由在抽象形態上與人的類本性相沖突,但在現實性上,人的意志自由落實于實踐中所產生的價值和意義,主要展現于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處理上。這種外在關系從與人的生存發展最切近的關系逐步外推而形成,既家庭、社會、國家、世界乃至包括自然界的整個宇宙在內。因此,“達理”所體現的基本能力就是維護家庭這一倫理共同體的倫理能力。家庭作為以血緣為本位的倫理共同體,其維系的主要力量便是情感。“血緣本位直接導致了人們對情感的重視,因為情感是家庭生活的絕對標準,血緣關系的絕對邏輯,而家族血緣又是情感培養的母胎,這種雙向的運動及其相互作用導致了情感在文化價值系統中的絕對意義。”[7]當然,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基于血緣關系的情感不再是自然性的情感,而是經由倫理的理性引導、意志自由參與其中的道德情感,如孝和悌不僅僅是出于子對父、弟對兄的一種自然親情流露,而且成為涵容理性認知上的“應當”和意志參與其中的“意欲”的情理或義理。這種基于家庭自然性的情理只是培養人的倫理能力的起點。人作為類的生命存在,其倫理能力不能僅局限于家庭之內,而要突破家庭的局限,向外、向具有更大普遍性的倫理共同體延展,即“治國”和“平天下”。倫理意義上的“治國”和“平天下”就是發揮道德情感的超功利性和合同性,以“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倫理胸懷實現“天下一家”的充滿溫情與平和的倫理抱負。
第三,從“道德”—“倫理”統一為“精神”的角度看,“達理”為“致中和”的自由和諧境界。倫理道德作為一種實踐精神,主要是通過人追求善的行動構建以自由與和諧為終極價值目標的生活世界,并展示人的內在精神世界。所謂自由和諧,在個體層面,意味著人人作為擁有意志自由的生命存在能夠超越自然情欲的束縛,進而實現個性的自由伸張;在群體層面,意味著道德主體在與他人、社會、國家、世界乃至自然宇宙的關系處理中能夠“倫理地在一起”,即在人與世界的共在共存中追求幸福美好生活。那么,以人之性情為基點的“達理”該如何實現自由和諧的精神境界?從道德哲學的角度看,“達理”在經由“道”之“德”的性情錘煉和“倫”之“理”的實踐智慧引導后,其終極價值追求便是“致中和”。何謂“中和”?《中庸》對此進行了明晰闡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從人的性情的角度看,“中”和“和”最直接的區別就是“性情”之未發與已發的區別,但是“已發”是否“皆中節”,則關涉到“情”的發育流行是否符合“理”和“道”的理性要求,因此,源于“情”的“達理”本身既是“理”引導“情”的過程,也是“情”之“達理”(“皆中節”)的精神境界追求。具體而言,人作為情理交融的生命存在,其生存于世不僅需要主動地建構理性秩序以獲得彰顯人的主體性自由的生命情態,即“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同時,也需要遵循以和諧為終極目標的情感邏輯,進而追求宇宙萬物各正其分、各得其位的美好生活,“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在道德哲學意義上,“各正其分、各得其位”的美好生活就是“達理”,“達理”既需要理性秩序(中國傳統文化所倡導的“禮”)的約束引導,更需要和諧情感的精神支持。“我們倫理地在一起”的終極追求不僅是一種理性秩序,更是一種情感邏輯。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理”據“情”而“達”正是在“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命情懷支持下追求與萬物共生并育的自由和諧境界,即追求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物與物之間能夠彼此成就并在相互成就中獲得各自順從本性的發展。
三、通情達理開啟的中國倫理精神傳統
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通情達理所展現的精神哲學邏輯是:“理”從“情”出,“情”據“理”而“通”,“情”通則“理”得,“理”由“情”而“達”,由此開辟了不同于西方情理二分的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這一傳統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為進路,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進內在道德與外在倫理有機統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智慧。“中國哲學的旨歸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傳統倫理思想是以情理融通為特質的心靈境界。在物欲泛濫、精神疲軟、心靈失序、精神家園荒蕪的現代社會,傳統倫理思想的特質和優勢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8]
第一,“克己”。在中國以情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克己”具有兩種內涵:一是從人性論的角度對生物本能、自然情欲的克制;二是以倫之“理”的心靈秩序建構把好惡之情提升為向善之情。在“克己”的情理結構中,“理”雖然源于“情”,在以倫理道德的方式化解自然情欲、好惡之情等“私欲”的基礎上凝結而成,但對于個體道德品質的形成而言,“理”居于主導地位。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與西方理性主義相比,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的“克己”精神中“理”只是居于主導地位而不是主宰地位。因此,關于如何對待自然情欲,中西方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文明理念:西方宗教型文化中,理性居于對自然情欲的主宰地位,“信仰—情感”結構不但與人的自然情欲無關,而且基于理性純粹認知的基礎上,通過自然感性遭受折磨甚至犧牲而建立對上帝的信仰與服從。以理性絕對主宰自然情欲導致的文化后果就是:低于上帝的信仰和服從以斬斷與此岸世界的一切情義關系為前提和代價,這種文化模式在現代性中一旦遭遇到“上帝死了”的文化挑戰,如何對待自然情欲就成為西方文明之痛;中國的情理精神則堅持“道始于情”,承認自然情欲的自然必然性,以道德的方式適當滿足自然情欲本身就是“理”,并且理性化的向善之情正是從人的自然之情中升華而來的。“情理之所以為情理,就在于有情斯有理,無情必無理;理從情出,情通理得。”[9]由此,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中國人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始終如一地聚焦于人在此岸世界的生存、生活、生命中,以構建有情的生命觀,在“克己”的生命展現中“理”源于情、引導“情”,卻又最終融于“情”中。同時,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的“克己”精神不僅展現為消極意義上的對自然情欲的克制和引導,而且因涵容道德意志的“理”對自然之情的主導和規范,在積極意義上還展現為由“克己”到“舍己”的人性崇高和圣潔,如儒家的“舍生取義”,道家以“清靜為天下正”的“無為而無不為”的生命智慧,佛家以“治心”破除貪欲的出世情懷,都展現了人所具有的崇高的道德力量。這些道德力量在面臨利與害的重大沖突時,能夠激勵人類強化自己作為人的道德義務和道德責任,滲入關切他人、社會利益的人道情懷。“個體離不開群體,每個社會群體為維持其生存、延續都要對個體做出各種行為的規范和準則,有時并要求個體做出各種犧牲包括犧牲生命,這就是社會的倫理秩序。”[1]156中國這一展現道德崇高性的克己精神,對有效化解當代中國面臨市場經濟逐利性、自利性等引發的精神危機具有重要的教化意義和價值范導功能。
第二,“愛人”。與“理”主導的“克己”精神相比,“愛人”展現為以利他為本質的對他人和社會的正面價值關切,“情”(確切地說是向善之情)居于主導地位,是契合人的類本性的倫理精神形態。還應注意的是,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克己”與“愛人”雖然表現出“理”與“情”的不同關聯,但二者不是彼此隔絕的,而是相互貫通的。“克己”由消極層面克制自身私欲向“舍己”的過度和升華,在現實性上表現為對他人同情、關懷的“愛人”精神。二者在道德哲學意義上都體現著人性的崇高和精神力量。當然,二者在形式和側重點上也有所不同,并形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緩解了倫理與道德、個體至善與社會至善之間的張力與沖突:“克己”致力于反求諸己,側重于挺立個體的道德主體性力量,有助于培育個體堅強的道德意志,以理性凝聚的意志力量升華人的自然之情,為克服個體自身道德冷漠、道德麻木而形成“愛人”精神提供了主體條件;“愛人”精神則強化了人的類本性,凸顯了人在關系中的價值和意義,肯定了人作為人的內在價值,世界中的每個人都應當被關愛和關心,人的尊嚴是在人與人之間充滿善意的良性互動中得以實現的,人類種族的綿亙、延續更需要“愛人”的精神力量,超越一己私欲,幫助人類克服一切生存和發展困境。在此種意義上,“愛人”在維系人與人之間情義的同時,又進一步強化了“克己”甚至“舍己”的理性意志力量,“情”的精神凝聚力也進一步凸顯。“愛”的情理融聚力量所具有的社會意義盡管在中西方道德哲學中屬老生常談,但從現代人類面臨的時代挑戰看,這一精神在今天仍需要強調。從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信息化社會的變遷,個體自由、個性伸張在現代民主社會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和實現,但是人作為類本性的生命存在,個體始終處于與家人、朋友、同事、同胞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之中,倡導個性獨立、彰顯個體權利的現代都市文明雖然對傳統熟人社會帶來顛覆性沖擊,但是人類會始終處于人與人、人與社會極為緊密的關系網中。而且與以往社會相比,現代社會更需要堅定的情義力量支撐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樂善好施、利人助人、尊老愛幼等彰顯“愛人”精神的道德規范在現代陌生人社會中的價值和意義更為凸顯。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儒家的仁愛精神、道家的慈愛精神、佛家的慈悲情懷在今天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依然熠熠生輝,并具有世界意義,就是源于“愛人”的情理融聚力。
第三,“萬物一體”。在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傳統中,基于“天—命—性—情—道—教”的本體建構,“通情達理”中的“通”和“達”不僅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可以相通,使“我”能夠成為“我們”,而且還追求人與萬物相通而融合為一體的極致境界,即“萬物一體”。“萬物一體”的境界追求既源于“克己”和“愛人”,同時也是對“克己”和“愛人”的超越,為“克己”和“愛人”內化為人穩定而持久的德性品質提供著本體性根據。之所以說“萬物一體”源于“克己”和“愛人”,是因為在“克己”與“愛人”的道德實踐中,個體既認識到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生命不可逆、人固有一死等有限性),同時作為有精神的生命存在,個體也體悟到人的價值和尊嚴應當超越有限而追求無限。何為“無限”?中國情理主義道德哲學的回答就是“萬物一體”的境界追求,并且這一境界追求是在情理融通的過程中不斷地獲得現實性。“情”據“理”而“通”的前提是萬事萬物相通而不相同,這種“相通”意味著世間萬物都處于普遍聯系之中。如何把這種聯系納入人的主體在世結構中,并且在這種在世結構中使人能夠追求美好生活?根據通情達理的精神邏輯,就是以“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責任感使萬物相通而成為“一體”。這種責任感的極致表現就是人在體悟到“萬物一體”時所產生的一種令人敬畏、仰望和崇拜的激情和熱情,這種激情和熱情能夠激勵個體超越有限追求無限,通過對“克己”和“愛人”的超越而仁愛萬物。誠然,在科技理性、經濟理性大肆流行的當今時代,對自然宇宙的科學探索固然重要,人作為生物性生命和精神性生命有機統一的生命存在,功利追求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人還應當超越功利而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人生在世,既不能離開大地,又總愛仰望上天;既要講科學,以求獲得自然物為我所用的實際利益,又有根本不計較任何利害的對真善美的追求(科學不僅有實用價值,其本身還有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的方面),甚至有至善、至美、至真的純真理想和目標的敬羨、向往和崇拜之情;既有‘人之去禽獸也幾希’的非神圣方面,又有‘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都有佛性’的神圣方面。”[10]當今時代因缺乏對精神境界的文化認同,在對科技理性和經濟理性迷狂之下過于執著對人、對世界的“主宰”,以至于戰爭、生態危機、科技異化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大挑戰。要應對這些挑戰,中國“萬物一體”宇宙情懷所彰顯的普遍意義和實踐智慧不失為一劑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