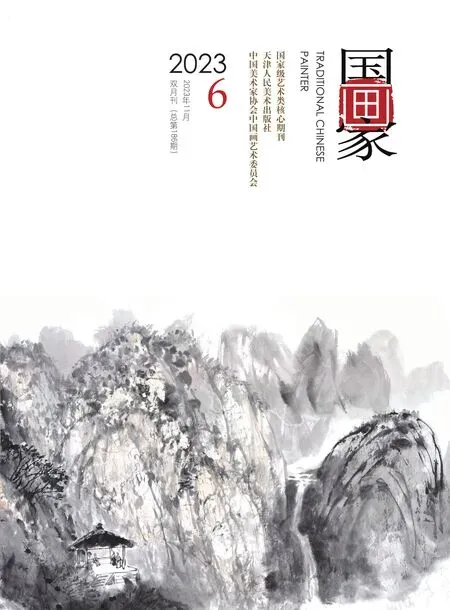崇實力行:力社書畫展覽會研究
臺北藝術大學/ 周予洵
文人結社自古有之,傳晉代慧遠法師于廬山東林寺,招賢士宗炳、雷次宗等與會,結為蓮社,眾人互相激勵,修西方凈業。[1]至民國時期,文人結社轉向社團組建,書畫家們紛紛設畫會、辦展覽、出版畫集等,宣傳自身的同時也推動了美術運動的發展。力社即眾多畫會之一,約1936年年中成立于上海,發起人有數十位之多,均為海上名家,如陳樹人、何香凝、王一亭、徐悲鴻、黃賓虹、謝公展、張聿光、張書旂、胡藻斌等。[2]其中,胡藻斌為力社主持人。力社發起人大部分是參加藝風社展覽會的,在藝風社第三屆展覽會舉行之后,覺得行有余力,又發起組建力社。如劉偉山所言,力社既以“力”名,顧名思義,有力則任何事情可干,無力則任何事情不能進行,政治、軍事、文藝、書畫都不例外。[3]力社本身即有匯集力量、團結努力、崇實力行之意。組建力社的原因大約有兩個:一是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發起力社意在倡導國人團結努力;二是自民國十八年(1929)的全國美展之后,雖有教學成績展、個展、聯展的不斷舉行,但是始終不夠力量,藝術界形成各自為戰的局面。有鑒于此,力社同仁欲聯合成堅強有力的團體,集體行動,保存發揚固有藝術。因力社目的高遠,加上諸發起人的影響力,不少畫壇名家紛紛加入,如洪庶安、袁松年、謝公展、陳澄源、林介如、汪亞塵、姜丹書、馬公愚、張小廔、熊松泉等,社員迅速發展到一百余人,規模可觀。集合了諸多名家后,社內無形中充實了力量,秋季時舉辦大規模展覽會,轟動一時。
一、展覽籌備到開幕
1936年7月9日,力社于功德林召開秋季展覽籌備會議。會議中,張小廔報告商借量才圖書館代為收發書畫情形;錢化佛報告征集書畫現狀,已征集作品五百余件;胡藻斌報告商借大新公司四樓為展覽會場,并獲允于8月間免費借用;張聿光、洪庶安報告經費支配、會計等;袁松年報告宣傳計劃與進展。[4]會議推定張聿光、張小廔、熊松泉、錢化佛、梁子真、袁松年、胡藻斌、張曼筠等為畫展籌備干事,負責辦理畫展各事項。會后,出席者還合作繪畫多幅,盡歡而散。
據《時事新報》1936年7月29日報道,籌備會征集到陳樹人、何香凝、王一亭、謝公展、孫福熙、張聿光、汪亞塵等一百三十余人作品,均為新近佳作。為了發揚國粹,還計劃選出代表作印制畫冊,以供觀眾攜回欣賞。[5]力社欲定8月4日在大新公司舉行畫展,但由于大新公司四樓化妝品展覽展期至8月7日,故重新訂實展期,決議于8月8日舉行。因展覽推遲四天,收件截止期亦延至5日。
1936年8月8日,力社書畫展覽會(或簡稱力社畫展)如期舉行,展期有半月,至22日結束,展覽時間為每天上午10點至下午7點,會場為南京路西藏路大新公司四樓。開幕當天,賓客如云,到場者有京滬文藝界李燄生、徐仲年、謝公展等,以及各國公使領事、社會名流、各報記者。展覽共收到作品2203件,來自京、滬、津、蘇、浙、閩、粵、桂、川等19個省市。因展場所限,只先陳列580多件,剩余作品每五天更換一次。該展集品之偉大,堪稱為全國美術展覽。[6]張書旂花鳥之活躍,郎魯遜雕塑之偉大,胡藻斌鳥獸之驚人,張聿光松鶴之勁秀,吳文質山水之秀美,錢化佛畫佛之古怪,均為不可多得之佳作。[7]展覽期間,力社印制展覽出品目錄冊頁贈送觀眾,也因作品繁多,只列入459幅。畫展匯集各名家流派作品,繪畫作品有國粹畫、新派畫、新國畫、折中畫、油畫、水彩畫、速寫畫,書法作品有篆書、隸書、楷書、草書,雕塑作品包含浮雕和立像。其中國畫作品占十分之九,油畫偏少,雕塑比油畫多一些。展品雖多,但會場布置井然有序,光線甚佳,平面作品與雕塑相映生輝。
展覽開幕后,上海報刊如《申報》《時事新報》《新聞報》《法文上海日報》《泰晤士報》等,均報道了力社畫展的盛況。特別是《申報》,連續近十天報道畫展的參訪、訂購、陳列等情況。參訪者方面,開幕當天即有六千三百余人,第二日、第三日均有三千余人,第四、五日觀眾比之前更眾,有五千多人,第六日有四千余人,第七至十日,每日參訪者不下五千人。至畫展的第十一天,參觀總人數已達五萬余人。展覽十分轟動,除了國內報界、藝術界、美術學校師生等團體的參訪,還有美國美術文化考察團、美國舊金山觀光團、日本考察團、南洋觀光團等,作品獲得中外人士贊許。很多國外觀眾對于國畫十分喜愛,不僅速記各作品信息,有的還詢問畫家年齡籍貫,然后訂購不少作品,如齊白石的大筆寫意畫、汪亞塵的金魚、張書旂的花鳥作品等,可見外國人深諳中國繪畫的神妙。隨著展覽的進程,天氣由高溫轉適宜,參訪者愈加多,訂購情況亦好。作品訂購方式簡單直接,訂購人付完錢后即可攜畫而歸,無需久候。作品價格大多數在數十元,最低價格是六元,最高標價如胡藻斌的虎,每幅一千元,令來會觀賞者為之咋舌。孫福熙、袁松年、林介如、錢化佛、郎魯遜、王祺等人的作品價格均在百元外。陳列方面,畫展作品定期更換,常顯新貌,吸引眾多參觀者,足以證明中國藝術的魅力。至閉幕前,多方請求延長展期,但當時社內重要成員均不在滬,如胡藻斌因事奔赴廣州,張聿光于四川舉行畫展,張小廔于泰山未返滬。籌備委員會決議于22日下午7點閉幕,如若可能時,會在南京或北平舉行冬季展覽會。
二、作品宣傳和評述
除了上述簡略的報道資訊外,力社還刊登作品、文章以作宣傳,更有專號、展評見于報刊,這些資料為我們了解畫展的作品面貌提供了依據,亦可窺見力社于展覽宣傳上的努力。
展覽期間,力社出版《力社畫集》,由上海福州路求益書社承印,封面書法由名家馬公愚題寫,序言《賀力社》由文學家徐仲年撰寫。徐仲年認為,力是生命的表現,寶貴而偉大。力社同仁都是努力分子,雖然此次畫展中,畫家作風各有造就,但是他們有一致的趨向即富有“力”的表現。徐還提出努力的三方面:一是精神上的建樹,二是品德的培植,三是技巧的修養,對于力社的未來努力寄予厚望。[8]據畫集目錄,有張書旂《花鳥》、胡藻斌《虎》、袁松年《春水綠波》、林介如《白鷺》、錢化佛《佛像》、熊松泉《松鷹》、張聿光《鵲》、張小廔《枇杷》、李遙岑《獨釣煙江》、洪庶安《菊》、沈一齊《白鳳》、張大壯《山水》,共十二幅作品。此外,在《中華》(上海)中刊載畫展作品專頁(圖1),計有作品十四幅,含張書旂《江南春色》、王一亭《無量壽佛》、熊松泉《虎》、林介如《悠悠碧水映霜衣》、徐悲鴻《貓》等作品。《時代》亦刊畫展作品專頁(圖2),有錢化佛《佛像》、陳樹人《丹桕》、張小廔《寒山詩意》、胡藻斌《長源展望》、徐悲鴻《松》、張書旂《梨花》等八幅作品。《美術生活》刊載胡藻斌《虎》、張書旂《鴛鴦》。有些作品刊登多次,卻取了不同名字,如《力社畫集》中張書旂的作品《花鳥》與《時代》刊登的《梨花》實際為同一作品。林介如的《白鷺》正是《中華》(上海)所刊的《悠悠碧水映霜衣》。畫集、期刊的宣傳主要以展示作品為主,沒有畫家介紹或作品解讀。

圖1 《中華》(上海)刊登力社畫展專頁

圖2 《時代》刊登力社畫展作品專頁
《時事新報》的《力社書畫展覽會特刊》除刊登了胡藻斌《勝乎敗乎》,陳樹人《丹桕》,何香凝《雪景山水》,劉既漂、孫福熙合作作品《朔雪那相妒》外,另有數篇文章值得注意。除了徐仲年的《賀力社》,劉偉山的《力社前途的展望》[9]從藝術現實發展角度,提出力社的組織以及此次展覽的必要性,評此次展覽會如“奇峰突起,晴天霹靂一樣”,有著璀璨的成績,力社同仁思想、信仰相同,繼而努力,必然有所建樹。介如的《現代國畫的新認識》[10]一文,提出藝術隨著時代而富有新生命,不應拘泥于某一家一派,而是要持有自由精神,團結努力,使新中國的藝術與時代共同發展。俠夫的《力社展覽前奏》[11]對畫展出品進行簡要品鑒,提及二十三位畫家的五十多幅作品。其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力社知名畫家及作品評價,不少作品是刊登在期刊中的,可獲得圖與評的史料對應。如張書旂《梨花》(圖3),取梨樹的邊角之景,繪幾只小鳥休憩枝頭,畫面清新自然。正如所評“用墨之奧妙,用色之雅艷,用粉之簡潔,章法超凡,命意新穎,行筆流暢”,堪稱新國畫的代表者。張書旂素有“白粉主義畫家”之稱,畫面中梨花以白色蘸水點染區分層次,愈顯明朗雅致。何香凝的革命經歷無疑對其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偏愛梅、竹、菊等題材,以表心志。在此次參展作品中,風景作品較多。如《無限江山圖》《雪景》(圖4),可見其用筆雄壯,革命精神與氣概充滿畫面,山勢峻偉,氣概不凡。陳樹人所繪《丹桕》(圖5),章法新奇,片片桕葉顯朱紅,稚樸有趣。另一部分內容是女性畫家作品及評價,如顧青瑤女士的《松山瀑布》,有清淡渾然的可愛之風。吳青霞女士所繪《荔枝雙鳥》《魚》《犬》等行筆頗值,足見功力。陳覺先、方君璧、張曼筠、張亞南等女士的作品,筆遒墨勁,古色古香,極其珍貴,展現出近現代女性畫家藝術作品的魅力。

圖3 張書旂 梨花 國畫 《時代》1936年第111期,第36頁

圖4 何香凝 雪景 國畫 《時代》1936年第111期,第36頁

圖5 陳樹人 丹桕 國畫 《中華》(上海)1936年第45期,第46頁
畫展作品豐富,上述式的泛泛品鑒、展記頗多,各有著重點。如《力社書畫展一瞥》《力社畫展參觀記》《力社作者瑣憶》等,簡評多位畫家及特色,多是稱贊。偶有批評的內容,如子彬在《力社秋季書畫展》[12]中指出力社出品在題材上的局限,多是花鳥山水,對于現實題材的關注過少。竹青在《力社的書畫展》[13]中評田桓的畫不及書法、孫福熙等人作品價格過高、王祺作品僅僅如此等。即便對于同一畫家,也有不同的評價,如王祺,有的觀眾認為他的作品名過其實,價格高于繪畫價值;也有評議者認為他的畫法不宗一家,潑墨淋漓,筆勢縱橫,自有風格。除了繪畫類作品,力社畫展中的雕塑作品也被關注。雕塑主要是郎魯遜的作品,有廖仲愷、徐朗西、史量才等先生的造像。在眾多繪畫作品中陳列雕塑作品,自然是引人注目的,圍觀品評的人甚多。一介的《力社展覽會的雕刻》[14]一文,評郎魯遜雕塑是力社畫展中的成功之作,得益于他精湛的技巧和深刻的表現,尤其是《廖仲愷像》浮雕作品,無論是面部塑造還是衣著表現都十分生動,穩健有力,技法純熟。在革命人物題材中,能夠運用合適的手法準確傳達人物個性,不愧為力作。綜合上述,不管是贊賞、批評還是爭議,都說明了力社畫展具有一定的話題性,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
三、代表畫家與觀念
力社書畫展覽會征集廣泛,不分界域,會場作品洋洋大觀,美不勝收,這是多數觀者的印象。而鮮為人知的是,這場盛大展覽背后,最賣力的畫家是胡藻斌。因為有豐富的展覽經驗,從展覽籌備到會場布置或雜務,他幾乎親力親為,負責了大部分工作。而他個人出品方面,也是十分豐富,有二十三幅作品之多,獲得社會美評。綜合來看,胡藻斌不僅是力社的主持人,也是力社的靈魂畫家。
胡藻斌(1897—1942),字顯聲,號靜觀樓主,廣東順德人。自幼熱愛藝術,家學淵源。15歲隨叔父胡錦清赴日,進入東京市立美工學校學習西方藝術。回國后,于廣州辦畫學研究社、美術學校,免費培養美術人才,獲社會稱頌。后陸續與張清泉、陳柱亭、周潤芝、梁鼎銘等創辦《兩粵日報》《越華報》《國華報》《廣東美報》《香花畫報》《革命軍畫報》等重要刊物。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出任總政治部藝術股股長。[15]北伐結束后,他曾服務于南洋英美煙草公司,后赴倫敦,游歷歐洲四十余國,開個人畫展于三十余國,宣揚中國繪畫,并注重收集關于虎的繪畫作品。[16]1933年歸國后暫居上海,潛心研究中國畫。1936年與海上藝術家創辦力社后,才有了此次展覽會的誕生。
胡藻斌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詩書畫印皆能。他的國畫題材擅以動物入畫,獅牛馬虎在他的筆下栩栩如生,尤其畫虎,堪與張善孖齊名。除了國畫,他對于西洋畫也有深入的研究,其油畫勁秀、水彩畫雅潔、粉畫艷麗、木炭畫奇妙、鉛筆畫秀整,散見于中外各報刊,為社會嘉許。[17]胡藻斌在繪畫上非常努力,家中常存三四百幅作品,仍然每天努力繪制。在畫展出品中,《臥牛》(圖6)用筆簡新,色調簡樸淡素,準確表現動物的姿態與神情,營造閑適懶散的情景。《辱國遺痕》《遼東有鶴不歸來》結合現實,以畫寄情思,表現出愛國精神。《萬里空寒》《暮春》《柳陰群翠》等,寫花鳥之精神,氣韻生動,滿紙書卷氣。與張書旂相比,可謂一華一樸,張書旂以艷雅見長,胡藻斌以蒼勁取勝。展覽宣傳中,亦不少胡藻斌繪虎作品,如《力社畫集》《美術生活》《時代》中均畫一只雄健老虎于奇巖中,或仰或臥,神態各異,栩栩如生。另有一幅作品《勝乎敗乎》(圖7)尤為知名。一是各報刊均刊登此圖,畫展評述也對此圖稱贊有加。比如徐仲年就十分欣賞此畫,將其推薦到法文《上海日報》發表,還將其名改為“美與力”。二是此作品參加了多個展覽,如廣州藝風社展、南京胡藻斌個展等,且被收錄于《藻斌畫集》。這幅作品畫的是一只老虎騰躍空中擒住孔雀的尾部,羽毛紛落的場景。構圖新穎,構思巧妙,命名引人深思。由孔雀尾脫而虎亦跌落的畫面,展現弱者可憐、勝者亦受傷之意。此畫婉而不諷,傷而不怨,尤見用心。[18]在國家衰弱遭受侵凌的社會情境中作此畫,足以鼓舞中華民族抗爭的勇氣。胡藻斌繪虎頗有經驗,在《寫虎略談》[19]中詳細闡述了作畫的步驟與畫虎的技法與要訣,可見其對于畫虎深有心得。此文曾得到畫虎名家何香凝、張善孖的推許。又出版《藻斌畫虎概況》,繪虎作品253幅,文字達16萬字,由虎的解剖、繪虎技法談及中西繪虎法的比較,無不詳盡。[20]說明胡藻斌不但具有深厚的繪畫功力,理論方面也有深遠的理解。

圖7 胡藻斌 勝乎敗乎
汪亞塵曾評胡藻斌“在西洋畫上面下過一番深刻功夫,依西洋畫的教養上來作成的國畫,其手法與趣味是他的獨到”[21]。方人定亦評“胡先生精通西洋畫,故能以西洋畫寫生法出之”[22]。又因胡藻斌生于嶺南地區且飽有革命精神,許多展評將胡藻斌歸為折中派的代表。實際上,據他本人的藝術主張,既反對傳統派的中國畫,亦反對折中派的中西畫,主張師造化而描寫自然,創造中國畫的新眉目,建設中國藝術的新精神。他認為社會是進化的,藝術也是跟隨進化的法則進行。古人的繪畫因作為、思想、社會背景等顯示出與現代不同的旨趣,完全抄襲與模仿是索然無味的。畫的珍貴之處在于保存繪時的情景、思想、記憶,繪畫的珍貴之處在于獨創,所以他追求“人自有人,我自有我”的表現。[23]胡藻斌的藝術觀念并沒有得到國粹派的同情,畫家田桓直接批評胡藻斌、林介如的作品是間接學日本棲鳳派的畫,用西洋畫法來畫中國畫是犯了重濁的毛病,俗不可耐。而在胡藻斌的《思想與技術的研究》[24]一文中指出,他提倡繪畫不分國界,吸收各家長處而發展自己的畫法。指出上海藝術界互相執著于偏見、猜疑,詆毀排除自身派以外的人物,是不利于中國藝術的發展的。由此也可以推見胡藻斌組織力社的初衷。
結語
力社成立的第二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社員四散,最終停止了活動。短暫的活動周期以及文獻材料的缺乏使得力社成為美術史上被忽略的個案。通過分析力社主持人胡藻斌的作品與藝術觀念,反映出該社有明確的學術追求,其團結藝術界復興文化的目標是值得肯定的。
考察力社的藝術活動,可發現力社書畫展覽會規模宏大,組織有序,作品精美,參觀者踴躍,轟動中外,在藝術普及方面功勞卓著。此次展覽會作品,既體現出畫家對于藝術創作的努力,也顯示了時代藝術的力量,對弘揚中國藝術、振興國民精神產生了積極作用。
注釋
[1]鄭逸梅,《鄭逸梅選集(第3卷)》,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6-717頁。
[2]徐昌酩,《上海美術志》,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年,第308頁。
[3]劉偉山,《力社前途的展望》,《藝風》,1936年第5-6期,第89頁。
[4]《力社籌備畫展》,《申報》,1936年7月10日。
[5]《力社畫展期定舉行訊》,《時事新報》,1936年7月29日。
[6]《力社畫展近訊》,《時事新報》,1936年8月4日。
[7]《力社畫展最后一天》,《時事新報》,1936年8月22日。
[8]徐仲年,《賀力社》,《藝風》,1936年第5-6期,第84-85頁。
[9]劉偉山,《力社前途的展望》,《時事新報》,1936年8月10日。
[10]介如,《現代國畫的新認識》,《時事新報》,1936年8月10日。
[11]俠夫,《力社展覽前奏》,《時事新報》,1936年8月10日。
[12]子彬,《力社秋季書畫展》,《時事新報》,1936年8月9日。
[13]竹青,《力社的書畫展》,《社會日報》,1936年8月13日。
[14]一介,《力社展覽會的雕刻》,《時事新報》,1936年8月18日。
[15]《胡斌先生畫(略歷)》,《申報》,1933年9月28日。
[16][17]《名畫家胡藻斌之生年》,《時事新報》,1936年8月22日。
[18][21][22]胡藻斌,《藻斌畫集》,漢文正楷印書局,1937年。
[19]胡藻斌,《寫虎略談》,《文華》,1934年第48期,第9-12頁。
[20]《藻斌繪虎》,《藝風》,1935年第12期,第86頁。
[23]胡藻斌,《寫畫談》,《新世紀》,1935年第1期,第12-13頁。
[24]胡藻斌,《思想與技術的研究》,《藝風》,1934年第9期,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