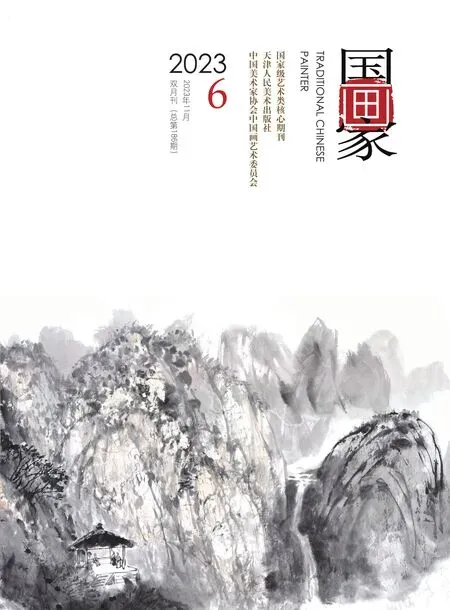元代以水域為視角的山水畫空間圖式
南開大學哲學院/ 張曉瑩
一、元代以水域為視角的山水畫空間的建構
元代文人選擇以水為視角,以其獨特的觀照方式,構建其獨特的山水空間,表現文人畫家臥游怡情于廣漠山水之間的逍遙、隱逸精神。
元代山水畫是以水為視角的山水畫空間,與唐宋以山為視角的山水畫空間相比較,因兩者對審美客體——自然山水形質的觀看方式不同,導致兩者對山水畫空間圖式的呈現也截然不同。元代山水畫以超越再現審美客體的方式表達個性化抒情式山水,唐宋山水畫以寫實再現的方式側重對真實山水的描述,以“山形步步移”的動態觀看方式,強調“可游”的空間動勢。
元代山水畫空間,以水為主體表現視域,如《山居圖》《羲之觀鵝圖》《吳興清遠圖》《洞庭東山圖》《水村圖》皆為元代典型山水畫范式。“三遠”繼北宋郭熙提出之后,衍生為韓拙“六遠”,其中“闊遠”第一次被提出來:“有山根邊岸水波亙望而遙,謂之闊遠。”[1]之后,黃公望《山水訣》將“三遠”重新定義:“平遠”“闊遠”“高遠”,進一步闡釋“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2]。可見,平遠成為元代山水畫空間建構的主要視覺向度。元代山水畫以水為主體表現視域,以平遠的觀看方式,視點變化的路徑簡省化,相對以山為主體的聯動式、多向度的視點流變,觀看方式相對靜態化。
元代以水域為表現主體,靜觀物象,山水畫空間的布陳不再沉浸于“可游”的“目”的動勢路線,而是純粹以“心”的秩序為設計準則的主觀意念抒發。故,元代山水畫空間的表達是跳脫視覺及理智思維的限制,以心靈意念建構的純觀念性空間,表達畫家根本的生命訴求,記錄瞬間的永恒的心之印記。如,倪瓚山水空間中,樹、石、山都是意象空間的一個抽象的、普遍性的語匯,像是家鄉岸邊的那棵樹、那片山,又好像不太像,是畫家生命觀照下的視覺經驗的產物,即藝術家與觀照對象相對靜止,靜觀于物,在瞬間超越生命本體,直接達到藝術家的精神暢游。在倪瓚的作品中,“空亭”是畫家表達心境的圖式符號。無人的空亭是“逸人”居所,于“荒寒寂寞之濱結茅以偃息其中,名之曰蘧廬”[3]。又言“天地一蘧廬”皆是人間過客,倪瓚以莊子“達生死齊物”逍遙于世間萬物之外,生死不過朝暮瞬息,人間富貴繁華皆是虛無。倪瓚以“空亭”象征莊子“無”的觀念,達到忘我的人生境界,營造“無己”曠達的山水意象空間。
二、元代山水畫空間的思想溯源
宗白華先生在談論“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時,以三種文化所呈現的三種空間表達方式舉例說:
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在他的名著《西方文化之衰落》一部偉大的文化形態學里面曾經闡明每一種獨立的文化都有它的基本象征物,具體地表象它的基本精神。在埃及是“路”,在希臘是“立體”,在近代歐洲文化是“無盡的空間”。[4]
故,每一種文化都有其所呼應的表征即藝術觀照的方式。中國山水畫的空間表現方式,自然與西方“焦點透視法”的三維空間原理截然不同。中國山水畫的空間觀照方式是中國哲學思想“天人合一”宇宙觀的表征。
《易經》中的俯仰觀法體現了古代先人“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價值觀、宇宙觀。《周易·系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5]“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6]“仰”“觀”“俯”“察”是中國哲學的觀物方式,是古代先哲對宇宙空間天地、遠近、上下、陰陽的直觀感知,是空間觀念的最早顯現。《易經》文化影響中國繪畫本體認知與方法論的獨特建構。古代畫家在易文化的觀照下,建立、融通了中國繪畫“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和體察悟道的觀物之法。中國山水畫空間的“觀”物之法,不單是視網膜成像的物理性原理的顯現,而且是先天的空間的認知結構與后天經驗(易文化的智慧、創作實踐經驗等)的綜合雜糅。故,俯仰“觀”法是綜合人類本身對自然空間的視覺、聽覺、嗅覺等感知覺體系,全方位多維度多層次的直觀感知活動,達到“天人合一”“同于大道”“與天為徒”的境界。如,中國人視陰陽相生為宇宙運轉、萬物生發的源動力,“一陰一陽,謂之道”[7]。中國山水畫空間以虛實、明暗、開合的表現方式,影射自然萬物的衍化之道。
綜上,山水畫空間的俯仰觀法融通了易文化宇宙觀、生命經驗、倫理價值觀等傳統觀念,綜合直觀感知覺,以繪畫之理為基礎,“外師造化”,經畫家心與腦的過濾、處理,以平面化的空間圖式展現山水畫之心靈意象。
三、元代以水域為視角的圖式
元代文人畫家在易文化俯仰觀法、莊子逍遙精神的影響下,以虛無、簡逸孕育生命的超逸空間,其視覺表現的具體形式也逐漸程式化,形成其以水域為視角的空間布陳——圖式。元代山水畫圖式以水域為表現主體,文人畫家選擇營造遼闊的水域表現空間圖式。
在繪畫風格上,元代水域圖式的營造體現了強烈的“超越”感。正如羅樾所言:“元代開始,‘山水畫內容或內在涵義突變……圖繪性藝術從此成為一種心智的、超越再現的藝術’。”[8]元代圖式的超越,是個人心性的直接體現,山水畫成為畫家抒情達意、塑造風格化的工具。抒情表意的超越性最直接的表現:“指與筆合一。”筆墨符號是山水畫風格化的直接表現。元代以前,唐宋山水畫,筆墨是再現自然物象的工具,筆墨形跡板刻、方硬、深沉、穩重。元代山水畫,筆墨直接抒情表意,超越物象形質的束縛,“書畫同源”“以書入畫”,追崇書法意味的筆墨語言。書法性用筆的超越,是畫家“物我合一”“忘適之適”自由創作境界的體現,不僅是對于技藝的超越,更是對自然之道的超越。書法性用筆的超越性落實在具體繪畫作品中,以“渴筆”的筆墨形式語言,穿越時空形質的限制,構建虛幻、縹緲的空間氛圍。元代“渴筆”語匯構建的先鋒,趙孟當之無愧。他的老師錢選的《浮玉山居圖》山石的肌理形式,雖以干、碎的筆觸皴擦,表現山石的體量感,但渴筆的語匯并未明確突顯。故,元代文士以渴筆為語匯符號,摒棄南宋視覺上沉重、板刻的筆墨描摹、氤氳浪漫,以從容淡雅的心性書寫,開創屬于元代文人簡逸、疏淡的超越性心靈圖式。
在畫面的結構上,“近岸廣水,曠闊遙山”,以一水兩岸、一水一岸、水環繞式的“水景格式”為主要程式。一水兩岸式,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展子虔《游春圖》以對角式的形式,呈現隔水相望之勢。五代董源的《瀟湘圖》則以水平式的兩岸隔水相望,橫向娓娓道來。錢選的《秋江待渡圖》與《游春圖》在圖式構成上實現了穿越時空的驚人一致性。兩幅作品在對山石堤岸的處理上皆以三角形為母題層疊推移,近岸與遠山呈現左低右高的對角遙望式,平靜的水面像一面鏡子影射待渡之意。《秋江待渡圖》是《游春圖》的進化版,對《游春圖》的圖式構成元素進行了平面化、裝飾化處理。如,《游春圖》中山石上蘑菇狀的小樹,在《秋江待渡圖》中簡化為胡椒點;樹冠造型如修剪般規整化、圖形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水環繞式的圖式表達,在元代水域空間頻頻上演,如錢選的《浮玉山居圖》《山居圖》,王蒙的《丹山瀛海圖》等。四面環水,開放式山水空間的營造,失重的圖式布設,打破唐宋山體均衡的全景化程式,更注重畫外之意的拓展,表現畫家渴望逃于世、隱于市的仙居于水上的桃源生活。王蒙《丹山瀛海圖》以嶗山為創作素材,在畫面表現上呈現出明確的不均衡性,以左側遼闊空白的水域空間與右側山林環繞的小島形成強烈的虛實對比,并且水天一體,暢游無限。王叔明自題:“人生不富貴,何如學神仙,神仙之居隔海水,樓閣飄渺棲云煙。”[9]
在如真如幻、無聲無色、直達靈府的虛空世界,元代文人觀之以心、觀之以情,以心造水域虛境,將直觀感知情愫轉換為空間圖式符號,天地在乎吾心,神思暢游無限。
結語
元代文人畫家,在易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觀照下,以心觀物,澄懷味象。元代文人畫家選擇以水為視角建構山水畫空間圖式,以水域空間為主體。“水”,虛靜、恬淡的審美內涵,象征了元代文人隱士,面對元廷統治的欺壓,遁隱江南水畔,所追求的審美人格、審美胸臆。文人士大夫以虛靜、無為的隱逸心態,靜觀水域空間,以平遠、無限延展的視覺向度,達到無、空、虛、簡的無限超越性空間,以心造境,“與道合一”“與天為徒”,游于方物之外,逍遙快樂豈不自在?

元 錢選 山居圖
注釋
[1]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年,第664頁。
[2]同上,第701頁。
[3]趙沛,《倪云林傳》,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第78頁。
[4]宗白華,《中國美學史論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1頁。
[5]趙安軍,《易經譯注》,三秦出版社,2018年,第525頁。
[6]同上,第506頁。
[7]同上,第507頁。
[8][美]方聞,《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李維琨譯,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年,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