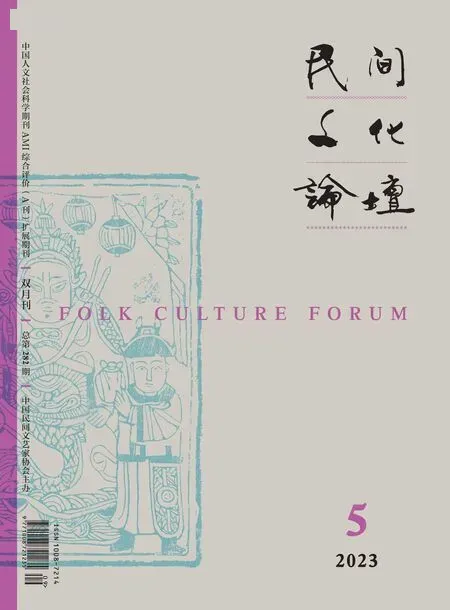民間藝術資源化與超村落發展
—— 以北京密云區石城村石頭畫為例
毛曉帥
在歷代文人作品中,村落常常被塑造為孤立封閉、自給自足的桃花源。然而,這只是文人騷客的想象,事實上中國的大多數鄉村都具有開放性。超村落發展是中國鄉村社會的一種重要文化傳統。當前,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超村落發展的文化傳統發生了哪些新變?這是個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本文以密云石城村為例,探討了該村在當下如何通過民間藝術資源化來實現超村落發展目標的實踐過程。剖析石城村這個案例,有助于為研究鄉村社會的民間藝術提供新的思路和視角。
一、村落的地域等級與超村落發展的文化傳統
在同一區域社會中,不同的村落往往會因其自然資源、地理位置、文化傳統等的差異而占據不同的等級地位。鄉村社會也因此呈現出一定的地域等級性差異。例如,距離城市較近的村落往往在地域等級上高于距離城市較遠的村落;自然資源越豐富、村民收入水平越高的村落在區域社會中所占據的等級地位也越高;擁有厚重文化傳統的村落一般會占據更高的等級地位;規模較大的村莊往往比人口稀少的村子更有優越感。村民會因為村落的地域等級性差異而產生不同的身份感和文化認同。這種地域等級性差異體現在區域社會中民眾的日常交流實踐過程中。劉鐵梁在門頭溝區進行田野調查時,就發現了這種地域等級性差異:“近年來,我們在北京各區縣進行民俗文化普查時發現,當地人在與北京城區關聯的身份認同上存在著地域等級感。例如,門頭溝區永定河西岸平原上的人,習慣上將山里的人稱作‘山背子’,而山里人又將張家口地區的人稱作‘臭板兒’。”①劉鐵梁、毛曉帥、魏甜甜、朱鵬、譚一帆:《2017 年度城鎮化與民俗文化發展報告》,張士閃主編:《中國民俗文化發展報告2018》,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57 頁。陳科錦以浙江海星村為例,指出以曬鹽為生的“海里寧”與以務農為生的“上等寧”之間的地域等級差異。他認為,“勞作模式形塑了地域等級認同,并影響了人們的社會交往,社會交往反過來又是對地域等級認同的強化。”①陳科錦:《區域社會轉型中的生計與地域等級認同——以浙江舊鹽區海星村為例》,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學位論文,2020 年,第95 頁。2019年,筆者在豫北大華村進行田野調查時,村民毛某這樣表達村落地域等級的差別:“我們村在鎮上算是最大的村了,村里初中、小學、幼兒園都有,孩子上學都不用出村。胡莊、小華村、永村這些小村有的連小學都沒有,還要跑到我們村來上學呢。”②講述者:毛某;采訪者:毛曉帥;訪談時間:2019 年11 月29 日;訪談地點:大華村。從毛某的講述中可以看出,他所在的大華村因為村莊規模更大,所擁有的教育資源更豐富而在區域社會中占據了更高的等級地位。毛某也因此產生了更優越的身份感和文化認同。
中國的鄉村社會從來不是絕對孤立或者完全封閉的,大多數村落都具有開放性。在中國歷代行政建制體系中,村落都是最基層的社會單元。但是,中國的村落大多具有超村落發展的文化傳統。村落中的民眾始終有一種超村落發展的愿望和訴求。所謂超村落發展,指的是村落社會中的民眾通過經濟貿易、科舉考試等途徑,突破村落社會的固有邊界,建立與城鎮、都市甚至是與國家的聯系,實現向上流動,進而促進村莊在區域社會內等級地位提升的過程。
(一)超村落發展的幾種傳統路徑
過去,村落實現超村落發展目標的途徑主要有集市貿易、科舉考試、廟會、民間藝術生產等。
在區域社會中,集市貿易是村民突破村落邊界,與周邊鄉村、上層社會建立聯系的重要路徑。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曾對集市的這一社會功能做過深入的研究。基于1949—1950 年在四川省的田野調查,施堅雅提出了“基層市場社區”的概念,“試圖通過集市這個承上啟下的樞紐打通微觀與宏觀、經濟與社會、底層村落與上層國家之間的‘斷層’”③鄧大才:《超越村莊的四種范式:方法論視角——以施堅雅、弗里德曼、黃宗智、杜贊奇為例》,《社會科學研究》,2010 年第2 期。。施堅雅發現:村落社會中的民眾不僅在集市上進行物品交換,同時他們也積極與周邊村落進行社交,集市圈的范圍大致也是村民通婚圈的范圍;小商人通過集市把村落與更高層次的市場和商人聯系在一起;不僅如此,鄉紳等地方社會上層人物通過集市把基層村落與更大的地方社會、與國家聯系起來。④[美]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史建云、徐秀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第40-55 頁。劉鐵梁也認識到集市與村落開放性之間的關聯,他敏銳地指出:“村落經濟‘自給自足’的極端形式,也許是不與外界發生商品交換關系的封閉性的生產與消費格局,但分散在各地的集市卻表明這種封閉的村落大約是不多的。”⑤劉鐵梁:《村落——民俗傳承的生活空間》,《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6 期。需要指出的是,傳統的集市市場具有一定的等級性,大多數村民能夠接觸到的是以鄉鎮行政中心所在地為核心的基層市場,集市的影響范圍大致與鄉鎮管轄的地域范圍相同。
在中國古代社會,科舉考試是村落社會中的民眾實現向上流動的最為重要的渠道。梁漱溟先生曾明確指出,與西方階級對立的社會相比,中國社會是一種職業分立的社會,“在此社會中,非無貧富、貴賤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轉相通。”⑥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第33 頁。在中國,下層民眾向上流動的渠道始終是暢通的,“科舉制取士不問流品和寒素,不僅徹底改變了世人的入仕觀念,也改變了門第觀念,為傳統社會的社會流動提供了通道。”①董雁偉:《社會流動論爭與 “富民社會” 視閾下的科舉制》,《思想戰線》,2020 年第3 期。村落社會中的平民百姓可以通過努力讀書,參加科舉考試而出人頭地,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脫掉藍衫換紫袍”的美好愿望是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實現的。通過科舉考試成為秀才、舉人或者進士及第的村民往往會在科舉成功后榮歸故里,修家譜、建祠堂,其所屬的家族、村落在區域社會中的等級地位也會因此而大大提升。
一些村落因為舉辦盛大的廟會活動而在區域社會中贏得廣泛贊譽,實現了超村落發展的目標。廟會是中國鄉村社會中很常見的一種民俗活動,也是“漢民族民俗宗教的基本實踐模式之一”②劉鐵梁:《廟會類型與民俗宗教的實踐模式——以安國藥王廟會為例》,《民間文化論壇》,2005 年第4 期。。村落中有沒有廟會,廟會舉辦的是否盛大,這是村民對其他村落進行評價時的重要指標。如果一個村落沒有能力舉辦廟會,那么該村在區域社會中的等級地位就比較低。那些有能力把廟會辦得很盛大、隆重的村子,往往會在區域社會中處于較高的等級地位。例如,筆者在豫北大河村進行田野調查時,村民劉華說:“小河村不行,他們連個廟會都沒有。我們村一年三次廟會。我們村過會的時候,他們都來我們這趕廟會。”③講述者:劉華;采訪者:毛曉帥;訪談時間:2019 年1 月20 日;訪談地點:大河村。一些村落因為能夠舉辦盛大的廟會而在區域社會中享有盛譽,并因此實現了超村落發展的目標。例如,河北省石家莊市趙縣范莊村每年農歷二月初二都會舉辦盛大的龍牌會廟會。廟會期間,來自范莊鎮周邊各村的花會表演隊伍都會自發到此進行走街表演,十分熱鬧。龍牌會不僅在河北趙縣家喻戶曉,而且近年來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的關注。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趙旭東、岳永逸,北京師范大學的劉鐵梁、高丙中,山東大學的張士閃等知名學者都曾到范莊做田野調查,并發表了相關的學術論文。④例如高丙中的《一座博物館—廟宇建筑的民族志——論成為政治藝術的雙名制》、岳永逸的《鄉村廟會中的人神互動:范莊龍牌會中的龍神與人》、趙旭東的《范莊龍牌會與兩種文本中的信仰表達》等。因此,該村在區域社會中的等級地位不斷提升,實現了超村落發展的目標。
通過生產年畫、剪紙等民間藝術產品而拓展村落生存空間,是村落實現超村落發展的重要途徑。一些村落因為生產的民間藝術產品全國聞名而實現了超村落發展的目標。例如,山東省濰坊市寒亭區的楊家埠村因盛產木版年畫而全國聞名。
(二)超村落發展傳統的新變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中國的鄉村社會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村民的勞作模式發生了徹底變化,進城務工代替原有的農業生產成為村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隨之滲透到鄉村。”⑤毛曉帥:《城市化進程中剪紙藝人的民俗角色嬗變——以長清剪紙傳承人王蘭美為例》,《藝術設計研究》,2020 年第5 期。周星教授稱之為一場“生活革命”⑥周星:《“生活革命”與中國民俗學的方向》,《民俗研究》,2017 年第1 期。。在這種“生活革命”的背景下,超村落發展的文化傳統發生了哪些新變?這是個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
當前,隨著互聯網的全面覆蓋和抖音、快手等各類媒體直播平臺的勃興,村落社會實現超村落發展目標的途徑更為多元。具體說來,超村落發展的文化傳統發生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新變。第一,原有的鄉村集市貿易體系繼續存在,但村民可以通過互聯網,將產品向全國各地甚至海外輸送,超越了原有的區域社會市場等級體系,影響范圍擴大至全國甚至是全球。越來越多的村落通過某種商品走向全國市場,通過市場經濟擴大村落的文化影響,拓展村落的發展空間。現在,市場經濟對村落發展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高考。過去,村落在區域社會中等級地位的提升主要是靠村落中人的向上流動來實現,現在則更多地依賴市場。一旦某個村落能夠占領市場,影響全國,該村在區域社會中的等級地位提升自不待言。第二,高考是傳統科舉制度的延續和發揚,隨著高中教育的逐漸普及,越來越多的農村學子通過高考走出鄉村,改變了命運。此外,各級各類職業技能培訓、參軍入伍等也成為村民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路徑。第三,一些村落通過文化、藝術的資源化來實現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進而實現村落在區域社會內的等級地位提升和村落發展空間的拓展。北京市密云區石城村就是通過民間藝術資源化,實現了超村落發展的目標。下面,本文將對石城村民間藝術資源化的實踐過程進行細致描述和深入分析。
二、民間藝術資源化
將某種民間藝術形式進行資源化利用,是近年來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下面,筆者將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總結,在此基礎上,對“民間藝術資源化”這一概念進行界定。
日本民俗學界較早關注文化的資源屬性問題,并提出了“文化資源化”的概念。山下晉司指出,文化與其他資源一樣,也可以被人們出于某種特定的目的而加以使用。他認為,所謂“文化資源化”,就是指文化如何成為資源的動態化過程。①[日]巖本通彌、山下晉司編:《民俗、文化的資源化:以21 世紀日本為例》,郭海紅編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8 年,第16 頁。巖本通彌聚焦于“故鄉”資源化的問題,他認為“資源化”還包括對已有文化內容進行重新解讀、賦予意義或者挖掘出新的意義進而加以利用的過程。②[日]巖本通彌、山下晉司編:《民俗、文化的資源化:以21 世紀日本為例》,郭海紅編譯,第6 頁。中井治郎探討了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的文化遺產化與觀光資源化進程,他提醒人們關注資源化體系下的負面機制。③[日]中井治郎:《“故鄉”的文化遺產化與觀光資源化——以京都府南丹市美山町的“茅葺之鄉”為中心》,郭海紅譯,《民俗研究》,2019 年第2 期。森山工辨析了“文化資源”與“文化資本”這兩個概念之間的聯系和差異性。④[日]巖本通彌、山下晉司編:《民俗、文化的資源化:以21 世紀日本為例》,郭海紅編譯,第64 頁。佐藤健二、渡邊日日、堂下惠等日本學者都參與了文化資源化的討論。
近年來,國內許多學者開始陸續關注到文化和藝術資源化的問題。唐德彪較早提出了在市場經濟影響下民族文化資源化的問題。⑤唐德彪:《論民族文化的資源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2 期。徐贛麗、黃潔探討了當代民間文化在國際化、現代化的影響下呈現出來的資源化與遺產化變遷趨勢。⑥徐贛麗、黃潔:《資源化與遺產化:當代民間文化的變遷趨勢》,《民俗研究》,2013 年第5 期。黃景春、周丹⑦黃景春、周丹:《對大禹神話的考古發現及其資源化轉變》,《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5 期。、張迪⑧張迪:《神話的資源化與地方文化生態變遷——以天水當代伏羲神話復興為例》,《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4 期。等學者聚焦于神話的資源化轉變實踐過程。李向振指出,少數民族非遺資源化保護是實現少數民族非遺長效保護的重要路徑,資源化保護與生產性保護、搶救性保護等既有路徑有根本性的差異。⑨李向振:《文化資源化:少數民族非遺保護理念轉換及其價值實現》,《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0 期。王曉珍基于美術教育的視角,分析了中華民族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化轉變的實現途徑。⑩王曉珍:《美術教育讓民族文化由“遺產”轉向“資源”》,《美育學刊》,2020 年第2 期。等等。
綜上,關于“文化資源化”這一概念學界已有較多研究成果,但其內涵和外延并沒有一個公認的、確切的定義。近年來,許多民間藝術形式也被人們有意識地當作文化資源來使用,出現了民間藝術資源化的現象。筆者認為,民間藝術資源化,指的是人們出于特定的目的,有意識地將某種民間藝術形式作為一種文化資源,賦予其意義,進而加以利用的動態化實踐過程。
三、石城村的民間藝術資源化實踐
石城村是密云水庫西岸一個普通的小山村。村民以從事旅游接待為主要收入來源。2015 年,村民開始學習在河卵石上作畫。此后,該村通過建立石城石畫館,舉辦石城石畫文化節,將石頭畫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并有意加以利用,實現了超村落發展的目標。筆者于2019 年7 月18 日至7 月22 日在石城村進行了為期五天的田野調查。下面,筆者就根據田野考察資料,對石城村民間藝術資源化的實踐過程進行分析。
(一)物質基礎:可視化景觀的建造
可視化景觀的建造是石城村民間藝術資源化的物質基礎。如劉鐵梁所說,“村落好像一個人一樣,有自己區別于他人的外在行為特征和內在心理特征。”①劉鐵梁:《村落——民俗傳承的生活空間》,《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6 期。石城石畫館就是石城村區別于其他村落的最顯著的外在特征。石畫館從村落共同體內部被抽離出來,不斷被“客體化”,成為旅游者欣賞的景觀。通過修建石城石畫館這樣的可視化景觀,村落內部的民間藝術才能通過游客的凝視和體驗成為一種公共性的文化資源。
石城村,位于北京市密云區石城鎮,是石城鎮政府駐地所在。該村緊鄰密云水庫和云蒙山風景區,山清水秀,風景秀麗,有著發展民俗旅游業的天然優勢。據現任村黨支部書記王坤介紹:早在20 世紀90 年代,該村就有兩戶村民自發開辦了農家樂,發展民俗旅游接待;截至2019 年,全村已有120 余戶村民專門從事民俗旅游接待,旅游業已經成為該村的支柱產業。
石城村河道密布,河卵石隨處可見。為了突出本土特色,村黨支部書記王坤萌生了讓村民在河卵石上作畫的想法。2015 年11 月19 日,石城石畫培訓班正式啟動。培訓期間,村委會免費為村民提供畫筆、顏料和午餐。全村共有五十多位村民參與了石畫培訓。經過一個冬天的培訓,許多村民都掌握了在石頭上作畫的技能。畫石頭畫成為石城人的新風尚,許多村民吃完飯就往畫室跑。說起當時學習畫石頭畫的經歷,村民任鳳琴激動不已:
2015 年冬天,村里組織我們學畫石頭畫。材料就是河套里的河卵石。那時候我們吃完飯就去大隊部學畫畫,村里管飯,顏料都是村里給買的,我們一分錢不用花。一開始也畫不好,后來跟著老師學,越畫越有興趣了。下了課我們就去河套里撿石頭。可熱鬧了。學了一個冬天,差不多三個月吧,我就能畫一些石頭畫了。我家里現在這些石頭畫都是我自己畫的。②講述者:任鳳琴;采訪者:毛曉帥;訪談時間:2019 年7 月18 日;訪談地點:石城村大地農家院。
2016 年7 月,石城村投資102.5 萬元,開辦了石城石畫館,這是國內首家石畫專業展館。石畫館由展品展示和畫石體驗兩個區域組成,建筑面積八百多平方米。石畫館中陳列展品一千多幅,共涉及24 個類別。展館中陳列的展品大多是村民創作的。石畫館免費對游客開放。自開館以來,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到此參觀游覽、體驗。
石畫館不僅是村落中的一個標志性建筑物,也是村落與外界建立聯系的重要窗口,是一個重要的旅游空間。通過石畫館這一可視化景觀,原本只屬于村落共同體內部的石畫藝術擁有了對外展示的空間,不斷被村落共同體之外來自全國各地的游客所欣賞、體驗、凝視,成為一種公共性的文化和旅游資源。石城石畫原本的主體是石城村村民,通過石畫館這一景觀,石城石畫成為村民和全國各地游客共享的民間藝術,其主體范圍大大地拓展了。

圖1 石城石畫館
(二)賦予意義:節日化建構與村落形象的形塑
具備了資源化的物質基礎之后,石城村進一步策劃舉辦了石城石畫文化節,通過節日化建構賦予石畫藝術新的意義,形塑了全新的村落形象。
2016 年7 月,首屆石城石畫文化節在石城村舉辦,來自密云區旅游局、文化局、石城鎮政府的地方官員,當地知名企業家,石城村的村民、學生代表等數百人共同參與了石畫文化節開幕式。2017 年,第二屆石城石畫文化節順利舉辦。相比于首屆,此次石畫文化節規模更大,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石畫愛好者。新疆的石畫名家馬益民、湖北武漢的石畫名家王永庭都聞訊趕來。在他們的影響和感召下,一大批石畫愛好者齊聚石城村,一起創作、交流。2018 年7 月25 日,第三屆石城石畫文化節在石城石畫館舉辦。本屆石畫文化節的主題是“慈善義賣”。來自全國各地的石畫愛好者自愿將自己創作的石畫拿出來進行義賣。村黨支部書記王坤現場主持拍賣,當天共賣出16 件石頭畫,拍得27000 元。石城村把這筆善款贈予了在7·16 北京暴雨中受災嚴重的黃峪口等村,幫助他們重建家園。2019 年7 月22 日,第四屆石畫文化節開幕。參與本次石畫文化節的除了當地村民、石畫愛好者、地方官員之外,還有來自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等高校的學者,以及密云當地的知名企業家代表。筆者也應邀參與了此次石畫文化節。開幕式當天,王永庭、陳雪瓊、師哲見、郝壯等四位石畫愛好者捐贈了自己的部分作品用于義拍。北京龍鳳酒業、北京漁陽旅游集團等多家當地知名企業參與競拍。當天義拍所得善款全部捐給英雄母親鄧玉芬的后代以及石城村患有大病的村民。

圖2 第四屆石城石畫文化節拍賣現場
1.石畫中心圈的建構
馬益民、沈川、陳雪瓊等石畫愛好者原本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獨立個體,他們沒有固定的組織和活動平臺,甚至沒有專門的石畫展館。由于缺乏群體的社交活動,這一趣緣群體的凝聚力并不是很強。石城村通過舉辦石畫文化節,編織了一張石畫愛好者自己的社交關系網,把這一趣緣群體網羅在一起,為他們提供了展示、交流、切磋、互動的機會和平臺,建構出石畫愛好者自己的圈子,而圈子的中心就是石城村。
石畫愛好者的這一社交關系網絡與石城村村落共同體內部的社交網并行不悖。大多數村民都是石頭畫從業者,因此他們大多在參與村落共同體內部社交活動的同時,也積極參與石畫愛好者的群體社交活動。石畫愛好者這一趣緣群體逐漸壯大,凝聚力也不斷增強。
2.節日的神圣性與石畫愛好者的“朝圣”
節日是民眾應生產、生活節律而創造出來的日常生活中特殊的時間節點。在石城村,石畫文化節就是村民建構出來的特殊節日。與大多數旅游節日不同,石畫文化節更像是石畫愛好者的宗教節日,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一年一度的石畫文化節已經成為石畫愛好者這一趣緣群體的專屬節日和神圣時間,石畫館是他們的公共空間,他們在這里創作,娛樂狂歡,盡情享受石畫藝術的饕餮盛宴。更為重要的是,石畫愛好者群體在這里實現了自我認同和群體的身份認同,石城村已經成為這一趣緣群體“朝圣”的中心。來自江西的沈川、湖北的王永庭、新疆的馬益民、山東的陳雪瓊、河北的陳智望等石畫愛好者都將石城村當作自己的大本營。他們每年都會帶著自己的弟子來這里聚會、創作、交流。經過四年苦心經營,加之媒體的宣傳報道,石城村已經被形塑為全國石畫文化的“圣地”和中心。
(三)資源利用:捐贈儀式與村落社會等級的提升
在第三屆和第四屆石城石畫文化節開幕式上,主辦方都特意安排了現場拍賣和捐贈儀式。石城村利用石頭畫這一民間藝術資源,通過節日儀式上的捐贈和拍賣實現了村落在區域社會內等級地位的提升。
1.角色升級:村落與村落的互動
在第三屆石畫文化節上,石城村組織了石畫義拍活動。石城村通過舉辦義拍活動幫助黃裕口等受災鄉村,提升了本村在區域社會中的角色地位,實現了雙方的互利共贏。受災鄉村的民眾是最直接的經濟受益者,義拍所得的善款能夠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石城村因為樂善好施而收獲贊譽。石城村與受捐助的黃裕口村等村落原本是同一區域社會中的同級村落。但通過石畫文化節上的義拍和捐贈,石城村扮演了捐贈人的角色,相較于受捐助的村落,其地位等級顯然提升了。
2.角色置換:村落與企業的互利
在石畫文化節上,石城村為當地企業搭建了宣傳平臺,雙方的角色發生了置換。原本石城村等村落大多是地方企業幫扶的對象。村落一般扮演著受助者的角色。但通過舉辦石畫文化節,石城村成了全國的石畫文化中心,其文化地位和知名度已經遠高于當地企業。相比電視臺動輒上百萬的高昂廣告費,參與石城村的慈善義拍活動顯得更為劃算,而且宣傳的效果并不差。對當地企業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宣傳機會。因此,當地企業也想借助村落的影響力來宣傳自己,擴大影響。在第三屆和第四屆石畫文化節上,參與石頭畫拍賣的都是當地知名企業。在石畫文化節上,石城村扮演了幫扶企業的角色,企業成為受助者,雙方的角色發生了置換。
“作為特定的行為方式,儀式與人類其他行為方式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其‘超常’性”①代玉啟、覃鑫淵:《世俗時代儀式的社會本質與教化功能》,《浙江學刊》,2021 年第4 期。。石城村策劃舉辦的捐贈儀式也是“超常”的。兩次拍賣和捐贈儀式都按照石城村事先設定的嚴格的等級結構來安排,石城村扮演著更高一級的捐贈者和幫扶者角色。捐贈儀式的實質是石城村村落實力的彰顯和村落地位的自我宣示。儀式上村民、官員、學者、游客、企業家等多方力量的共同見證使得這一新的等級關系變得可視化。新聞媒體的宣傳和報道敘事,使得這一等級關系進一步穩定和固化。
總之,石城村通過建造石城石畫館這一可視化景觀,為石城石畫這一民間藝術形式的資源化奠定了物質基礎;通過舉辦石畫文化節,石城村村民、地方官員、企業家、學者、石畫愛好者等多方力量共同參與,在共謀與磋商中賦予了石城石畫以新的文化意義,使其成為當地人與外界共享的一種文化資源。如徐贛麗、黃潔所說:“文化一旦成為資源,就意味著價值化。”②徐贛麗、黃潔:《資源化與遺產化:當代民間文化的變遷趨勢》,《民俗研究》,2013 年第5 期。石頭畫對石城村的價值就在于,通過民間藝術資源化的實踐,石城村的村落形象被重新形塑,其在區域社會中的等級地位獲得了提升,村落的發展空間得到了拓展。
結 語
在中國的鄉村社會中,不同的村落往往會呈現出一定的地域等級性差異。中國的大多數村落都不是孤立封閉的,而是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超村落發展是中國鄉村社會的一種重要文化傳統。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和城市化進程的迅速推進,超村落發展的文化傳統呈現出多元化的新變樣態。其中,通過民間藝術資源化來拓展村落發展空間,提升村落在區域社會內的等級地位,是發揚超村落發展文化傳統的一種重要方式。石城村的民間藝術資源化實踐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通過修建石城石畫館、舉辦石畫文化節,石頭畫這一民間藝術形式被村民、畫家、學者、媒體、企業等多方力量共同賦予了新的意義,成為村落社會中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源。通過對這一文化資源的利用,石城村被形塑為全國石畫文化的中心和圣地,村落的發展空間得到拓展,村落在區域社會中的等級地位大幅度提升。與此同時,石城村還實現了與周邊村落、當地企業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石畫愛好者之間的多方良性互動,實現了互利共贏。那么,促成這一結果的動因是什么呢?地方企業的經濟利益驅動、密云區地方政府的政績追求、石畫愛好者的群體認同需要、媒體的宣傳報道是促成這一民間藝術資源化實踐過程的主要外在動因。而真正的內驅動力,則是石城村自身超村落發展的強烈愿望和訴求。舉辦石畫文化節是石城人對當地民間藝術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也是對中國鄉村社會超村落發展文化傳統的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