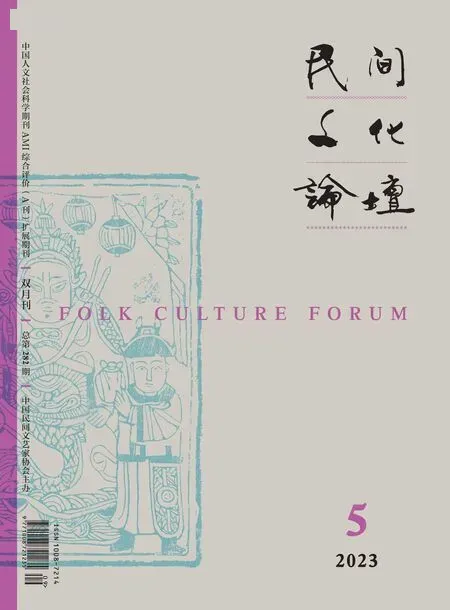論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民間文化的關系
—— 一個“非遺學”學科進路的前提性思考
孫玉芳
現代意義的學科是西方分析哲學框架下的一種知識分類,是循著一定的秩序、規律,采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對人類既有經驗、知識進行的有機排列組合。概而言之,學科是人類及其社會生存與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知識分類的產物,新學科的產生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這正如美國教育家伯頓·克拉克(Burton R. Clark)所說的:“各門學科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它們隨時間遷移而發展。”①[美]伯頓·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年,第15 頁。伴隨著全球化時代、后工業社會人類對于世界遺產體系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物質主義”的反思,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②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更準確的中文翻譯應為無形文化遺產。一般認為,它源自日語“無形文化財”的英譯。但不同國家的對譯情況又有差異,如法語中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的對譯詞是L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德語則是Immaterielles Kulturerbe,都意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中國,人們也習慣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譯法,簡稱“非遺”。這一文化表現形式得以正式確立。這被許多學者視為一種挑戰西方遺產理念、承認非西方遺產表述與實踐、尊重文化多樣性的積極傾向。在我國,非遺這一晚近概念于21 世紀初廣泛進入社會各界的視野,與“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中國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形成合流③“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是當時馮驥才等領導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于2002 年發起的,同年10 月10 日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項目”,項目編號02@ZH010;“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是2003 年1 月由文化部倡議實施的國家重點文化建設項目,并接納“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為子工程。,很快上升到了作為“維護我國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權的基本依據”④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37.htm,發布日期:2008 年3 月28 日;瀏覽日期:2022 年9 月3 日。的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作為學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簡稱非遺學)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中,借由本國對非遺和此前民間文化概念的認知、理解、實踐和思辨,從西方話語主導的知識分類中獨立、發展而來的。非遺學是中國話語和自主知識體系整合與建構的努力,是一種新的學科范式的嘗試。在非遺學近二十年的學科進路中,非遺與民間文化的關系這一關乎其學科獨立與合法性的前提,理應引起學界的關注。
一、中國語境中的非遺與民間文化
中國學界、政府層面對非遺的認知與保護實踐最初都與民俗學關系密切,前面提到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參與者中有大量的民俗學者。可以說,國內學界和政府層面關于非遺這一外生性概念的探討與接受過程都離不開民俗學及其研究對象民間文化,但兩者關于非遺概念“在地化”及其與民間文化關系的認知存在分歧和差異。
首先,學界關于非遺與民間文化的關系問題大體上限定在民間范疇內,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看法。
其一,許多民俗學家嘗試將非遺作為一種新生的文化事物、時代賦予的文化機遇,納入到既有學科框架下進行定義、分類、闡釋和理論建設。例如陶立璠《民俗學》(修訂本)在第一章中增加了“民俗學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一節,用以探討兩者的關系,認為非遺是一種特指的文化現象,分散在民俗學框架下物質民俗、社會民俗和精神民俗的各個領域,只是其傳承者的范圍包括了一部分精英階層,較民俗中的“民”更為寬泛而已①陶立璠:《民俗學》(修訂本),北京:學苑出版社,2021 年,第21—25 頁。。許多知名民俗學者都持有相似觀點。其中,烏丙安、劉鐵梁等學者還對非遺持一定的警惕態度。烏丙安強調,“任何形式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研究,都不是民俗學自身的學科研究或學術研究;更不應該也不可能用它取代民俗學的研究”,并明確指出“民俗學人理應守土有責”②烏丙安:《21 世紀的民俗學開端: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結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方法》,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 年,第262 頁。。劉鐵梁則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個關于文化分類和價值判斷的概念, 主要指的就是那些行將消失或者發生根本改變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民間文化的價值及價值的實現問題則“既被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所激活,又被這個概念所攪亂”③劉鐵梁:《民俗文化的內價值與外價值》,《民俗研究》,2011 年第4 期。。進一步說,他們都立足于民俗學本位,認為非遺不具備構成學科的要件和理論框架,非遺研究只是民俗學的一種應用研究,是民俗學發展的一個良好契機,主張在民俗、民間文化的基礎上探討和研究非遺。
其二,一部分民俗學家、文化學者在21 世紀初就提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的概念,并一直致力于借鑒民俗學、藝術學等學科的理論、方法、經驗等,對非遺進行獨立學科框架下的定義、分類、闡釋和理論建設。先后出版有向云駒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2004)④向云駒:《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銀川: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年。、王文章主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2006)⑤王文章主編:《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年。,苑利、顧軍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2009)⑥苑利、顧軍:《非物質文化遺產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黃永林、肖遠平主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教程》(2021)①黃永林、肖遠平主編:《非物質文化遺產學教程》,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 年。等一系列非遺教材。上述教材大都強調了作為非遺學科邏輯起點的非遺的獨特屬性、價值與保護原則,具體分類則基本參照了民俗學的分類法。例如苑利、顧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第二版)從傳承主體、傳承時限、傳承形態、原生程度、傳承品質、傳承范圍的角度,將杰出傳承人的支撐,悠久歷史,活態傳承,原汁原味傳承,重要歷史認識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社會價值等作為構成非遺的前提條件,闡述了非遺的保護方法、原則、評估標準,普查與申報,產業化開發,傳承主體與保護主體問題,并參照民俗學與《公約》對非遺進行再分類②苑利、顧軍:《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苑利和顧軍強調非遺“并不是簡單的民間文學、表演藝術、傳統工藝美術、傳統工藝技術、傳統節日儀式以及傳統農業生產技術,而是其中最為精華、最為重要,特別是那些已經進入各級《名錄》的部分”③同上,第8 頁。。與第一種看法相比,這一觀點雖然強調了非遺有別于其他民間文化的特殊性,但本質上還是將非遺視為從民間文化本體中提升出來的一類特指文化事象。
其三,近年一些學者在建構非遺學交叉學科的基礎上展開非遺與民間文化關系的思辨。例如“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發起人、組織者馮驥才提出,非遺是一種“歷史傳承至今并依然活著的文化生命”④馮驥才:《非遺學原理》(上),《光明日報》2023 年3 月19 日,第12 版。,而在20 世紀后期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轉型期文化語境下,原有的民間文化概念增加了遺產的意涵,或者說,民間文化被遺產這一概念激活了,因此可稱之為“民間文化遺產”,意指“農耕時代民間的文化形態、文化方式、文化產品,一切物質和非物質的遺存”⑤馮驥才:《搶救與普查: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靈魂不能下跪:馮驥才文化遺產思想學術論集》,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36 頁。。馮驥才認為非遺與民間文化遺產是本質相同的兩個概念,但在中國本土文化這一特定背景中,非遺的概念來自政府,是由各國政府共同確定的,在文化實踐中大量參考、借鑒了既有的民俗學、藝術學的知識、經驗;而民間文化遺產的概念則來自學界,是一個整合性的學術概念、文化概念,代表著一種新崛起的非遺學的立場。他主張學界從新的角度——遺產的角度來認識民間文化遺產,認識非遺。由此,馮驥才對非遺和民間文化的范圍做了進一步界定,認為非遺是民間文化范圍內“歷史文化的代表作,是當代遴選與認定的必須傳承的文化經典”⑥馮驥才:《非遺學原理》(上),《光明日報》2023 年3 月19 日,第12 版。。也就是說,非遺是民間文化中能夠構成遺產的那一部分內容,正是遺產的屬性決定了非遺不同于民俗學、藝術學等學科視野中的民間文化,它本質上有著對立檔、保護和傳承等一系列的內在要求。
具體到政府層面,非遺概念的“在地化”(Localization)與民間文化聯系緊密,但更傾向于符合中國語境和文化實際的傳統文化概念。自引入非遺概念之初,我國民間文化的釋義中率先做出了整合非遺的嘗試。例如2004 年文化部發布的《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實施方案》(簡稱《方案》)這樣解釋民間文化: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56 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僅創造了大量的有形文化遺產,也創造了豐富的無形文化遺產,包括各種神話、史詩、音樂、舞蹈、戲曲、曲藝、皮影、剪紙、雕刻、刺繡、印染等藝術和技藝及各種禮儀、節日、民族體育活動等。中華民族血脈之所以綿延至今從未間斷,與民族民間文化的承續傳載息息相關。⑦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國家中心:《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普查工作手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第184 頁。
民間文化原本指的是社會底層的、平民的、大眾的文化,是一種民眾的知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非遺概念本身承自《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簡稱《建議案》)中的民間創作(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字面翻譯為“傳統文化與民俗”),民間創作的一般理解即是民間文化。《方案》的整合嘗試通過例舉法,將表述的重點放在了民間文化作為無形文化遺產的一面,同時將傳承主體由《公約》中的“社區、團體、有時為個人”轉換為國家敘事意義上的“中華民族”。2005 年,國務院印發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簡稱《辦法》)、《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和《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簡稱《通知》),《辦法》首次在正式的政府文件中采用非遺的提法,《通知》則參照《公約》界定了非遺的概念: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①國務院:《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26.htm,發布日期:2008 年3 月28 日;瀏覽日期:2022 年9 月3 日。
201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簡稱《非遺法》)再次對非遺進行定義:
本法所稱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②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http://www.npc.gov.cn/npc/c12488/201102/ec8c85a83d9e45a18bcea0ea7d81f0ce.shtml,發布日期:2011 年2 月25 日;瀏覽日期:2022 年9 月3 日。
較之于《公約》中非遺的定義,《辦法》《通知》和《非遺法》突出強調了“傳統”一詞。尤其是《非遺法》,在對非遺的具體分類中多次——6 個類別中5 次冠以“傳統”字樣,既是對作為民俗術語的民間創作、民間文化的回歸,主體指向現實中的民間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及其相關的實物和場所,但又超出了民間范疇,實際上將非遺的界定從《公約》的“文化遺產”傳遞、轉換到更符合中國語境的“傳統文化”上來,傳承主體也變成了更符合我國民族具體實際的“各族人民”,非遺的概念由此延伸至全部的文化傳統——比如古琴、書法等精英文化進入世界非遺名錄,顯示出非遺與民俗框架、民間文化錯綜復雜的關系。
綜上可知,學界與政府層面關于非遺和民間文化的一般看法是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我國學界關于非遺的認識與思辨、實踐大多是在民俗框架下進行的,而政府層面有著在多重語境中力爭國際文化話語權,建構、傳播國家文化形象和價值觀等文化戰略的不同考量。我們可以從民俗框架下非遺的生成與表述、世界非遺名錄里的多元文化表征兩個方面分別進行闡釋和分析。
二、民俗框架下非遺的生成與表述
非遺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種新的文化表現形式。在世界遺產體系中,文化遺產的理念和實踐主要承自意大利、法國、英國的傳統,自然遺產最早的國際標準是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組織(IUCN)與美國合作制定的,非遺的生成則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一些非西方國家或者說南方(南半球)國家的社會文化保護話語實踐,尤其是日本的干預和影響。國際上對非遺概念的認知和接受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將《公約》發布前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重要的相關公約、憲章與同期相關國家、區域具有國際影響的立法、建議、行動等比照來看,可大致推理出相關文化理念的關聯與演進脈絡——事實上這也是我國學界關于非遺認知與思辨的脈絡,有助于厘清非遺與民俗框架下民間文化的嬗遞關系(見表1)。

表1 《公約》發布前相關立約、立法及文化行動參照簡表(1950—2003)① 參考以下文獻編制:馮驥才主編:《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普查手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向云駒:《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彭兆榮:《聯合國及相關國家的遺產體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日]愛川紀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與韓國》,沈燕譯,《民間文化論壇》,2016 年第2 期;[日]愛川紀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約——從通過到第一次政府間委員會召開》,白羲譯,《民間文化論壇》,2011 年第6 期。
由上表可知,非遺話語表述與實踐是一個有著多重關聯的曲折的文化過程,大致經歷了從無形文化財、非物質遺產、民間創作、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嬗變。其中,民間創作、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國際層面的通用術語。它們一脈相承,又判然有別,顯示出非遺與民俗學及其研究對象民俗、民俗文化或者說民間文化的相當復雜的分合關系。
一方面,非遺的生成離不開民俗學的支持。作為一種嶄新的遺產理念,非遺的背后有著較為復雜的歷史文化依據和地方經驗,而遺產理念的發現、歷史文化經驗等的積累乃至于相關國際對話的展開都離不開民俗學提供的文化、學術、法理和現實操作層面的支持。比如國際上一般認為非遺的緣起與日本的“無形文化財”關系密切。“無形文化財”是日本于20 世紀50 年代以法律形式確立的文化范疇——主要指對日本來說“具有較高歷史、藝術價值的戲劇、音樂、工藝技術和其它無形文化事象”,并于后面的修訂中導入了“重要無形文化財”(1954)和“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1975)指定制度①原日本文部省:《文化財保護法》,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325AC0100000214,瀏覽日期:2022 年9 月5 日。。“無形文化財”的出現與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的相關研究,如《民間傳承論》(1934)、《鄉土生活的研究法》(1935)的民俗分類有很大的關系。其中,民俗文化財(含無形民俗文化財)及其前身“民俗資料”的界定更是直接受到柳田民俗學的影響。再如玻利維亞政府于1973年10月建議《世界版權公約》(Universal Copyright Convention)中增加一項關于民俗保護的議定書——《保護民俗國際文書提案》,也是通過民俗話語在國際上主張對民謠《老鷹之歌》(El Condor Pasa)的權利,并由此引發了國際上對傳統民俗及其所屬社區、群體權益的持續關注。198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給出文化遺產的新定義:
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包括其藝術家、建筑師、音樂家、作家和科學家的作品,也包括的作品、人民精神的表達以及賦予生活意義的主體價值。它同時包括該民族賴以表達其創造力的和作品:語言、儀式、信仰、歷史遺跡和紀念物、文學、藝術作品、檔案和圖書館。②UNSECO,“The Mexico City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Policies, ”https://culturalrights.net/descargas/drets_culturals401.pdf, 發布日期:1982 年7 月26 日—8 月6 日;瀏覽日期:2022 年10 月2 日。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定義中“匿名藝術家”和“無形的作品”的提法,都是對玻利維亞建議案的某種回應。這直接影響了198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和實施《建議案》——由著名芬蘭民俗學家勞里·航柯主筆,促使非西方主導的另一類文化遺產即活態的民俗遺產進入全球的視野。在這一時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要提倡在民俗學科體系中對無形的活態文化——無形文化遺產(非遺)加以物化、固化,實際保護的是文化的記錄和表達文化的器物,各國的非遺調查、保護普遍有民俗學家參與乃至發揮主導作用,具體實踐中也借鑒和應用了大量的民俗學方法。
另一方面,非遺的確立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挑戰、反對民俗學的文化過程。如前所述,《建議案》是一份以民俗學框架為主導的草案,試圖以西方民俗學科的理念將所謂的民俗、民間文化“對象化”,實際上是民俗學經驗的一種推廣和應用。但據1995 至199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結果,8 個區域、次區域會議及其與美國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s)合作召開《建議案》實施效果的國際評估會議(簡稱華盛頓會議)的成果顯示,《建議案》所倡導的民俗保護思路受到了嚴肅的批評,甚至于“民俗”術語本身也遭遇了廣泛的質疑。與會的很多學者認為民俗一詞過于強調結果(product-oriented),未能賦予相關的象征、過程和價值以首要的意義;一些來自阿拉伯、太平洋地區等非西方/南方國家的聲音更是表達了對“民俗”概念的強烈不滿和負面看法,認為它是一個不恰當的、貶義的術語①UNSECO,“A Global Assessment of the 1989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 Local Empowerment and Local Co-operation,”https://ich.unesco.org/doc/src/05284-EN.pdf,發布日期:2002 年1 月14 日;瀏覽日期:2022 年11 月5 日。。例如一些太平洋地區學者談及自己的殖民化歷史和土著文化時表示:
“民俗”這個詞是不可接受的。我們的文化不是“民俗”而是與傳統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的神圣的規則(sacred norms)——這些規則為我們的傳統社會設定了法律、道德和文化價值。它們是我們的文化認同。②Sivia Tora,“Report on the Pacific Regional Seminar,”https://folklife.si.edu/resources/Unesco/Tora.htm,瀏覽日期:2022 年11 月5 日。
與會者最終達成了兩個共識:一方面針對“民俗”提法的負面意義,決定尋求可替代的術語;一方面在記錄、保存無形文化遺產(非遺)的同時,將主要文化定位轉向優先考慮活態文化所屬社區、群體和持有者個人對保護實踐的參與中來,強調“通過鼓勵世代相傳和復興無形文化遺產”,“在它產生的原始氛圍中保持它的活力”③[日]愛川紀子:《無形文化遺產:新的保護措施》,《民族學通訊》,2003 年第138 期。。華盛頓會議重估、批評,幾乎顛覆了《建議案》的民俗學框架思路,雖然非遺概念因未能強調民俗、傳統文化的社會作用等原因而遭到批判,但仍作為替代相關民俗概念的核心術語得到新的界定,并在各方的磋商與妥協中得以延續下來。此后《公約》的擬定某種意義上也被一些學者視為“去民俗化”的過程——“對理論上的民俗學的基礎概念的排除”④[日]巖本通彌:《世界遺產時代與日韓的民俗學——以對世界遺產二條約的接受兼容為中心》,宗曉蓮譯,《文化遺產》,2014 年第5 期。。隨著非遺對民俗概念的取代,非遺與民俗、民間文化的理念、意涵相近但并非同義這一事實也在源頭上被忽視了。
三、人類非遺名錄里的多元文化表征
無論是中國語境中非遺與民間文化范疇的復雜關系,抑或是民俗框架下非遺曲折的生成、表述過程,其背后都有著深層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歷史文化背景。非遺是一種多重語境的文化表達。多重語境包括非遺原生的地域文化語境,本土范圍內地域文化之間、地方與國家層面的互動語境,以及全球視野的國際文化語境。正如美國民俗學家芭芭拉·基爾申布拉特—吉姆布萊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所陳述的:
世界遺產首先是一份名錄。名錄上的一切,無論其之前的背景如何,現在都被安放在與其他杰作的關系之中。這個名錄是名錄上所有內容的語境。①William S. Logan and Laurajane Smith,“Introduction,”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eds., Intangible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9,p.4.
在這種意義上,世界非遺名錄——比如《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08—2022)及其前身《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2001、2003、2005),便構成了一個不同文化主體表達各自文化訴求的場域,隱含著國際語境中不同文化主體的博弈關系,而這正是我國政府層面優先考慮的文化實際。據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助理總干事顧問、非物質文化遺產處前主任愛川紀子(Noriko Aikawa-Faure)回憶,《公約》問世之前全球不同區域都表達了各自的文化關切和優先事項,其中很多亞洲國家特別考慮到基于各自傳統的高文化(high culture)的問題,希望民間文化之外的高文化也可以進入非遺,而西歐國家則更多擔心文化多樣性面臨的威脅,認為應該重點考慮少數群體傳統文化與民俗②[日]愛川紀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成型——一場關于“社區參與”的敘事與觀察(上)》,高舒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0 年第1 期。,這些在后來世界非遺名錄中有具體的反映。
所謂高文化進入非遺,其背后的邏輯是包括我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文化敘事策略。比如中國的昆曲、古琴藝術、書法、篆刻,日本的能樂、凈琉璃文樂木偶戲,韓國的皇家祭祖儀式和宗廟音樂,越南的雅樂,柬埔寨的柬埔寨皇家芭蕾等,都被優先申報列入了《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舉例來說,中國政府官網關于古琴藝術的介紹中便明明白白地指出,“繼承古琴藝術中所包含的儒家傳統精神及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境界,將為生活在現代化環境中的人們調整與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不斷認知體驗‘天人合一’哲學觀的深刻性和合理性,帶來許多新的啟示。”③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介紹——古琴藝術》,http://www.gov.cn/ztzl/whycr/content_638408.htm,發布日期:2007 年6 月6 日;瀏覽日期:2022 年11 月3 日。日本的能樂是其武士階級的高尚文化,屬于無形文化財而非無形民俗文化財或者說民間文化——日本的無形文化財、無形民俗文化財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為“國家性的(national)內容”,后者是“地方性的(local)內容”④[日]巖本通彌:《世界遺產時代與日韓的民俗學——以對世界遺產二條約的接受兼容為中心》,宗曉蓮譯,《文化遺產》,2014 年第5 期。,等等。這些非西方/南方傳統的精英文化、宗教文化被各自政府作為優先項目,申報列入了世界非遺名錄,目的在于建構、傳播理想的國家文化形象和國家價值觀,展現民族的獨特氣質與人文精神,提高國家、民族文化身份的辨識度,推動國際視野的審美、哲學層面的深度交流等。這一做法招致了一些西方學者的批評,例如吉姆布萊特稱: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接受了那些與宮廷、宗廟相關的文化形式——只要它們不是歐洲的,保留西方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分歧并制造了一個虛幻的非遺名單,一個不是土著的、不是少數族裔的、不是非西方的名單,盡管依然是非物質的。⑤Laurajane Smith, Use of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6,p.112.
吉姆布萊特認為《公約》所制造的世界非遺名錄與此前的《世界遺產名錄》一樣,都是排他性的。她與冰島民俗學者沃爾迪瑪·哈福斯坦(ValdimarHafstein)同時認為:
創建名錄的行為不僅是一種排斥行為,也是一種意義創造的表現。在此過程中,“遺產”將根據預先定義的“標準”被“識別”和“評估”。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對被質疑的遺產進行新的意義和價值的再創造或改寫。無論我們處理的是有形遺產還是無形遺產,該遺產的主要價值、意義都是通過其在名錄上的位置及其在一系列標準下的地位來確立和理解的。①William S. Logan and Laurajane Smith, “Introduction,”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eds., Intangible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9,p.4.
前面所謂的高文化申報人類非遺乃是一種非西方/南方國家在國際層面上塑造自身的文化行為。事實上,《公約》被非西方/南方國家視為對西方權威遺產話語的挑戰,在投票時得到了它們的大力支持,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尤其積極,不但給予聯合國教科文組相關資金、物質方面的資助,而且在《公約》實施初期非遺的申報數量上出現了鮮明的“亞洲轉向”(Asian turn)。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丹麥、加拿大和瑞士等國則出于對非遺的不理解,對既有民俗學框架的堅持或者國內民族政治等復雜因素的考量而棄權;加入《公約》的西方國家,如意大利、法國等申遺時都是在現行民俗、民間文化范疇內履約的,反映出作為一個復雜、動態的文化場域,人類非遺名錄所隱含的中心與邊緣、地區之間、國家之間、國家與地方等不同層面的文化互動、表征與博弈關系。
四、結語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曾表示:“學術領域反思自身的一個方法是回顧自己的歷史。”②[美]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160 頁。我們回顧非遺學學科進路中非遺概念的歷史,無論是它的生成與表述、外生性概念的“在地化”,還是人類非遺名錄中的文化博弈與表征,都離不開對非遺與民俗、民間文化的關系這一前提性思考。在嶄新的非遺學學科框架下,馮驥才提出的非遺的立場——“從遺產的立場出發,來認識民間文化”③馮驥才:《非遺學原理》(上),《光明日報》2023 年3 月19 日,第12 版。變得格外緊迫與鮮明。某種意義上,非遺是西方權威遺產話語中“遺產”內涵與“在地”民間文化互動的產物。須得承認,盡管非遺與民間文化的糾葛仍有待學理、實踐層面的進一步的闡釋、探索,作為世人矚目的重要文化事實,它已經構成了一種與全球化背景下個人、家庭、社區、地方乃至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相關聯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不僅有可能修改遺產的定義,更有可能重新界定全球和本土的地方感”④William S. Loganand Laurajane Smith,“Introduction”,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eds., Intangible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9,p.7.,對于我國的國家文化戰略、民族文化身份、文化自信的建構乃至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意義重大。學界理應在更高的文化、學術高度上,統籌思辨非遺與民間文化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