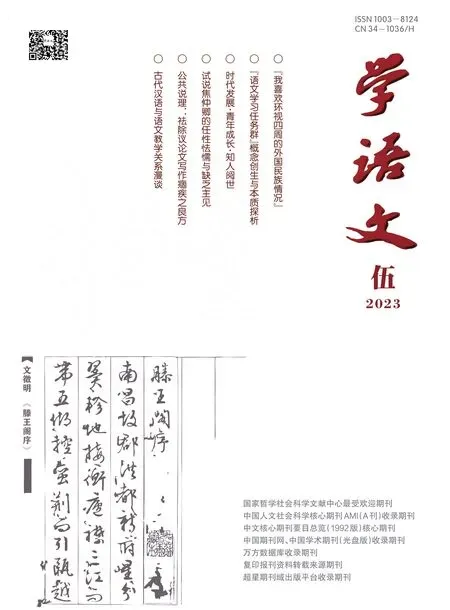公共說理:祛除議論文寫作痼疾之良方*
□ 紀 順
議論文教學常常重視常規技法與寫作知識的灌輸而忽略從真正意義上培養學生的說理能力。議論文的核心是說理,無說理則不成文。揆諸現實,讓人擔憂的是議論文寫作教學似乎在滑向迷失說理與崇拜技巧的深淵,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議論文寫作教學的真正航向。因此,我們不得不提出必要的策略來消解或減輕這種現狀可能造成的危害。我們把目光聚焦到了“公共說理”上,首先要從議論文寫作的痼疾說起。
議論文最核心的要求是說理,但學生在議論文寫作中卻暴露了諸多問題。首先是缺少認知積累,視野狹窄。受快餐文化的影響,學生似乎形成了懶惰的思維慣性,不愿躬身讀經典,不愿意主動思考問題。因之,論證觀點時,其捉襟見肘、手足無措之狀,便不難想見;其次,欠缺邏輯思維能力,觀點模糊,論證表面化。學生在議論文寫作中,觀點不明確或幾乎沒有主要觀點,多使用例證法及并列式結構,論證淺表化;最后,缺失語言的說服力,語詞含混而干癟。議論文中詞不達意或含混不清,闡述觀點的語言混亂而指向不明,這幾乎不能將自己的觀點有效傳達給閱讀者。此外,語言不具體、缺少各類修辭等也是常見的問題。
當議論文寫作能力不能完全依靠寫作者自我反思而獲得提升時,寫作教學者即教師就該思考從寫作能力要素上尋求突破。因此,為拓展學生的認知視野、提升學生的思維品質、增強議論文說服力,我們認為在教學中引入“公共說理”是理之必然。
議論文重在說理。余黨緒老師認為,說理是議論文的核心和靈魂,而說理又與學生認知視野、邏輯思維及表達密不可分。認知視野指向對周遭世界感知的范圍和水平,邏輯思維是對事物或現象的分析、判斷與綜合,表達是思維的外顯,一定程度上對說理具有強化作用。這三個方面又是當前議論文寫作容易出現問題的地方。那么,該如何解決?我們可以引入公共說理,它是革除議論文教學痼疾的良方。公共說理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早已落地生根,成為教育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的國民教育中,還未形成體系。但經一部分研究者的推廣,似乎蔚然成勢。
什么是“公共說理”?張璐璐在論文《學會公共說理》中這樣定義:“公共說理主要是指在公共領域里,一個公民面對面或者憑借一定的傳播媒介,與其他公民公開地、自由平等地就具有討論價值的話題進行有理性地、有邏輯地言說和對話。”[1]
按照定義,有幾個要素我們不能不關注。第一,對話的對象是公共領域中“有價值的話題”,這正好與議論文寫作中學生欠缺廣博的認知視野相關。第二,公共說理包括三個基本部分:主張、理由和保證。主張即說理者的結論和觀點,理由是說理的依據,這是“說理”與“非說理”的重要區別。“非說理”只有結論,沒有理由與推論過程。比如網絡上很多新聞跟帖評論,有一部分是情緒的宣泄而非真正的“說理”。這就要求“言說和對話”要“理性地”“有邏輯地”進行,這與議論文需要一定的邏輯思維不謀而合。第三,公共說理是“與其他公民公開地、自由平等地”言說和對話,這意味要考慮言說對象及言說中的基本姿態,反映到議論文中就是要充分考慮讀者意識和語言表達。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公共說理都是引導當前幾近滑向黑暗深淵的議論文教學走向光明的天使。此外,公共說理還有助于培養學生平等交流的意識和表達可靠言說的能力。在公共場域里,說理是一種基于理性精神的表達與交流,并對別人可能產生說服作用的話語形式。它歡迎其他人加入到對話中來,不是以一種對抗和壓倒的姿態來使對方屈服,而是以公正和平等的交流為前提,進而理性地發表觀點。除了必要的邏輯,徐賁先生認為信譽也很重要。信譽涉及說理者的氣質和性格,有了信譽會讓人感覺到說理是可靠且值得信任的。從上述視角來看,公共說理對議論文寫作者從學生個體成長為公民個體不無裨益。
公共說理指向學生面對公共領域中值得探討的話題進行理性思考和寫作。這些話題有的比較寬泛,有的比較具體。全國卷作文試題很早就考查到了,例如1985 年全國卷,讓考生針對污水事件,以“澄溪中學學生會”名義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寫一封信,“申述理由”并呼吁解決問題,還有2015年全國卷“女兒舉報父親在高速公路上打電話”以及近年教育部考試中心新命制的作文試題“手機該不該進校園”等。
在針對這些公共事件進行說理時,需要公共說理的素質。這種素質是現代公民核心素養的體現,也是議論文寫作的應有之義。在公共說理教學策略的使用上,我體會比較深的有指向公共說理的課程、指向公共說理的辯論、指向公共說理的演講及寫作四類,試依次論述。
一、指向公共說理的課程
以徐賁先生《明亮的對話》為中心,我們從說理的內涵、說理的結構、說理的信譽與形象、說理的情緒與措辭以及說理的邏輯謬誤等多個維度設計說理課程,建構公共說理教學體系,幫助學生從形式和內容上相對全面地了解公共說理,為說理練習及議論文寫作奠定基礎。
其中,“說理的內涵”主要為了更新學生對于說理的認知,為演講、辯論、寫作等實踐活動打下觀念的地基。說理不是說服,不是壓倒,它不以攻擊為目的。可以通過微型課程,讓學生知道說理是攤開的手掌,不是攥緊的拳頭。此外,說理的目標不是絕對的“確實”,它討論的是不確定的事,無論提供的證據如何充分,永遠具有“或然性”而沒有確定且必然的結論。因之,說理總是可以再說理,它是一個過程,不是最終結果。
“說理的結構”包括主張、理由和保證。主張指向觀點,理由指向論據,保證指向前提,類似三段論中的大前提。無論是演講還是寫作,都需要最基本的結構,以確保相對充分的說理。我們在講解時以劉瑜的《素什么質》為例,引入圖爾敏論證模型(包括主張、保證、論據、支持、語氣和反駁等六個方面)進行具體分析。《素什么質》通過人們對于“素質”的不同理解,一步一步分析“素質”的內涵。在闡述中,舉出各國體制的特征,運用自我反駁的手法來論證觀點,層層遞進,邏輯嚴謹且發人深省。這樣的分析會引導學生在寫作時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
“說理的信譽與形象”指向說理者個人的修養,中學生一般能符合要求。“說理的情緒與措辭”則指向面對不同人群,有針對性地使用不同的語言風格,以達到說理的目的。在演講時,注重以飽滿的精神狀態強化語言的感染力;在辯論時,則注重語言的邏輯性和說服力。最后,“說理的邏輯謬誤”指向在說理中可能會出現的邏輯問題,包括情緒性謬誤、形象性謬誤以及邏輯謬誤等方面,理解以及規避這些問題可以更好地進行議論文寫作。
由此,我們通過公共說理的教學,建構了說理實踐的教學體系,在實際操作中,以此為依托,輻射辯論會、演講及寫作等多個言語訓練的實踐活動。
二、指向公共說理的辯論
辯論是訓練學生有邏輯表達自己觀點的重要方式,能讓學生獲得邏輯思維、辯證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的發展,與語文核心素養之一的“思維發展與提升”及學習任務群“思辨性閱讀與表達”的內涵一致。辯論表面上是一種“說”的體式,實際上兼容了聽、說、讀、寫等言語實踐活動,并涉及人的言語動機、態度、價值觀等精神內蘊,能有效訓練學生的議論文寫作能力。
針對文藝理論界學者對周國平散文的重估與批判,我們組織了一場關于周國平散文的辯論。辯題是“周國平散文是否是自我標榜、故弄玄虛與矯揉造作”。
辯論前我們發布了任務,正、反雙方需要根據對辯題的理解,搜集材料,明確“自我標榜”“故弄玄虛”“矯揉造作”這些概念的定義及適用范圍,設想對方的觀點及可能出現的邏輯謬誤(如訴諸無知、轉移論題、錯誤類比等)并進行反駁準備。
辯論主要分為立論、駁立論、質辯、自由辯論及結辯等五個環節。
立論階段由雙方的一辯選手來完成。正方針對己方觀點“周國平散文是自我標榜、故弄玄虛與矯揉造作”進行闡述,要明確立論的框架,有最基本的主張、理由與保證,語言通暢,邏輯清晰。反方亦是如此。駁立論階段由雙方的二辯來進行,旨在針對對方的立論環節的發言進行回駁和補充己方的立論觀點,如正方二辯不同意反方一辯的立論,可以針對其邏輯漏洞逐一分析,各個擊破。質辯環節由雙方的三辯來完成,雙方的三辯針對對方的觀點和本方的立場設計三個問題,由一方的三辯提問對方,雙方的三辯交替提問。無論是正方,還是反方,所提的三個問題都要求與辯題相關。自由辯論階段,辯論雙方交替發言。在這個環節中,說理者的信譽及形象、情緒及措辭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有的沉著冷靜,有的幽默風趣。有的詭辯而被對方識破,有的偷換概念而被對手還擊。結辯階段,雙方四辯針對對方的觀點并從己方的立場出發,總結本方的觀點,闡述最后的立場。
總之,辯論是檢驗或提升學生公共說理能力的有效手段,能較為全面地呈現學生對公共說理的掌握和運用能力,可為提升學生寫作的思維品質導夫先路。
三、指向公共說理的演講
說理演講主要采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形式。線下主要是課前演講,要求學生選擇近年有爭議的時事,在展示矛盾各方的觀點后,利用公共說理課學到的知識,提出自己的主張并要求聽者評述其觀點和推理過程是否符合邏輯、有無恰當理由以及觀點是否公正,這是同伴校準,有助于演講者反思自我觀點。學生選擇的議題有“圣誕節是否該進入校園”“對明星的吐槽與評價是否合宜”等,每一次演說都很火爆,學生的觀點大多較為中肯。線上以學生錄制公共說理短視頻并發到公眾號上為主要方式,共推送了近20期。例如,某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揮部發布的《第40 號公告》第九條中有“對主動進行核酸檢測以及自覺身體不適,主動前往醫療機構就診并說明情況,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的人員,經核實后獎勵1 萬元”這樣一句話,可以作為“公共說理”的材料,于是我讓學生閱讀其文,且進行了提示:我們是從學生的角度,以公民的視角,用語文的眼光發表看法,不妄議政府為防控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所做出的積極努力。
張楷欣同學這樣說道:
在我看來,此規定確鑿無合理之處。首先,在政府的要求下,在發現不適應癥狀(主動進行檢測)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這不僅體現了對自我病情的重視,更表達著對其他人民的負責。因自我疏忽而導致全市的癱瘓,實屬為不正之舉。因此,主動做核酸是必當之舉而非自愿之為,并無給予獎勵的必要。其次,“檢出有陽性給予獎勵”,獎勵是一種對人正向行為的激勵,但檢測出陽性難道是正當行為?此條規定難道是對人們被檢測到陽性的一種激勵?故此規定違背了對獎勵一詞涵義的理解。第三,“一萬元獎勵”。該不該獎勵姑且不談,但這“一萬元”確實會惹人深思。對大多數人而言,“一萬”并非小數字,我們無法排除有人因財而故意感染,那么這獎勵還有其真正價值嗎,難道不成了幫倒忙的工具?
上述內容從公民義務、獎勵內涵及影響等多個角度進行了分析,觀點明晰,有理有據。原因分析多維且邏輯層次清楚,因而體現出一種使人信服的力量。需要明確的是,演講活動不一定注重結果,要關注學生說理的態度與邏輯,關注其理由與結論的聯系程度,關注學生搜集和遴選議題的過程。
四、指向公共說理的寫作
進行公共說理教學應該構建系統化的目標設計,從一般性的閱讀訓練入手,由概述觀點、區別細節、識別論證中的“原因”“結果”“客觀事實”“個人觀點”等初級批判性閱讀訓練逐步過渡到公共話語的真實背景中,去訓練學生判斷信息來源、評估推理過程、識別謬誤、尋找假設等技術,再融入到批判性寫作訓練中去。新課標學習任務群中的“思辨性閱讀與表達”要求學生在表達觀點時“論據恰當,講究邏輯……學習反駁,能夠做到有理有據,以理服人”[2],這與公共說理及議論文寫作的要求相吻合。培養公共說理能力首先要求學生閱讀一定量的時文、雜文和學術論著,再進行寫作。
在寫作中,我們提倡學生寫日札,讓學生運用說理的知識,在寫作中明確概念意識、讀者意識,學會透過現象看到問題的本質,以聯系和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思考問題,學會包容和善待他人的觀點并審視自己的主張。安·蘭德的《人類最荒謬的一句口號》是訓練學生說理的好材料,能有效訓練學生的思維。孫柏同學讀完此文后,在他的《淺議“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中這樣寫道:
本文不無道理,實則不在道理。文章開篇舉四例,未免有偷換概念之嫌。納粹迫害猶太人,錯,但并非錯在少數人犧牲了,而是錯在他們的犧牲毫無價值,利益到了沙文主義者和希特勒的手里,而非利于大多數人,故而這是一場屠殺與騙局;匪徒殘忍殺害一個人,錯,但并非錯在一個人為一群人犧牲了,而是錯在死者這一個人是一個代表,代表了所有正直守法、熱愛生活的平等的人們,這一小群匪徒侵犯這個人的利益,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發展,侵犯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錯。
再來看另外兩例,51%的人奴役了49%的人,九個人吃掉了一個人,錯,這就體現了作者的一個觀點:“大多數人不會為少數人犧牲,大多數人開始犧牲他人。”為此,作者提出“每個人通過自己自由的努力,得到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這不錯,但請想一下,什么促使了上述兩例慘狀的產生?是人性,別讓集體主義背這個鍋。
此文沒有盲從安·蘭德提出的“‘多數人的利益’是用來欺騙人類的最荒謬的口號之一”,從概念分析與本質分析兩個角度提出自己的主張,體現了可貴的批判性思維,非常難得。此外,我們還聚焦“王錚校長的北大附中改革”“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谷愛凌與冬奧會”等公共事件進行了公共說理寫作,并精選好文章發布到班級語文公眾號上推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學生的說理能力與說理興趣。
上述的教學內容是為教學體系的構建服務的,最終指向學生的成長。當然,以現有的說理環境以及教學成果為參照,“公共說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奧威爾曾說,一個糟糕的用法可以通過成例和模仿影響到年輕人,而他們本可以更有質量的思考。我們不希望充斥于現實或網絡的偏激與情緒化表達影響學生的人格發展,公共說理是急先鋒,是方法,也是目的。它是公民應該具備的一項基本能力,能讓學生在訓練中擺脫自我中心帶來的偏見、片面和絕對,為學生進入復雜的社會生活做好理性應對的準備。在寫作教學中有意識地進行公共說理教育只是培養學生理性、提升寫作能力的策略之一,要從根本上扭轉議論文寫作的不良現狀,任重而道遠。不過,君子當弘毅,在教學中不斷滲透公民教育與批判性思維教育,放眼未來,在議論文寫作領域甚至是教育領域,定能繁花似錦,一片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