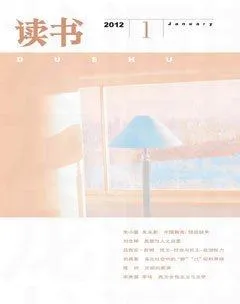“神圣的俄羅斯”之爭
李珂
一九七四年,冷戰最高潮之際,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境,后來定居美國。同一年,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斯出版了《舊制度下的俄國》(Rus s ia under the Old Regime )一書。兩人原本素不相識,不約而同地反對美國對蘇緩和政策,后來卻成了輿論場上的敵人,而這本書是點燃矛盾的導火索。
派普斯并非土生土長的美國人,而是出生在東歐的猶太人,一九三九年為了躲避歐洲的戰亂和反猶運動,隨同家人遷居美國,先后進入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深造,后來成為哈佛大學俄國史教授、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舊制度下的俄國》是他的代表作“俄國史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這一領域的重磅之作,被許多大學當作參考書目,并被翻譯成好幾種外語。
在個人回憶錄《活過:一個無根之人的回憶錄》(Vixi:Memoirs ofa Non-Belonger )里,派普斯這樣解釋自己的作品:《舊制度下的俄國》講述了從古代到十九世紀晚期俄羅斯國家地位的演變,強調了沙皇權力的世襲壟斷本質,這一特點延續到了蘇聯。在其看來,這種權力與西方的專制主義截然不同,因為后者一直受到私有財產制度的制約。
派普斯最初對索爾仁尼琴頗為欽佩,一九七四年夏天甚至取消了去蘇聯的訪問,以抗議他被驅逐。次年十一月,派普斯把《舊制度下的俄國》寄給了他,隨書附上一封信,以為他會“在我們的觀點中發現幾個巧合”。
當時,派普斯對索爾仁尼琴的政治立場一無所知,還以為后者是同道中人。然而,索爾仁尼琴雖然反對蘇聯當局,卻對沙皇俄國懷有深厚的感情,而這本書里卻對它的諸多傳統進行批判。當他翻開正文,映入眼簾的第一句話就是“無論俄國的愛國主義史學家們如何書寫,上帝在創造人類時,都并未將俄羅斯人置于他們今日所處之地”,接下來敘述了斯拉夫人遷徙的歷史,暗示俄羅斯具有與美國相似的殖民性質,它那廣袤的領土幾乎都是沙皇侵略擴張的產物。這樣一本書被送到自己手中,在索爾仁尼琴看來幾乎是一種挑釁。
一九七六年末,索爾仁尼琴在美國加州胡佛研究所發表演講時,對派普斯和這本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當時的派普斯沒有做出回應,后來在回憶錄里評價道:“他完全沒有歷史知識,對革命前的俄羅斯有一種天真的浪漫主義觀點,并將俄羅斯的苦難完全歸咎于從西方進口的各色革命意識形態的影響。”一九七八年六月,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上,剛剛獲頒該校榮譽博士學位的索爾仁尼琴,又對著美國開炮,稱他所避難的國家在精神上軟弱無力,并深陷庸俗的唯物主義之中。美國人很膽怯,很少有人愿意為自己的理想而死,因此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倉促投降。
冤家路窄,作為哈佛教授的派普斯剛好在典禮上與他碰面,于是問道:“為什么您認為同樣的人,有著相同的歷史,說著相同的語言,生活在同一領域,可以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個晚上變成完全不同的事物?即使是生物學上,也沒有這種突然和極端的突變。”
可能是聽出了派普斯話中的諷刺之意,索爾仁尼琴的怒火越燒越烈,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他在一切可能的公開場合對派普斯進行抨擊。當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向蘇聯播放《舊制度下的俄國》節選時,他甚至表示抗議。一九八0年,他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寫道:“理查德·派普斯的書《舊制度下的俄國》可能是一長串關于俄羅斯扭曲形象的聲明里的典型。……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國家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對一具尸體的解剖。這本書只允許得出一個可能的結論:俄羅斯民族在本質上是反人類的,在其一千年的歷史中,它一無是處,就任何未來而言,它顯然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案例。派普斯甚至把發明極權主義的榮譽頒給了尼古拉一世……我對派普斯的一種‘學術’技巧感到特別痛苦。俄國諺語約有四萬條,它們的統一性和內在的矛盾性構成了一座耀眼的文學和哲學大廈。派普斯從這些諺語中挑出半打適合自己需要的諺語,并用它們來‘證明’俄國農民的殘忍和玩世不恭的本性。這種方法對我的影響,就像我想象中羅斯特羅波維奇(音樂家)不得不聽一只狼拉大提琴時的感受一樣。有兩個名字被所有有這種傾向的學者和散文家反復提到: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但你也能輕易找到兩三個國王—在英國、法國或西班牙,甚至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中—殘酷性絲毫不減。”
索爾仁尼琴剛來美國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警告總統福特,要避免與他見面。基辛格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索爾仁尼琴是一位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觀點甚至讓他的持不同政見者同胞感到尷尬,他與總統會面不僅會冒犯蘇聯人,還會引起美國的一些盟國的爭議。”福特聽從建議,讓索爾仁尼琴吃了閉門羹。雖然福特的繼任者里根總統開始遏制蘇聯,但仍然沒有青睞索爾仁尼琴。繼基辛格之后,索爾仁尼琴的老對手派普斯,將會成為他通往白宮之路的第二個絆腳石。
領取諾貝爾獎,前往西方,是索爾仁尼琴的高光時刻。但是,來到美國之后,他的命運卻一路下沉。而理查德·派普斯,這個被他形容成像“一只狼拉大提琴”的學者,卻節節高升。
隨著索爾仁尼琴在西方做了幾次不合時宜的演講,西方媒體對他的批評愈演愈烈,一些歐美政要甚至公開表態不同意他的觀點。他索性退居到美國佛蒙特州鄉下,在接下來的十七年里致力于創作《紅輪》(The Red Wheel )。
索爾仁尼琴與海外俄裔的關系,也十分微妙。在十月革命和蘇俄內戰后,有一批移民逃離俄國,被稱為“白俄”。他們大多是內戰“白軍”的支持者,與蘇聯“紅軍”針鋒相對。出現在西方后不久,索爾仁尼琴就與“白俄”移民組織關系密切,成為其精神領袖,將多本作品都授予他們發行。相比之下,六七十年代的蘇聯新移民,雖然人數比當年更多,而且差不多與索爾仁尼琴同時來到,卻遭到后者的鄙視,因為他們對宗教和俄羅斯民族意識的復興漠不關心,只想到西方追求更好的生活。
理查德·派普斯在《舊制度下的俄國》里,曾總結沙皇俄國時代的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特點:為了維護沙皇的統治,斯拉夫派創立了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想,通過貶低西歐來抬高俄羅斯。斯拉夫派對他們自己所排斥的東西,即法律、財產,以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一無所知。至于“西化派”,只是歷史學家們為“斯拉夫派”創造的一個鏡像,除了反對之外,很難找到將它們統一起來的共同點。
仿佛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吸引力,索爾仁尼琴抗拒學英語,無法融入美國社會,卻在沙俄的遺老遺少里如魚得水。雖然他希望表達一種“治愈的、有益的、溫和的愛國主義”,但是美國媒體習慣性地把他與專制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混為一談,因為他的小圈子里不乏此類人士。
與索爾仁尼琴一路下沉的命運相反,理查德·派普斯這段時間里順風順水。他在哈佛大學教授有關俄羅斯帝國和俄羅斯革命的大型課程,場場爆滿,還指導八十多名研究生獲得博士學位。《舊制度下的俄國》啟發了許多歷史學者,二十一世紀德國學者曼弗雷德·希爾德邁爾的《俄國史:從遠古到十月革命》(Ge s c h i c h t eRusslands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Oktoberrevolution )仍有它的影響。除了學術,他還獲得了影響政治的權力。從一九七六年起,派普斯領導了中央情報局(CIA)的B 組分析小組,負責分析蘇聯的軍事政治戰略和目標。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他成為里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東歐和蘇聯事務主任。
一九八一年四月,在索爾仁尼琴的提議下,“白俄”移民的一個重要組織——“俄羅斯裔美國人協會”(Russian American Foundation)籌劃一場大規模的明信片活動,要求白宮解雇理查德·派普斯。無巧不成書,同樣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一位美國參議員向白宮提議,安排索爾仁尼琴與里根總統會面。派普斯正好是負責東歐事務的專家,無論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還是出于對政治風險的擔憂,他都建議里根不要與其直接見面,而是在某個合適的場合向索爾仁尼琴致以公開祝賀。
當年秋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名工作人員再次提議,邀請索爾仁尼琴與總統見面。這次會面以午餐會的形式進行,他將會與一群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出席。“白俄”移民媒體在幾天后的報道中暗示,索爾仁尼琴因為沒有被單獨邀請而生氣了。于是,白宮的眾人決定,在午餐之前給他安排十五分鐘與總統的臨時會面,由理查德·派普斯起草會面邀請函。但是,這一邀請函被白宮延遲發出,根據派普斯的說法,是“在辦公室里被放錯了地方”。
索爾仁尼琴感到自己不僅被怠慢,還被不懷好意地捉弄,斷然拒絕前來。取而代之的是,他給里根總統寫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指責美國“存在各種各樣的黑暗勢力,策劃針對俄羅斯人口的種族滅絕的核攻擊……”在信件結尾,他大筆一揮,“當你(里根)將不再擔任總統,并享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如果你碰巧在佛蒙特州,我誠摯地邀請你來拜訪我”。
理查德·派普斯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原以為里根會做出憤怒的反應。但讀完這封信后,他平靜地說,作者顯然不愿與那些持不同政見者為伍。……自由電臺公開廣播了對他的信,還荒謬地指責美國有一個針對俄羅斯人口的種族滅絕策略。俄羅斯移民媒體,指責我出于個人目的“陰謀破壞”了它的英雄與總統的會面。二十年后,索爾仁尼琴回憶他在美國的生活時,為這一事件指責我,指責我對他懷有“個人仇恨”,因為他幾年前批評我的《舊制度下的俄國》。
派普斯所說的是索爾仁尼琴的回憶錄《落在兩個磨盤之間的小谷粒》(The Little Grain Fell Between Two Millstones )。索爾仁尼琴在二十年后仍舊余怒未消,認為自己就像一顆“小谷粒”,夾在強大的蘇聯和西方兩個磨盤之間。當自己與蘇聯進行斗爭時,感受到了西方精英的滿滿惡意,他們似乎在抓住每一個機會對自己進行圍追堵截。索爾仁尼琴還對自己的老對手進行評價:派普斯是一位杰出的俄羅斯學者,也是一位隨心所欲地將俄羅斯傳統與專制、神權、反猶太主義和帝國主義等同起來的學者,對俄國傳統的懷疑多于尊重,還認為索爾仁尼琴是“正統、民族主義和專制”的危險代表,將他自己視為“永恒的俄羅斯”。
索爾仁尼琴以一種殉道者的姿態來描寫自己的處境,似乎是夸大其詞。但是,至少有一點沒錯—他的確是在為“神圣的俄羅斯”而戰。派普斯這樣的西方精英針對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那“神圣的俄羅斯”。
《舊制度下的俄國》是一本現象級的書,從誕生之初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議。
在以往俄國的歷史書里,基輔羅斯—莫斯科大公國—沙皇俄國是一個神圣的世系,是東羅馬帝國的繼承者。這一世系往往被戴上耀眼的光環。但是,派普斯在書中寫道:在蒙古征服基輔羅斯之后,莫斯科大公之所以從諸大公中脫穎而出,成為全羅斯大公,正是通過討好蒙古大汗,為其征收賦稅、鎮壓叛亂,而后反客為主,奪得國家的控制權。“沒有一個王公曾踏足過君士坦丁堡,而他們對通往薩萊(金帳汗國首都)的道路則太熟悉了。正是在薩萊,他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絕對君主制的運行,觀察到‘一種不容人們協商而必須無條件服從的權威’。”幾百年來,沙皇俄國憑借西方的先進技術向東方一路擴張,無往不利,卻因為慣用高壓手段而被西方當作異類。在十九世紀多次改革失敗后,沙皇俄國建成了一個漏洞重重的官僚 — 警察制國家,注定了滅亡的結局。
同時代的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學者唐納德·特里戈爾德(DonaldW.Treadgold)在《斯拉夫評論》上寫道:“他給了我們一本博學且深刻反思的書……然而,人們希望在一本關于一個偉大民族的悠久歷史的書中看到更多的積極品質,更值得贊揚的事情,以及對所討論的人類更多的同情和溫暖。”
在二十世紀的西方史學界,關于俄國史最重要的分歧是對沙俄晚期政權的態度。如果認為沙俄政權無法進行改革,那么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合理的。
維護沙俄的保守派,往往寄希望于斯托雷平,把他推行改革的時代描述為一個可以脫胎換骨的時期。索爾仁尼琴在《紅輪》里認為沙皇俄國并非是一個腐朽專制的政權,而是被暴力橫加摧毀的理想國,呼吁猶太人認領自己的罪過。例如,沙俄首相斯托雷平遇刺身亡,兇手德米特里·博格羅夫是一個猶太人。在索爾仁尼琴看來,他之所以刺殺斯托雷平,不是因為后者大肆捕殺革命黨,而是因為推行改革,為沙皇俄國力挽狂瀾,因為“對俄羅斯有利的事情,對于猶太人來說卻是壞事”。對此,派普斯評價道:“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反猶主義。索爾仁尼琴不是種族主義者……這基本上是宗教和文化問題。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些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狂熱的基督徒和愛國者,也是一個狂熱的反猶主義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曾在沙俄暢銷一時,后來更是被“白俄”流亡者奉為政治圣經。其中充滿政治隱喻的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檢察官故事。耶穌基督再次來到世間,卻被逮捕下獄。檢察官對耶穌說,他的教義是殘酷的,因為它允許靈魂的自由,很少有人能夠承擔,只能打開通往邪惡的道路。只有由一個精英的鐵腕控制,才能拯救人民免受其自身無法無天的激情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來為沙皇的專制辯護,無獨有偶,索爾仁尼琴的理想也是一個仁慈的神權專制國家,他認為這植根于俄羅斯歷史,是自然而然的。雖然他承認沙俄治下人們的苦難,卻認為他們應該默默忍受,等來統治者推行的德政,而革命者推翻沙俄,是被西方輸入的思想蠱惑了。
派普斯也許會驚訝于索爾仁尼琴的不切實際,這個與自己不約而同地主張封鎖蘇聯的人,居然還幻想在蘇聯解體之后復興“神圣的俄羅斯”,仿佛生活在十九世紀。但是,他在別的問題上比自己的對手更加感情用事。在《俄國革命史》里,他花了四十四頁來描述末代沙皇尼古拉一世全家被處決一事。后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寫作過程中,他眼前浮現的是猶太同胞被屠殺的慘象,這兩幕重疊了起來。他同情沙皇,把沙皇一家代入了那些像雞蛋一樣被碾碎的猶太家庭,卻忘了沙皇不會同情他們猶太人。在一九0五至一九0七年俄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尼古拉二世都進行過反猶屠殺。派普斯家族原為加利西亞猶太人,被沙俄大軍屠殺驅逐,聚居區毀于一旦。他的父親是奧匈帝國波蘭軍團的一名士兵,“一戰”后遷居西里西亞,后來又被納粹德國逐出歐洲。
索爾仁尼琴將自己視為“神圣的俄羅斯”的化身,為其承受西方的惡意,但是,“神圣的俄羅斯”被西方排斥,領導它的沙皇難辭其咎。一九一五年在加利西亞的首府利沃夫,尼古拉二世在演講中說:“這里沒有加利西亞,只有偉大的俄國。”從結果來看,派普斯這樣的東歐猶太人才是受害者,是夾在泛斯拉夫主義的擴張和德國的尚武之間的炮灰。直覺,往往比嚴密的邏輯更直截了當,索爾仁尼琴能夠感覺到派普斯反對的是什么,派普斯也清楚索爾仁尼琴想追求的是什么。矛盾在一百年前已經埋下,即使隔著冷戰意識形態的重重障幕,也能分出朋友和敵人。即使沙俄滅亡、蘇聯解體,他們的仇怨仍然不會化解。
結束流亡后,索爾仁尼琴回到俄羅斯,住進了莫斯科郊外的由總統贈與的別墅里,將斯托雷平和“白軍”首領高爾察克的畫像高懸于室。盡管這兩個人備受爭議,但在他眼里卻能夠拯救俄國。憂國憂民的姿態,大國師和預言家的外表,讓他并未像西方精英們預言的那樣被時代拋棄。通過對傳統的召喚,他贏得了新一波的榮譽。在被白宮拒之門外二十年之后,他終于找到了另一條路,通往克里姆林宮的鋪著紅毯的道路。
理查德·派普斯在回憶錄里曾評價索爾仁尼琴:“他想象中的‘神圣的俄羅斯’未能在蘇聯解體的瞬間重現人間,這一定使他非常失望。”二0一七年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又說:“過去一百年沒有任何改變。……人們仍然想要那樣的政客……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他,讓他來管理。而他們本身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
(《舊制度下的俄國》,[ 美] 理查德·派普斯著,郝葵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二0二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