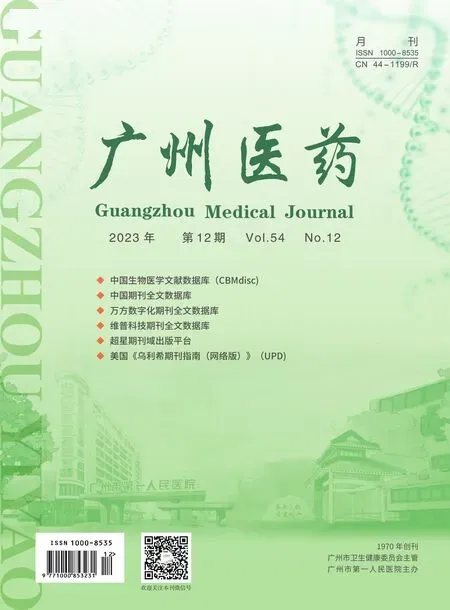小膠質細胞在帕金森病中的雙向作用:神經保護和疾病惡化
王 霞 黃 浪 項宗勤 牟 斌 曹海紅 劉振華 唐北沙,3 劉 勇
1 華南理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神經免疫與健康實驗室,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廣東廣州 510180)
2 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神經內科(湖南長沙 410008)
3 南華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腦疾病多組學研究中心、神經內科(湖南衡陽 421000)

圖片摘要:小膠質細胞在帕金森病中的異質性包括但不僅限于對抗疾病(Against disease)和促進疾病(Disease accelerative)的作用。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第二大神經退行性疾病,在50歲以下的人群中不常見,隨著年齡的增長發病率逐漸增加,在85歲至89歲之間達到發病高峰[1]。PD在男性中更常見,男女的發病比例為1.4∶1.0[1],在65歲及以上人群中,每年每10萬人中就有160人新患PD[2]。PD的病理特征是黑質致密部(substantia nigra compacta,SNc)的多巴胺(dopamine,DA)能神經元的變性死亡以及路易小體(Lewy body)的聚集,路易小體是由α-突觸核蛋白錯誤折疊組成的神經元包涵體[3]。隨著疾病的進展,路易小體的聚集不僅影響大腦邊緣和新皮質區域,還影響其他區域的非多巴胺能神經元[4]。此外,中樞神經系統外的神經元如腸系膜系統中的神經元也隨著PD進展而惡化[5]。
PD的主要運動癥狀為靜息性震顫、運動遲緩、肌肉僵硬和姿勢不穩定等;而非運動癥狀包括認知能力下降(癡呆)、嗅覺功能障礙、精神異常(抑郁、冷漠、焦慮)、便秘、睡眠障礙及疲憊等,PD的非運動癥狀通常表現在運動癥狀出現之前[3,6]。由于PD患者癥狀表現的復雜性,有約10%的患者早期被診斷為其他疾病[7]。DA轉運-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掃描(DATSPECT)、結構磁共振成像(MRI)、磁共振擴散加權成像(MR-DWI)和基因檢測常被用于PD的臨床診斷[5]。由于大約有90%的PD患者存在嗅覺減退或嗅覺缺失,臨床檢查中常用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嗅覺識別測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mell Identification Test,UPSIT)或嗅探棒測試進行嗅覺功能測試[8]。
PD的主要起因是多巴胺能神經元的進行性病變,導致釋放到紋狀體的DA水平逐漸降低。目前對于PD的常見治療方法主要采用左旋多巴來替代DA[3]或使用DA受體激動劑[5],而這些對癥治療的方法均無法減緩疾病的進程。隨著神經退行性病變的進展和臨床癥狀逐漸加重,治療效果會逐漸減弱[9]。PD的運動癥狀通常出現在疾病的晚期,即當50%的多巴胺能神經元丟失后,患者才會出現運動障礙[10]。因此,尋找早期生物標志物以及在疾病的前驅期靶向分子損傷和炎癥表型進行干預非常重要。現在已知潛在的生物標志物是由小膠質細胞釋放到胞外的細胞因子[11],而在PD患者的大腦中顯示存在受損和過度激活的小膠質細胞,PD進展可能是由死亡神經元和小膠質細胞狀態之間的惡性循環驅動的,通過氧化應激、自噬和自噬功能障礙、突觸核蛋白積累和促炎因子釋放[11]。因此,認識小膠質細胞在PD中的多面性,研究清楚小膠質細胞異質性的具體細節,對今后PD的研究和治療具有重要的意義。
1 PD 的病因
PD發病的原因十分復雜,既包括環境因素,也有遺傳因素。環境因素如經常接觸殺蟲劑、缺乏運動、頭部受傷和壓力等情況[12]。1-甲基-4-苯基-1,2,3,6-四氫吡啶(MPTP)中毒的人與PD具有相同的癥狀[13]。農村環境中接觸較多的除草劑和農藥暴露也與PD的發病風險有關[14]。遺傳因素中包括常染色體顯性的PD基因突變如編碼α-突觸核蛋白(SNCA)和富含亮氨酸重復激酶2(LRRK2)的突變均能引起線粒體的功能障礙[15]。SNCA突變的患者大腦中呈現路易小體的聚集和多巴胺能神經元的變性壞死[16]。LRRK2突變常見的變異有G2019S、R1441C、R1441G和R1441H,這些突變通過影響囊泡運輸、細胞骨架功能、蛋白質合成和溶酶體系統等生理功能,從而導致DA神經元的死亡[17]。而常染色體隱性的PD基因突變如Parkin、PTEN誘導激酶1(PINK1)和DJ-1編碼的蛋白質參與了線粒體通路。DJ-1、PINK1和Parkin基因突變會損害線粒體的呼吸鏈,線粒體膜電位減少,氧自由基增加,從而使黑質DA神經元發生損傷壞死,最終出現臨床癥狀[18-19]。線粒體自噬對于維持線粒體的整體質量和穩態具有重要的作用,可選擇性的清除多余或損傷的線粒體[20]。PINK1、Parkin和LRRK2等基因的突變可導致線粒體的自噬異常,穩態受到破壞,進而促使多巴胺能神經元變性,最終導致PD的發生[21-23]。
2 PD 的分子機制
PD的發病機制包括α-突觸核蛋白聚集(alpha synuclein,α-syn)、氧化應激、鐵死亡、線粒體功能障礙、神經炎癥和腸道失調等[5]。α-syn定位于細胞質、線粒體和細胞核,在突觸囊泡動力學、細胞內運輸和線粒體功能中發揮作用[24]。α-syn在可溶性單體形成低聚物時具有神經毒性,這些低聚物結合成微小的原纖維,最終形成較大的、不可溶的原纖維[25]。在生理條件下,自由基或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在宿主防御、基因轉錄、突觸可塑性調節和細胞凋亡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26]。然而,當ROS超過細胞抗氧化活性時,就會發生氧化應激。細胞毒性物質在神經元中累積,最終導致蛋白質崩潰、酶衰竭、脂質分解和細胞死亡[27]。另外,異常的鐵代謝和嚴重的脂質過氧化可觸發鐵死亡,可導致氧化應激和細胞死亡[28],研究顯示鐵死亡也參與了PD的DA神經元死亡[29]。線粒體功能障礙在PD的發病機制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大部分DA神經元壞死由鈣離子的調節啟動,線粒體內鈣離子的持續性超載可使機體更易患PD[30]。線粒體復合物I作為線粒體電子傳遞鏈中最大的復合物,位于線粒體呼吸鏈的起始端,提供了40% 的質子泵,是ATP合成的主要場所[31]。研究顯示PD患者的線粒體復合物I在SNc中大量減少[32],線粒體復合物I的功能異常導致SNc中DA神經元退變。此外,大量研究顯示在PD患者死后的大腦中存在神經炎癥相關損傷[33-34]。在PD患者中,活化的小膠質細胞密集分布于中腦和殼核,與DA轉運體配體活性降低相關[35]。最后,腸道菌群在神經系統疾病中的作用已經獲得了越來越大的關注,腸-腦微生物群信號包括中樞神經系統、腸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和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5]。動物實驗也證實α-syn病理可沿腸-腦軸擴散,向腸壁注射α-syn可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的病理改變[36]。上述PD的發病機制之間并非獨立存在,可相互影響,這導致了PD疾病的進展具有多因素和復雜性。
3 PD 的治療策略
目前對PD的治療主要為對癥治療,左旋多巴(L-DOPA)是多巴胺的前體,幾乎所有PD患者在疾病進展過程中都使用左旋多巴進行多巴胺替代治療。盡管左旋多巴是PD治療的“金標準”,并且能夠顯著緩解PD的癥狀,但隨著疾病的進展,晚期PD患者會產生左旋多巴誘導的運動障礙(LID)[37]。多巴胺受體激動劑也作為PD治療的選擇,紋狀體棘神經元具有兩種DA受體,靶向D2受體家族的激動劑如麥角生物堿溴隱堿能激活5-羥色胺(5-HT),但它與心臟瓣膜纖維化和胸膜肺纖維化有關,這引起了重要的安全問題[5,38],相比之下,非麥角堿類藥物則不存在這個問題[38]。多巴胺受體激動劑的半衰期雖然比左旋多巴長,但它們的總體效果卻不如左旋多巴,而且更容易引起嗜睡和沖動控制障礙[39]。由于左旋多巴在外周代謝過程中,兒茶酚-甲基轉移酶(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COMT)可將藥物甲基化,抑制COMT可改善左旋多巴的生物利用度和半衰期,因此COMT抑制劑聯合左旋多巴常用于PD患者的一線治療方案[40]。單胺氧化酶B(monoamine oxidase type B,MAO-B)抑制劑也可有效改善PD患者的運動和非運動癥狀[41]。上述針對DA能治療雖然對緩解PD的癥狀有顯著的效果,但卻仍然不能阻止疾病的進程,且無法避免藥物帶來的毒副作用,因此,尋求非DA能靶點是格外重要的。本文將重點關注大腦中的小膠質細胞在PD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探討小膠質細胞對干預PD進展的可能性。
4 小膠質細胞概述
小膠質細胞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常駐免疫細胞,約占大腦所有細胞的12%,有一定的異質性[42-43],發揮對大腦的先天免疫監視及維持中樞神經系統內穩態的作用[44]。體內譜系追蹤研究證實,成年小膠質細胞起源于胚胎第8天之前出現的由卵黃囊產生的原始髓系祖細胞[45]。小膠質細胞既能在生理上發揮穩態維持作用,也能在疾病中發揮促進疾病發展的作用。小膠質細胞分泌營養因子促進神經前體細胞增殖、成神經細胞遷移和神經元分化,參與成年海馬神經元發生的生理過程[46];小膠質細胞釋放的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調節突觸可塑性和樹突棘密度[47];小膠質細胞通過促進程序性細胞死亡和在不引起炎癥的情況下清除凋亡的神經元和膠質細胞參與大腦發育過程[48]。小膠質細胞通過其細胞突起不斷巡視腦實質,對急性和慢性損傷、神經退行性病變或生理衰老產生的病理信號迅速做出反應[49],但在某些病理條件下或衰老進程中,其維持穩態和吞噬的功能會受到抑制[50-51]。
近幾十年來,關于小膠質細胞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一直受到如“靜息vs激活”和“M1 vs M2”等二分法的限制。例如過去研究者們將小膠質細胞對損傷的反應通常稱為“激活”,包括遷移或擴展到受損部位、細胞增殖、吞噬和產生可溶性分子[52]。這種對小膠質細胞好與壞的二元分類方法與近年來闡明的小膠質細胞在發育、可塑性、衰老和疾病中的廣泛狀態和功能出現了不一致[53]。小膠質細胞現在被認為是健康成熟大腦中最具活力的細胞,這一開創性的發現促使人們將“靜息”的小膠質細胞重新描述為surveying[54-55],并提出了小膠質細胞從不靜止的概念。事實上小膠質細胞總是活躍的,即使在健康狀況下,小膠質細胞也保持著動態活動,持續監測周圍環境,根據不同的環境變化,其不斷地對中樞神經系統做出反應。近期研究發現,小膠質細胞突起的動態活動在神經活動降低的時候明顯增加,以及其應對急性損傷反應能力增強,這種神經活動的降低包括了麻醉和睡眠狀態,這提示小膠質細胞的動態活動及功能會根據機體狀態的改變而做出調整[56-58]。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在大腦中觀察到小膠質細胞的空間異質性,不僅在密度和功能標記方面,而且在轉錄組譜方面[59-60]。此外,小膠質細胞的表型變化,包括形態、蛋白質組學特征和行為的改變均顯示與疾病的進展相關[61-62]。小膠質細胞表型的空間異質性和對年齡相關變化的區域恢復力表明,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空間模式可能與局部小膠質細胞的表型有關[63]。衰老大腦中的小膠質細胞分支減少,減少了它們的監視區域,這可能導致穩態功能受損[64-67]。而患病大腦中的小膠質細胞形態也隨疾病的空間位置和階段而變化。小膠質細胞形態的多樣性可歸因于病理環境的強度和持續時間[68],但也可能與小膠質細胞對不同刺激的不同反應有關[69]。因此,在應對創傷、損傷、感染、疾病和其他挑戰時,小膠質細胞的反應不能簡單用“靜息和激活”來描述。
全基因組關聯研究提示,許多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包括阿爾茨海默病(AD)、PD、精神分裂癥、自閉癥和多發性硬化癥(MS)等的很多風險基因均是由小膠質細胞表達的,提示靶向小膠質細胞有望為眾多神經精神相關疾病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70-72]。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人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來描述這些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特征,但關于小膠質細胞在神經退行性疾病中的功能仍有待闡明。希望未來技術和工具的快速發展將帶領我們去探索更多未知的領域。活體腦細胞成像、單細胞轉錄組學和蛋白質組學的進展,以及更尖端的載體操縱小膠質細胞功能狀態的工具的出現,將促進該領域的快速發展[73]。
5 小膠質細胞在帕金森病樣模型的研究
由于帕金森病的特征是SNc的DA神經元退行性病變,因此針對帕金森病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神經元的選擇性丟失,以確定神經保護的靶點。然而關于神經膠質細胞在PD發病機制中的作用的研究較少,有研究顯示包括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在內的神經膠質細胞可能通過失去正常的內穩態功能或者單獨獲得神經毒性功能而促進PD的發病[74-75]。很多PD相關研究顯示了小膠質細胞的增生,同時強調了神經炎癥在PD中可能的重要作用[76]。PD相關的動物模型研究通過病理實驗強調了小膠質細胞的吞噬作用,并認為一些小膠質細胞在PD病程的晚期仍然具有其吞噬功能,然而這種吞噬標記未必與其吞噬能力相關[77]。已有證據顯示,小膠質細胞的形態變化只能說明其細胞受損,進而不能執行其固有的功能[78]。由于對多余的有害物質的清除對保持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是至關重要的,小膠質細胞的吞噬和降解失調可能在PD的發病機制中起關鍵作用,下文將介紹在幾種不同PD模型中小膠質細胞的研究情況。
5.1 神經毒素模型
1982年,一群吸毒成癮者在注射合成海洛因后,出現了PD患者常見的癥狀,這為PD的潛在機制提供了線索,而該藥物成分為1-甲基-4-苯基-1,2,3,6-四氫吡啶(1-methyl-4-phenyl-1,2,3,6-tetrahydropyridine,MPTP)。MPTP在大腦中代謝生成的1-甲基-4-苯基吡啶陽離子(MPP+)通過抑制線粒體呼吸鏈機制復合體1,可作為神經元細胞死亡的高效啟動劑,從而損害黑質致密部的多巴胺能神經元,導致典型的PD癥狀[13,79]。MPTP模型已被廣泛應用于研究PD,在MPTP誘導的PD小鼠模型研究發現,SNc中的小膠質細胞數量增加和形態改變先于多巴胺能神經元的減少[80]。當觀察到嗅覺功能障礙等非運動癥狀時,可以檢測到SNc中早期的小膠質細胞激活[81]。在予以MPTP誘導建模后,用米諾環素可顯著降低小膠質細胞的激活率、胞外IL-1β的水平及多巴胺能神經元的死亡率。米諾環素治療還降低了MPTP誘導的小膠質細胞激活關鍵酶iNOS和NADPH-氧化酶活性(兩種酶都可介導小膠質細胞的神經毒性)以及促炎因子TNF-α的水平[82-83]。在嚙齒動物MPTP急性誘導的PD模型中,給予急性劑量MPTP后小鼠的SNc中出現早期和短暫的反應性小膠質細胞,且出現在神經元發生損失之前,在MPTP毒素暴露后的幾周內逐漸消失[84]。靈長類動物MPTP研究發現,在MPTP注射1年后,其SNc的反應性小膠質細胞仍然存在[85]。
在多巴胺能神經元-小膠質細胞共培養的研究中,在給予魚藤酮治療時顯示,與IFN-γ受體缺陷小膠質細胞相比,野生型的小膠質細胞多巴胺能神經元丟失更多。在另一項大鼠的研究中,魚藤酮與LPS一起通過小膠質細胞介導的NADPH氧化酶激活和ROS釋放,引發神經退行性病變[86]。另外,在6-羥多巴胺(6-OHDA)模型中,在SNc或紋狀體注射6-OHDA顯示能強烈誘導小膠質細胞的激活,且根據6-OHDA注射的部位的不同,小膠質細胞的激活被描述為DA神經元退化的早期、中期和晚期[87]。經紋狀體注射6-OHDA后,組織學上可檢測到反應性的小膠質細胞[87]。上述在基于神經毒素模型的研究顯示,DA神經元損失過程中存在小膠質細胞的早期和持久激活,而小膠質細胞在其中的具體作用機制和功能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5.2 α-突觸核蛋白模型
α-syn是一種在中樞神經系統突觸前及核周表達的可溶性蛋白質,在PD的發病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α-syn基因的增殖或突變與家族性PD密切相關[88]。在PD的發病進程中,α-syn從可溶性的纖維復合物逐漸轉變為不可溶性的纖維復合物,可能是通過中間可溶性的寡聚物形式導致神經元功能障礙[89]。大量研究以α-syn為基礎開發的模型試圖復制在PD患者中觀察到的α-syn病變。這些模型包括野生型人α-syn或A53T突變人α-syn的過表達,以及在DA神經元中過表達截斷的人α-syn[90-93]。負責編碼α-syn的SNCA基因的重復、三倍復制和點突變(A30P、A53T、E46K、H50Q和G51D)導致常染色體顯性形式的PD[11]。SNCA的小鼠模型中包括α-syn、人α-syn過表達和插入人α-syn點突變。已知給與α-syn和α-syn 過表達處理均可產生小膠質細胞ROS、TNF-α、IL-1β、COX2、iNOS的表達升高[94]。LPS在過表達人源A53T突變α-syn的轉基因小鼠中誘導了持續的小膠質細胞增生、炎癥分子的產生和黑質紋狀體神經元的進行性變性,但在野生型α-syn小鼠中沒有,這表明小膠質細胞在介導PD的慢性變性中累加了神經炎癥和α-syn誘導的細胞損傷[95]。此外,對α-syn過表達的小鼠和靈長類動物的研究證明,無論是否出現DA神經元的變性,都顯示出激活的小膠質細胞的表型[96-97]。雖然這些模型不能復制PD的主要特征,如進行性和嚴重的DA神經元損失和運動障礙,但極大地增強了對α-syn誘導的毒性的理解。
5.3 LRRK2模型
富亮氨酸重復激酶2(leucine rich repeat kinase 2,LRRK2)基因突變是PD最常見的病因,與高達3%的特發性PD病例和5%~15%的家族性PD病例相關[98]。G2019S LRRK2突變是顯性遺傳性PD最常見的突變,與激酶活性增加有關,具有G2019S LRRK2突變的PD患者的臨床和病理表型幾乎與特發性疾病難以區分[99]。攜帶LRRK2基因突變的細胞或小鼠為晚發性帕金森病中神經炎癥和DA神經元變性之間的因果關系提供了直接證據,在病理條件下,LRRK2在活化的小膠質細胞中表達上調,而LRRK2的消除或抑制阻止了炎癥反應,導致LPS后炎癥細胞因子的產生減弱,NF-κB轉錄活性降低,小膠質細胞的形態激活、趨化和吞噬活性降低[100]。一項基于LRRK2突變的轉基因小鼠模型的研究表明,抑制LRRK2可以通過阻止激活的小膠質細胞的招募和潛在的骨髓細胞浸潤來防止DA神經元的丟失,而過表達LRRK2會導致神經元的損傷和加重神經炎癥[77]。這些研究均暗示了LRRK2與小膠質細胞在PD 的進展中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但是二者間的具體作用機制仍有待研究。
6 小膠質細胞在帕金森病中的保護作用
小膠質細胞介導的神經炎癥在PD的發病機制中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在疾病的早期發揮神經保護作用,而在疾病后期則對PD的進展起著促進作用。在PD的早期階段,小膠質細胞釋放抗炎細胞因子如IL-10和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FGF)、生長因子如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集落刺激因子1(colony-stimulating factor-1,CSF-1)、神經營養生長因子等,促進細胞碎片和錯誤折疊蛋白的吞噬和增強組織恢復和修復相關基因的表達[101-102]。小膠質細胞在PD中可通過分泌BDNF發揮其對DA神經元的保護功能,同時也可通過分泌有毒性的炎癥因子導致神經元的死亡,小膠質細胞在PD進展中根據不同的時空以何種方式發揮其作用越來越受到研究者們的關注[77]。大腦不同區域的小膠質細胞對神經炎癥刺激的反應不同,CD200是一種主要來源于神經元的抗炎蛋白,可作為抑制中腦小膠質細胞激活的局部線索。研究人員利用CD200缺陷小鼠系來分析CD200在調節中腦正常神經元-小膠質細胞穩態和在α-syn過表達模型中多巴胺能變性中的表型作用。在SNc注射rAAV-hSYN誘導的PD小鼠模型中,CD200-/-小鼠在SNc中比野生型小鼠表現出更多的多巴胺神經元損失。CD200融合蛋白激活CD200受體可減輕PD小鼠SNc的神經炎癥和神經元死亡。這些發現表明,CD200對中腦穩態至關重要,并在控制與PD發病機制相關的小膠質細胞特性方面起著關鍵的局部調節作用[103]。
Smad3信號通路已被證明是小膠質細胞發育和穩態所必需的,并在調節小膠質細胞活性中發揮關鍵作用[104]。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Smad3通路通過抑制小膠質細胞激活和促炎/免疫反應參與TGF-β1在腦內的抗炎特性[105]。有研究利用SIS3(Smad3的特異性抑制劑,鼻內注射,每側4 μg)和/或LPS(腹腔注射,1 mg/kg)對大鼠進行治療,結果顯示與對照大鼠相比,SIS3和LPS誘導大鼠有明顯的行為缺陷和黑質紋狀體多巴胺能神經退行性病變。SIS3和LPS均可誘導大鼠SNc中小膠質細胞的明顯激活和促炎因子(IL-1β,IL-6,iNOS和ROS)水平的升高[106]。通過對Smad3信號通路的調控可能對小膠質細胞發揮對PD的保護作用具有一定的意義。雖然調節PD中關于小膠質細胞極化的分子機制目前正在研究中,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知。
7 小膠質細胞促進帕金森病的發展
在PD的早期階段,小膠質細胞的促炎表型和抗炎表型共存,而在疾病進展的晚期,這種平衡慢慢偏向于促炎小膠質細胞的表型[77]。關于人的研究報告了在PD病人腦積液和血清中促炎因子和抑炎因子同時升高,這表明了在大腦中促炎型和抑炎型小膠質細胞可能共存,而小膠質細胞復雜的表型變化可能會促進PD病程的進展[107]。促炎小膠質細胞產生炎癥因子和趨化因子,如TNF-α、白細胞介素IL-6、IL-1β、IL-12和趨化因子配體CCL2等,進一步促進PD的進展[102]。小膠質細胞來源的促炎因子已被證實可誘導DA神經元丟失,進而誘導炎性細胞向病變部位聚集,加重PD多巴胺能神經退行性病變[108]。這些小膠質細胞位于少數剩余的黑質DA神經元附近,表現出活化和吞噬細胞的特征形態,并且顯示出人類白細胞抗原免疫反應性增加,一些小膠質細胞含有明顯的吞噬神經黑色素(黑質DA神經元的特征色素)的證據[79]。α-syn可由神經元分泌,并被鄰近細胞,特別是小膠質細胞和星形膠質細胞吞噬和降解,這有助于調節大腦中的α-syn的穩態[109]。在主要的腦細胞類型中,小膠質細胞在腦實質中對α-syn聚集物的降解率最高[110]。早期腦組織研究表明,SNc中的小膠質細胞上調,人類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II類(MHC-II)分子表達升高,而在人類血清和腦脊液中,檢測到IL-1β、IL-6、TNF-α、IL-2、IL-18和IL-10等細胞因子濃度升高[11,111]。上述可見小膠質細胞在PD的進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促進作用,未來的研究關鍵在于如何在PD疾病的早期及早干預和最大程度讓小膠質細胞發揮其有益的一面。
8 小 結
盡管目前對于探索PD發病機制和尋找最佳治療方法的研究正在廣泛開展,但是現有的治療手段均不能阻止PD的疾病進程,且在疾病晚期難免帶來一些副作用。當下關鍵的問題是,我們的研究不能僅局限于多巴胺能神經元的替代治療,著眼于其他非靶向多巴胺神經元的機制的研究已迫在眉睫。此外,雖然現有的各種動物模型對于PD的研究起著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仍缺乏接近PD病人生理上最真實的模型。小膠質細胞作為大腦中的常駐免疫細胞,對于大腦的先天免疫監視及維持中樞神經系統的穩態發揮重要的作用[44],關于小膠質細胞在各類神經退行性疾病中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作用細節,目前的研究尚不能完全闡釋清楚。小膠質細胞在生命的不同階段、中樞神經系統的不同區域、物種、性別和健康或疾病作出反應,展現出不同的狀態和執行不同的功能[53]。同樣,小膠質細胞是否僅作為促進疾病的角色參與PD也不清楚,在病理情況下,外周免疫細胞可能穿過血腦屏障參與PD的進展。對PD患者的腦組織、血清和腦脊液中的細胞因子進行評估,可能對小膠質細胞的致病因素提供線索[77]。靶向小膠質細胞活性以降低其神經毒性,同時保留其有益的神經保護作用,可能是開發有效治療方法干預PD甚至其他相關神經退行性疾病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