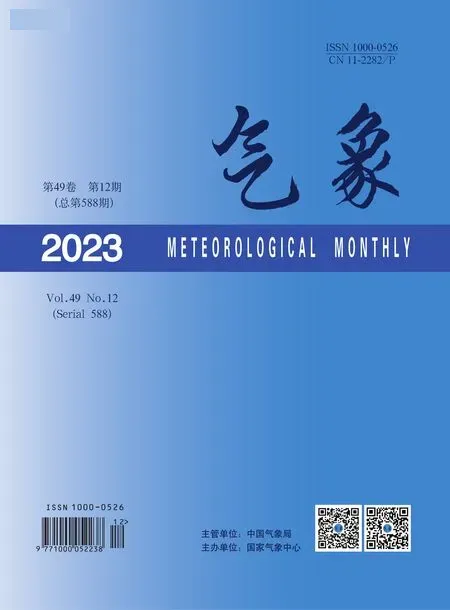“23·7”華北特大暴雨過程的水汽特征*
張芳華 楊舒楠 胡 藝 宮 宇 秦華鋒
1 國家氣象中心,北京 100081 2 中國氣象局水文氣象重點開放實驗室,北京 100081
提 要: 基于常規地面和探空觀測以及ERA5再分析資料,分析了2023年7月29日至8月1日華北特大暴雨過程(簡稱“23·7”過程)的水汽輸送、收支及其極端性等特征,探討了太行山地形對持續性水汽輻合與垂直輸送的重要作用。結果表明:此次過程發生在臺風杜蘇芮殘渦北上,受高壓壩阻擋,并有雙臺風(杜蘇芮、卡努)水汽輸送的有利背景下,降水時間超長、日降水量和累計降水量極大,在華北地區均有顯著極端性。低層強盛的東南急流源源不斷向華北地區輸送水汽,暴雨區南邊界和東邊界均為水汽凈流入,尤以南邊界為主。偏東風在太行山東麓地形高度梯度區強迫抬升,形成強的水汽輻合與垂直輸送中心,并穩定維持,是造成此次特大暴雨的重要原因。持續的水汽輸送與輻合使得整層可降水量最大值超過75 mm,距平超過氣候平均3個標準差,具有較強的極端性。對比“23·7”過程與2016年7月19—20日華北特大暴雨過程的水汽特征發現,二者低層水汽來源不同,前者主要來自西北太平洋和我國南海,后者則主要來自我國南海和孟加拉灣;前者區域平均水汽輻合強度明顯弱于后者,單位時間內較強的短時強降水站次亦少于后者,但影響時間長于后者,說明相較于雨強而言,超長的降水時間是產生“23·7”極端強降水更為關鍵的因素。
引 言
我國地處東亞季風區,降水具有顯著的季節性變化特征,是世界上暴雨洪澇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暴雨的研究很早就得到氣象工作者的高度重視。20世紀80年代,《中國之暴雨》的出版標志著我國暴雨系統性研究的開始。21世紀以來,丁一匯(2019)、壽紹文(2019)、趙玉春(2014)、羅亞麗等(2020)和高守亭等(2018)在暴雨新規律特征、新形成機理、新預報技術等領域均取得多項創新性成果。在全球增暖背景下,我國暴雨發生頻次和強度都明顯增多增強(Gong and Wang,2000;Zhao et al,2010;Huang et al,2021),2004—2015年期間我國每年因暴雨洪澇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一千億元人民幣,受災人口上億,年均死亡人數逾千(鄭國光等,2019)。因此,暴雨洪澇災害的預報和防御始終是我國防災減災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受東亞夏季風階段性季節北推的影響,每年的7—8月是華北主汛期,這其中又以傳統的“七下八上”(七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更為集中(陶詩言,1980)。地理位置和地形分布的特殊性,使得華北暴雨的環流形勢和影響系統很有特色,其中北上臺風就是其關鍵影響系統之一,例如著名的“75·8”暴雨和“96·8”暴雨。研究發現,“75·8”暴雨是由7503號臺風深入內陸停滯少動造成的,臺風渦旋與熱帶輻合帶相連,輻合區北側一直存在一支強偏東氣流,成為向臺風長期輸送水汽的通道(丁一匯等,1978;丁一匯,2015;陶詩言,1980);“96·8”暴雨則是由9608號臺風低壓與副熱帶高壓之間形成的強偏南風低空急流將低緯度地區高溫高濕空氣源源不斷地向華北輸送,并與近地面層弱冷空氣相互作用造成的(江吉喜和項續康,1997;連志鸞等,1999;徐國強和張迎新,1999;邊清河等,2006)。周璇等(2020)進一步由華北56次持續性極端暴雨過程歸納發現,減弱的登陸熱帶氣旋與西風帶系統相互作用造成的極端暴雨事件由經向型環流主導,易造成更充沛的水汽輸送、更強的上升運動和更深厚的大氣不穩定層結狀態。
除了北上深入內陸的臺風外,還有一些因臺風遠距離水汽輸送而產生的華北特大暴雨個例。孫建華等(2005)研究表明,臺風遠距離作用型暴雨約占華北暴雨個例的32.2%,這類暴雨主要由臺風東側東南低空急流提供水汽輸送。如在北京“7·21”暴雨和鄭州“7·20”暴雨過程中,臺風韋森特和臺風煙花、查帕卡遠距離水汽輸送分別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廖曉農等,2013;孫建華等2013;徐洪雄等,2014;冉令坤等,2021;汪小康等,2022;李超等,2022;徐珺等,2022;Xu et al,2022)。這一方面表明臺風對華北暴雨水汽輸送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暴雨水汽來源和輸送特征的多樣化。因此,通過對典型暴雨事件的水汽輸送特征對比,可更全面了解不同暴雨過程發生發展的異同點。如陸婷婷和崔曉鵬(2022)對比研究了北京2012年“7·21”和2016年“7·20”特大暴雨過程中的水汽輸送差異,指出前者來自中國中東部及沿海地區的水汽貢獻最突出,而后者來自印度半島—孟加拉灣—中南半島、中國南海—西北太平洋—日本海等區域的水汽也有較大貢獻。
2023年7月29日至8月1日,臺風杜蘇芮減弱后的低壓北上,在華北地區停滯,造成歷史罕見的持續性特大暴雨過程(簡稱“23·7”過程),導致嚴重的山洪、泥石流、山體滑坡和城市內澇等次生災害,海河流域出現“96·8”以來的首次流域性大洪水,永定河等6條河流發生有實測記錄以來最大洪水,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巨大損失和社會影響。基于此次過程發生在臺風北上以及雙臺風水汽輸送的特殊背景下,本文將重點分析其水汽特征,并與2016年7月19—20日華北特大暴雨過程(簡稱“16·7”過程)進行對比,以期從多角度認識華北持續性極端強降水的水汽特征,為預報預警提供有益參考。
本文采用的資料包括國家氣象信息中心提供的地面國家氣象站和自動氣象站1 h降水量資料及常規探空觀測資料,歐洲中期數值預報中心發布的ERA5再分析資料(時間分辨率為1 h、空間分辨率為0.25°×0.25°),以及NCEP全球數據同化系統(GDAS)分析數據(空間分辨率為1°×1°,用于水汽質點后向軌跡追蹤)。
1 強降水過程特點
2023年7月29日08時至8月2日08時(北京時,下同),河南北部、山東中西部、河北南部和中部、山西東部、北京、天津等地出現持續性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北京西部、河北中部和西南部等地還出現特大暴雨(符嬌蘭等,2023;楊曉亮等,2023),日降水量達250~500 mm,有19個國家氣象觀測站日降水量突破歷史極值,大部分出現在7月30日08時至31日08時。基于國家氣象信息中心提供的資料統計(圖1a),京津冀大部地區過程累計降水量在100~250 mm,其中,北京西部、河北中部和西南部等太行山東麓地區累計超過500 mm(圖1b),最大出現在河北邢臺臨城梁家莊,達1003.4 mm,有26個國家氣象觀測站7月29日08時至8月1日08時的3 d累計降水量突破歷史極值,單站累計降水量超過“63·8”過程(2051 mm)之后的其他華北極端強降水過程(章淹,1990;江吉喜和項續康,1997;諶蕓等,2012;符嬌蘭等,2017)。

圖1 2023年7月29日08時至8月2日08時(a)累計降水量分布(單位:mm),(b)累計降水量超過500 mm的站點分布(散點)與地形高度(填色)Fig.1 (a)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over 50 mm (unit: mm), and (b) stations with accumulated precipitation over 500 mm (dot) and the terrain height (colored) from 08:00 BT 29 July to 08:00 BT 2 August 2023
相比于過程累計降水量,小時雨強的極端性并不是非常突出。過程中大部地區最大雨強一般為20~50 mm·h-1,北京西部和南部、河北中部等地個別站點超過80 mm·h-1,局地達100 mm·h-1以上,主要出現在7月31日,且國家站中僅有1個站雨強超過歷史極值。從降水持續時間來看,整個過程影響4 d,也超過“63·8”過程之后的其他華北極端強降水過程。京津冀地區降水時間一般在40~80 h,平均每天有一半以上的時間有降水,北京西部、河北中部和西南部等地降水時間達80 h以上(楊舒楠等,2023)。北京地區平均降水時間長達83 h,僅次于“63·8”過程的144 h。因此,降水持續時間也具有顯著的極端性。強降水主要集中在7月29日夜間至31日白天,其中,29日夜間至30日夜間為“杜蘇芮”殘渦東側螺旋雨帶影響階段,影響范圍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累計降水量最大,約占過程總降水量的一半以上;31日凌晨至白天為切變線影響階段,影響范圍集中在河北中北部、北京和天津北部。
2 環流形勢
此次過程發生在2023年第5號臺風杜蘇芮減弱后的殘渦北上,受華北高壓阻擋移動停滯,并與第6號臺風卡努共同持續輸送水汽的環流背景下。
過程開始時(圖2a),500 hPa位勢高度場為“兩槽一脊”穩定環流型,其高壓脊位于蒙古國中部至我國西北地區東部,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以下簡稱副高)呈塊狀分布,西界位于我國東北地區南部至華東沿海。“杜蘇芮”減弱后的低壓中心位于副高西側,二者之間對流層低層在我國華東地區形成強盛的偏南至東南急流,850 hPa風速達24 m·s-1以上。此時 “卡努”位于副高南側的菲律賓以東洋面,其北側偏東氣流匯入“杜蘇芮”以東的東南急流中,共同為強降水提供水汽和能量供應。29日夜間開始,副高西伸與大陸高壓脊打通,在華北北部形成西北—東南向的高壓壩并發展加強,500 hPa位勢高度偏離氣候態超過2~3個標準差(圖略),為臺風殘渦持續影響華北提供了有利的背景條件,這也是華北特大暴雨的典型環流形勢(章淹,1990)。此次過程沒有中緯度低槽與臺風殘渦的相互作用,這是區別于“75·8”等著名北上臺風強降水過程的顯著特點。

注:紅、藍色圓點分別為臺風杜蘇芮、卡努的中心位置。圖2 2023年7月(a)29日08時,(b)30日08時,(c)31日08時500 hPa位勢高度場(等值線,單位:dagpm)和850 hPa風場(風羽,填色:≥12 m·s-1);(d)29日20時200 hPa位勢高度場(等值線,單位:dagpm)和風場(風羽,填色:≥30 m·s-1)Fig.2 Geopotential height at 500 hPa (contour, unit: dagpm), wind field at 850 hPa (barb,only speeds over 12 m·s-1 colored) at (a) 08:00 BT 29, (b) 08:00 BT 30, (c) 08:00 BT 31, and (d) geopotential height (contour, unit: dagpm), wind field(barb, only speeds over 30 m·s-1 colored) at 200 hPa at 20:00 BT 29 July 2023
對流層低層低壓中心北上過程中(圖2b),在河南、山西與河北三省交界處發展加強并維持12 h以上,低壓倒槽沿著低空和超低空急流方向呈逆時針旋轉,自東南向西北影響京津冀大部地區,此為京津冀降水最強的階段。31日早晨開始(圖2c),副高西界逐漸西伸,低壓及倒槽減弱西移,但“卡努”逐漸向我國華東沿海靠近且強度加強,為華北地區持續提供水汽輸送,北京、天津及河北中部受東南急流和切變線影響,出現第二階段的強降水。
在整個過程中,對流層高層200 hPa(圖2d)在西北地區東部維持經向度較大的低槽,華北地區受槽前高壓脊控制。從風場演變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高空西風急流核穩定位于內蒙古中東部至東北地區,京津冀地區位于200 hPa高空槽前以及高空急流入口區右側的強輻散區,具備了產生區域性持續強降水的穩定而強大的高空輻散條件。
3 水汽特征
3.1 雙臺風水汽輸送
此次過程發生在雙臺風杜蘇芮、卡努水汽輸送的有利背景下。925 hPa風場和水汽通量演變(圖3)表明,29日上午(圖2a,圖3a),“杜蘇芮”減弱后的低壓中心位于湖北東部與湖南、江西交界處,其東側與副高之間形成寬廣而強盛的超低空急流,貫穿江南東部至黃淮地區,急流核位于浙江北部至江蘇一帶,20 m·s-1以上的急流水平寬度約為300 km,南北跨度為400 km,急流核風速大于24 m·s-1。此時 “卡努”遠在菲律賓以東洋面上,其北側的偏東風在副高引導下轉向匯入副高與“杜蘇芮”之間的東南急流區。這支超低空東南急流攜帶了海洋上的大量暖濕氣流向我國東部地區輸送,江南東部至黃淮為水汽通量大值區,最大中心位于江蘇中南部,強度達40 g·cm-1·hPa-1·s-1。隨著低壓和急流北上、倒槽向東北方向延伸,華北水汽通量逐漸增大且大值區覆蓋京津冀大部地區,30 g·cm-1·hPa-1·s-1的極值中心也由河北南部(圖3b)逐漸北移到河北中部至京津地區(圖3c),并在太行山東麓形成強梯度區,持續性強降水即主要出現在該梯度區(圖略)。31日,低壓中心減弱填塞,超低空急流的強度和范圍顯著減弱,來自“卡努”方向的水汽輸送使得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等地的水汽通量維持在25 g·cm-1·hPa-1·s-1上下(圖3d),區域性強降水的中心也北移至此,河北西南部強降水明顯減小。
從垂直方向看,在30日20時之前,850、700、925 hPa三層的水汽通量表現出較一致的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之后,850 hPa和700 hPa偏東急流越過太行山北段向河北北部、內蒙古中部一帶擴展,水汽通量也明顯減弱,與925 hPa在山前出現水汽通量強梯度區的分布特征形成鮮明對比,表明地形對低層系統維持有明顯作用,這將在下文進一步分析。
為了更清晰地追蹤持續性強降水的水汽來源,本文選用NOAA ARL(Air Resources Laboratory)的HYSPLIT(HYbrid Single Particle Lagrangian Integrated Trajectory Model)跡線模式(Stein et al,2015)對水汽質點的后向運動軌跡進行追蹤,所用數據為1°×1°的NCEP全球數據同化系統(GDAS)分析數據。水汽質點選取水汽通量大值區(35°~40°N、116°~120°E)范圍內的水汽質點矩陣,質點間隔為1°×1°,共計30個質點,質點高為1 km。從7月29日20時至8月1日20時,每隔12 h進行一次追蹤,計算水汽質點矩陣96 h的后向運動軌跡。
計算結果顯示,29日20時(圖4a),低層強水汽輸送以東南急流為主,水汽質點通過東南或偏南路徑匯入強降水區。水汽軌跡總體呈現為偏南和偏北兩條水汽輸送帶的疊加,其中,偏南的水汽質點源自中國南海和菲律賓以東洋面,而偏北的質點則來自于15°N以北的西北太平洋洋面,該側的水汽軌跡數量約占總軌跡數的三分之二。30日,隨著“杜蘇芮”北上,進入華北地區的低空急流偏南分量增大,其水汽質點的軌跡分布特征與29日相似(圖略)。31日20時(圖4b)的水汽質點追蹤顯示,來自南海的水汽質點減少,而來自西北太平洋的水汽質點占據主導,其水汽軌跡占總軌跡數的90%,之后逐漸演變為華北強降水區唯一的水汽來源。在參與計算的7個時次共計210條水汽質點后向運動軌跡中,有167條(占比79.5%)來自于西北太平洋洋面的水汽輸送,且維持時間更久。更加定量的水汽源地貢獻及其演變特征有待于進一步分析。

注:矩形框示意質點位置(35°~40°N、116°~120°E)。圖4 2023年7月(a)29日20時,(b)31日20時HYSPLIT跡線模式計算的水汽質點矩陣的后向軌跡(計算時間96 h)Fig.4 Backward trajectory from HYSPLIT method (in last 96 hours) of water vapor particle matrix at (a) 20:00 BT 29, (b) 20:00 BT 31 July 2023
3.2 不同方向的水汽收支
為了對不同方向的水汽收支情況進行定量診斷,選取強降水區即(35°~42°N、113°~120°E)的方形區域作為水汽收支計算的邊界范圍,分別計算南、北、西、東邊界的水汽收支,圖5給出了1000~500 hPa 各邊界的水汽收支垂直積分及其時間演變。從圖中可以看出,在整個分析時段,南邊界均為水汽凈流入,北邊界反之。具體來看,7月29日至31日上午,區域總體為凈的水汽收入,主要貢獻者依次為偏南和偏東的水汽流入,這與低層環境風場為東南風一致,其中南邊界水汽收入大于區域總和,其峰值接近20×104g·cm-1·s-1,是東邊界水汽收入峰值(7×104g·cm-1·s-1)的近3倍。之后,低層環境風場減弱,并由東南風轉變為西南或偏南風,西邊界逐漸由流出變為流入,與東邊界呈反向變化,南邊界和東邊界水汽流入呈波動式下降趨勢,偏南水汽收入仍為最主要的貢獻者。

圖5 “23·7”過程(35°~42°N、113°~120°E)范圍內1000~500 hPa 各邊界水汽收支垂直積分的時間演變Fig.5 Time evolution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water vapor budget from 1000 hPa to 500 hPa at four boundaries of (35°-42° N, 113°-120°E) during the “23·7” event
進一步分析南邊界(圖6a)和東邊界(圖6b)各層水汽收支及其時間變化發現,29日白天至夜間,對流層低層偏東風或東南風持續增強,南邊界水汽凈流入由4×102g·cm-1·hPa-1·s-1快速增大至6×102g·cm-1·hPa-1·s-1,大值中心位于900 hPa附近高度,且表現出夜間增強、白天減弱的日變化特征,出現多個峰值,與低空急流的日變化規律較吻合。31日白天后,各層水汽收入在波動中減小,與區域平均降水的演變趨勢一致。與南邊界相比,東邊界水汽收支情況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各層水汽凈流入明顯小于前者,中心層次偏低、峰值出現時間偏后約24 h,最大值僅為3.5×102g·cm-1·hPa-1·s-1,且為單峰結構。在強降水集中時段,即29日20時至31日20時期間,東邊界600 hPa及以下層次為水汽凈收入,且集中出現在900 hPa及以下;31日20時之后,副高西伸,低層東南風逐漸轉為偏南至西南風,東邊界變為水汽凈流出。

圖6 “23·7”過程(a)南邊界(35°N、113°~120°E范圍內),(b)東邊界(35°~42°N、120°E范圍內)水汽收支總和(等值線,單位:102 g·cm-1·hPa-1·s-1)及平均水平風場(風羽)的高度-時間變化Fig.6 (a) Height-time variation of the total water vapor budget (contour, unit: 102 g·cm-1·hPa-1·s-1) and average horizontal wind (barb) at (a) the southern boundary (accumulation at 113°-120°E along 35°N) and (b) eastern boundary (accumulation at 35°-42°N along 120°E) during the “23·7” event
3.3 水平流場及其與地形作用導致的強烈水汽輻合
大范圍持續性強降水需要源源不斷的水汽輸送,而低層水汽輻合更是產生強降水的關鍵過程。925 hPa水汽通量散度分析表明,7月29日傍晚開始,隨著低壓倒槽和偏東急流北上,河北西南部太行山山前地區先后受倒槽前部東北氣流和倒槽的疊加作用,出現水汽通量輻合大值區,從-0.1×10-3g·cm-2·hPa-1·s-1增大至-0.6×10-3g·cm-2·hPa-1·s-1(圖7a),并穩定維持,在河北西南部產生持續性強降水。30日,東南風急流加強北推,倒槽向北京方向延伸,水汽通量輻合區也向東北方向發展,逐漸在河北西南部、河北中部至北京一帶分別形成南北兩個中心。30日傍晚之后(圖7b),南側中心略有減弱,北側中心繼續發展,并在太行山北段山前維持至31日夜間,影響時間長達40多小時,最強輻合達-0.6×10-3g·cm-2·hPa-1·s-1,造成河北中部至北京西部地區的持續強降水。

注:彩色散點為其后1小時累計降水量(≥10 mm)。圖7 2023年7月30日(a,c)00時,(b,d)18時(a,b)925 hPa風場(風羽)和水汽通量散度(等值線,≤-0.1×10-3 g·cm-2·hPa-1·s-1),(c,d)1000~500 hPa整層積分水汽通量散度(等值線,≤-1×10-2 g·cm-2·s-1)和700 hPa風場(風羽)Fig.7 (a, b) Wind (barb) and water vapor flux divergence at 925 hPa (contour, only values ≤-0.1×10-3 g·cm-2·hPa-1·s-1 shown), (c, d) integrated water vapor flux divergence from 1000 hPa to 500 hPa (contour, only values ≤-1×10-2 g·cm-2·s-1 shown) and wind (barb) at 700 hPa at (a, c) 00:00 BT 30 and (b, d) 18:00 BT 30 July 2023
水汽通量輻合中心隨高度向西傾斜,強度減弱。分別計算1000~700、1000~500、1000~300 hPa 整層積分的水汽通量散度。結果顯示(圖略),整層積分的水汽通量散度分布形態及演變特征與925 hPa基本類似,大部分時次隨著積分厚度的增加,整層水汽通量輻合強度減小,高低層差異最大的區域位于太行山地形附近。具體對比925 hPa和1000~500 hPa整層積分的水汽通量散度可見,30日00時,二者在太行山中段山前均存在水汽通量輻合區,前者(圖7a)沿地形呈南北向分布,與其后1小時降水落區分布更為一致,而后者(圖7c)則為準東西向分布;30日18時,與925 hPa(圖7b)相一致,在1000~500 hPa(圖7d)也有南北兩個輻合中心,925 hPa水汽通量輻合帶與北京西部至河北西南部一帶的強降水落區和形態基本一致,但太行山中段的輻合中心隨積分高度的增高向西推移至山西東部,偏離了最強降水中心。說明在太行山東麓低層穩定維持的水汽通量輻合中心與山前的強降水區有更密切的關系,也反映了太行山地形對強降水發展與維持的重要作用。
以29日夜間至30日上午太行山中段的強降水階段為例,進一步分析地形對水汽輻合及垂直輸送的作用。沿37.5°N的水平水汽通量散度、垂直水汽通量和垂直環流的緯向剖面(圖8)表明,29日23時(圖8a),“杜蘇芮”殘渦北側的低層偏東風在太行山東麓迎風坡受阻抬升,形成隨地形高度向西傾斜的水汽輻合中心,上升氣流也造成垂直方向的水汽輸送,通量中心位于850 hPa附近,其值達50×10-1g·cm-1·hPa-1·s-1,較2小時前(圖略)明顯增大。30日02時(圖8b),低層東風持續并在山前形成大梯度區,山前輻合抬升作用快速增強,強大的動力強迫抬升使得垂直水汽通量快速增大,并向高層擴展,強大而深厚的水汽輻合抬升非常有利于在地形附近產生強降水。30日05時(圖8c),900 hPa及以下層次的輻合系統仍維持在太行山東麓,而其上層系統已西移進入山西東部,上升運動和垂直水汽輸送都明顯向西傾斜,但強度弱于河北西南部。

圖8 2023年7月(a)29日23時,(b)30日02時,(c)30日05時的水汽通量散度(藍色等值線,≤-1×10-4 g·cm-2·hPa-1·s-1)、垂直水汽通量(紅色等值線,單位:10-1 g·cm-1·hPa-1·s-1)和垂直環流(箭矢)沿37.5°N的緯向剖面Fig.8 Height-latitudinal profile of horizontal water vapor flux divergence (blue contour, only values ≤-1×10-4 g·cm-2·hPa-1·s-1 shown), vertical water vapor flux (red contour, unit: 10-1 g·cm-1·hPa-1·s-1) and vertical circulation (vector) along 37.5°N at (a) 23:00 BT 29, (b) 02:00 BT 30 and (c) 05:00 BT 30 July 2023
由圖8也可知,114.0°~114.2°E附近是偏東風迎風坡地形高度梯度的大值區,對應37.5°N附近海拔高度約為600~800 m,與925 hPa高度相當,是低層偏東風強烈輻合,首先出現強水汽通量輻合并長時間維持的區域,此次過程累計降水量達1003.4 mm的河北邢臺臨河梁家莊站(測站海拔高度為681 m)便位于此區域。另外,113.5°~114.0°E(山西東部)是偏東風強迫抬升的次大值區,受900 hPa 以上的東北風影響也產生較強降水。
上述分析更加直觀地體現了太行山東麓地形對低層偏東風的強迫抬升,對低層輻合系統的阻擋以及對水汽的垂直輸送過程,也表明太行山地形是造成此次持續性強降水的關鍵因素。
充沛的水汽輸送和輻合導致華北地區絕對水汽含量非常高。7月29日至8月1日925 hPa 比濕一般有16~18 g·kg-1,局地達20 g·kg-1以上,高濕區影響范圍大、持續時間長。ERA5再分析資料顯示整層可降水量一般在65~75 mm,部分地區超過75 mm,距平超過氣候平均3個標準差(圖9a),利用探空觀測資料計算的整層可降水量最大值也達79.67 mm(北京氣象觀測站,31日20時)。強降水集中期,區域最大整層可降水量基本在75 mm以上,平均值也達55~62 mm(圖9b)。因此,無論觀測數據還是再分析結果,均為近年來歷次華北極端強降水過程少有的高值(諶蕓等,2012;孫軍等,2012;符嬌蘭等,2017),具有較強的極端性。

圖9 “23·7”過程(a)7月30日20時大氣整層可降水量(等值線,單位:mm)及其標準化異常值(填色),(b)(35°~42°N、113°~120°E)區域最大(紅線)和平均(藍線)大氣整層可降水量的時間演變Fig.9 (a) Integrated total precipitable water (contour, unit: mm) and normalized value (colored) at 20:00 BT 30 July, and (b) time evolution of maximum (red) and average (blue) amounts of the integrated total precipitable water at (35°-42°N,113°-120°E) of the “23·7” event
低層持續的暖濕輸送也使得華北地區維持一定的不穩定能量。29日20時北京和邢臺的探空分析(圖略)表明,對流層中低層存在一定的條件不穩定層結,對流有效位能(CAPE)分別達1151.2 J·kg-1和936.6 J·kg-1。受“杜蘇芮”低壓倒槽、低空急流及太行山東麓地形等的影響,低層產生強烈的垂直上升運動,有利于不穩定能量釋放,觸發對流性強降水。
4 與“16·7”過程的水汽特征對比
2016年7月19—20日,受深厚的低渦系統(地面為黃淮氣旋)影響,華北地區出現區域性極端強降水天氣,簡稱“16·7”過程。華北大部過程累計降水量為100~250 mm,其中河北西南部、北京西部和南部等地有250~400 mm,河北西南部局地超過600 mm;山西中部、河北西部、北京中西部降水持續時間在36~48 h,局地超過48 h(符嬌蘭等,2017),累計降水量和降水持續時間均不及“23·7”過程。兩次過程的共同點是:低層均有低渦系統影響,太行山地形對降水的增幅作用顯著。但兩次過程的影響系統亦有明顯差異,主要區別在于“23·7”過程的低渦源自北上臺風殘余環流,伴有雙臺風水汽輸送,但無明顯西風槽參與,而“16·7”過程是由中緯度斜壓系統的低渦和地面氣旋強烈發展所導致的。因此,二者在動力、水汽和不穩定機制等方面均表現出一定差異,本文著重對比分析它們的水汽條件。
“16·7”過程的強降水可分為兩個階段(圖略),分別是7月19日白天低渦北側偏東氣流在太行山中段山前輻合抬升產生的強降水,以及20日凌晨開始,低渦北上造成的大范圍系統性強降水。分析這兩個階段的水汽輸送特征可知,7月19日(圖10a),低層水汽由來自孟加拉灣和我國南海的西南急流一路向北輸送至華北南部,水汽輸送帶上925 hPa風速達18 m·s-1,水汽通量大值中心位于華中地區,其中心達30 g·cm-1·hPa-1·s-1。20日凌晨開始,隨著低渦北上并強烈發展,低渦中心東北側的東南急流顯著加強并逐漸成為主要的水汽輸送通道,925 hPa 風速增至30 m·s-1,明顯大于“23·7”過程,華北地區水汽通量也逐漸增至50 g·cm-1·hPa-1·s-1(圖 10b)。第二階段東南風水汽輸送顯著增強,但西南水汽匯入仍非常明顯,且從流場和水汽質點96 h后向軌跡追蹤(圖略)均可發現,低層水汽來源主要是西南至偏南方向,即我國南海海域及孟加拉灣,這與陸婷婷和崔曉鵬(2022)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圖10 2016年7月(a)19日08時,(b)20日12時925 hPa風場(風羽)和水汽通量(填色,≥10 g·cm-1·hPa-1·s-1)Fig.10 Wind (barb) and water vapor flux (colored, only values ≥10 g·cm-1·hPa-1·s-1 shown) at 925 hPa at (a) 08:00 BT 19 and (b) 12:00 BT 20 July 2016
由此可見,“16·7”和“23·7”兩次過程低層均存在西南和東南兩支水汽通道,“16·7”過程的主要水汽通道為來自我國南海和孟加拉灣的西南急流,而“23·7”過程則是來自西北太平洋及我國南海轉向的東南氣流(圖3和圖4),反映了“杜蘇芮”“卡努”及其生成之前熱帶擾動的水汽輸送作用。
進一步對比(圖11)發現,兩次過程的低層主導風向均為東南風,且一直維持高濕狀態,“23·7”過程(圖11a)900 hPa以下平均比濕達16~18 g·kg-1,而“16·7”過程(圖11b)略小,為14~16 g·kg-1,但風速更大,水汽通量更強。二者水汽通量強輻合區均集中在900 hPa及以下層次,超低空急流造成的強水汽輻合以及高濕的環境有利于降低抬升凝結高度,產生低質心、高效率的短時強降水,降水強度的增大與水汽通量輻合增強有一定的關系。“16·7”過程水平風隨高度順轉更加清晰,表明有比較深厚的暖平流,有利于產生強烈的系統性上升運動,水汽通量散度輻合的層次也更高、平均輻合強度明顯強于“23·7”過程,加之存在高空干冷空氣侵入,有更強的不穩定層結和CAPE值(圖略),單位時間內“23·7”過程(圖11c)出現30 mm·h-1以上和50 mm·h-1以上短時強降水的站次比“16·7”過程(圖11d)明顯偏少,但影響時間長。這與上文對“23·7”過程小時雨強極端性不是很突出的分析結論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超長的降水時間是導致“23·7”過程累計降水量極端性顯著的主要因素。

圖11 (35°~42°N、113°~120°E)區域平均(a,b)水汽通量散度(填色,≤-0.5×10-5 g·cm-2·hPa-1·s-1)、水平風矢、比濕(等值線,單位:g·kg-1)的時間演變,(c,d)不同等級小時雨強站次的時間演變(a,c)“23·7”過程,(b,d)“16·7”過程Fig.11 (a, b) Height-time cross-section of water vapor flux divergence (only values ≤-0.5×10-5 g·cm-2·hPa-1·s-1 colored), horizontal wind (vector), specific humidity (contour, unit: g·kg-1) averaged at (35°-42°N, 113°-120°E), (c, d) evolution of the station numbers with different hourly rain intensities (a, c) the “23·7” event, (b, d) the “16·7” event
5 結論與討論
2023年7月29日至8月1日,華北地區出現了“63·8”以來最強的特大暴雨過程,造成了嚴重的災害影響。本文基于常規地面和探空觀測以及ERA5再分析資料等,分析了其降水和環流的基本特征,重點分析了產生特大暴雨的水汽條件,探討了太行山地形對持續性水汽輻合與垂直輸送的作用,并與“16·7”過程的水汽特征進行初步對比。得到結論如下。
(1)“23·7”過程發生在臺風杜蘇芮殘渦北上,受強大的高壓阻擋而在華北南部停滯,并有雙臺風杜蘇芮、卡努持續水汽輸送的天氣背景下,高層輻散穩定維持,是一種非常典型的華北特大暴雨環流形勢。本次過程降水時間超長、日降水量和累計降水量極大,在華北地區均有顯著極端性。
(2)“23·7”過程低層有西南和東南兩條水汽輸送通道,南邊界一直為水汽凈收入,且大于整個區域凈收入。提前96 h水汽質點后向軌跡追蹤表明,低層水汽來源主要為西北太平洋和中國南海,其中以前者占據主導,反映了臺風杜蘇芮、卡努及其生成之前熱帶擾動的水汽輸送作用。
(3)太行山東麓地形對低層偏東風的強迫抬升,使得山前出現水汽通量梯度區以及強水汽通量的水平輻合與垂直輸送中心,并對低層特別是925 hPa及以下層次輻合系統的移動起到阻擋作用,使得山前輻合抬升增強且影響時間長達40 h以上,是造成此次持續性極端強降水的關鍵因素,最強降水主要出現在地形高度梯度的大值區。
(4)充沛而持續的水汽輸送與輻合使得華北地區水汽含量相當高,925 hPa比濕普遍達16~18 g·kg-1,整層可降水量高達75 mm以上,對應距平超過氣候平均3個標準差,具有較強的極端性;同時維持一定的不穩定能量,配合低層強烈的上升運動,有利于觸發對流性降水。
(5)“23·7”過程與“16·7”過程的水汽特征對比表明,二者低層水汽來源不同,前者主要來自西北太平洋和我國南海,后者則主要來自我國南海及孟加拉灣;“23·7”過程區域平均水汽輻合強度明顯弱于后者,垂直伸展層次較低,單位時間內較強短時強降水站次偏少,但影響時間長于后者。這些差異與二者主要影響系統的特點密切相關,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相較于雨強而言,超長的降水時間是導致“23·7”過程累計降水量極端性顯著的更為關鍵的因素。
本文僅對“23·7”過程的水汽特征進行了初步分析,下一步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華北不同類型極端強降水過程的水汽輸送、動力抬升、能量維持以及太行山精細地形作用等的共性和差異,細致分析不同高度、不同階段的水汽來源及其定量貢獻,研究持續暖濕輸送和強降水背景下的大氣能量轉換和維持機制等。這些對于加深華北區域性極端強降水的機理認識有很重要的意義,也可為預報預警業務提供有益參考。
致謝:感謝國家氣象信息中心曹麗娟、谷軍霞,北京市氣象臺張迎新、趙瑋等專家在觀測資料、歷史數據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