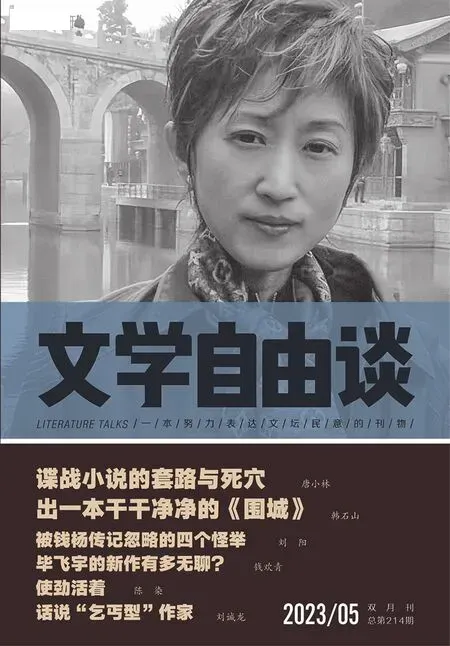“馮書輝抄襲”事件的下半場
□朱孝兵
禍起“茶葉門”
今年過半,“馮書輝抄襲”應該可以預訂“2023中國詩壇最具影響力事件”的席位了。
此次抄襲事件,主要由網絡自媒體起底揭露,相關文學期刊隨后陸續(xù)發(fā)布“嚴正聲明”,再由“澎湃新聞”報道,繼而廣為人知(這里的“廣”,乃是限于文壇而言)。直到有稱馮為“親愛的丈夫”者發(fā)出馮已“與世長辭”的消息,熱度才開始逐漸消退——盡管此消息的真實性備受質疑。
復盤整個事件,無論是“瓜眾”津津樂道的“茶葉門”(據(jù)稱,馮書輝能大量發(fā)表作品,原因在于他給各大刊物的編輯部寄茶葉),還是幾道“嚴正聲明”本身,以及馮本人自始至終不承認抄襲的態(tài)度,都暴露出詩壇乃至文壇光怪陸離的亂象。其所透露的問題,雖不至于“燒腦”,卻也值得琢磨。
馮書輝抄襲性質的認定,一點也不復雜,所以除了他本人的矢口否認,并無多少爭議。他抄襲的方式非常低級,主要是套改別人的作品,整句整節(jié)地照搬照抄,可謂率意而為、簡單粗暴——對照原作看一眼,但凡專業(yè)的文學從業(yè)人員,便知那是抄襲。但是,“涉事期刊”的“聲明”中,竟都稱該“抄襲行為”先由他者(“熱心讀者”以及“讀一首好詩”和“阿獨在寫詩”兩個微信公眾號)“反映”,然后雜志社編輯部才認定的——好像沒人“反映”的話,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不知道。
按正常邏輯,抄襲之作發(fā)表的時候,雜志的編輯、主編應該是被蒙在鼓里的。那么,問題來了:如此拙劣的抄襲行徑,是如何逃過那么多純文學期刊的編輯乃至主編的法眼的?
“聲明”的時間差或有玄機?
你可能會說,全國有那么多文學期刊,一個編輯肯定無暇通讀,更不可能一一查證,所以出現(xiàn)漏網之魚在所難免。但問題是,如果只有一家文學刊物“中招”,是個案,那么這樣的理由還講得通;但實際情況是,涉及刊物不止一家,而且,兩撥“聲明”的發(fā)布存在著“時間差”,其中仿佛暗藏玄機。
第一撥發(fā)布“嚴正聲明”的,是《西湖》和《作品》:《西湖》的聲明是2023年4月24日發(fā)布(馮的詩歌刊于2023年1月的第1期),《作品》是4月25日。第二撥分別是《文學港》《雨花》和《北京文學》,時間都在7月1日前后;其中,馮書輝的抄襲之作,《文學港》是第7期(可算當期)發(fā)表,《雨花》是第4期,《北京文學》則是第5期。順便說一句,這幾種雜志都是月刊,其期號與出刊的月份相同。
這么說,有人可能會覺得,這第二撥“團隊”是不知前車之鑒。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我們看,相關抄襲之作在《雨花》發(fā)表,是4月份,即在第一撥“聲明”發(fā)布時已經發(fā)表;《北京文學》是5月份,即便當時知道了馮有抄襲“前科”,可能也已來不及撤換稿子——一般雜志多在本月下旬就已出下一期的大樣,甚至都已下廠付印了。《文學港》則可謂得到了“最痛”的“領悟”:6月30日發(fā)布聲明時,眼見其第7期雜志的發(fā)行都是現(xiàn)在完成時,或現(xiàn)在進行時,最不濟,也是箭在弦上了。這次第,簡直比一頓飯的最后一口吃出一個蒼蠅還悲催。所以,所謂“傷之深,行之切”,其“聲明”也是第二撥中唯一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的,即,在同行刊物之間“建立抄襲者名單”,并“永不錄用”其作品。至于其他兩家,聲明中都沒寫出具體可行的辦法,只說“要加強與同行刊物的交流溝通”云云。
然而,當讀到《作品》“聲明”之末尾,我就感覺自己為他們想得太多了——“為震懾抄襲者,我刊將加強與同行刊物的溝通聯(lián)系,建立相應的名單,互通消息,共同維護尊重原創(chuàng)禁絕抄襲的文學生態(tài)。”要知道,《作品》的“聲明”是4月25日發(fā)布的。那么,其他雜志過了那么久才發(fā)出“聲明”,是因為《作品》那邊沒有將“黑名單”與同行“共享”嗎?如果確實做到了“互通消息”的話,為什么《雨花》和《北京文學》的“聲明”那么晚才發(fā)布?為什么《文學港》前腳發(fā)布“聲明”,后腳還要發(fā)行“問題雜志”?如果當時馮就上了業(yè)內“黑名單”的話,不用別人反映,這些雜志的編輯們上網輸入幾個關鍵詞搜一搜,就能發(fā)現(xiàn)其抄襲問題;即便被抄襲的作品沒上網,也可根據(jù)相關作品的題目(馮的有些抄襲作品,題目都跟原作類似甚或同樣),自行查重。而各雜志的“聲明”稱發(fā)現(xiàn)抄襲之作的途徑,竟然都來自讀者反映,這是否可證明,一些文學雜志的編輯已經不看同行雜志刊發(fā)的作品了?
退一步說,現(xiàn)在不要說詩歌圈子,就是整個文學圈子,都算不上大。老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如今移動互聯(lián)時代,則是“壞事秒傳天下知”。插點題外話——有人會說這是一種看客心態(tài),體現(xiàn)了魯迅所說的國民劣根性,得批判。我認為,有些人太習慣拿魯迅說事了。此非國民的劣根性,而是人性中的“劣根性”使然——許多行業(yè)、領域都是鐵板一塊、密不透風,你再不允許草根屁民對狗茍蠅營之輩有點幸災樂禍的心理,那也太不人道了。前不久,刀郎《羅剎海市》的爆紅,就說明了這一點。
當然,有的圈子里出圈的新聞有壞事,也有好事;但是,有的圈子,基本是死水微瀾,有一點小風浪,也彌漫著酸臭味兒。在這樣的時代,作為一個詩歌編輯或主編,你有手機吧?手機能上網吧?只要能上網,估計系統(tǒng)都會根據(jù)你的職業(yè)類型、瀏覽習慣,給你推送“讀一首好詩”或“阿獨在寫詩”的微信公眾號文章。這些公號中,關于馮抄襲的那些“爆款”文章,在《西湖》《作品》發(fā)“聲明”那會兒就有,馮的大名可一直都在呀!而且,6月9日,“讀一首好詩”公號又發(fā)了一篇關于馮抄襲的文章,又有兩家刊物“踩雷”,但至今未回應……如此這般的“大事件”,第二撥團隊中的相關編輯、主編不會不知道吧?知道了后,卻無動于衷,莫非仍心存僥幸?
再仔細查看這幾道“聲明”的發(fā)布時間及其內容,就感覺更有意思:都是前一天相關微信公號曝光抄襲事件,第二天相關雜志發(fā)布“嚴正聲明”;而且,“聲明”中將此時間寫了進去,給人一種處理特別及時的感覺。然而,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難免會設想:這幾道“聲明”,其實是被那兩個微信公號給逼出來的。
還有,這些“聲明”都是在網絡上發(fā)布的,我還沒看到有一家雜志在其紙質刊物上白紙黑字地印著——這里面有幾個意思?
從目前的信息分析,第二撥團隊中有些成員,可能早就知道自己“踩雷”了,至于這雷什么時候“爆”,就等人家公號那“第二只靴子”落地。話說回來,如同老師在課堂上批評曠課的學生一樣,這些發(fā)布“聲明”的還都算“好學生”,盡管有個別的遲到了——不是還有好多家被網友點名的刊物,發(fā)了馮的抄襲之作卻至今仍在裝聾作啞嗎?
這幾份“嚴正聲明”,還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被抄襲者總共有七八位詩人(只有兩家的“聲明”寫出了被抄襲者的名字,共四人),但舉報者都不是原作者本人。——或許,有的原作者可能現(xiàn)在都還不知道這個事兒呢。
這說明了什么?綜合以上推斷,我大膽猜測如下:如今,純文學刊物發(fā)表的詩歌,除了作者和責編,基本沒人看了。這幾種雜志“涉事”的那一期,都沒刊發(fā)原作者的作品,他們自然不會去看。這跟某些學院派的學術文章、某些系統(tǒng)評職稱所需的論文的境遇,已經毫無二致。文學刊物淪落到這種地步,已是積重難返。至于“茶葉門”之類,更是虱子多了不嫌咬,不管真假,都如九牛一毛,沒什么追究的必要了。
如此看來,這類抄襲之事,對某些文學刊物來說,實際上已經成了“民不舉,官不究”的存在。只因為那些起底文章的影響力太強了,動輒幾萬、十幾萬的瀏覽量,雜志這邊再裝深沉玩高冷,就是掩耳盜鈴、自取其辱了。
文中提到的那兩個公號,其內容基本都是舉報詩歌抄襲和披露詩壇亂象的,點擊量都不低。所以,別怪圈里圈外的人就愛八卦詩壇的“臟亂差”,現(xiàn)在的詩壇,真的是遠看金碧輝煌,細觀一片荒涼。
為什么要抄襲?
此次抄襲事件,還有一點耐人尋味:馮書輝為什么要抄襲?
有人說是為了稿費。這就既高看了稿費,也看低了馮書輝。詩歌稿費一般是按行算。我咨詢過寫詩的朋友,都說現(xiàn)在文學雜志的詩歌稿費很低,三四十行的組詩,也就三四百元;組詩稿費能拿到上千元的,應該都算名家或“關系戶”了。而馮書輝在名刊中,也就算一般作者,一個月能發(fā)表三兩首詩,頂天了吧?作為茶商和工程師的他,幾百元的稿費收入,值得他為此汲汲營營?
在此,本人要給那些想靠稿費養(yǎng)活自己的年輕人,順便潑一盆冷水——網絡文學、影視編劇類的圈子,我了解不多,但聽說也是一猛子扎下去后上不來的居多;今天咱們只說純文學領域。當下,純文學領域,絕大多數(shù)作家單靠稿費收入,是養(yǎng)不活自己的。我們看到的那些茅獎、魯獎獲得者,那些作協(xié)主席、副主席們,大都有文化宣傳系統(tǒng)內的編制,用以前的話說,叫“文化干部”,是“吃國庫糧的”。如果單靠稿費收入,沒有編制內的收入,估計有些人真得喝西北風。
不說別的,單說作家出書這一塊——你有沒有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文學類書籍,版權頁上還有“印數(shù)”這一項嗎?我看了一下最近幾年買的這類書,標明“印數(shù)”的也就這么幾本: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2020年3月第61次印刷,印數(shù):1947001—2 147000;遲子建的《白雪烏鴉》《額爾古納河右岸》《偽滿洲國》《煙火漫卷》,最低的印數(shù)是1萬冊;梁曉聲的《人世間》,我買的版本是從11萬冊加印至13萬冊,印了兩萬冊。而像曾經的茅獎作品,如有些版本的《北上》《主角》《長恨歌》《白鹿原》,都沒寫明印數(shù),盡管有的從其版次、印次看,是加印了幾次,但就是不提印數(shù)。問做出版的朋友,說,就是印數(shù)太少了,不好意思寫上;而能寫上的,一般是1萬起印;也就是說,一部純文學小說,能起印1萬,就算暢銷書了!那么,這1萬冊書,作者能拿多少報酬呢?假設作者拿的是版稅,按10%版稅率,定價50元、印數(shù)1萬的書,作者繳納所得稅后,實際得到的,還不到5萬元!一部長篇小說,從開寫到成書,怎么也得一兩年吧?這一兩年里,版稅加上雜志稿費(通常會先發(fā)在雜志、后出單行本),可能也不到10萬塊錢——這還得是有點名氣的作家,更多的寫作者,每個月的稿費收入甚至都達不到上稅的“門檻”。若沒有薪資收入墊底,就靠這點稿費,你覺得他能在城市里生活下去嗎?
所以,千萬不要認為抄襲能“發(fā)家致富”。這個“歪門”,前些年或許還可以,如今,文藝多元化了,文學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式微。名刊的目錄上都是熟悉的作者名字,報紙的數(shù)量也越來越少,有副刊的報紙更是稀缺。大多數(shù)文學寫作者,想只靠稿費生存,基本不可能。除非你真的像李白、蘇東坡、余華、余秀華、雙雪濤等人一樣,天賦異秉,就是為文學而投胎的,否則,還是不要為了所謂的文學夢,破釜沉舟,孤注一擲。
當然,這些話都是對圈外人講的。馮書輝寫詩的時間不短了,且是中國詩歌學會會員,算是門里人,應該不會為了那點稿費去抄襲以求發(fā)表。那是為了晉升?肯定也不是。從目前網絡信息看,馮并非作協(xié)系統(tǒng)在編人員,寫詩作文,只是個人愛好而已,對于其工程師的崗位、前途無半點助益,也不會讓他多賣一盒茶葉。
據(jù)網傳,馮甚至想拿錢擺平此次抄襲風波。若這方面的信息為真,就不由得讓人慨嘆:就為一個愛好,就為發(fā)表幾首詩,花了錢,還送了命(疑似),冤不冤?何況,他始終沒有承認自己抄襲,辯稱是幫其改稿的老師借用了別人的一些詩句……
我想,馮書輝之所以有如此結局,可能出于這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過于熾熱的文學情懷,二是對文學行業(yè)、文學抄襲的錯誤認識。
說到文學情懷,最為典型者,要數(shù)某些退休老干部,能謅幾句打油詩、順口溜,就特別想加入作協(xié)。作為一名報紙副刊編輯,我總對這樣的“文學老年”說,別把愛好當成負擔,別把作家身份看得太神圣。心有所感了,就來兩句打油,發(fā)在網上,轉到朋友圈,獲得一堆點贊,都是極好的,可別想著一定要變成鉛字,甚而當作入作協(xié)的必備材料,還要擠破腦袋、動用人脈……如此,就算最后入了作協(xié),也是得不償失。把簡單的愛好搞復雜了,到頭來成了為會員證而寫作,無異于買櫝還珠。不知道馮書輝是不是為了入作協(xié)而抄襲;如果是,那可真是徹底跑偏了。某些文學愛好者可能不知道,“作協(xié)會員”只是一種身份而已,作協(xié)是不會給會員發(fā)米的。
馮對于抄襲的錯誤認知,可以說是行內清楚、門外糊涂。要不然,《作品》的“聲明”中,也不至于小心翼翼地用了“涉嫌抄襲”的字眼。這方面,有些人一直就存在認知誤區(qū),認為將別人的文章掐頭去尾,改幾個字,敲幾下回車鍵,就是詩歌創(chuàng)作。到現(xiàn)在,仍有學者為木心涉嫌抄襲的某些詩歌辯護,由此可見,入此誤區(qū)者,不在少數(shù)。看來,各級作協(xié)真有必要針對抄襲現(xiàn)象對新會員進行入門教育,就像駕考等候室里播放車禍現(xiàn)場紀錄片那樣,也把典型抄襲事例做成專題片,新會員看完才給發(fā)證。
至于文學期刊“建立抄襲者名單”一事,建議還是由中國作協(xié)出面來牽頭組織吧。不然的話,大家都是兄弟單位,做起事來,分不清大小王,很容易流于形式。懲治老賴的“個人征信”系統(tǒng),早已通行,文學界的“個人原創(chuàng)征信”制度,文學作品“查重”的大數(shù)據(jù)系統(tǒng),也能早日建立起來為好。
文學原創(chuàng)從寫出“自己的話”開始
其實,堅守文學原創(chuàng),對作者來說,說起來也容易,就是主動創(chuàng)作;但要創(chuàng)作出好作品,卻并不容易——你不要讓文章中所有的漢字、詞語、成語,給人的印象,像洪流中的漂浮物一樣,草草消失于逝川;你得讓它們鮮活起來,讓你的文章成為某個成語的有力注腳,讓人們通過你的文章重新認識這個成語。你不要盲目跟風,去追求那些所謂潮流,那些千人一面的東西;你要聽從自己的聲音,說自己想說的話(如果沒啥想說的,可以不說)。
馬爾克斯說:“有人因為青春而表達,有人因為表達而青春。”這句話向我們透露了一個關于寫作的秘密,那就是作家應該有巨大的傾訴和表達的欲望;他們不僅有這種欲望,而且像說書人一樣善于表達。如果你沒有這種表達的欲望,那么不要從事寫作;如果你有這種欲望,但不擅長書寫表達,那么你可以閱讀、練習,從寫好一句話開始,從一個形象的通感或比喻開始,寫出你“自己的話”……
是的,我們不僅要堅守文學原創(chuàng),更要堅持充滿激情和活力的文學原創(chuà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