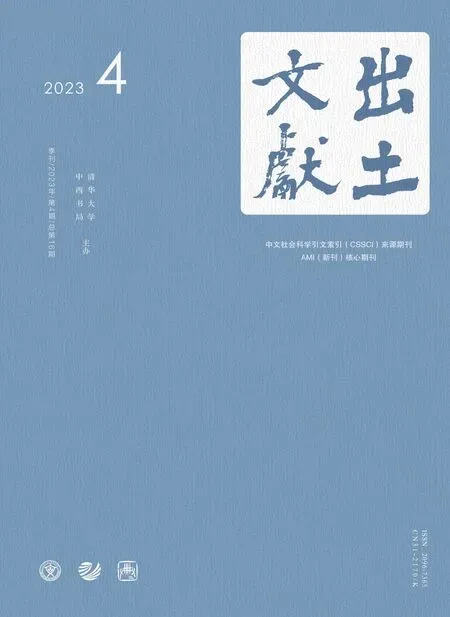從長沙出土“君教”簡牘文書看東漢三國縣級長吏的徭使*
徐 暢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引言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長沙市中心出土的東漢、三國孫吳簡牘中,均存在一類形制與內容較為特殊的官文書,這類文書寫于竹木牘、木兩行或竹簡冊書之上,(1)走馬樓吳簡君教文書多寫于單枚牘上,偶見君教文書殘簡(20枚左右),整理者以為系竹牘縱向斷裂而致,詳參徐暢: 《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簡牘官文書整理與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第88—89頁。五一廣場簡君教文書書寫載體則包含木牘、木兩行及竹簡,參角谷常子: 《長沙五一広場出土の君教簡·牘》,《奈良史學》第38號,2021年,第42—61頁;李均明: 《五一簡所見與“君教”相關的三種文書形式》,王沛主編: 《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13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12—24頁。頂頭部分通常可見濃墨書寫的“君教”二字,而覆蓋二字上方或下方往往有草書勾勒,其中不少可釋讀為“諾”字。由于以“君教”開頭(少部分以“君”開頭,無“教”字)的顯著特征,中、日簡牘研究者多將其歸納為“君教”簡牘文書,并圍繞此類文書的格式、形制及反映的行政過程,展開了熱烈的討論。(2)參伊藤敏雄: 《長沙吳簡中の生口売買と「估銭」征收をめぐって—「白」文書木牘の一例として—》,《歷史研究》第50號,2013年,第97—128頁;關尾史郎: 《從出土史料看〈教〉——自長沙吳簡到吐魯番文書》,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新探索: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2014年;凌文超: 《走馬樓吳簡舉私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占募》,《文史》2014年第2輯;徐暢: 《釋長沙吳簡“君教”文書牘中的“掾某如曹”》,楊振紅、鄔文玲主編: 《簡帛研究 二〇一五(秋冬卷)》,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31—236頁;楊芬: 《“君教”文書牘再論》,長沙簡牘博物館編: 《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 中西書局,2017年,第247—256頁;邢義田: 《漢晉公文書上的“君教諾”——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札記之一》,簡帛網,2016年9月26日;楊頌宇: 《從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簡牘試探漢代的“君教”文書》,原載黎明釗、馬增榮、唐俊峰編: 《東漢的法律、行政與社會: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探索》,香港: 三聯書店,2019年,修訂本見簡帛網,2020年3月11日;汪蓉蓉: 《“君教”文書與東漢縣廷治獄制度考論——從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說起》,《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角谷常子: 《長沙五一広場出土の君教簡·牘》,《奈良史學》第38號;等等。
因同出一地,東漢與三國君教文書的形制大體一致,但亦有細微差別。就內容完整的單枚文書牘而言,五一廣場東漢君教木牘長22.3~23.6厘米,寬4.2~4.8厘米,有兩道編痕,文字以編繩為欄界,分三欄書寫:(3)參李均明: 《東漢簡牘所見合議批件》,楊振紅、鄔文玲主編: 《簡帛研究 二〇一六(春夏卷)》,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56—264頁。首欄為君教及相關批示。第二、三欄豎行連寫,先錄由某曹史起草并上請的具體事件概要、經過,再錄參與討論的丞、掾簽名及討論后的處理意見,以“復白”“白草”等語收束,結尾為年、月、日信息。而走馬樓三國孫吳君教文書牘長23~24厘米,寬3~4厘米不等,牘面有兩道刻線,文字以刻線為欄界,分三欄書寫: 首欄為君教及批示。第二、三欄亦豎行連寫,右行通常寫丞某如掾,掾某如曹,隨后是期會掾(或典田掾、都典掾)、錄事掾校,左行寫主簿、主記史某某省,結尾為雙行小字,寫明年、月、日,所白事由等。(4)參徐暢: 《釋長沙吳簡“君教”文書牘中的“掾某如曹”》,《簡帛研究 二〇一五(秋冬卷)》,第231—233頁。
目前,關于此類文書中“君”的含義,相關長吏與屬吏的官府級別,文書所記載的行政主體,論者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君”為縣令長之敬稱,(5)漢晉間各級地方行政長官皆有敬稱,州刺史稱“使君”,郡太守稱“府君”,縣令長稱“君”,傳世文獻中有諸多語例,不再一一引證。而君教文書為臨湘縣級行政公文。(6)參徐暢: 《走馬樓簡牘公文書中諸曹性質的判定——重論長沙吳簡所屬官府級別》,《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然而圍繞漢、吳君教文書,尚有不少疑難問題。首先是關于文書的具體性質,學界表述各異,其中五一廣場所出君教文書牘,陳松長、周海鋒稱為“奏請文書”,(7)陳松長、周海鋒: 《“君教諾”考論》,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 中西書局,2015年,第325—330頁。李均明據牘中“丞、掾議”的記載,認為存在著僚佐內部的行政合議,故稱之為“合議批件”。(8)李均明: 《東漢簡牘所見合議批件》,《簡帛研究 二〇一六(春夏卷)》,第256—257頁。而由于走馬樓君教簡牘中有期會掾,凌文超、徐暢在認可所謂合議、集議表述的前提下,進一步將這類文書定義為審查期會類文書。(9)凌文超: 《走馬樓吳簡舉私學簿整理與研究——兼論孫吳的占募》,《文史》2014年第2輯;徐暢: 《釋長沙吳簡“君教”文書牘中的“掾某如曹”》,《簡帛研究 二〇一五(秋冬卷)》,第231—236頁。持不同意見的學者如侯旭東,他提出君教簡牘及上之簽署,只是文書流程上的轉單聯署,并不存在實體的“期會”。(10)侯旭東: 《湖南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性質新探——從〈竹簡(肆)〉涉米簿書的復原說起》,《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9—97頁。而鷹取祐司則依據五一廣場簡君教文書中丞不在署而掾議的情況,提出應靈活理解簡文中的“議”字,“議”未必表示多人合議,只是研究、斟酌之義,或并不存在丞與掾合議。(11)鷹取祐司: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君教文書新考》,慶北大學人文學術院: 《東西人文》第15號,2021年;中譯本《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君教文書新考》,陳金泉譯,《中國中古史研究》第9卷,上海: 中西書局,2021年,第325—328頁。
其次是關于文書首欄“君”或“君教”下的注記,即濃墨草書的單字或多字勾勒,業已得專家釋讀為“諾”“已出”“已核”“重核已出”等,(12)參王素: 《“畫諾”問題縱橫談——以長沙漢吳簡牘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17年第1期。系長吏批示或檢校記錄。但部分文書中還存在“君”字后既無“教”字,亦無畫諾及檢校記錄,只是以與正文類似字體連寫某特殊事項的情況。僅舉證一枚五一廣場所出木牘:
教屬曹今白。守丞護、兼掾英議請移書賊捕掾浩等考實奸
君追殺人賊小武陵亭部。詐。白草。
延平元年四月廿四日辛未白。
(選釋·二五)(13)五一廣場簡目前已出版七卷,分別為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之《選釋》、壹至陸卷(上海: 中西書局,2015—2020年),下文征引五一廣場簡簡文,一般情況下隨文標明其所屬卷數及出版號,不再一一注明對應該卷的頁碼。
待事掾王純曾于延平元年(106)四月廿二日致書縣廷,陳述在過往執法中因公格殺殺人賊,后遭其親屬復仇,請縣廷遣吏考實并護佑全家(參選釋·一三九)。本牘展示的是兩天后縣左賊曹史等將此事件梗概上奏,提請縣廷商討處理方案的過程。對首欄的“君追殺人賊小武陵亭部”注記,整理者陳松長、周海鋒最初以為應斷讀,“追殺人賊”的主語不是“君”,而是當事人王純。隨后不少學者注意到這種特殊注記并指出舊說疏失,即“君+動賓短語”應理解為“君”本人的活動記錄,但并未就“君”的相關活動予以進一步關注。(14)參李均明: 《東漢簡牘所見合議批件》,《簡帛研究 二〇一六(春夏卷)》,第256—264頁;李松儒: 《五一廣場“君教”類木牘字跡研究》,《中國書法》2016年第5期;楊芬: 《“君教”文書牘再論》,《長沙簡帛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247—252頁;楊頌宇: 《從五一廣場出土東漢簡牘試探漢代的“君教”文書(修訂本)》,簡帛網,2020年3月11日。

上述君的各項活動,應當可以理解為長吏不在署而外出執行公務。然所謂“執勤”非時人語,或可借用《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常繇咸陽”,(17)《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344頁。《漢書·蓋寬饒傳》“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中的“繇”及“繇使”來予以界定,據顏師古注,“繇”通“傜”“徭”,(18)《漢書》卷七七《蓋寬饒傳》,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第3244—3245頁。原始含義為由中央或郡國面對編戶民中的傅籍男子所征發的一般性力役及常規兵役;(19)陳松長: 《秦漢時期的繇與繇使》,《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而“徭”之語義在秦漢社會具體使用時存在著寬泛的一面,刑徒所承擔的懲罰性勞役,以及服公事者被官府差使所從事的各種外出工作,亦可稱為“徭”,分別概括為“奴徭”“吏徭”。(20)孫聞博: 《秦及漢初“徭”的內涵與組織管理——兼論“月為更卒”的性質》,《中國經濟史研究》2015年第5期;朱德貴: 《岳麓秦簡所見“徭”制問題分析——兼論“奴徭”和“吏徭”》,《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吏徭,作為早期勞役之重要類型,應于郡縣制、官僚制肇建之際已存在,岳麓書院藏秦簡中即有秦初并天下時新地吏以徭使為名私自返回他郡縣的記載:“廿六年正月丙申以來,新地為官未盈六歲節(即)有反盜,若有敬(警),其吏自佐史以上去繇(徭)使私謁之(四十八)它郡縣官,事已行,皆以彼(被)(四十九)陳(陣)去敵律論之。”(21)陳松長主編: 《岳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第48—49頁。而據里耶秦簡《遷陵吏志》(7-67+9-631)記載,秦代遷陵縣有額定縣吏(編制內)103人,而實有縣吏86人,其中外出徭使者就有35人,(22)里耶秦簡博物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中心編: 《里耶秦簡博物館藏秦簡》,上海: 中西書局,2016年,第163—164頁。占到定員數的30%、實員數的40%;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遷陵守丞巸就曾指出該縣“居吏柀(徭)使……居吏少,不足以給事”(8-197)的實際狀況。(23)陳偉主編: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08—109頁。據統計,遷陵吏因執行上計、押解人員物資、采購、校讎律令等各種公務而離開縣境,越過郡治,行蹤遠至他郡,甚至京師,其離縣時間通常超過一月,甚至半年。(24)參讀王勇: 《里耶秦簡所見秦代地方官吏的徭使》,《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遷陵縣吏的外徭,恰可視為秦帝國各級官吏頻繁且長距離徭使的縮影。過度徭使吏民,被視為秦政之弊,(25)西漢文士曾揭示秦時郡縣鄉小吏被驅使外徭之苦,見賈誼《新書》之《屬遠》篇(閻振益、鐘夏校注: 《新書校注》卷三,北京: 中華書局,2000年,第116—117頁),桓寬《鹽鐵論》之《疾貪》篇(王利器校注: 《鹽鐵論校注》卷六,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第414—415頁)等。在西漢,統治階層曾通過對上計、考課、選官等制度的調整,減輕吏徭。但就西北漢簡反映的邊塞郡縣、尹灣漢簡反映的東海郡縣情況看,吏徭依然常見,且頻度不減。
實際上,綜觀秦漢國家的中央與地方,各級行政機構所涉日常事務細密而繁多,除通過文書的渠道上傳下達政令外,還必須有大量的官吏,被外派活動于基層政務辦理的一線,處理通過文書無法解決的具體事務,如案獄、錄囚,同時也察觀風俗,幫助在首都及各級治所的長吏了解地方情況,加強社會控制。吏徭,是保障國家機器運轉不可或缺的行政技術手段,也應視為秦漢國家的行政常態。
近來不少學者借助出土簡牘中的基層吏員名簿及活動記錄,討論吏徭問題,但就時段而言,關注點主要在秦及西漢;就研究對象而言,主要關注中央至地方各級屬吏的徭使,鮮少談及長吏的徭使問題。(26)參沈剛: 《徭使與秦帝國統治: 以簡牘資料為中心的探討》,王勇: 《里耶秦簡所見秦代地方官吏的徭使》,并載《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劉自穩: 《里耶秦簡所見秦徭使吏員的文書運作》,《出土文獻》2023年第2期;侯旭東: 《傳舍使用與漢帝國的日常統治》,初刊《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收入氏著《漢家的日常》,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9—33頁。實際上,相對于屬吏,郡、縣長吏是處理地方行政事務的最終責任人,反映在文書層面,亦應是眾多上、下行文書處理的末端。長吏如因事徭使在外,理論上應在地方公文檔案中保留更豐富的記錄,如尹灣漢簡《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共錄22位縣級長吏外出公干信息,而上述長沙出土東漢、三國孫吳簡牘中亦保留不少郡、縣長吏外徭的記載,尤其是其中形制特殊的君教文書,更是追蹤縣級長吏動向的一手材料。隨著五一廣場簡的分卷整理出版,東漢君教文書大量涌現,而走馬樓吳簡中的君教文書牘,亦將隨著《竹木牘》特輯得以完整公布。(27)走馬樓簡牘整理組: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木牘》特輯,北京: 文物出版社,待刊。筆者有幸參與相關工作,以下將綜合漢、吳簡牘信息,以長沙郡臨湘地方的個案,探討東漢至三國縣級長吏,尤其是行政長官從事外務而徭使的種種情況,希望豐富對帝制中國早期官僚制及國家日常統治的歷史認知。
一、 兩漢郡縣長吏徭使的制度背景
兩漢的大部分時間,地方行政為郡、縣二級制。(28)西漢初一度大規模分封諸侯王,形成郡、國交錯的局面,至武帝時厲行郡縣制;東漢雖仍以諸侯國與郡并行,但王國封域甚狹,郡縣制是主流,參周振鶴: 《西漢政區地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曉杰: 《東漢政區地理》,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郡、縣僚佐主要由行政長官、佐官、屬吏三部分組成,其中,郡、縣行政長官及佐官俱由中央任命,合稱“長吏”。(29)參讀鄒水杰: 《秦漢“長吏”考》,《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張欣: 《秦漢長吏再考——與鄒水杰先生商榷》,《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3期。郡、縣日常政務的辦理,實行長官負責制,郡太守、縣令長作為行政長官,全面承擔了轄域內理訟斷獄、維護治安、按比戶口與征發賦役、管理軍隊、勸課農桑、興辦學校、教化吏民、賑恤窮寡等與政治、經濟、文化相關的各項要務。(30)參鄒水杰: 《兩漢縣行政研究》,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2—147頁。庶務的處理,部分環節可委派佐官、屬吏,但最終環節皆需提交長官審核處理。理論上講,郡、縣行政長官需坐鎮官府,不得擅離職守。在漢代的地方行政實踐中,有二千石(郡太守)不離郡界,病與賜告不得歸家的做法,至遲到西漢中后期,相關規定被著為法令遵行,(31)《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上》顏注引孟康曰:“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第6頁)事亦見《漢書》卷七九《馮野王傳》,第3304頁。至東漢一仍之。(32)《后漢書·酷吏列傳》載瑯琊太守李章欲發兵營救被囚之北海太守,掾吏以“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止之。見《后漢書》卷七七,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2493頁。值得辨析的是,郡守、縣令長之坐鎮與在職,并不應機械理解為居署辦公,還應包括在其轄內巡行視察。按照古者郡方千里,縣方百里的理想制度,(33)《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頁。只要不是跨界厘務,這種出行往往歷時不久,事成即歸,于上述各項要務辦理無礙。
關于郡太守之巡察,《續漢書·百官志》“郡太守”條本注:“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34)《后漢書》志二八,第3621頁。可知東漢時,郡太守于每年春耕之時外出周行屬縣,頒布月令,勸民農桑,而立秋以后派遣督郵分部監察,平決冤獄,已成為慣制。
相比郡太守,目前并未見到對縣令長應在署或出巡的明確制度規定,不妨依據傳世、出土文獻保存的實例,略作推測。《后漢書·趙咨傳》載滎陽令曹暠奉迎過縣界之舊日恩主、東海相趙咨,“送至亭次,望塵不及”,遂乃“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35)《后漢書》卷三九《趙咨傳》,第1314頁。由此可知,一般情況下,縣令長亦不得擅離縣界。不過縣令長在縣內的行動是相對自由的。西漢中后期至東漢,刺史行部、郡守行縣,作為上級官員對下級單位的日常巡視與監督,被逐漸固定下來,(36)參楊寬: 《戰國秦漢的監察和視察地方制度》,《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2期;劉太祥: 《試論秦漢行政巡視制度》,《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與此相對應,縣令長應當也需要定期巡行鄉亭。《二年律令·具律》獄事“當治論者”條列舉(縣)令、長、丞有他事的情況,包括病、不存,行鄉官、謁屬所二千石官等,(37)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3頁,簡一〇三至一〇六。似提示縣長吏行鄉官(38)鄉的治事場所稱“官”,如《管子·立政》:“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鄉屬。”《校注》引王引之云:“鄉官,謂鄉師治事處也。”(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 《管子校注》卷一《立政第四·首憲》,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第66、70頁。)《漢書》卷八九《循吏傳·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顏注:“鄉官,鄉所治處也。”(第3629—3630頁)為一種常見的行政現象,而《后漢書·魯恭傳》亦記載了中牟令魯恭陪同前來視察的河南尹仁恕掾“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與兒童語的情境。(39)《后漢書》卷二五《魯恭傳》,第874頁。雖然現存律令遺篇中尚未見有關縣令長巡行的制度與機制約束,但由上舉證可知,縣令長巡行鄉亭已然成為兩漢的地方行政實踐。筆者認同相關學者的推測,縣“有租稅壓力,需直接與民眾打交道”,“縣令長是要經常巡視鄉行政工作的”。(40)參鄒水杰: 《兩漢縣行政研究》,第329—330頁;劉太祥: 《試論秦漢行政巡視制度》,《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
兩漢三國存在關于刺史、郡守、令長在轄區內巡行的制度規定已無異議,然而這種不離行政轄區的觀風察俗、決獄理訟,似乎出于各級行政長官的本職,屬于例行工作,以“徭使”來界定,是否準確呢?(41)侯旭東先生認為繇(徭)對應官吏在本轄區以外的公務,參其2023年5月8日、7月9日來函。要理解這一問題,恐怕還要從秦漢“徭”的原始含義切入。“徭”的根本特征是強制性與普遍性,(42)朱德貴: 《岳麓秦簡所見“徭”制問題分析——兼論“奴徭”和“吏徭”》,《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從制度普遍化了的兩漢來看,刺史行部、太守行縣,恐怕已經不僅是長吏本人的行政“自由”,不僅是“做做樣子”,(43)相關學者推測“郡守行春多做做樣子,文獻說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參鄒水杰: 《兩漢縣行政研究》,第329—330頁。而成為地方行政的必然要求。如《漢書·韓延壽傳》記宣帝時傳主為左馮翊,到任一年多“不肯出行縣”,郡中以丞掾為首的屬吏一再敦促之,“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44)《漢書》卷七六《韓延壽傳》,第3213頁。《后漢書·崔篆傳》中,在新莽時亦有類似情節。(45)《后漢書》卷五二《崔骃列傳》記崔篆新建大尹任上行春事(第1704頁)。屬吏的規諫,某種程度催化了制度的強制力,在這種背景下,長官巡行轄境,當然應屬于“徭使”。至于郡太守、縣令長跨出轄境的重要工作,如上計、赴上級行政單位期會、送正卒衛士番上、調配物資到指定地點,等等,自然更符合徭使的含義。(46)尹灣漢簡《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可見東海郡縣長吏“右十三人繇”之記錄,俱為跨出縣轄境的公干。連云港市博物館等編: 《尹灣漢墓簡牘》,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第96—97頁。秦漢編戶民的徭役有“中”“外”之別,即“邑中徭役”與“御中發征”,而長吏在轄境內與跨越轄境的徭使,亦可比照理解。(47)參王彥輝: 《秦漢時期的“更”與“徭”》,《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
郡縣長吏除太守、令長等行政長官外,尚有丞、尉等佐官,以上重點梳理了行政長官的徭使。還需注意的一個情況是,同為長吏,佐官執行外徭的可能性遠遠大于行政長官。以縣級行政的情況為例,尹灣漢簡《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記錄了22例縣級長吏徭使的情況,其中由丞、尉、獄丞出使多達19例,而由縣長、侯相親赴外徭者僅3例,分別為“費長孫敞十月五日送衛士”“建陽相?唐湯十一月三日送保宮□”“山鄉侯相□□十月……”。(48)連云港市博物館等編: 《尹灣漢墓簡牘》,第96—97頁。前兩例信息較完整,據廖伯源解讀,應系從屬縣送人或物至京師之皇宮,事關要重,故由東海郡太守特遣縣令長親執其事。(49)廖伯源: 《〈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釋證》,《簡牘與制度: 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增訂版)》,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01—205頁。
這種情況也與制度規定的長官、佐官的行政分工,以及職掌直接相關。縣內大部分公文與政務的最終裁斷,須由行政長官作出。而佐官中的縣尉本職就與外務有關。一縣中,縣尉與令長別治,常備五兵,職在捕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奸宄,以起端緒”,(50)《續漢書·百官志》,《后漢書》志二八,第3623頁。自然需要經常外出,與更基層的屬吏游徼、亭長等一起承擔穩定治安、緝捕盜賊等公務。除捕賊外,據出土簡牘所示,縣內賦稅征繳(如五一簡貳·四六〇“守左尉區祾案筭離鄉”),跨縣的錢物輸納(如尹灣簡“輸錢都內”)、護送戍卒(如尹灣簡“送罰戍上谷”)等工作,皆存在由縣尉承擔的情況。(51)廖伯源: 《漢代縣丞尉職掌雜考》,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 中華書局,2005年,第438—448頁。
相比本就奔走在一線的縣尉,丞為令長之副,應與其同治所。據《續漢書·百官志》“丞署文書,典知倉獄”,(52)《后漢書》志二八,第3623頁。丞的主要職責是輔助令長署理文書(副署),處置政務,但這并不意味著丞以文書工作為主,不需外出。首先,丞是令長之副,縣令長一旦有重要政務(含外出公干),先托付給縣丞;其次,東漢以降,隨著縣級屬吏系統的完備,尤其是門下吏、諸曹吏作為在縣廷吏,越來越多地承擔了長吏交辦的任務,丞之職權實際被削弱,在文書副署與縣政集議中,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反而時常被令長派出執行公務。在出土文獻中,兩漢三國時期縣丞承擔的外務包括跨縣的錢物出納(輸錢都內及齊服官),物資采買(市魚就財物河南)及護送刑徒戍卒(送徒民敦煌、送罰戍上谷),(53)舉例皆見《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連云港市博物館等編: 《尹灣漢墓簡牘》,第96—97頁。以及縣內的捕賊、給貸貧民、送新兵等(吳簡記載,詳表1),種類繁多。

表1 吳簡君教文書所見嘉禾年間臨湘侯國長吏動向
二、 五一廣場君教簡所見東漢縣級治安事務中的長吏徭使
明了了長吏徭使的制度史背景后,以下將重點嘗試借助以君教簡為主的長沙出土簡牘,對東漢、三國兩個不同時期臨湘縣級長吏不在署而徭使的日常實踐予以情景式呈現。先看東漢的情況。
長沙五一廣場簡已刊布的材料中,有關臨湘地方長吏審理刑事糾紛、判決案件,而屬吏在方位部及鄉亭緝捕盜賊的簡例甚多,有學者據此認為,東漢和、安時期,荊南長沙一帶社會動蕩,賊盜多發,治獄之風嚴切。(54)參李均明: 《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例亭”等解析》,《出土文獻》2020年第4期;馬力: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孫詩供辭不實案”考證》,王捷主編: 《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9輯,北京: 法律出版社,2020年,第373—400頁。由于這批簡牘的性質、歸屬問題尚未得到完滿解決,較難根據一口井內所出一批簡的記載重點,去判定東漢時期本地的一般情況(有觀點指出,J1所出可能主要是臨湘縣賊曹保藏的文書,因而多與捕賊事務有關(55)參吳婷、郭瀟雅: 《長沙發掘萬枚簡牘 再現東漢早期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7月8日第1版;周海鋒指出五一簡以左賊曹與長吏官署文書居多,參所撰《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文書的歸屬與性質問題》,《長沙五一廣場簡與東漢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48—160頁。),但可以肯定的是,治安管理無疑是彼時長沙郡、臨湘縣日常行政運作中的核心事務之一。李均明就指出,臨湘縣存在一套完備的治安體系,警備事務實行縣、部、亭三級分層責任制,最基層的警務,由同一警區(即方位部)的賊捕掾、游徼及具體案發地所在亭的亭長共同執行,并將執行結果以文書的形式上報縣廷,縣廷由賊曹專與外部吏對接,而縣尉督責之;發生重大案件之后,往往需要由縣尉出面協調,甚至親自外出辦案。(56)參李均明: 《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反映的臨湘縣治安體系初探》,《長沙五一廣場簡與東漢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8—24頁。簡文中多見臨湘縣兩尉(左、右二人)行外徭以捕賊的案例,如“守左尉胤追殺人賊廣亭部”(肆·一四七二),范圍不限于本縣轄內部與亭,還存在跨境追捕的情況,如“守右尉追豫章劫人□”(壹·一),“左尉之下雋未還”(肆·一三三〇),豫章郡與長沙郡毗鄰,下雋與臨湘同為長沙郡屬縣,(57)《續漢書·郡國志》載長沙郡十三城,“臨湘 攸 荼陵 安城 酃 湘南侯國 連道 昭陵 益陽 下雋 羅 醴陵 容陵”,見《后漢書》志二二,第3485頁。臨湘尉遠至他郡他縣,概為捕賊。
既然臨湘地方存在著相對完備的治安管理網絡,并有作為長吏之一的縣尉總領其事,為何會出現君出追賊,即臨湘縣行政長官親力親為的情況?這恐怕與上級行政單位下派的捕賊任務繁重,且時限緊張,而縣內捕賊之吏力不從心,時常無法按期完工以復命有關。簡文中多見由臨湘基層捕賊小吏發出,請求“假期”的上行文書,稱為“解書”,如:
兼左部賊捕掾馮言逐捕殺
人賊黃康未能得假期解書 十二月廿八日開
(貳·五三〇)
按:“十二月廿八日開”為后書文字。
·兼左部賊捕掾則言逐捕不知
何人燒石裦等宅假期書 詣左賊 八月廿七日
(壹·三二四)
按:“八月廿七日”為后書字。

府告臨湘: 前卻、詭課,守左尉傿、梵趣逐捕殺鄉佐周原男子吳主、主子男
□賊王傅、烝于、烝尊不得,遣梵詣府對。案: 傅、于、尊共犯桀黠尤無狀,梵典負被書,受詭逐捕,
訖不悉捕得。咎在不以盜賊責負為憂,當對如會。以傅已得,恐力未盡,冀能自效,且復假期。記


長沙大守丞印。 延平元年五月十九日起府。
(叁·一一四二+肆·一二四一)
臨湘左尉親出逐捕殺鄉佐周原等人賊。從所謂“咎在不以盜賊責負為憂”“恐力未盡冀能自效”“勉思方謀”的表述看,或許所捕為要重罪犯,郡太守對臨湘尉經辦的捕賊不力一事非常在意,深加切責,同時恩威并施,為其假期兩個月,希望最終能順利捕賊歸案。
作為治安事務主官的臨湘尉所面臨的壓力自然不小,但捕賊績效并非僅與分管治安的縣尉有關,縣令亦需承擔責任,《二年律令·捕律》明載追捕盜賊一項政務由“尉分將,令兼將”,《捕律》中還有懲罰條款,盜賊發,若發生地縣級長吏令、丞、尉未能及時發覺并妥當處置,需繳納罰金,而多次捕賊不力,長吏甚至要被免職,“一歲中盜賊發而令、丞、尉所(?)不覺智(知)三發以上,皆為不勝任,免之”。(58)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第27—28頁,簡一四〇、一四五。相關法令在東漢時仍沿用之。(59)《后漢書》卷四六《郭陳列傳》載陳忠上疏:“自今強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糺罰。”(第1559頁)可知緝捕盜賊一事不僅與縣尉,甚至與縣行政長官的政績攸關。兩漢縣令長考課中應有盜賊課一項,(60)《漢書》卷七八《尹翁歸傳》載其入守右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第3208頁)。縣長吏應亦有盜賊課。青島土山屯出土堂邑縣行政文書中就有《盜賊命簿》及《君視事以來捕得他縣盜賊小盜傷人簿》,(61)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黃島區博物館: 《山東青島土山屯墓群四號封土與墓葬的發掘》,《考古學報》2019年第3期,第405—438頁。是縣令長責兼弭盜,維持治安的明證。
當然,縣令長責兼盜賊,并不必然代表他們需要奔走在捕賊的一線,五一廣場簡中出現的“君追賊某亭部”的情況,與永元至永初年間臨湘縣屬吏整體上執行捕賊任務不力的情況有直接關系。即以本文開頭提到的兩枚“君追(殺人)賊小武陵亭部”文書牘為例,臨湘縣令于延平元年(106)四月、永初元年(107)正月頻繁造訪同一亭部捕賊,背景是該亭部盜賊多發,縣尉曾頻繁發出指示給所部(或許是東部)賊捕掾、游徼、亭長,令其盡力捕賊,而此一干屬吏塞責之,不肯效力。見于君教文書木牘,有所謂“左尉檄言: 小武陵亭比月下發賊捕掾、游徼逋留塞文書,不追,賊捕掾周、并,游徼李虎知盜賊,民之大害,至逋不追,當收正”(叁·一一〇六)的表述,說明小武陵亭不能按期完成捕賊任務,縣尉通過文書的形式督責所部。而據“守左尉祾追賊小武陵亭部”(叁·一一三四),縣尉還曾親至該亭部,或許與上級交辦的要案遲遲得不到解決有關。還應注意到上引叁·一一四二+肆·一二四一號木牘交代的情況,延平元年的春天,臨湘左尉在全力辦理郡府交辦的逐捕殺鄉佐周原等賊的專項事務,且未能按期完成;同一時期右尉行蹤不知,大概率也奔走在捕賊一線,或詣府參加期會,(62)臨湘右尉參與捕賊,以及因捕賊不力假期詣府例,參上引壹·一、選釋·二一號文書。總之兩尉均忙于執行任務;而小武陵亭的要案,也就只能由縣令自己外出辦理了。紙屋正和討論漢代縣長吏職掌時曾推測,“沒有縣尉的縣、列侯國,當然也會發生盜賊”“縣丞權限較大,但盜賊發生時追捕的軍事指揮權卻有限,應該考慮由令、長來擔當維持治安任務”,(63)紙屋正和: 《漢代郡縣制的展開》,朱海濱譯,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39頁。揆諸五一廣場簡所示東漢臨湘縣的情況,應當是可以成立的。
相比縣尉、縣令,縣丞雖很少操兵外出捕賊,仍然負擔了維持治安的相關工作。縣丞的名字時常出現在君教簡牘的中欄,與掾一起,針對由外部吏、諸曹吏提交給縣廷、待處理的相關事宜(如訴訟案件),提出進一步的工作方案。也就是說,縣丞居內,在官署以“議”的形式參與一縣重大事務的處理;而考察延平元年、永初元年這兩年間丞、掾所議要事,(64)有明確紀年或可考屬此二年者,鷹取祐司收集到16例,參所撰《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君教文書新考》,《中國中古史研究》第9卷,第337—342頁。還可補充陸·二四九七1例。亦多與逐捕殺人賊(見選釋·二五、壹·一三六、陸·二四九七),處理官民斗訟(選釋·四七、貳·四二九+四三〇),敦促屬吏捕賊(叁·一一〇六)等治安事務相關。可以理解為,包括丞在內的臨湘縣長吏,通過不同的工作形式,共同承擔了維持社會穩定的行政責任。
三、 走馬樓孫吳君教簡牘所見臨湘侯國長吏徭使

不過,與東漢簡情況類似,吳簡中亦多見縣廷長吏、屬吏處理事務而形成的君教文書。在此類文書參議及審核中扮演主要角色的長吏,主要是縣令、丞,在孫吳為侯國相、丞,文書首欄為令/侯相批示,中欄有丞參與的記錄。所不同的是,東漢君教文書有丞、掾議,即向縣令提交處理方案的具體環節,而孫吳君教文書僅書“丞某如掾”“掾某如曹”,相當于只有丞、掾的姓名、列位。盡管如此,借助首欄、中欄的相關注記,我們仍然可以嘗試復原孫吳嘉禾年間臨湘侯相、丞的具體活動,尤其是關注其離開縣廷而徭使的情況。經過最終整理,吳簡中共可見書寫在竹木牘上的君教文書84件,有明確紀年或可考知年份者計60件,時段集中在嘉禾二年至五年(234—236),下面嘗試抽離出其中的長吏記錄,列表如下:
結合表中數據及《竹木牘》整理組提供的君教文書圖版、釋文信息分析可知,嘉禾二年初至五年三月的三年里,臨湘侯相大部分時間居署辦公,顯示在60件君教文書中,絕大部分文書的首欄有個性化的濃墨草書批字,疊壓在“君教”二字上,應視為侯相本人親手所畫諾。少部分文書無“若(諾)”字,但“君教”下方有“已核”等濃墨批字,亦可視為侯相之履職。侯相缺位,由他職代為在首欄署名的情況僅1例,而84件君教文書中侯相缺位僅2例。但侯國丞的情況相當復雜,60件君教文書(除1件信息不全外)中欄書明“丞如掾”,且有丞名之花押的情況僅4例;而僅書明“丞如掾”,無簽署的情況20例;其余35例,丞后均書明具體動向,說明不在署,比例高達近60%。
下面具體分析侯相、丞不在署的情況。49號嘉禾三年十月十八日君教文書以“府主簿”“已核”開頭,應是侯相因事不在,主簿暫攝其位。而62號的記載較為具體,謹移錄原牘文如下:
1 君 出送柏船 領丞寬 如曹期會掾烝若錄事掾謝 韶校
二月三日舉行集議當時,臨湘侯相不在署,而從事“出送柏船”的外務,由領丞寬、主簿郭宋等省察文書。牘文無明確紀年,正可以從送柏船一事切入。吳簡中屢見有關臨湘本地制作柏船的記載,柏船即柏木制作的船只。柏木是一種優質木材,淡褐色,性耐旱耐濕,表面光潔,堅固耐用,可制為船舶,經久不壞。臨湘柏船的制作由船曹負責,而具體造作者稱“匠師”,見于以下簡例:
草言府移邸閣李嵩(68)“嵩”字原缺釋,今據圖版補。出米十五斛給稟柏船匠師……事 閏月八日船曹掾番棟白(陸·575)
船(69)曹名原缺釋,今據圖版補。曹移送吏妻子宮中出米十五斛給稟柏舩匠師□□□等二人事 閏月八日書佐烝赟封(陸·565)

相較而言,同一時間丞所承擔的徭使,如“追捕何賊”“送新兵到漚口”“出給民種糧”,大多屬于縣級行政常務,徭使的地點多在轄境內或距離不遠。(71)漚口,據《三國志·吳書·呂岱傳》“召岱還屯長沙漚口”,屬長沙。見《三國志》卷六〇,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1385頁。但丞不居署辦公的頻率遠遠高于侯相。嘉禾三年上半年,丞琰于正月、二月、五月分別承擔了侯國捕賊、送新兵、賑貸貧民種糧的外務,至當年十月以后,丞又罹患疾病而無法視事,這樣的狀況持續半年之久;嘉禾四年五月以后,丞回宮(應指建業宮)治病,一直到五年三月,新丞紀到任。可以認為,自嘉禾三年十月至五年三月這一年半時間里,侯國丞的位置一直空缺。這樣的情況,與五一廣場君教簡牘所示延平元年、永初元年之間丞優大部分時間在署而參與縣廷議請,僅有“詣府對”“行驛”兩次外務的情況(壹·三三一、肆·一二七六),判然有別。
究其原因,丞作為令長之佐貳,在東漢早中期的縣廷重大事務集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到東漢后期至三國孫吳,一方面,諸曹機構擴張,諸曹掾史主要負責為縣廷疑難案件提供處理方案,基本上無須與丞商議,體現為丞、掾議、請環節的簡化或取消;(72)鷹取祐司認為,曹實際成為君教文書所涉事務的真正負責者,見《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君教文書新考》,《中國中古史研究》第9卷,第317—328頁。另一方面,作為縣令長親近的大吏,“錄下事,省文書”的主簿,“主錄記書,催期會”的主記室史地位日漸凸顯,(73)《續漢書·百官志》,見《后漢書》志二七、二八,第3614、3621頁。通過省察、檢校諸曹吏、外部吏制作的文書,而參與縣廷要務的實質處理,成為連接諸曹掾史與令長、侯相的樞紐,丞的作用日漸微弱,(74)凌文超稱為縣丞的閑散化,參所撰《黃蓋治縣: 從吳簡看〈吳書〉中的縣政》,《“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1本第3分,2020年,第463—517頁。以致在縣廷集議中,丞是否“如掾”,成為無足輕重的事情,反而不得不奔走于縣內繁雜而常規性的外務。由君教文書提供的實例,可一窺東漢至三國縣級行政機構諸吏之地位升沉。
余論
上文借助長沙出土漢吳簡牘考察了東漢至三國縣級長吏不在署而奔走徭使的情形。最后,再談下長吏徭使問題中的特例——行政長官長期外徭的情況,以及上述情況對地方行政的影響。
首先,如本文第一節所述,行政長官因在轄境內定期巡察,或辦理例行公務而離署,系制度規定,且大多數屬于短期出行,事成即歸,不但不會對地方行政產生不良影響,反而被目為循吏之政。《漢書·循吏傳》所記文翁、龔遂、召信臣等郡守,皆有單車巡行,傳布教令,勸課農桑的事跡,其中深得吏民愛戴的南陽太守召信臣甚至“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75)《漢書》卷八九《循吏傳》之文翁、龔遂、召信臣,第3625—3626、3637—3642頁。
另一種情況是,為履行上級專達之要務,或參與全國性的政治、經濟、軍事行動,行政長官不得不代表地方親行外出辦理,并長久滯留在官署以外。上引吳簡君教文書62號“君出送柏船”,即為一則典型事例。孫吳立國江南,由于頻繁的戰爭及交通運輸等方面的需求,仰賴大量的民用、軍用船只,臨湘地方所在湘州,為孫吳政權轄內著名的造船基地,(76)盧海鳴: 《論六朝時期造船業的發展狀況》,《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因而承擔了供給國用的任務,并由地方行政長官親自運送物資至首都。由長沙至建業送船,當行荊揚水路,由湘水入洞庭湖,再入長江,沿江東下,過中游重鎮夏口、武昌,終至下游之建業。臨湘侯相此行需要多長時間呢?學者曾據《宋書·州郡志》記載的湘州長沙至京(建康)水路里程(3300里),估算由建康至長沙行船的時間,認為90、60里是當時從長江下游上溯一日行程的上、下限;(77)參何德章: 《六朝建康的水路交通——讀〈宋書·州郡志〉札記之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19輯,武漢: 武漢大學文科學報編輯部,2002年,第59—71頁。而由長沙至建業為順流,若以日行110里計,30天方能至,往返則需兩個月。這也意味著,侯相將長期不在署。
行政長官長期在外,是否會使縣級政務受到影響呢?雖然到東漢中后期,縣級官文書的處理已走向程式化,門下吏、諸曹吏、外部吏各司其職,(78)參徐暢: 《東漢三國長沙臨湘縣的轄鄉與分部——兼論縣下分部的治理方式與縣廷屬吏構成》,《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4期。縣令長原則上只需畫諾,但負責人缺位的影響肯定還是存在的。《三國志·吳書》記載的黃蓋治理石城縣事,即為最好例證。石城縣守長黃蓋主要在外征討山越,不親政務,導致縣內以兩掾為首的大吏在文書制作與經辦過程中上下其手,以謀私利,終被黃蓋以軍法賜死。(79)事詳《三國志》卷五五《吳書·黃蓋傳》“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一節(第1284頁),不贅引全文。黃蓋委政于兩掾(或以為主簿、主記室史,或以為主簿、功曹,或以為功曹、廷掾)(80)前兩說詳凌文超: 《黃蓋治縣: 從吳簡看〈吳書〉中的縣政》,《“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1本第3分,第473—482頁;后說詳邢義田: 《漢晉公文書上的“君教諾”——讀〈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札記之一》,簡帛網,2016年9月26日。的情節,恰可與上引吳簡49號君教文書牘對照,說明主官如長期不在署,為保證縣級政務的運轉,往往實行他吏代理制,東漢末至三國,常見以門下吏之首——主簿代理相關事務。
附記:文章修改過程中得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侯旭東先生及匿名審稿專家的幫助,謹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