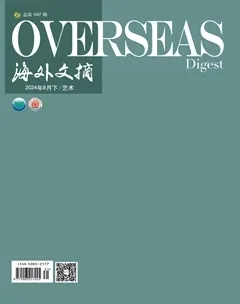《檀香刑》歌劇改編敘事角度的偏移
《檀香刑》小說改編成歌劇后,受到時長的限制,作了很多刪改。“貓腔”和“刑罰”在《檀香刑》小說中是極其重要的存在,也是生產意義的主體。歌劇對這兩個元素作了許多的改動,本文將圍繞歌劇《檀香刑》對“貓腔”和“刑罰”的刪改展開討論,以便探究在刪改之后,歌劇相較于小說在情節、人物、意義等方面具體產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檀香刑》是莫言的長篇小說,2001年3月首次出版,字數超過30萬。這部歌劇改編自莫言的小說,是國家藝術基金2016年資助的大型舞臺劇目,由山東藝術學院制作。劇本由莫言和李云濤共同編寫,李云濤負責作曲,陳蔚執導。歌劇的時長僅有一個半小時左右,受到時長的限制,歌劇對小說進行了大量刪改,包括主要人物和情節的簡化,次要人物的減少。因為時長的緣故,歌劇相較于小說的簡化是難以避免的,本文將圍繞小說中的兩個最重要的元素——“貓腔”和“刑罰”——展開討論,探究歌劇刪去相關部分之后具體發生的變化。
1“貓腔”的改編與意義生成
在200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檀香刑》的后記部分,莫言提到了在小說創作中聲音的重要性。他認為,這部作品或許更適合在公共場合由一位聲音沙啞的朗讀者大聲誦讀,周圍聚集著聽眾,這種閱讀方式不僅用耳朵,還涉及全身心的投入。為了適應這種適合在廣場上朗讀的形式,他特意采用了大量韻文,并運用了戲劇化的敘述技巧,以創造出一種流暢、易懂、夸張且富有裝飾性的敘述風格。在小說中,莫言用不同人物的視角塑造出不同的聲音,豐富了小說的聲部,提高了小說的藝術性。同時,莫言大量地描寫貓腔,這是流行于山東高密地區的一種小戲,唱腔悲涼凄切,為小說奠定了哀婉的基調,也增加了小說的神秘性和民族色彩。
對“貓腔”的描寫貫穿全文,串聯起故事情節的發展,小說中,孫丙遠遠目睹妻兒被殺卻無能為力,他唱貓腔:“目北望家園,半空里火熊熊滾滾黑煙。我的妻她她她遭了毒手葬身魚腹,我的兒啊~~慘慘慘哪!一雙小兒女也命喪黃泉~~可恨這洋鬼子白毛綠眼,心如蛇蝎、喪盡天良、枉殺無辜,害得俺家破人亡、形只影單……”受“檀香刑”的孫丙唱貓腔:“俺身受酷刑肝腸碎~~遙望故土眼含淚~~”義貓率領貓腔戲班眾人在受“檀香刑”的孫丙面前唱貓腔:“貓主啊~~你頭戴金羽翅身披紫霞衣手持著赤金的棍子坐騎長毛獅子打遍了天下無人敵~~你是千人敵你是萬人敵你是岳武穆轉世關云長再世你是天下第一~~”他們的吟唱帶動了民眾,而后德國人用槍械將其全部射殺,至此貓腔一脈全部覆滅,全文的戲劇張力達到高潮。小說在孫丙的一句“戲……演完了……”中結束。
貓腔的象征意義不容忽視,莫言在后記中寫道:“高密東北鄉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都能夠哼唱貓腔,那婉轉凄切的旋律,幾乎可以說是通過遺傳而不是通過學習讓一輩輩的高密東北鄉人掌握的。[1]”貓腔不是習得而是生來就有,這也許并不是一種夸張,而是高密東北鄉貓腔的盛行讓人耳濡目染所產生的結果。莫言的這句話直接揭示了貓腔在小說中的象征意義——貓腔于高密東北鄉人而言是母語般的存在,與之血脈相融,也可以說貓腔就直接代表著高密東北鄉人。歌劇中這一點作了較大的改動,歌劇主要使用的是西方的交響樂,配上演員的美聲唱腔,氣勢恢宏,亦能動人心弦,但進一步思考,在一出清末抗德的大戲中,用西方的樂器作為抗擊西方的背景音,是有些不和諧的。歌劇中雖然也有貓腔的加入,如朱文斌指出的,在《檀香刑》的歌劇中,如第三幕的《孫丙與小山子的獨唱與對唱》以及《舍得我一死喚醒眾鄉黨》,還有第四幕《趙甲、眉娘、孫丙三人的唱段與眾人的合唱》等孫丙參與的部分,都明顯地融入了貓腔的唱腔特色。此外,樂隊的變奏部分也加入了貓腔的元素[2]。但是,貓腔只是作為人物某些時候的唱腔出現,失去了“母語”的身份,和高密人也沒有產生特別的聯系。一些關于貓腔的重要情節也被刪去了。例如,小說中圍觀孫丙的民眾是被貓腔喚醒的,歌劇中改成了被眉娘的央求喚醒。歌劇將音樂作為一種演唱背景,不作為生產意義的內容,而小說中的貓腔并不是作為藝術的點綴而存在,而是民族的化身,這是改編者所沒有關注到的地方[3]。這樣的改編也與莫言書寫小說的目的背道而馳。莫言認為,傳統民間說唱藝術曾是小說創作的根基。在小說從民間通俗藝術逐漸轉變為高雅文學的當下,以及在借鑒西方文學的潮流蓋過繼承民間文學傳統的今天,《檀香刑》可能顯得不夠時尚、先鋒。這部作品代表了他在創作旅程中一次有意識的撤退嘗試,但他認為他還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撤退程度。歌劇和西方文化的融合迎合了市場,卻消除了莫言的“撤退”,又從“俗”成了“大雅”的藝術。
也許是因為歌劇里對貓腔的突出不夠,于是歌劇的臺詞里直接加入了很多和“貓腔”有關的臺詞,在歌劇中,小山子自愿成為孫丙替身,眉娘贊賞他的大義,說要將他“編進貓腔戲,讓千人歌頌,讓萬人歌唱”。孫丙勸小山子逃走對他說:“你毀容入獄忠義千秋,足夠青史之上把名留。”孫丙在眉娘和叫花子們來救他時說:“如果我怕死脫逃,被人家編進戲里,豈不落下千古的罵名?”孫丙在赴死前說:“我一生的事跡要成為一場戲,我演了半輩子戲,我就是一場戲。我如果逃跑,是一場貪生怕死的戲。我讓人替死,是一場不仁不義的戲,我要演一場慷慨激昂的戲,我要讓人把我當成英雄寫進戲,我要用我的死喚醒天下人。”這些臺詞使貓腔戲得到了強調,但是卻隱秘地使人物的精神內核發生了偏移,將之與小說里的描寫對比——小說里眉娘感謝小山子是這樣描寫的:“‘如果俺爹能夠活出來,俺一定讓他把您編進貓腔里,讓千人傳誦萬口唱……’那漢子睜開醉貓一樣的眼睛看了俺一眼,翻了一個身,又呼呼地睡了過去。”可以看出小山子其實并不在意是否被編進戲里,他之所以愿意替孫丙死,一方面是敬佩他的大義,另一方面是他自己也不想活了;小說里孫丙面對叫花子們來救自己時的內心活動是這樣的:“朱八哥哥,松手啊,你把我卡死就等于毀了我名節,你不知道,俺舉旗抗德大功剛剛成一半,如果俺中途逃脫,就是那虎頭蛇尾、有始無終。俺盼望著走馬長街唱貓腔,活要活得鐵金剛,死要死得悲且壯。”孫丙固然是在乎自己名節的,但是他不愿意逃跑主要是因為他抗德進行到一半,不能半途而廢。也就是說,小山子和孫丙的行為,有更內在的原因,而被寫進戲里,被人傳唱,是一個次要原因。小說里人物是飽滿的,所以在人物提到要被編進戲里時,讀者能夠清晰地識別,這其實是一種人物自我安慰的話語,更增添了人物的大義凜然與悲壯感。孫丙在小說里普通人的一面在歌劇里沒有呈現,歌劇里的孫丙是一個完全正面的英雄形象,但歌劇對人物的塑造并不充分,使得人物缺乏其他的動機,又為了突出貓腔,在人物的臺詞中反復提到貓腔,不知不覺地將人物的動機偏移到戲上,仿佛他們的行為主要是為了成為戲里的英雄,這讓人物的動機變得外在,削弱了人物的精神內核。這同時又會讓人反過來思考,貓腔在歌劇中的意義是什么呢?在這樣的處理下,它似乎變成了一種追求,是高于人的,與高密人失去了血脈相融的關系,更無法呈現孫丙說的“俺盼望著走馬長街唱貓腔,活要活得鐵金剛,死要死得悲且壯”的意味,貓腔成了增加民族特色的點綴,不再進行意義的生產。
2“刑罰”的刪減與背后蘊含
許多文章批評莫言筆下的刑罰過于殘忍,將痛苦審美化。筆者認為,雖然痛苦和死亡在許多文學中都承擔著深刻的意義,但是不代表每部小說都一定要賦予痛苦和死亡意義,這部小說中真正產生意義的是“施刑”這個行為,是“施刑”背后的制度,乃至看客的心理[4]。拋出倫理,似乎為小說的闡釋找到了一條明確的可行之路,但是這難道不是一種懶惰嗎,也往往偏離了小說,變成對作者本人的批評,正如陸建德所說:“討論文學的倫理必須具體入微, 不能搬出一套套空洞的倫理觀念來遮掩懶惰和庸俗。[5]”從史實上看,莫言的描寫和當時真正的刑罰是不符合的:“晚清時期凌遲固然殘酷,但早已不是‘千刀萬剮’而基本上是‘八刀刑’。即便被清廷恨之入骨的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所受之凌遲也不過‘凡百余刀’”[6],莫言也坦白說過關于行刑的部分是他自己的想象:“沒見過劊子手行刑的場面,甚至也沒查到有關的一條資料記錄,只能靠想象。[7]”這種對刑罰的想象和突出,的確容易遭到質疑[8]。
歌劇中刪去了施刑場面,也刪去了對各種刑罰的介紹,僅僅在歌劇尾聲時有一段對“檀香刑”的刻畫:“都說那檀口輕啟美人曲,鳳歌燕語啼嬌鶯,都說那檀郎親切美姿容,拋果盈車傳美名;都說是檀板清越換新聲,梨園弟子唱升平;都說是檀車煌煌戎馬行,秦時明月漢時兵;都說是檀香繚繞操琴曲,武侯巧計保空城;都說是檀越本是佛家友,樂善好施積陰功,誰見過檀木橛子把人釘,王朝末日缺德刑。”歌劇對“檀香刑”所塑造的內涵主要在“檀香”上,描寫了檀木所象征的美好,突出典雅的檀木和對人施刑的器具之間的沖突,縱觀全劇,幾乎沒有對“檀香刑”的其他塑造。因此,“檀香刑”更多只是作為一種懲罰施加到孫丙身上的,主要突出了對孫丙的殘忍和不公,但失去了背后的蘊含。對貓腔和刑罰的改編處理,大大削弱了歌劇的復雜性,歌劇雖然仍有二者的出現,但其實無法再去承載對于民族和王朝統治的深層次的討論。小說中的袁世凱、慈禧太后、咸豐皇帝,在歌劇中幾乎都沒有出現。總的來說,這些角色變得可有可無,加上對貓腔和刑罰的刪減,使得歌劇中承擔意義的主要是四位主角。原本小說中難以抗拒的時代的力量被削減了,歌劇中更多呈現的是正反派之間的沖突,個人的主觀意志成為行為的主體,然而,略顯單薄的人物塑造又難以給予這樣的沖突更多的意義,甚至還會產生意義上的偏移。
3 結語
受到時長和體裁的限制,要在歌劇中呈現廣闊的社會畫面或許是有些苛刻的。總體而言,歌劇的布景、音樂、演員的精彩表演也帶來了很好的審美體驗。歌劇尾聲時借眉娘口道出了這樣一句臺詞:“人中戲,戲中人,難以分辨,人生本是一出戲,曲終人散離合悲歡。有的戲沒開演已經演完,有的戲演完了重新上演。”這是小說里沒有的臺詞,寥寥數語就將全劇總結, 帶出“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的思考,相較于《檀香刑》小說,這是歌劇所增加的意義。■
引用
[1] 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2] 朱文斌.文樂融通——論民族歌劇《檀香刑》音樂中的“文學思維”[J].中國戲劇,2023(5):86-88.
[3] 吳曉佳.寓言性的消失與歷史的力比多化——以《銀城故事》《檀香刑》《人面桃花》為中心[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62(6):55-65.
[4] 李建軍.文學的態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81.
[5] 陸建德.文學中的倫理:可貴的細節[J].文學評論,2014(2): 18-20.
[6] 林晨.晚清“文”“史”參照下重解《檀香刑》[J].文藝爭鳴,2016(10):56-63.
[7] 莫言.莫言對話新錄[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264.
[8] 張清華.莫言與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以《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為例[J].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35-42.
作者簡介:伍泳霏(2001—),女,四川達州人,研究生,就讀于西南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