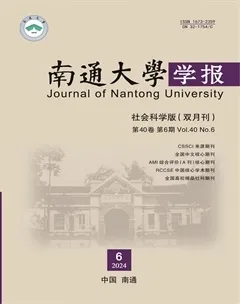精神的機器,抑或生命的魔法
摘" 要:當代的技術(shù)哲學正在普遍經(jīng)歷著經(jīng)驗轉(zhuǎn)向和物轉(zhuǎn)向。但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技術(shù)與精神這個看似古舊卻仍然極具當下現(xiàn)實性的問題。當代語境中關(guān)于技術(shù)之精神性的討論,大致可分為三個主導方向。一是如穆爾和納斯鮑姆那般重歸古希臘,重思技術(shù)與悲劇精神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二是如艾呂勒那般直面當下的技術(shù)社會,深刻批判各種精神技術(shù)與精神機器,并試圖以去根基之力進行回應乃至變革。三是在德勒茲那里得到深刻闡發(fā)的魔法概念。它不僅將精神性與內(nèi)在性密切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更是經(jīng)由對諸多神秘主義文本的重釋,重新敞開了因果斷裂和幽深能量這兩種極具去根基意味的道路。
關(guān)鍵詞:技術(shù);精神性;實質(zhì)性;艾呂勒;德勒茲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359(2024)06-0021-12
作者簡介:姜宇輝,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guān)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著名的技術(shù)哲學家費爾貝克(Peter-Paul Verbeek)在2005年出版的《事物之用》(What Things Do)一書中,曾不無嚴厲地指摘了(尤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所謂“經(jīng)典技術(shù)哲學”的兩大癥結(jié)①:首先,它們往往過于抽象,僅關(guān)注“大寫的技術(shù)(Technology)”,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具體的技術(shù)對象和現(xiàn)象的多樣性。其次,它們又大多太過悲觀,進而無視了技術(shù)所已經(jīng)、正在或?qū)⒁獛淼母鞣N利好。在這個意義上,即便將其代表人物形容為“技術(shù)恐懼論者(technophobic)”②,似乎也并不為過。與此針鋒相對,費爾貝克倡導技術(shù)哲學理應實現(xiàn)兩個轉(zhuǎn)向:一是轉(zhuǎn)向經(jīng)驗,直面具體多樣的技術(shù)現(xiàn)象;二則是轉(zhuǎn)向“物本身”,深入洞察它們的具體面貌,全面呈現(xiàn)它們與人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
他的這個倡導絕非一己之見,而是恰好呼應了國際學界近一二十年來的一個主流趨勢,不妨就用“物轉(zhuǎn)向”來概括。確實,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guān)注物質(zhì)、對象、物質(zhì)性等等關(guān)鍵問題,而物導向、物本體、物媒介、物文化等等也每每成為期刊與會議的熱點。然而,僅就技術(shù)哲學本身而言,這個轉(zhuǎn)向或許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克服了經(jīng)典技術(shù)哲學的兩個頑疾,但是否又由此走向了乃至深陷于另一個同樣病入膏肓的癥狀,即精神性(spirituality)的缺失?僅從物本身、物與人的角度,是否就足以揭示技術(shù)的本質(zhì)?在一個數(shù)字網(wǎng)絡和人工智能的時代,再來談論精神和精神性是否有些不合時宜?那又如何理解伴隨技術(shù)的不斷加速也同樣在全球蔓延的各種“復魅”潮流呢?在本文之中,我們就試圖結(jié)合艾呂勒(Jacques Ellul)與德勒茲的技術(shù)之思,對技術(shù)與精神性的深刻關(guān)聯(lián)進行反思與闡釋,進而回應一個根本難題:數(shù)字時代所激活的,到底是操控性的精神機器,還是更具差異性與生成力的生命魔法?
一、技術(shù)與精神:從先驗到超越
我們還是從費爾貝克的經(jīng)典概括入手。在他看來,經(jīng)典技術(shù)哲學的立場,亦可以在經(jīng)典哲學史的意義上被界定為“先驗(transcendental)”①。先驗與經(jīng)驗相對,它不僅先于經(jīng)驗,而且是經(jīng)驗得以可能的根本前提。這個立場的最經(jīng)典表述,或許恰是海德格爾在名文《技術(shù)的追問》開篇的那個斷語:“技術(shù)不同于技術(shù)之本質(zhì),……同樣地,技術(shù)之本質(zhì)也完全不是技術(shù)因素。”②僅僅關(guān)注技術(shù)本身是遠遠不夠的,只看到技術(shù)所展現(xiàn)、具有、發(fā)揮的那些可見而明顯的“因素”也是相當膚淺的,真正的技術(shù)之思理應從技術(shù)深入到其背后、深層的本質(zhì),正如哲思者也理應從具體的在者回歸存在本身。
不過,我們的這個援引似乎不無含混。費爾貝克對“先驗”這個關(guān)鍵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康德的批判哲學的意義上,這就與海德格爾的技術(shù)哲學中的先驗概念有所差異。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的導言中曾明確指出,“我把一切與其說是關(guān)注于對象,不如說是一般地關(guān)注于我們有關(guān)對象的、就其應當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認識方式的知識,稱之為先驗的”③。顯然,先驗的思考并不直面對象,而更是反思那些直面對象的理論本身,并致力于將它們建構(gòu)成普遍、完備、必然的理性體系。然而,若反觀、細讀《技術(shù)的追問》的文本不難發(fā)現(xiàn),即便海德格爾在其中的論述始終充溢著濃厚的思辨氛圍,也明確強調(diào)從技術(shù)向本質(zhì)的轉(zhuǎn)向,但他不再僅將技術(shù)視作有待思考的對象,甚至也不限于對既有的各種技術(shù)理論進行辨析與綜合,而更是試圖經(jīng)由技術(shù)來通達更為根本的生存之本真、存在之真理。正是在這里,體現(xiàn)出經(jīng)典技術(shù)哲學的另一個更值得深思的特征,那正是實質(zhì)性(“substantial”)。實質(zhì)性與工具性截然相對④,所強調(diào)的正是這個根本要點:技術(shù)不只是中性的工具,有待人類的感知、思考、使用和評判;正相反,從根本上來說,技術(shù)無論從生存論還是本體論上來看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yōu)先性,它既是人類在世生存的基本結(jié)構(gòu),同時又是世間萬物得以存在、運動、變化的根本前提。
海德格爾的技術(shù)哲學所揭示的正是技術(shù)在生存論上的優(yōu)先地位。因此,“transcendental”這個立場,在他的語境之下理應更恰當?shù)乇晦D(zhuǎn)譯作“超越”。先驗是人類認知與思考的前提,超越則相反,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結(jié)構(gòu)。先驗主要是一個等級鮮明的司法模型,它致力于上升至一個更高的裁決法庭。而超越則更是一個水平延展的視覺、空間模型(“l(fā)ooking beyond”⑤),它試圖從可見的人、事、物拓展至更大的、不可見的界域、背景與關(guān)聯(lián)。技術(sh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構(gòu)成了人類生存的“實質(zhì)性”超越。它不僅建構(gòu)起日常生活中人與物交織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更是全面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構(gòu)成了整個世界的基本媒介與潛在背景。“一切本質(zhì)性的東西,不僅是現(xiàn)代技術(shù)的本質(zhì)性的東西,到處都最為長久地保持著遮蔽”①。這不只是形而上的思辨,而更是提示我們理應深入社會生活,直面現(xiàn)實世界,全面而透徹地洞察技術(shù)的那種不可見的、拓展的、關(guān)聯(lián)性的超越運動。
進而,晚近興起的人類紀思潮則更是將技術(shù)上升至本體論的優(yōu)先性。關(guān)于人類紀有各種不無含混、彼此抵牾的界定,但其原初的含義相對清晰,正是將以技術(shù)發(fā)明為根本動力的人類活動從根本上視為“遍布的、深層的”、并由此足以與各種自然力“相抗衡”的基本力量②。概言之,人類并非只是地球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旁觀者和研究者,甚至也早已不滿足于僅作為改造者和參與者;正相反,人類的技術(shù)力量,正與風、水、光等宏大的自然力一般,深刻、持久甚至往往不可逆地改變著整個地球。從這個方面看,人類紀所展現(xiàn)的已不再只是技術(shù)對人類生存的實質(zhì)性超越,而更是對物質(zhì)世界本身的實質(zhì)性的構(gòu)成、改造乃至操控。但無論是超越還是操控,各派實質(zhì)性的技術(shù)哲學都可以歸結(jié)為這個根本立場:“技術(shù)活動并非外在于、異于我們:它就是我們之所是(what),我們之所為(how)。”③
或許正是因此,實質(zhì)性立場也往往會陷入難以化解和掙脫的困境。這也導致,經(jīng)典的技術(shù)哲學總是多少會帶有濃重的悲觀色彩。既然技術(shù)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結(jié)構(gòu),那么它固然可以引導人類走向超越和自由,但或許首先、起初對人類所施加的更是限制與束縛。既然技術(shù)是世界的根本媒介,那么對于萬事萬物來說,技術(shù)既是根本的原理,但同時又注定是難以掙脫、無從抗拒的命運。在人類的眼中,上升至、深化為實質(zhì)性力量的技術(shù),早已遠非只是透明而中性的工具,而更化身為強力的主宰,進而展現(xiàn)出一種人類無法掌控甚至無從理解的獨立自主的力量。技術(shù)的決定論(“determinism”)、技術(shù)的自律地位(“autonomy”④)以及由此在人類心靈中激發(fā)的揮之不去的悲觀主義的情愫,正是經(jīng)典技術(shù)哲學的三重痼疾⑤。
深陷于實質(zhì)性困境中的人類,顯然舉步維艱;同樣,深陷于實質(zhì)性立場中的哲學,也是困難重重。那么,出路何在呢?精神性或許正是一個要點。在首開先河的著作《技術(shù)與精神》之中,伊格納西奧·格茨(Ignacio L. G?tz)對此給出了諸多關(guān)鍵啟示。首先,他明確指出,之所以要將技術(shù)與精神性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這并非空穴來風或一廂情愿,而是因為“在古希臘,技術(shù)本身就是神圣的”⑥。但神圣性在這里并非僅指向超越而主宰的神明,而更是與人類的生存密切相關(guān),并尤其展現(xiàn)為一種為技術(shù)所引導、所塑造和所解放的精神運動。技術(shù)固然從根本上引導人類走向、模仿著超越的神明與宇宙,但它同時也喚醒著人對自身的反思與關(guān)切。神性與人性之間的此種精神性,正是古希臘所起始的技術(shù)之思的一個根本特征。然而,格茨對這個要點的進一步闡釋初看之下卻令人生疑。一開始,他試圖在海德格爾的意義上將技術(shù)之超越理解為“經(jīng)由創(chuàng)制所實現(xiàn)的解蔽(a made revelation)”⑦。但接下去,他對此種實質(zhì)性超越的精神歷程的理解卻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對柏拉圖的重釋,進而在柏拉圖的理念論的意義上將精神性界定為從可感世界向理念世界的“心靈轉(zhuǎn)向”①。
這樣一種詮釋的策略顯然暴露出明顯的問題。誠如很多學者所指出,技術(shù)作為“創(chuàng)制性的知識(craft knowledge)”,在柏拉圖的哲學中根本上處于一個從屬和低微的位置②。首先,從人類的各種精神能力的等級上來看,技術(shù)顯然要低于那些“高貴的形式”,比如“智慧(sophia)”“努斯(nous)”。其次,從存在的等級來看,技術(shù)所處理的是具體的感性之物,又要遠低于普遍而必然的理念與本質(zhì)。再次,從人類社會的等級來看,從事技術(shù)的人員也顯然低人一等,他們只能是為別人服務,而絕對無法發(fā)號施令。既然如此,那么格茨有何切實的理據(jù)將技術(shù)視作人類的精神超越的本質(zhì)性道路呢?這就涉及對柏拉圖乃至古希臘的技術(shù)概念的重釋,并尤其引出了“脆弱性(fragility)”這個為納斯鮑姆重點闡釋的關(guān)鍵要點。
比如,以戴維·羅奇尼克(David Roochnik)為代表的眾多研究者就指出,技術(shù)在柏拉圖哲學中本就占據(jù)著一個相當重要、不可低估的地位。他在《論藝術(shù)與智慧》一書中,就明確進行了兩點糾偏:首先,對于古希臘的文化與社會來說,“技術(shù)之追問”向來位居核心③;其次,即便就柏拉圖哲學的總體發(fā)展演變來看,技術(shù)也始終是一個相當關(guān)鍵的“范式”④。筆者在這里無力亦無意細審他的考據(jù)與論證的細節(jié),而僅聚焦于技術(shù)作為“理性之悲劇”這個極具啟示的說法。他進一步指出,古希臘哲學中之所以如此重視技術(shù),顯然是因為技術(shù)作為一種基本的人類活動方式和重要的認知方式,體現(xiàn)出很多明顯的優(yōu)點。對此,不妨借用納斯鮑姆的經(jīng)典研究,將其概括為“普遍性”“可教性”“準確性”和“對說明的關(guān)注”這四點,并由此將技術(shù)界定為“把人類智慧審慎地應用于周圍世界,從而得到對運氣的一些控制,技術(shù)與需求的管理、預期以及對未來偶然性的控制都相關(guān)”⑤。
但既然如此,又究竟如何理解柏拉圖反復重申的那個要點和難點,即美德的知識是“非技術(shù)性(nontechnical)”⑥的呢?羅奇尼克敏銳地指出,這或許并不意味著美德與技術(shù)就是對立的,或人們必須否棄技術(shù)才能獲致美德。正相反,這無非只是表明,追尋美德的過程本質(zhì)上注定是一個悲劇性的過程,一個不斷趨向于邊界甚至突破著邊界的運動,但又無法最終完成和實現(xiàn)的理想⑦。悲劇,卻未必悲觀。正是通過此種運動,才讓人類理性的思考技術(shù)不斷經(jīng)受考驗和錘煉,進而推動人類的精神不斷趨于向善和求真的艱難歷程。他在《理性的悲劇》一書中更是明確指出,如尼采那般在古希臘的悲劇精神與蘇格拉底式的理智技術(shù)之間所人為制造的對立顯然失之偏頗①。實際上,在古希臘的技術(shù)概念之中,恰恰體現(xiàn)出人類精神的最深刻的悲劇性運動,它不斷否定自己,超越自身,沖撞著邊界②,卻并未由此就深陷絕望與崩潰的境地,而恰恰是一次次經(jīng)歷了悲劇的時刻而不斷地自我凈化(“katharsis”)、自我肯定③。
二、精神機器:從艾呂勒到庫茲韋爾
實際上,上文重點援引的納斯鮑姆的那個技術(shù)之界定,同樣包含著對此種悲劇精神的深刻洞察。技術(shù),作為理性的運用,首先就要直面一個充滿偶然、未知、風險乃至災禍的世界。技術(shù)的根本精神,因此正是在一個危機四伏、脆弱不安的世界之中明確地將人的不可還原的“被動性”視作思考的起點,然后再一步步腳踏實地、因地制宜地探尋“合理化”的種種可能與途徑。④技術(shù)的悲劇運動,也正是要在“有限風險均衡下”實現(xiàn)“有限控制”,“只信任可變的和不穩(wěn)定的事物”,進而追求一種“柔軟的、有孔的,但具有一定結(jié)構(gòu)的靈魂”。⑤顯然,這樣一種技術(shù)的精神,與近現(xiàn)代社會之中對技術(shù)的那種充滿男性氣質(zhì)的界定(“知識就是力量”,技術(shù)就是控制與征服)或許正相對反。因此,我們在這里頗為認同約斯·德·穆爾(Jos de Mul)的那句名言,即確有必要令“悲劇重生于技術(shù)精神”,進而清醒地意識到,“能夠加強現(xiàn)代技術(shù)的悲劇潛在性的是它們標準的歧義”:一方面,它是“令人敬畏”的咄咄逼人的甚至展現(xiàn)出一種遠超人類掌控之外的巨大的自主力量⑥;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斷將人類一次次拋回到“巨大的脆弱性”面前,從而展現(xiàn)出一種或許為技術(shù)所獨有的“悲劇的人文主義”。⑦
在艾呂勒的技術(shù)哲學之中,我們似乎發(fā)現(xiàn)了此種悲劇精神的最為典型而極致的體現(xiàn)。那不妨圍繞實質(zhì)性、悲劇與精神這三個要點逐次推進。
將艾呂勒的技術(shù)哲學界定為實質(zhì)性的立場,這似乎并無多少疑義。僅就他自己對技術(shù)的那個集中而聞名的定義而言,這一基本特征已然清晰呈現(xiàn)⑧。技術(shù)的本質(zhì)不等于技術(shù),而更是具體技術(shù)背后的那個開放而廣闊的網(wǎng)絡。技術(shù)的形態(tài)本身是多樣的,從物質(zhì)性、社會性到精神性等等不一而足,而不同的技術(shù)形態(tài)又緊密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形成一個龐大的總體。這個總體又由此對人類生活與生存的方方面面施加著全面的堪稱巨細無遺的滲透、影響乃至操控。這幾乎是實質(zhì)性立場的最凝練而深刻的概括了。
進而,他對技術(shù)尤其是現(xiàn)代技術(shù)的七個本質(zhì)特征的描述與解析(《技術(shù)社會》第二章第二節(jié)),也就隨之鮮明體現(xiàn)出決定論、自律論和悲觀主義這三種傾向。關(guān)于艾呂勒的決定論,很多學者也都做出過相似論斷。比如穆爾就明確指出,在“技術(shù)決定論者如艾呂勒”看來,“技術(shù)是自發(fā)的,獨立于人的意圖,……技術(shù)都有自己的動力,這或多或少會作為一種命運的形式降臨在人身上”①。此種近乎宿命論的傾向,在艾呂勒自己的論述中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比如,在他的文本之中,不止一次地反復出現(xiàn)如“不可逆”“必然”“不可避免”“被決定(determined)”等等表述。實際上,他的七重描述可說是層層推進,烘托出“自律”這個終極的難逃的命運。也正是在這里,凸顯出精神性這個關(guān)鍵要點。他明確斷言,“自律就是技術(shù)發(fā)展的最本質(zhì)前提”②,進而將其惡果概括為三個趨勢。首先,愈發(fā)自動、自律、自我組織甚至自我封閉的現(xiàn)代技術(shù)系統(tǒng),不斷獨立于社會的其他系統(tǒng)之外(比如政治與經(jīng)濟),并由此對整個社會施加著愈發(fā)主導的影響。其次,技術(shù)的自律還體現(xiàn)于它對人的精神及其價值的深刻作用。自律的技術(shù)有著自身的動力、目的乃至價值,因而越來越脫離人的認知與控制,還會反過來對人本身施加外來的往往是改造性乃至破壞性的影響。最后,這些自律的趨勢匯合在一起,最終有可能導致技術(shù)對人的取代甚至毀滅。③
但這一番看似如此宿命論和悲觀主義的實質(zhì)性論述,真的就是艾呂勒的最終結(jié)論和根本精神嗎?或許不盡然。也許他更為接近穆爾所闡釋的悲劇精神,而遠非只是杞人憂天甚至無病呻吟的悲觀主義者。他自己在后來的修訂版序言中就明確拒斥了悲觀主義、宿命論(fatalism)這樣的極不恰當?shù)慕缍āK牧霾皇潜^主義,因為他只想進行事實性的客觀的描述,而無意進行任何事先的理論預設和價值判斷。④同樣,他的闡述也不能被歸結(jié)為宿命論,因為二者的邏輯存在著根本差異⑤。宿命論主張,事實已經(jīng)如此,這就是鐵的必然性的規(guī)律,無法更改,只能順從。但艾呂勒的邏輯則更是條件式,即“如果這樣下去,則注定是死路一條”。這亦正是悲觀與悲劇之間的根本區(qū)別。悲觀是一開始就已經(jīng)放棄希望,并阻斷一切別樣的可能性。而悲劇則正相反,它看似也從極為客觀而實證的事實性描述出發(fā),但最終是為了在鐵定的規(guī)律之中撕開裂痕,在冰冷的事實面前敞開可能。這正是艾呂勒反復重申的“辯證立場”⑥:事實是決定論的,但由此為人的自由敞開了別樣的可能。我們看到,這個立場其實理應更恰切地在穆爾的意義上被概括為現(xiàn)代技術(shù)的悲劇人文主義。而著名社會學家莫頓(Robert K. Merton)在為《技術(shù)社會》英譯版所做的序言之中,也是開篇就明確強調(diào)了“悲劇”這個要點。
艾呂勒在《技術(shù)之秩序》這篇提綱挈領(lǐng)的論文之中又更進一步,將此種悲劇精神與人類生存本身的脆弱性(“危險,錯誤,困境,誘惑”⑦)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這就更為契合我們上文的闡述。在這篇論文中,精神及其脆弱性不僅成為明確的主旨,而且它在艾呂勒的技術(shù)哲學中的兩個基本面向也清晰呈現(xiàn)。
第一個面向可概括為“自律”式的技術(shù)精神。這也正呼應著悲劇精神的第一個方面,即當技術(shù)變得越來越龐大而自律,它也就愈發(fā)展現(xiàn)出那個超越人類之外、凌駕于人類之上的近乎神圣的力量。實際上,在這樣的技術(shù)力量面前,人類本身也就會自然地激發(fā)出近乎宗教性的膜拜和敬畏⑧。伴隨著技術(shù)的加速發(fā)展,它在人的眼中也就愈發(fā)近乎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甚至隨心所欲的新的造物主。技術(shù)與宗教之間尤其是新技術(shù)與世界之復魅之間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不僅在艾呂勒的文本之中是一個反復凸顯的主題,也每每為研究者們所關(guān)注和強調(diào)。他自己不僅是一位虔誠而深刻的神學家,也多次結(jié)合如夏爾丹(Teilhard de Chardin)等人的宗教神學的論述深入闡發(fā)了新的技術(shù)與新的宗教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安多尼·阿隆索(Andoni Alonso)更是從晚近興起的所謂“賽博精神性(cyberspirituality)”潮流的角度出發(fā),對艾呂勒的洞見給出了一個現(xiàn)實的印證。①
第二個面向則直指人類的精神自身,尤其體現(xiàn)出上文明示的技術(shù)對于人的精神所施加的全面深入的影響與操控。這個面向由此可被相應稱作“精神技術(shù)”。實際上,艾呂勒在《技術(shù)社會》一書中已經(jīng)明確使用了這個說法,并將其形容為“人根本不可能掙脫【技術(shù)】社會”②這個令人憂懼的傾向。人的精神已經(jīng)徹底跟技術(shù)綁定在一起,幾乎徹底喪失了自我掌控、自我反思、自我決斷的可能。在自律的技術(shù)前面,人反而日漸喪失了自身的自律。即便當我們真的想要激發(fā)自己的自由行動與思考之際,也會悲哀地發(fā)現(xiàn),其實除了技術(shù)限定好的手段之外別無可能。也正是因此,艾呂勒旗幟鮮明地將這個精神的面向與主體性這個哲學主題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人類在技術(shù)社會所面臨的終極難題和困境,難道不正是人的精神愈發(fā)被技術(shù)所操控、改造和取代,進而愈發(fā)從主體淪落為客體?③主體性的喪失與消亡,正是技術(shù)社會所發(fā)明與濫用的各種精神技術(shù)、精神機器對人類所帶來的最嚴重的惡果。
這個面向或許遠比所謂的復魅文化或新宗教更與當下的現(xiàn)實相關(guān)。一方面,艾呂勒在這里所鮮明而深刻地觸及的,無疑近似斯蒂格勒和韓炳哲等人所提出的精神政治理論,但時間卻提前了近半個世紀。這也足見其預見性與洞察力。另一方面,他所著重闡發(fā)的精神機器這個概念又與AI技術(shù)和數(shù)字社會的晚近發(fā)展有著直接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實際上,我們在庫茲韋爾(Ray Kurzwell)的早期名作《機器之心》(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之中,幾乎能夠毫無含混地發(fā)現(xiàn)艾呂勒曾著力批判的每一個要點。首先,庫茲韋爾全書以一種異常宏大的圖景開篇,從宇宙創(chuàng)生講到人類進化,這無疑正是對技術(shù)所給出的至為終極的實質(zhì)性的描繪與界定。技術(shù)遠非只是工具,而更是環(huán)境。技術(shù)的目的遠非只是獲取和改造自然資源,更是體現(xiàn)出一種根本的超越傾向;不僅是對“構(gòu)成材料的一種超越”④,更是對人類生存本身的不斷超越。從根本上說,技術(shù)就是人類進化的終極動力,而且這個動力愈發(fā)展現(xiàn)出不斷加速的趨勢。這也是全書的一個核心論據(jù),即“加速回報定律:秩序以指數(shù)速度增加,時間也隨之以指數(shù)速度加速”⑤。技術(shù)之所以能引領(lǐng)人類的進化,那正是因為它自身的不斷加速的進化能夠給人類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帶來“不斷增強的秩序”⑥:“我們走的道路是用黃金鋪就的,鋪滿了我們絕不會拒絕的好處”⑦。技術(shù)的進化,不僅是無可辯駁的事實,更是值得向往的理想。
若轉(zhuǎn)用納斯鮑姆的那個經(jīng)典界定,恰可以說,技術(shù)如今真正成為拯救脆弱的人、令其得以對抗運氣的根本性力量。但令人遺憾和擔憂的是,如今的技術(shù)早已不再是古希臘意義上的主動思考、能動選擇、積極判斷,而更是蛻變成人類精神只需被動接受的各種現(xiàn)成的“不可避免”的“最優(yōu)解”。在古希臘,主導精神技術(shù)的是集知、情、意于一身的理性思考,由此實現(xiàn)的是理性本身的悲劇運動;而在現(xiàn)代的技術(shù)社會,承擔起這個任務的卻最終唯有智能,由此導向的是近乎宿命的決定論秩序。庫茲韋爾指出,“我認為‘智能’就是對有限的資源(包括時間)進行最優(yōu)化利用以達成各種目標,……就是在混亂中發(fā)現(xiàn)秩序的能力”①。但從混亂到秩序的演變,背后主導的只是技術(shù)的加速回報原理。而這個原理在人類精神之中的根本體現(xiàn),正是那種以計算和算計為宗旨的全面機器化的“智能”。這里,新興的數(shù)字技術(shù)和人工智能所實現(xiàn)的并非各種五花八門的新宗教流派所盲目贊頌的“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即技術(shù)的加速發(fā)展在增強人類力量的同時,也從根本上讓人類掙脫了各種既定的束縛(身體、智能、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有限性”)②。庫茲韋爾式的精神機器更為變本加厲之處在于,它在“增強”的同時也“取代”,它看似提升了人類精神,但或許最終所帶來的只能是毀滅。“一旦掌握了精神過程,我們自然而然地可以模擬智力、情感和心靈體驗,隨心所欲地控制它們,適時鞏固這些體驗”③。這是一個美好的愿景,但又何嘗不是一個終極的夢魘?因為我們總可以反唇相譏:這部看似完美的精神機器,它的開關(guān)到底掌控在誰的手中?
三、去根基(Anarchy)的技術(shù):德勒茲的生命魔法(magic)
固然,確實不乏學者針鋒相對地辯駁道,其實數(shù)字技術(shù)與精神性本是水火不容④。但庫茲韋爾式的宿命論卻顯然在當下有著更多的擁躉、更廣的影響。“不過,讀到后記部分的時候,所有的不確定都會變得明朗起來,就好像您從一開始就打算選擇這樣的順序”⑤,但他的言下之意并不只是讀書,而顯然更影射著這個技術(shù)的精神愈發(fā)自律、人類的精神淪為機器的世界。
那么,艾呂勒的技術(shù)哲學是否給出了進一步回應乃至抵抗的途徑?這就導向了宗教精神這第三個面向,并涉及去根基這個關(guān)鍵概念。誠如范弗里特(Jacob E. Van Vleet)在專研艾呂勒的辯證神學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其實他的神學與哲學這兩個維度始終處于辯證張力之中。他的技術(shù)哲學論述雖然深刻,卻并未給出令人信服的解決方案;反過來說,他從神學的角度雖然明確給出了解答,但理據(jù)上的探討又稍顯薄弱⑥。因此,只有將兩個方面結(jié)合在一起,才能珠聯(lián)璧合。而面對技術(shù)社會所甚囂塵上的各種精神暴力⑦,去根基就是艾呂勒給出的根本解答。然而,他充其量也只是觸及了這個要點,而并未進行深入的推進。拒斥一切暴力和政治⑧,幾乎就是他的全部答案了。如果說對居伊·德波的偏愛,還體現(xiàn)出他揮之不去的烏托邦情結(jié),那么,每每將宗教啟示作為最終解藥,就多少暴露出他的保守與僵化。
那么,不妨就從去根基這個概念著手,由此轉(zhuǎn)向德勒茲的更具魔法精神的技術(shù)之思。關(guān)于這個概念,我在別處已經(jīng)多有論述,在此不必贅言。僅需提及一個對推進下文論證至關(guān)重要的線索。在當代哲學中,海德格爾無疑對此進行過最早、最深入也最持久的思考。而根據(jù)舒爾曼(Reiner Schürmann)的重要研究,他所強調(diào)的一個核心主旨正是“行動”與“根基/本原(archē)”之間徹底斷裂的關(guān)系①,也即,沒有任何理由、原因、原理得以為人的行動提供必然、普遍、絕對的根基。進而,后來阿甘本在《王國與榮耀》一書中重拾這個概念之時,雖然主要是基于神學的背景,但仍然鮮明突出了存在與行動之間的去根基的“間斷(caesura)”②。這正是引導我們思考從技術(shù)向魔法進行轉(zhuǎn)向的一個關(guān)鍵線索。
斯蒂夫斯(Richard Stivers)在《技術(shù)作為魔法》這部首開先河的名作中雖然頗有啟示地將技術(shù)與魔法等同,但初看之下,他對魔法的諸多特征的界定卻與眾多復魅的新宗教潮流大同小異。魔法作為愿望的達成,作為精神能量的激發(fā),作為神秘體驗等等③,在數(shù)字時代復興的各路神學與宗教之中都能找到相應的諸多體現(xiàn)。然而,他在第一章結(jié)尾處點出的愿望及其實現(xiàn)之間的非理性的斷裂與鴻溝(“gap”)卻展現(xiàn)出別樣的去根基的意味④。實際上,正如他自己所坦承,這個洞見明顯源自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對于魔法的聞名界定。首先,魔法不同于技術(shù),后者所秉承的是因與果之間的連續(xù)性關(guān)系(愿望與實現(xiàn),行動與結(jié)果,制作與作品等),但前者則正相反,它在因與果之間插入了別樣的、異質(zhì)的乃至不可理喻的斷裂。⑤其次,魔法也不同于宗教,后者追求至上的理念,對信徒的生命施加限定(“prescribe”),要求其做出自我否定的犧牲;但前者又相反,它竭力激發(fā)、釋放那些“低級”、混沌、暗黑的力量,如欲望、本能、沖動等等,并以各種邪惡的咒術(shù)來肯定它們的精神能量。⑥我們將看到,因果斷裂和幽深能量也正是德勒茲的生命魔法的兩個核心特征。就此不妨說,他的技術(shù)哲學的旨歸,恰恰是從技術(shù)轉(zhuǎn)向魔法,從帶有否定性的悲劇轉(zhuǎn)向充溢著肯定性的生成。這或許也正是他與艾呂勒之間的根本差異所在。
然而,初看之下,他的技術(shù)之思卻又與艾呂勒存在著諸多相似乃至相通之處。首先,和艾呂勒一樣,德勒茲的基本立場無疑也是實質(zhì)性的。雖然“機器”是他的哲學中的一個核心術(shù)語,而且他與加塔利也確實一起談論了眾多形態(tài)各異的機器,但他們所謂的機器遠非具體的對象,也不僅局限于可見的技術(shù)要素,而更是如艾呂勒所曾明確界定的那般指向更大的社會性網(wǎng)絡、異質(zhì)性聚合。因此,說德勒茲的機器首先是社會性的,然后才是技術(shù)性的⑦,這并不為過。
其次,他雖然從未鮮明提出如“技術(shù)社會”這樣的總括性概念,但也確實基于新技術(shù)的發(fā)展對當代社會做出過影響深遠的根本判定:“我們正在進入控制社會,這樣的社會已不再通過禁錮運作,而是通過持續(xù)的控制和即時的信息傳播來運作。”①新的信息技術(shù)對人類生活與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廣泛的深入的甚至徹底的,以至于唯有直面這些新技術(shù)現(xiàn)象,細致描繪、深入剖析,方能洞察這個世界的根本癥結(jié)及治療之道。
再次,即便德勒茲自己未曾明言,但還是有很多后繼者在他的文本之中讀出了濃重的宿命論意味。技術(shù)在加速,加速是不可避免的,加速的技術(shù)在逾越人類的掌控,這些或明或暗的潛臺詞也讓一眾加速主義者將德勒茲奉為自己的理論先驅(qū)。在麥凱(Robin Mackay)和阿瓦內(nèi)西安(Armen Avanessian)合編的《加速主義讀本》中,德勒茲與加塔利就被視作“醞釀期”的代表性人物,而其中收錄的那個《反-俄狄浦斯》中的章節(jié)也幾乎毫不掩飾地以一種宿命論的語調(diào)收尾:“那么,解決方案是什么?……要不斷前行(To go still further),……也許,流還沒有被充分解域和解碼,……不要從這個過程中抽身而退,而是要前行,要‘加速整個過程’。”②這聽上去確有幾分近似艾呂勒式的悲劇精神,但或許骨子里所透露出的更是庫茲韋爾式的對技術(shù)加速的盲信與狂熱。
那么,又如何理解德勒茲的那句名言“相信此世”呢?信念源自何處?顯然,那既不是悲劇人文主義,也不是加速主義,而更是要在數(shù)字技術(shù)的時代去重新激活精神之“魔法”。在此,不妨先對德勒茲的精神性這個往往為人忽視的背景稍加介紹。
之所以精神性在德勒茲研究界鮮有關(guān)注,一是因為缺乏豐富的可資引證的文本依據(jù),二則是出于德勒茲哲學自身的特征。精神性往往與宗教、神學、神秘體驗等等密切相關(guān)。而對于德勒茲,這些顯然都遠非重要的主題。甚至有學者明確指出,“在他那代人中,德勒茲看似對宗教最少關(guān)注”③。如果再從尼采這個重要的思想來源來看,德勒茲身上的那種反宗教的傾向就會顯得更順理成章。但這或許只是一個表面的印象。事實上,德勒茲在對斯賓諾莎、鄧斯·司各脫等人的討論之中已經(jīng)深刻觸及了諸多神學主題,內(nèi)在性就是其中相當關(guān)鍵的一個。此外,在他的文本之中,也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各種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思想家的引文。比如,他早期對數(shù)法(Mathesis)的熱衷④,《差異與重復》中對雅各·波默(Jakob Boeme)和弗龍斯基(Ho?né Wronski)這樣的神秘主義者的屢屢引用,等等,都是明證。更為直接的例證似乎正是《千高原》,其中關(guān)于魔法、巫術(shù)、秘教(occult)的描述幾乎比比皆是。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德勒茲與精神性的關(guān)系呢?如何由此深刻反思“技術(shù)作為魔法”這個主旨呢?辛普森(Christopher Ben Simpson)在《德勒茲與神學》一書中,做出了頗具洞察的闡釋。德勒茲思想中的宗教成分,大致可區(qū)分為世俗(“secular”)與懺悔(“confessional”)這兩個主要類型。其實更準確地說來,不妨稱之為內(nèi)在性宗教與神秘性宗教。前者主要與內(nèi)在性這個核心原理結(jié)合在一起,強調(diào)物質(zhì)與精神的連貫性運動,進而不再僅將精神視作超越于物質(zhì)之外、之上的超越性本原、目的或力量,而更是將其視作自物質(zhì)宇宙內(nèi)部所不斷涌現(xiàn)出的創(chuàng)造性運動。由此,確實可以將傳統(tǒng)宗教和神學中的精神用大寫標示(“Spirit”),反之將德勒茲的內(nèi)在性宗教中的精神寫作復數(shù)、小寫甚或形容詞的形式(“spirits”或“spiritual”)①。實際上,這就與柏格森這個至關(guān)重要的思想來源直接相關(guān)。柏格森在《道德與宗教的兩個來源》一書中,就明確區(qū)分了靜態(tài)宗教與動態(tài)宗教這兩種基本形式:借用《千高原》中的那對相關(guān)的概念,靜態(tài)宗教呈現(xiàn)出結(jié)域、層化、節(jié)段化等等相對靜止、穩(wěn)定、恒常和體制化的面向,它的主要手法是“復制和再現(xiàn)現(xiàn)實的”的神話故事②;但動態(tài)宗教則正相反,它致力于直接回歸、表現(xiàn)生命本身的蓬勃動力和自由的“創(chuàng)造性能量”③。在這個意義上,德勒茲的內(nèi)在性宗教當然是極具動態(tài)的,這也與他在《差異與重復》開篇所暢想的具有舞蹈和音樂般動態(tài)的全新哲學形態(tài)形成呼應。
其實,柏格森論及的動態(tài)宗教已經(jīng)與諸多神秘主義流派直接相關(guān)。而這也正涉及德勒茲的宗教哲學的第二個面向。重視精神的體驗與運動的過程,不斷突破、僭越既定的種種體制與認知的邊界,向未知、異質(zhì)與差異的力量敞開,這些神秘主義的特征也往往滿溢在德勒茲的各種哲學論述之中。但他對秘教、巫術(shù)、神秘主義文本的直接援用或許還只是一個表面現(xiàn)象。在本文的語境之中,更應該揭示他的生命魔法所獨有的去根基面貌,進而與艾呂勒形成呼應、對話與引申。實際上,因果斷裂和幽深能量這兩個要點向來在他的思想發(fā)展之中占據(jù)著相當明顯的位置,甚至可說是兩個貫穿性的關(guān)鍵主題。
首先,在《差異與重復》之中,無根基、去根基(“Ungrund”“sans fond”)這些反復出現(xiàn)的關(guān)鍵詞已經(jīng)是對波默的明顯指涉④。而在第四章重點提及弗龍斯基的“同時具備實證主義、彌賽亞主義和神秘主義性質(zhì)的體系”⑤之時,也更是為了闡釋理念與思想本身的那種“從潛能之物發(fā)展到現(xiàn)實之物”⑥的生成運動。德勒茲在該章最后大量援引的生物學材料,如“胚胎”“卵”“動物”等等,皆是為了更加生動形象地展現(xiàn)此種充滿動力的“精神的戲劇化”⑦過程。我們看到,經(jīng)由微分數(shù)學所深入闡釋的理念的精神運動,既是對內(nèi)在性宗教這條線索的深入推進,但同時又極為切實地為此種看似神秘的運動補充上了具體的機制。用弗龍斯基自己的話來說,他所創(chuàng)發(fā)的正是一種“生命的數(shù)學”,由此試圖對“純粹的生命,絕對而理念性的生命”的那種“絕對具體的綜合(La synthèse concrète)”進行淋漓盡致的描繪與闡釋⑧。生命的數(shù)學與生命的哲學會通在一起,共同建構(gòu)起生命本身的動態(tài)的、內(nèi)在性的宗教,這或許就是德勒茲的真意。
進而,在《意義的邏輯》一書中,不僅深度與表層之辯是一條引導性的主線,也屢屢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幽深能量的種種描述(阿爾托的“無器官的身體”正是其中的典型),而且,準因(quasi-cause)這個別出心裁的概念的引入,又在無根基的深度與后續(xù)的種種思考(時間性、事件、單義性等)之間直接建立起了關(guān)聯(lián)的紐帶。在集中論述準因的第14個系列之中,開始處關(guān)于因果斷裂的明示與整節(jié)最后所回歸的“無基底、精神分裂癥的深淵”⑨恰好形成了完美呼應。這也堪稱是德勒茲的魔法概念的最凝練概括:真正的精神性魔法,一方面要以因果斷裂為基本手法,而另一方面要在“瀕臨深淵”的生命和精神的歷程之中,既不斷汲取著從潛能到現(xiàn)實進行轉(zhuǎn)化的創(chuàng)造性能量,但又時時處處面臨著跌入深淵、陷入毀滅的終極危險。概言之,在這樣“一些非凡的時刻,是哲學在其中使無基底進行言說,并發(fā)現(xiàn)其憤怒、無定形、盲目的神秘語言的那些時刻:波默、謝林、叔本華”①。而如何在一個技術(shù)加速進化的精神機器的時代,重新喚醒哲學的“神秘語言”,在臨于深淵的危險之處不斷喚醒生命的創(chuàng)造性魔法,或許正是從艾呂勒到德勒茲的技術(shù)之思帶給我們的深刻啟示。
四、結(jié)語:哲學作為“精神歷練(ordeal)”
在全文的最后,不妨再圍繞精神性這個核心概念進行拓展性比較。
福柯晚期的著述不僅令“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這句名言廣為人知,也讓哲學和精神性之關(guān)系再度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福柯那里,精神性這個原本帶有濃厚宗教與神學意味的概念,進一步展現(xiàn)出了激進的倫理與政治的向度;同樣,在德勒茲這里,精神性也早已突破了其傳統(tǒng)的狹義,帶著其獨有的魔法之力令我們深思、介入當下的技術(shù)社會。
進而,福柯與德勒茲的精神概念還體現(xiàn)出進一步的內(nèi)在相通。如果說前者的理念最終可概括為“精神修煉(exercises)”,那么,后者則可以相應地被稱作“精神歷煉”②。福柯之所以大量縷述早期基督教的隱修踐行,也正是為了導向“哲學作為苦行,即作為主體的自我構(gòu)成”:“這是一種在主體通過自我與經(jīng)由他者的變化中尋找到其實踐的運用。……正是這個構(gòu)成了哲學的現(xiàn)代存在”。③而對于德勒茲來說,他雖然鮮有直接論及這段古代的歷史,但在那些對于神秘主義、巫術(shù)魔法的直接間接的援引之中,他想要探尋的也正是這樣一種源自深淵又臨于深淵的現(xiàn)代哲學的精神性。
責任編校 張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