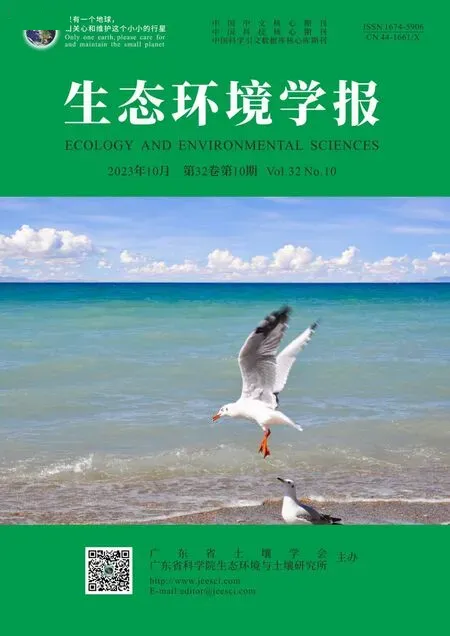柳江不同河網位置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特征及其影響因子差異比較研究
周佳誠,宋志斌,苗芃,譚路,唐濤*
1.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2;2. 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049
環境過濾和空間擴散過程如何影響生物群落的空間格局是淡水生態學近年來關注較多的問題之一(Gothe et al.,2013;Sarremejane et al.,2017;Mruzek et al.,2022)。大多數研究發現,雖然河流生物多樣性格局主要受環境過濾作用驅動(Astorga et al.,2012;Gr?nroos et al.,2013;He et al.,2023),但是空間過程因為限制生物擴散的距離和方向,所以對河流生物多樣性也有重要影響(Cottenie,2005,Karna et al.,2015,Lansac-Toha et al.,2021)。不過現有研究多將同一區域的所有調查樣點視為一個整體,探究環境過濾和空間擴散過程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差異。
然而,河流獨特的樹枝狀網絡結構制約著水生生物的空間遷移和擴散(Chaput-Bardy et al.,2017),對區域水生生物多樣性格局具有重要影響。通常來說,河網邊緣河段之間相對孤立,生物在這些位置間的擴散往往較困難(Brown et al.,2010)。而河網中心位置對上游河流生物具有匯聚作用,使得物種擴散變得相對容易(Altermatt et al.,2013;Trigal et al.,2015)。因此,空間擴散過程對河網邊緣和中心位置的水生生物多樣性具有不同的貢獻(Brown et al.,2011;Heino et al.,2015)。此外,不同河網位置的棲息地環境也有較大差異。河網邊緣由于連通性低,不同河段間的水體理化環境異質性較高(Meyer et al.,2007;Clarke et al.,2008)。河網中心由于連通性高,水體中的物質隨水流在此匯集、交換,該區域的水體理化狀況差異變小。因此,環境因子對河網邊緣和中心位置的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也具有明顯差異(Lansac-Toha et al.,2021)。雖有少數研究比較了不同河網位置生物多樣性的差異,但多集中于比較物種數量的變化(Hitt et al.,2011;Mazor et al.,2016),而對群落組成的影響差異研究較少。
大型底棲動物(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是指生命周期的全部或者至少一段時間生活在水體底部的大于500 μm 的水生無脊椎動物群(劉建康,1999)。河流大型底棲動物多樣性高,時空異質性分布特征明顯,且對環境變化響應敏感(Williams-Subiza et al.,2020;Masese et al.,2021;Quanz et al.,2021),作為水生生物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是河流生態學關注的重要類群之一。本研究基于柳江水系大型底棲動物的調查數據,探究水系內的河網邊緣和河網中心位置之間的大型底棲動物群落格局差異,并比較不同河網位置環境因子和空間因子對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組成的影響差異。擬驗證以下科學問題: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組成差異在河網邊緣受環境因子和空間因子的共同影響,在河網中心主要受環境因子的影響。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與樣點設置
柳江位于107°27′—110°34′E,23°41′—26°30′N間,發源于貴州省獨山縣,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象州縣匯入西江,是西江水系第二大支流(盧玉典等,2023)。柳江干流全長751 km,流域面積為58 520 km2,流域內水系發達,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大部分屬喀斯特地貌(楊昆等,2016)。該區域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四季較分明,年均溫18—20 ℃,年降水量1 400—1 800 mm,4—8 月為雨季,雨季降水量占全年72%(李佳靜等,2020)。流域內森林植被豐富,生境復雜多樣,有較高的生物多樣性。
于2022 年3—4 月低水位期對柳江水系81 個樣點開展調查。本研究根據Strahler 法(Strahler,1957),以柳江1∶1 250 000 水系圖為依據,確定各調查樣點的河流級別。沒有任何支流匯入的源頭河流為1 級河流,兩個同級別的河流匯流后河流級別便升高1 級,兩個不同級別的支流匯流后河流級別仍然為匯流前級別較高的那一級,依次類推,直到最下游樣點。研究中將1、2 級河流樣點視為河網邊緣樣點,大于2 級的河流樣點作為河網中心樣點(Henriques-Silva et al.,2019)。按此分類,共有39個樣點位于河網邊緣位置,42 個樣點位于河網中心位置(圖1)。

圖1 柳江流域樣點分布圖Figure 1 Locations of the sampling sites in the Liujiang River network
1.2 大型底棲動物數據
使用網篩孔徑為0.42 mm 采樣面積為0.09 m2的索伯網(Surber net)采集大型底棲動物。可涉水樣點在整個河段選擇采樣區域,不可涉水樣點則在水深小于0.5 m 的近岸河段采樣。每個樣點在縱向100 m 范圍內根據不同底質類型所占比例采集5 個重復。采樣時將索伯網放置于河床上,先隨水流仔細清洗網內的大型石塊,使石塊上的大型底棲動物流進索伯網內,然后攪動河床下的底質,攪動的深度大于10 cm,使底質中的大型底棲動物隨水流進入索伯網內。采樣結束后將采集到的大型底棲動物揀出,將每個樣點的5 個重復樣本裝入同一個標本瓶,并用95%的乙醇溶液現場固定。標本帶回實驗室后,參照國內外相關分類文獻(Morse et al.,1994;Merritt et al.,2019;周長發等,2003),在解剖鏡下鑒定并計數。大部分動物鑒定到屬級別,搖蚊等少數類群鑒定到亞科級別。根據鑒定數據計算大型底棲動物的分類單元數、密度及平均相對豐度,并將平均相對豐度大于1%的分類單元定義為優勢分類單元。
1.3 環境因子
大型底棲動物采樣前,用水質分析儀(YSI ProPlus)測定水體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DO)、電導率(Conductivity,Cond)和濁度(Turbidity,Turb)。此外,用預先清潔的聚乙烯瓶采集約100 mL水樣,并用濃硫酸酸化至pH<2,低溫保存運回實驗室。然后,根據《水和廢水監測分析方法》利用連續流動水質分析儀(SAN++,Skalar)測定總氮(Total nitrogen,TN)、總磷(Total phosphorus,TP)和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等水質指標(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2)。采集底棲動物的同時,測量每個采集處的水深,將5 個重復采樣處的平均水深作為樣點的水深。用直讀式流速儀(Global Water FP101)測定每個大型底棲動物采集處的流速,將5 個重復采樣處的平均流速作為樣點的流速。
1.4 空間因子
大部分河流大型底棲動物屬水生昆蟲,它們在幼蟲時期主要隨水流沿河道擴散,成蟲階段有翼,可以在陸上進行飛行擴散(Canedo-Argueelles et al.,2015;Arce et al.,2023)。為量化大型底棲動物的空間擴散過程,根據采樣點的經緯度坐標計算2 個距離指標:陸上距離(Overland distances)和河道距離(Watercourse distances)。陸上距離是指樣點間的直線(歐幾里得)距離,河道距離表示沿河流網絡樣點間的成對最小路徑距離。這兩種距離都使用ArcGIS 10.5(ESRI,2017)軟件計算,其中陸上距離用點距離分析工具計算,河道距離則用Network Analyst 工具計算。
1.5 數據分析
分析前對大型底棲動物豐度數據和除pH 外的環境因子數據進行log(x+1)轉換,以降低極端值的影響,并根據Pearson 相關系數剔除相關性較高的環境因子(r>0.8)。
首先,用Mann-Whitney U 非參數檢驗分析河網邊緣和河網中心的環境因子、大型底棲動物分類單元數和密度的差異。其次,基于每個樣點每種大型底棲動物的密度數據計算樣點間的 Bray-Curtis 相異度作為β 多樣性指數,Bray-Curtis 相異度的取值范圍由0(兩個群落組成完全一致)到1(兩個群落完全不同)。用基于Bray-Curtis 相異度的非度量多維尺度分析(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NMDS)展示河網邊緣和河網中心的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組成差異。該分析設定,當Stress 值小于0.2 時,表示NMDS 結果合理(Khalaf et al.,2002)。使用置換多元方差分析(Permutational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PERMANOVA)進一步檢驗河網邊緣和河網中心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的差異顯著程度。該方法是基于F 統計的方差分析,依據距離矩陣(本研究為Bray-Curtis 相異度)對總方差進行分解的非參數多元方差分析方法(Anderson,2001)。接著,用“bio-env”函數篩選出與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相關性最高的環境因子組合。“bio-env”函數能夠對所有可能的環境因子組合進行檢驗,并計算出群落相異性矩陣和不同環境因子組合之間的相關性,從而得出與群落相關性最高的環境因子組合(Clarke et al.,1993)。最后,使用Mantel test 分析檢驗大型底棲動物Bray-Curtis 相異度(β 多樣性)與環境距離矩陣(使用 “bio-env” 篩選出的環境因子計算歐氏距離)、空間距離矩陣(陸上距離矩陣、河道距離矩陣)之間的相關性(Astorga et al.,2012)。當Mantel 相關性指數r>0,表示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隨著環境距離、空間距離的增加而增加。此外,應用Partial Mantel test 分析來檢驗環境距離矩陣和空間距離矩陣對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的單獨影響。
以上分析均在R(Version4.1.3)中進行。Mann-Whitney U 檢驗使用“stats”包,置換多元方分析(PERMANOVA)、非度量多維尺度分析(NMDS)、bio-env 和Mantel 檢驗均使用“vegan”包。
2 結果
2.1 理化環境狀況
根據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對柳江水質狀況進行分析(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等,2002)發現:總氮、總磷濃度在河網邊緣多數樣點達到Ⅲ類水質標準,在河網中心多數樣點達到Ⅳ類標準;溶解氧和化學需氧量含量在河網邊緣和河網中心大都達到I類水質標準。總體而言,河網邊緣樣點的水質優于河網中心樣點。Mann-Whitney U 檢驗發現,大部分理化環境指標在河網邊緣和中心位置間存在顯著差異。電導率、總氮、化學需氧量和水深在河網邊緣較低,而溶解氧和流速則在河網邊緣較高(表1)。

表1 河網邊緣和河網中心環境因子差異Table 1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between the edge and center positions of the Liujiang River network
2.2 不同河網位置大型底棲動物群落格局差異分析
2.2.1 物種組成及優勢種差異
本研究共采集到大型底棲動物5 門8 綱21 目75 科132 個分類單元。分別隸屬于節肢動物門的昆蟲綱和甲殼綱、環節動物門的蛭綱和寡毛綱、軟體動物門的腹足綱、雙殼綱、線形動物門的鐵線蟲綱,扁形動物門的渦蟲綱。其中,昆蟲綱共109 個分類單元,占總分類單元數的82.6%。
河網邊緣、中心位置樣點采集到的大型底棲動物分類單元數分別為129 和114 個,河網邊緣、中心位置的平均分類單元數分別為32 和22,平均密度分別為2.29×103ind·m-2和1.04×103ind·m-2。差異性檢驗顯示河網邊緣樣點的大型底棲動物豐富度和密度均較河網中心位置高(圖2)。

圖2 不同河網位置大型底棲動物分類單元數和密度箱線圖Figure 2 Boxplots displaying differences in taxonomic units and density of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s between the edge and center positions of the Liujiang River network
平均相對豐度大于1%的大型底棲動物分類單元在河網邊緣有12 個,在河網中心有10 個(表2)。花翅蜉屬(Baetiellasp.)和高翔蜉屬(Epeorussp.)為河網邊緣獨有的優勢分類單元。在河網邊緣和中心位置樣點共有的10 個優勢分類單元中,四節蜉屬(Baetissp.)、寬基蜉屬(Choroterpessp.)、扁蜉屬(Heptageniasp.)、細蜉屬(Caenissp.)、鋸形蜉屬(Serrattellasp.)等蜉蝣目類群和蚋(Simuliumsp.)在河網邊緣的平均相對豐度較高,而直突搖蚊亞科(Orthocladiinae)、長足搖蚊亞科(Tanypodinae)、搖蚊亞科(Chironominae)、朝大蚊屬(Antochasp.)等雙翅目類群則在河網中心的平均相對豐度較高(表2)。

表2 不同河網位置優勢分類單元相對豐度Table 2 Relative abundance of dominant taxonomic units of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s between the edge and center positions of the Liujiang River network %
2.2.2 群落相似度差異
非度量多維尺度分析(NMDS)排序圖顯示,柳江水系河網邊緣位置與和中心位置的樣點在NMDS 軸1 上有明顯分離(圖3)。置換多元方差分析(PERMANOVA)表明,河網邊緣和中心位置樣點的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組成存在顯著差異(F=4.96,P=0.001)。

圖3 基于Bray-Curtis 相異度的柳江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組成非度量多維尺度分析(NMDS)排序圖Figure 3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NMDS) plot based on inter-site Bray-Curtis dissimilarity of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 communities in the Liujiang River network
2.3 不同河網位置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與環境距離、空間距離的關系差異
用“bio-env”篩選出與河網邊緣大型底棲動物群落最相關的環境因子。其中,溶解氧和水深與河網邊緣和中心位置的大型底棲動物組成都顯著相關;此外,河網邊緣樣點的大型底棲動物組成還與化學需氧量有關,而河網中心位置樣點則還受流速、總氮的影響(表3)。

表3 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與空間距離(陸上、河道)和環境距離的相關性Mantel 檢驗Table 3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 beta diversity and spatial distances (Overland, Watercourse)and environmental distances with Mantel test and partial Mantel test
Mantel test 分析顯示(表3),河網邊緣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與環境距離、陸上距離、河道距離皆顯著相關,兩個空間距離對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的單獨影響相近,而環境距離的單獨影響約為空間距離的2 倍。河網中心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與環境距離、陸上距離顯著相關,但陸上距離主要通過與環境距離的協同作用影響β 多樣性。
3 討論
通過分析柳江水系的理化環境指標發現,河網邊緣位置電導率、總氮、化學需氧量和水深比河網中心低,而溶解氧和流速比河網中心高。河網邊緣位置因為水淺、光照充足,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強,溶解氧含量高。而中心位置水深增加,水生植物光合作用減弱,溶解氧減少。現場調查時發現,中心位置樣點附近多有城鎮,并且存在工業污染。顯然,過多的人類活動可能是導致水體中總氮、化學需氧量和電導率升高的主要原因,以往關于柳江的研究也證實了這點(李鑫等,2021;張婉軍等,2021)。此外,河網中心位置由于水域開闊,僅在淺水緩流區采樣,所以采樣時測定的流速較低。
本研究發現,柳江水系不同河網位置的環境特征和大型底棲動物群落格局存在明顯差異。河網邊緣大型底棲動物物種豐富度和密度都顯著高于河網中心,這與河網邊緣位置水淺、溶解氧含量較高等環境特點有關(Richardson,2019)。當然,因河網邊緣位置大部分樣點為可涉水河段,為全河段采樣,而河網中心位置由于水較深,大部分樣點僅在淺水區采樣,采樣不充分等因素也可能影響了河網中心的大型底棲動物多樣性。與柳江河網位置的環境特點相對應,調查發現雖然河網邊緣與河網中心位置的優勢分類單元大都為蜉蝣目和雙翅目,但耐水流沖刷的能力強,更適應高氧環境(Poff et al.,2006;Belmar et al.,2013)的蜉蝣目類群平均相對豐度在河網邊緣位置更高。而更適應相對低氧環境的雙翅目類群平均相對豐度則在河網中心位置較高(Calapez et al.,2021)。此外,邊緣位置的大型底棲動物還受化學需氧量影響。因為這些位置的河流靠近河岸帶(Turunen et al.,2017),有機物(如枯枝落葉)較多,影響水體中化學需氧量的濃度(楊鈣仁等,2012),但這些有機物也可作為大型底棲動物的食物來源(Oester et al.,2023),從而影響其生長。中心位置的大型底棲動物還受流速和總氮影響。較慢的流速可能造成溶解氧供應不足,影響需氧量高的大型底棲動物生存。總氮的增加可能引發藻類的大量生長(Dodds,2006),進而影響大型底棲動物的分布。本研究表明無論是在河網邊緣還是河網中心,環境距離與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均顯著相關。并且環境距離與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的相關性比空間距離更高,說明環境因子對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組成的影響比空間因子更大(Gothe et al.,2013;He et al.,2020;Zheng et al.,2023)。
通過分析不同河網位置空間距離與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的關系,發現空間距離(陸上距離、河道距離)與河網邊緣的大型底棲動物β 多樣性顯著相關,但在河網中心則關聯性不顯著。因為河網邊緣的群落之間相對孤立,大型底棲動物在這些位置之間擴散更加困難而導致群落相異度增加(Wang et al.,2018;Gauthier et al.,2020;Li et al.,2021)。而在河網中心受水流單向流動和交匯作用等的影響,不同樣點間的大型底棲動物物種交換、補充變得相對容易。所以,河網中心的大型底棲動物群落格局主要受環境因子的影響。
4 結論
通過比較柳江水系不同河網位置的大型底棲動物群落格局發現,河網邊緣大型底棲動物物種豐富度和密度都顯著高于河網中心位置。溶解氧、水深、化學需氧量、總氮和流速是影響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空間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大型底棲動物群落格局在河網邊緣受環境因子和空間因子的共同影響,在河網中心則主要受環境因子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