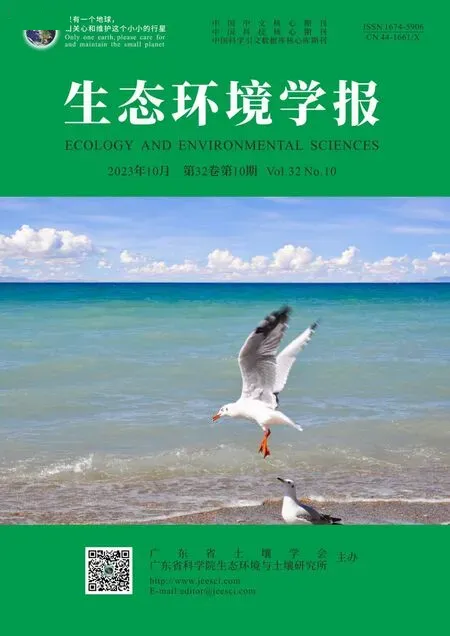圍網與圍塘養魚下沉積物微生物量和群落結構特征差異
梁川,楊艷芳,俞姍姍,周利,張經緯,張秀娟
1. 安徽師范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江淮流域地表過程與區域響應安徽省重點實驗室,安徽 蕪湖 241002;2. 安徽師范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隨著自然水產資源不能滿足人們對水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水產養殖業逐漸成為我國水產品的重要來源而迅速發展。微生物是水產養殖區生態系統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評價養殖區生態系統健康的重要指示生物(Vezzulli et al.,2002;Liu et al.,2020)。漁業養殖是水產品養殖重要組成部分。漁業養殖活動可導致肥料、抗生素、餌料和魚類排泄物大量積累(Wu,1995;Kucuksezgin et al.,2021),改變了養殖區沉積物環境狀況(裘瓊芬等,2013;Zhou et al.,2020;Kucuksezgin et al.,2021),進而影響了微生物群落結構(裘瓊芬等,2013;Zhou et al.,2020;Zhou et al.,2021)。有研究表明漁業養殖改變了原始濕地土壤微生物組成(周雅心等,2021),導致土壤細菌、真菌、革蘭氏陽性及革蘭氏陰性細菌的生物量顯著升高(張廣帥等,2020)。漁業養殖也可促使海邊濕地沉積物細菌密度及生物量增長了3 倍多(Chelossi et al.,2003),且革蘭氏陰性細菌等耐藥性微生物數量增加(Chelossi et al.,2003;Zhou et al.,2021)。而高度集約化的網箱養殖模式下沉積物細菌群落多樣性和均勻度均顯著降低(裘瓊芬等,2013)。魚類養殖品種、養殖規模和魚食來源對沉積物微生物組成和群落結構特征均有顯著影響(Chelossi et al.,2003;Tamminen et al.,2011;Liu et al.,2020)。同時漁業養殖還可能導致沉積物環境潛在的致病細菌和病原微生物富集(Vezzulli et al.,2002;Tamminen et al.,2011;Zhou et al.,2021)。圍網和圍塘養殖是淡水湖泊兩種主要漁業養殖模式。圍網養殖區保持著與湖泊的優質水環境聯通性,溶解氧豐富,養殖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的稀釋和擴散也較迅速,但也可能存在因投放餌料和魚類排泄物導致水體環境污染的問題(吳慶龍等,1995)。圍塘養殖與湖泊自然水域隔絕,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水體生態系統,其餌料與抗菌劑投放和魚類排泄物等產生的污染均在圍塘內。當前這兩種漁業養殖模式下沉積物環境差異及其對微生物群落結構影響的研究甚少。長江沿江湖泊群是我國水產養殖重要水域,“十年禁漁”政策更是促進了該水域水產養殖業蓬勃發展。因此,本文采集了長江沿江湖泊菜子湖圍網與圍塘養殖區沉積物樣品,分析了沉積物基本物理化學性質指標,同時利用PLFAs 方法解析了微生物量和群落組成,探討養殖方式對養殖區沉積物微生物的影響及其生態指示意義,以期豐富養殖模式對養殖區微生物生態影響的認識,同時為科學合理漁業養殖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菜子湖位于安徽省長江北岸,跨安慶及銅陵兩市,位30°43′—30°58′N,117°01′—117°09′E,由菜子湖、嬉子湖和白兔湖3 部分組成,是長江中下游濕地和安徽省沿江濕地自然保護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前“引江濟淮”工程雙線引江布局的主力線路,總面積17.3×103hm2。4—10 月為豐水期,11 月至翌年3 月為枯水期。研究區自上世紀50 年代開始大規模圍墾,至80 年代開始退耕還湖,且不同退耕還湖區域因地制宜恢復成自然濕地或水產養殖區。2017 年開始,由于“引江濟淮”工程開始拆除菜子湖圍欄網,禁止湖面養殖。
1.2 樣品采集
菜子湖湖區漁業養殖模式主要有兩種。圍網養殖區是在天然湖泊水域中進行的圍欄網養殖區;圍塘養殖區是指人工筑壩與自然湖泊水體完全隔開的養殖區。魚類養殖品種主要是鰱魚(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草魚(Ctenopharyngodonidella)、青魚(Mylopharyngodonpiceus)、鳙魚(Aristichthysnobilis)和鱖魚(Sinipercachuatsi)。2018 年3 月,沿菜子湖邊水域分別選取6 個漁業養殖區,在區內又分常年淹水區樣地和季節性淹水區樣地。季節性淹水區在豐水期,尤其每年6—8 月處于淹水狀態,而枯水期露出水面。T1、T2和T3位于開圍網養殖的季節性淹水區,T4、T5、T6位于圍塘養殖的季節性淹水區。季節性淹水區優勢種植被均為苔草(Carexspp),伴生少量蘆葦(Phragmitesaustralis),但圍網養殖區植被覆蓋度為75%—95%,而圍塘養殖區植被覆蓋度為20%—70%。由于2018 年春旱,采樣時植被長勢較差。T1位于嬉子湖水域西南岸的觀蓮咀,T2位于先讓村西北側,T3位于盛家咀頭西南側,T4位于兔兒咀,T5位于西瓜咀,T6位于走馬墩湖。D1、D2、D3位于圍網養殖的常年淹水區,D4、D5、D6位于圍塘養殖的常年淹水區。D1位于走馬墩湖西南側,D2、D5位于菜子湖水域東側,其中D5位于王家咀西南處,而D2位于D5的堤壩外區域,D3位于盛家咀頭西南側。D4位于小木咀南側;D6位于盛家咀頭南側。每一個樣地由3 個樣點組成,每個樣點樣品再由3 個采樣點的土壤混合而成。分別用鐵鏟和抓斗式采樣器采集季節性淹水區和常年淹水區沉積物樣品。采樣深度均約為10 cm。沉積物樣品用聚乙烯塑料袋密封編號,裝入存有冰袋的冷藏箱臨時存儲和運輸至實驗室。
1.3 沉積物基本理化性質測定
沉積物有機質、全磷、有效磷、全氮、堿解氮等基本理化性質的測定方法主要參照魯如坤主編的《土壤農業化學分析方法》(魯如坤,2000)。沉積物粒度采用貝克曼COULTER LS230 型激光粒度分析儀進行測定,沉積物pH 按水土質量比2.5∶1測定。
1.4 沉積物微生物PLFAs 分析
采取修正的Bligh & Dyer 方法進行磷脂脂肪酸提取(Bossio et al.,1998)。具體步驟:取3 g 凍干土于50 mL 三角瓶中,加入磷酸緩沖液:氯仿:甲醇緩沖液,體積比為3.2∶4∶8,振蕩提取脂類;通過固相抽提柱層析得到磷脂脂肪酸,然后經過堿性甲基化得到磷脂脂肪酸甲脂,采用MIDI 微生物鑒定儀(Agilent 7890A)進行檢測。將單個磷脂脂肪酸摩爾百分比低于0.4%的剔除,篩選得到37 種標記物,磷脂脂肪酸鑒定分為6 類(Frostegrd et al.,1996;于小彥等,2020):真菌2 種(16:1 ω5c,18:2 ω6c)、放線菌5 種(16:0 10-methyl、17:1 ω7c 10-methyl、17:0 10-methyl、18:1 ω7c 10-methyl、18:0 10-methyl)、革蘭氏陽性細菌8 種(14:0 iso、15:1 iso ω6c、15:0 iso、15:0 anteiso、16:0 iso、17:1 iso ω9c、17:0 iso、17:0 anteiso)、革蘭氏陰性細菌11 種(16:1 ω9c、16:1 ω7c、17:1 ω8c、17:0 cyclo ω7c、18:1 ω9c、18:1 ω7c、19:1 ω6c、19:0 cyclo ω7c、20:1 ω9c、21:1 ω3c、22:1 ω3c)、厭氧菌2 種(15:0 DMA、18:0 DMA)、其他細菌9 種(14:00、15:00、16:0 N alcohol、16:00、17:1 anteiso ω9c、17:00、18:00、20:00、22:00)。
1.5 數據處理與分析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軟件進行微生物多樣性指數計算,并對實驗數據進行處理;采用SPSS 20.0 對數據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應用Origin 2019繪制柱狀圖及顯著性可視化;應用CANOCO 5.0 基于DCA<3.0,選擇冗余分析(RDA)來評估細菌群落與環境因子間的關系;應用R 語言(R.4.1.2)繪制相關性熱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沉積物物理化學性質指標
兩種養殖方式下沉積物粒度組成以粉粒為主,其中圍網養殖區常年淹水沉積物粉粒含量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表1)。常年淹水沉積物pH 和全磷顯著高于季節性淹水,但不同養殖模式間差異不顯著;圍塘養殖區常年淹水沉積物有機質和全氮含量顯著低于其他3 個生境,而其他3 個生境間差異不顯著;圍塘養殖區的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堿解氮顯著高于其他3 個生境,而其他3 個生境間差異不顯著;而4 個生境間有效磷含量均無顯著性差異。總體上,除圍塘養殖區沉積物堿解氮顯著高于圍網養殖區,養殖模式對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其他指標均未有顯著性影響;圍網養殖區常年淹水沉積物粉粒、有機質和全氮含量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其他指標的兩種養殖模式間無顯著差異。

表1 研究區沉積物基本理化性質特征Table1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ediments in the studied area
2.2 沉積物各類群微生物PLFAs 含量
不同生境下微生物生物量主要以細菌為主(表2)。圍網養殖區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總生物量、細菌總生物量、放線菌、厭氧菌和真菌生物量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而2 種養殖模式下季節性淹水沉積物革蘭氏陽性菌(G+)和革蘭氏陰性菌(G-)生物量間無顯著性差異。圍網養殖區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總生物量、細菌總生物量(B)、放線菌、厭氧菌生物量、G+、G-和真菌(F)生物量均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

表2 研究區不同養殖模式下沉積物微生物PLFAs 含量Table2 The amount of sediment microbial PLFAs under different fish farming models in the studied area
2.3 沉積物微生物群落結構和多樣性
研究區沉積物微生物以細菌為主,真菌生物量相對比例較小(2.86%—5.32%)(圖1a)。圍網養殖區常年淹水沉積物真菌生物量相對比例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其他各種群微生物生物量相對比例間無顯著性差異。圍網養殖區沉積物F/B 均高于圍塘養殖區,但僅常年淹水生境下達到顯著性差異。圍網養殖區沉積物Shannon 指數均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Simpson 指數則低于圍塘養殖區,但均未達到顯著水平。季節性淹水和常年淹水沉積物G+/G-在不同養殖模式下均未有顯著性差異(表3)。

圖1 不同養殖模式下微生物各種群PLFAs 含量相對比例及其顯著性檢驗Figure 1 Relative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microbial population PLFAs in total microbial PLFAs under different fish farming model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ests
2.4 微生物指標與沉積物因子間的相關性分析和冗余分析
研究區季節性淹水沉積物pH 與微生物總量、G-和真菌生物量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季節性淹水沉積物有機質與總微生物量、G-和放線菌生物量達顯著正相關關系(圖2aI)。常年淹水沉積物粉粒含量與總細菌生物量和除了放線菌微生物外的其他類群生物量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常年淹水沉積物有機質與總微生物量、G+、放線菌、真菌和厭氧菌生物量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而全氮與放線菌、真菌和厭氧菌生物量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圖2aⅡ)。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Shannon 指數與粘粒含量呈顯著正相關,與砂粒和全磷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而Simpson 指數與粘粒含量顯著負相關,但與砂粒和全磷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F/B 與有效氮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圖2bⅢ)。常年淹水沉積物G-生物量相對比例與粘粒和pH 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與砂粒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真菌生物量相對比例與粘粒、pH 和全氮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與砂粒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其中G+/G-與粘粒和pH 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而與砂粒呈顯著正相關;F/B 與粉粒含量、有機質和全氮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與砂粒量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圖2bⅣ)。
研究區微生物PLFAs 含量和環境因子間的RDA 分析表明,季節性淹水沉積物的物理化學性質指標僅能解釋71.8%的沉積物微生物量差異(圖3a)。有機質是解釋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量差異的主要環境因子,其單獨解釋量高達 36.2%(P=0.010);其次pH 與全磷解釋量分別為25.4%(P=0.046)和21.4%(P=0.072)。若按照不斷加入環境因子后所能增加的解釋量計算,有機質具有季節性沉積物各菌群微生物量差異最大的累積解釋量(36.2%),且達到顯著水平(P=0.010)。本文所分析的理化性質指標能解釋86.6%的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量差異(圖3b);粉粒、有機質、全氮、有效磷和全磷是解釋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量差異的主要環境因子,其單獨解釋量分別為45.1%、31.4%(P<0.01)、27.7%、19.0%和14.1%(P<0.05);具有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量差異較大累積解釋量的是粉粒、有效磷、有機質,其解釋量分別為45.1%、25.9%和10.8%(P<0.01)。

圖3 研究區微生物生物量和群落結構指標與環境因子的RDA 分析Figure 3 RDA analysis of microbial biomas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dex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ied area
RDA 分析結果表明本研究所分析的理化性質指標僅能解釋39.4%的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群落結構差異(圖3c);砂粒是解釋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群落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單獨解釋量為16.1%(P=0.080),也是最大累積解釋量因素(16.1%)。所分析常年淹水沉積物理化性質指標能解釋68.0%的微生物群落結構差異(圖3d);有機質、粉粒、有效磷、砂粒和全氮是解釋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群落分布的主要環境因子,其單獨解釋量分別為35.9%(P=0.006)、20.7%(P=0.030)、18.1%(P=0.016)、13.4%(P=0.056)和11.8%(P=0.088);有機質、砂粒和有效磷是具有較大累積解釋量的環境因子,其累積解釋量分別為35.9%、12.5%和12.0%,且均達到顯著水平(P<0.01)。
3 討論
微生物PLFAs 既能反映出微生物數量的大小,又能反映出微生物活性潛力(Frostegrd et al.,1996;Bossio et al.,1998)。有研究發現漁業養殖可導致沉積物微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增長(Chelossi et al.,2003)。研究區除G+細菌和G-細菌生物量外,圍網養殖區季節性淹水沉積物中微生物PLFAs 總量、細菌總PLFAs 量和其他微生物量均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圍網養殖區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PLFAs總量、細菌總PLFAs 量、各類細菌生物量和真菌生物量均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高的養分條件是沉積物具有較高微生物量的重要因素(Bahram et al.,2018;于小彥等,2020)。漁業養殖活動可促使養殖區餌料、魚類排泄物和殘體大量富集(Wu,1995;Kucuksezgin et al.,2021),促使水體和沉積物養分含量大量提升(Zhou et al.,2020;Kucuksezgin et al.,2021)。確實研究區圍網養殖區季節性淹水和常年淹水沉積物養分含量均高于圍塘養殖區,但在常年淹水沉積物中表現更為顯著(表1)。相關性分析也表明,研究區季節性淹水沉積物有機質與總微生物量、G-和放線菌生物量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常年淹水沉積物有機質與總微生物量、G+、放線菌、真菌和厭氧菌生物量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常年淹水沉積物全氮與放線菌、真菌和厭氧菌生物量均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RDA 分析進一步表明解釋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量差異的有機質、pH 和全磷等環境因子中,有機質累積解釋量最高;而解釋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量差異的粉粒、有機質、全氮、有效磷和全磷等環境因子中,粉粒、有效磷和有機質具有相對較大的累積解釋量。有研究發現粘粒和粉粒含量相對高的土壤擁有更高的微生物量(劉秉儒等,2019),研究區圍網養殖下常年淹水沉積物粉粒含量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但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則無顯著性差異。總體上本文所分析的理化性質指標能解釋71.8%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量差異和86.6%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量差異,表明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影響養殖區沉積物微生物量的差異。有研究表明人類活動干擾可導致土壤微生物PLFAs含量下降(Martensson et al.,2012),如在漁業養殖過程中會施用抗生素、抗菌劑等(Chelossi et al.,2003;卓麗等,2019),均可能促進養殖區沉積物微生物量降低。相對于與自然水體連通的開放式圍網養殖區,圍塘養殖區封閉式環境下投入的抗生素類污染物更容易在沉積物累積,不利于沉積物微生物生長。因此,研究區不同養殖模式導致沉積物理化性質及抗生素類污染狀況存在差異,促使圍塘養殖區沉積物微生物量顯著低于圍塘養殖區;微生物量較好地響應了研究區養殖模式對沉積物生態系統的影響,但在常年淹水沉積物中表現更為顯著。
漁業養殖不僅影響養殖區沉積物微生物量,也影響著微生物群落結構(裘瓊芬等,2013;Zhou et al.,2020;Zhou et al.,2021)。養殖區整體上兩種養殖模式下季節性淹水沉積物放線菌生物量相對比例顯著高于常年淹水沉積物,而常年淹水沉積物真菌生物量相對比例顯著高于季節性淹水沉積物。這符合土壤放線菌是好氧腐生細菌的屬性(de Menezes et al.,2015),也與濕地土壤圍墾養殖可以導致真菌生物量升高(張廣帥等,2020;周雅心等,2021)的結果相似。圍網養殖區季節性淹水和常年淹水沉積物真菌生物量相對比例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同時季節性淹水和常年淹水沉積物真菌細菌比也均表現為圍網養殖區高于圍塘養殖區,但僅在常年淹水條件下具有顯著性差異。一般認為細菌偏好分解容易分解的有機質;而真菌偏好難分解的纖維素和木質素以及高碳氮比的有機物(Ingwersen et al.,2008)。研究區圍網養殖區沉積物有機質含量相對較高,且主要來源于覆蓋度更高的濕地植物,適宜真菌降解和生長,而圍塘養殖區更多來源于較易于分解的餌料,有利于細菌生長。由于真菌細菌比是微生物群落結構重要指標之一,高的真菌細菌比意味著更穩定的生態系統(De et al.,2006)。因此,研究區圍網養殖區沉積物生態系統比圍塘養殖區更穩定。水產養殖改變了沉積物理化性質及污染等環境狀況(裘瓊芬等,2013;Zhou et al.,2020;Kucuksezgin et al.,2021),進而影響了微生物群落結構(裘瓊芬等,2013;Zhou et al.,2020;Zhou et al.,2021)。本研究區分析結果也表明不同養殖模式下沉積物化學指標存在差異(表1),同時沉積物F/B、G-生物量相對比例、真菌生物量相對比例等微生物群落結構指標與沉積物粘粒、砂粒、有機質、全氮等物理化學指標存在顯著相關性(圖2b)。有研究認為沉積物有機質、磷素和氮素等化學性質影響著沉積物微生物群落結構(楊長明等,2018;于小彥等,2020;Zhou et al.,2020)。同時土壤質地也深刻地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王群艷等,2016),有研究發現鄱陽湖濕地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組成與土壤砂粒含量呈顯著相關關系(張廣帥等,2018)。RDA 分析也表明研究區砂粒是解釋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群落特征差異的重要環境因子;有機質、砂粒和有效磷是解釋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群落特征差異的重要環境因子。然而,所分析的理化性質指標僅能分別解釋39.4%研究區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群落結構差異和68.0%常年淹水沉積物微生物群落結構差異,表明尚有一些其他影響因素。在漁業養殖過程中施用了抗生素、抗菌劑等(Chelossi et al.,2003;卓麗等,2019),可促進沉積物中耐藥性更強的革蘭氏陰性菌生物量的增加(Chelossi et al.,2003;Zhou et al.,2021)。研究區G-是沉積物中生物量相對比例最大的菌群(圖1),且常年淹水沉積物G-生物量均高于季節性淹水沉積物,但未達到顯著水平。總體上,研究區微生物群落結構指標基本上反映了養殖模式對沉積物生態系統影響及其穩定性,但養殖模式的影響在常年淹水沉積物表現更顯著。
一般生物多樣性高的生態系統穩定性就高。圍網養殖區沉積物微生物多樣性及豐富度顯著高于圍塘養殖區,但優勢度較圍塘養殖區低,且差異不顯著。同時微生物多樣性指數與真菌細菌比相互佐證了圍網養殖區沉積物生態系統更加穩定。沉積物細菌多樣性主要由pH 和養分狀況等環境因子決定和控制(楊長明等,2018;Bahram et al.,2018;于小彥等,2020;Zhou et al.,2020)。研究區季節性淹水沉積物微生物Shannon 指數與粘粒含量呈顯著正相關,與砂粒和全磷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而Simpson 指數與粘粒含量呈顯著負相關,但與砂粒和全磷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而常年淹水沉積物Shannon 指數和Simpson 指數與所測理化性質指標均未有顯著性相關性。同時含水量、土壤有機質等養分非均質分布是導致土壤微生物分布和多樣性重要因素(Zhou et al.,2002;Curd et al.,2018;王好才等,2021)。相對于季節性淹水沉積物環境,常年淹水增加了微生物在沉積物環境中的移動性、氧化還原電位和養分分布均勻性,破壞了沉積物空隙隔離效應(朱義族等,2019)。同時長期性淹水條件增加了微生物群落的環境壓力,導致了沉積物具有相對高抗壓的微生物優勢種群,但促使微生物多樣性降低(朱義族等,2019)。另外漁業養殖過程施用抗生素、抗菌劑等(Chelossi et al.,2003;卓麗等,2019)更易于在圍塘養殖區沉積物中累積,而圍網養殖區水體與自然水體連通交換,可能是導致圍塘養殖區沉積物微生物多樣性更低的另一因素。相對于圍網養殖區,圍塘養殖區更強烈的人類活動可能也破壞了養殖區沉積物異質性,加上抗生素類污染物的影響,促使微生物多樣性較低。因此,沉積物微生物多樣性指數基本上反映了兩種養殖模式下沉積物生態系統狀況及其漁業養殖模式的影響。
4 結論
菜子湖不同養殖模式下人類干擾活動強度和自然水域連通性不同,導致不同養殖模式下沉積物環境物理化學性質及抗菌劑類污染物影響存在差異,沉積物微生物通過調整生物量和種群組成以適應環境差異,進而促使沉積物微生物生物量和群落結構發生改變。研究區內沉積物微生物生物量和群落結構均較靈敏地反映了養殖模式的影響,常年淹水下養殖模式的影響更為明顯。相對于圍塘養殖區,圍網養殖區沉積物擁有更高的微生物生物量和多樣性,更有利于維持養殖區沉積物生態系統功能和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