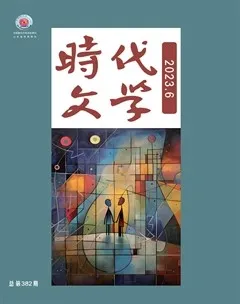每個人的“黃河百景圖”
孫利娟 謝尚發
辛亥革命時期,山東獨立革命如曇花一現般,僅維持了十二天。獨立時間很短,但其事件背后的波瀾洶涌,各方勢力的觸斗蠻爭,恐怕是難以說清道明的。作家常芳選擇這一歷史事件作為其小說故事原型,企圖通過《河圖》描繪出辛亥革命時期屬于山東的歷史一景,這無疑非常考驗作家的創作功力。無論是回溯山東當時獨立斗爭的革命史實,還是還原山東其時歷史風貌,都是對材料的艱難尋找與篩選過程,更不必說這宏觀的事件架構下,還有眾多微觀的史實細節的鉤織。小說作品的成功,在于虛構的真實,在于虛構敘事的形象化思維,能夠使接受群體產生情感與移情。這就需要創作者使用一系列的手段來描寫、刻畫,以激活接受者的心理活動。一部好的作品不在于宏觀架構上如何激動人心,而在于細節的塑造上如何打動人。
文學是情感的世界,情感是文學創作的原料,如葉圣陶在《怎樣寫作》中所講的:“有了好的原料才可以制作器物。”(葉圣陶:《怎樣寫作》,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019.07,第2頁)蘇珊·朗格在《藝術問題》中指出:“藝術品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就是情感的意象。”(蘇珊·朗格:《藝術問題》,滕守堯,朱疆源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03,第129頁)南帆認為:“文學世界的根本特征在于以虛構的內容呈示流蕩于人們內心的真實情感”(南帆:《理解與感悟》,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11,第5頁。)而對于接受者即讀者來說,他們的閱讀活動是復雜的認知活動,他們在閱讀中跟隨創作者的意圖進行解碼然后創造文本意義。讀者憑借故事中的場景描寫、人物活動、事件,及其所展現的修辭效果等,在文學語言營造的文本之中感受、發現、體驗,進行審美的欣賞。讀者可以通過閱讀,在文學的歷史長河里體驗到人類精神的長明。作者常芳以其出色的藝術敏銳做到了這一點,她抓住人物行為的深層動機,賦予每一個人物以靈魂。其筆下的山東獨立革命故事脫去革命文學的激流敘事,而是采用了“鵝籠書生”式的故事結構模式。《鵝籠書生》是梁朝吳均《續齊諧記》中的一篇中國古代志怪小說,又叫《陽羨書生》,這篇小說講述了陽羨人許彥肩背鵝籠行走,路遇一書生,要求坐到鵝籠中。途中休息時,書生口吐肴饌,與許彥共享,并吐出一女子陪伴他。而女子并不滿意書生其人,對他懷有怨氣,趁書生醉臥,口吐一男子與之相會。這男子又不真心對待此女子,又口吐一婦人與之戲談。在書生覺醒前,男子口納所吐婦人,女子納男子,最后書生納女子及諸器皿,留一大銅盤給許彥作紀念。《河圖》的“鵝籠書生”式故事結構模式,不僅表現在整體敘事上,也體現在人物敘述上,每個人各有其故事和其動人之處,這些故事互相關聯,使得人物共生。
魯迅曾在其《中國小說史略》中考察過《鵝籠書生》的敘事模式源頭,這其實是源自佛經故事,“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于有意或無意用之,遂化為國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04,第28頁)佛經中用來表達佛家理論“圓融互攝”的故事,到了中國文人那里便被創新轉化為中國書生的故事,帶上了獨特的文化標識。作者常芳也將創作觸角伸向我國古典文化資源,使其進行當代的創作轉化,讓傳統文化資源成為生生不息的創作源泉。《河圖》擁有套娃般的故事敘事模式,將敘事聚焦在民間立場上,從老百姓的視角出發,挖掘他們的意向性立場。作者注重每個人物行為背后的信念、愿望和價值觀,在心緒回憶、聯想等心理活動認知的能動敘事之間,蛛網式勾勒山東獨立革命中的波瀾壯闊,以及這“黃河百景圖”式故事背后,每一個平凡的人在凡俗人生中的信仰與堅韌。
老百姓眼里的“山東獨立革命”
小說《河圖》并沒有將敘事視角聚焦到山東獨立革命的正面戰場,聚焦到那些在獨立斗爭中能產生舉足輕重影響的勢力代表身上,而是將聚焦視角邊緣化,將視角放在了濟南城里的濼口鎮——一個緊挨著黃河的小鎮上。南家花園是敘事聚焦的中心,其里面的各色人物是《河圖》中反映山東獨立斗爭的主角。這些主角只是濼口鎮上的普通人物,沒有遮天的權勢,沒有巨額的財富,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獨立”是個什么概念,但正是因為將視角聚焦到他們身上,作家才得以有一種平民式的書寫。如此小說才能得以從歷史史實纏繞的桎梏中抽身,遠離宏大語境的壓迫,以其審美情趣和創作個性來塑造理想的、屬于山東獨立革命的敘事文本。
作家沒有將故事視角聚焦到獨立革命正面現場,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山東革命失敗的理解,就像魯迅先生的《藥》《風波》《阿Q正傳》等作品,旁敲側擊式,便讓我們在這人間世象中得以體察革命失敗的深刻原因。在作家的筆下,濼口鎮交織著民間幻術、偏方、傳說、寓言、歷史故事,和那漂洋過海隨著宣教士而來的圣經故事,為文本營造了一種詭譎的情境,讓人忍不住一探究竟。
邊緣化是《河圖》獨立革命斗爭敘事的主要特征,相比于整部小說的篇幅,正面描寫革命斗爭勢力角逐的篇幅是很小的。也許正是因為這邊緣化的特征,游離于主體之外,給創作者一種審視距離,才能更深入百姓的內心世界,描摹他們眼中的革命模態。《河圖》里的獨立革命模式交織著日常生活,如《清明上河圖》一般,充斥著日常世情的瑣碎,充滿著生活的細節與真實。東西方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等帶來的文化沖突交織在這片土地上,隨著獨立革命的進程而躁動不安。
在《河圖》的敘事模式上,作家總體上采用全知敘事,像鵝籠里的書生,《河圖》里無論過去還是未來的故事都裝在了敘事者的肚子里,給倒敘、插敘、預敘、延宕等敘事藝術留出了足夠大的揮灑空間。敘事者將人物、事件線索處處勾連,編織成一張繁密的、布著懸念的敘事大網。也因此,在微觀敘事層面上,敘事者似乎抽離了獨立革命事件的激情,帶著冷靜的敘事距離,在詩意的抒情中,對人物的經驗背景進行描述與評判,為的似乎只是把這張“河圖百景圖”呈現在讀者面前。
例如故事開頭的周約瑟,作為南家花園的仆人,自幼成長于貧苦底層,在宣教士蘇利士的幫助下才得以成人。在中國鬼怪故事和圣經故事熏陶下長大的周約瑟,他的認知里充滿著兩種信仰的混沌,看世界總有一種魔幻的色彩。這樣的世界里,事物真實的質地總是夸張而變形的,到處充滿著瑰麗的想象。在這修辭的表征之下,是普通百姓在面臨變革時迷茫的恐懼。再如南家花園主人南海珠作為一名保守派,認為世間各種變革都是鵝籠,不過是人心相異、爾虞我詐的結果,而不變的世界才充滿著信仰與溫情。反之在他弟弟南懷珠這位革命派的眼中,現有世界的一切都是落后的、死氣沉沉的,因此需要變革以獲得新生。如此,小說中每個人物視角里的世界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世界匯聚在同一個文本空間內,構成了一幅被籠罩著不同視角情感的圖畫。這幅圖使得文本充滿了世情生活的煙火與細節,一章一景,由小及大,從古至今,從中國到海外,從傳說到現實。文本的每一章并不是割裂的,因果關系、歷史的偶然與必然都隱匿其中,它以山東獨立革命的時間發展為緯線,濼口鎮上人物活動為經線,跨越歷史現實、古今中外,交叉穿織,最終生動地顯現出了屬于山東的辛亥革命敘事動圖。
吞吐式蛛網交叉的結構
鵝籠里的書生不僅自己有故事,他還能吐出一個人來講故事,吐出來的人還能再吐出一個人講故事。按此,故事似乎可以無限生長下去。這樣無限生長的故事結構主要是通過各種人物的出現來連接與傳遞的。在這里,人成了敘事模式與故事結構擴張的主要紐扣,而人物關系的鏈接則是《河圖》敘事模式重要的結構動力,小說中很多人物的出場都是通過一個人物的敘述出現的。志怪小說《鵝籠書生》中,從一張嘴里跳出一個人物,再從這個人物嘴里又跳出另一個人物,看似人物獨立,但其實都被包攬在書生這個大框架之中。同樣,《河圖》里的人物也都被包含在一個大的框架之內,不僅被籠罩在一個歷史事件背景里,也被籠罩在中國文明的文化密碼之中。
小說開頭前三章便通過一個又一個人物的鏈接關系,交代了故事的主要人物。如在小說開頭出現的南家仆人,專門負責往濟南城里送醋的車夫——周約瑟。通過周約瑟之眼,引入了一個重要的火車意象。火車這種工業文明的巨物,對于當時落后的農耕文明,無異于外星人之于地球的震撼。這種震撼給周約瑟帶來了類似于臆想的精神幻象,他想起了宣教士蘇利士給他講的圣經故事,他想起了父親給他講的神話傳說,他想起了幼時母親給他使用的偏方。西方文明、東方文明、民間文化在小說的開頭便矛盾地交織,構成了一幅奇幻的景象,奠定了小說開頭獨特的氣質。通過對周約瑟的視角及心理狀態描寫,不僅牽出了濼口鎮當時的風貌狀態,也牽出了相關人物,如周約瑟家人、西方傳教士、南家花園主人南海珠、濼口鎮的商人等。
作為《河圖》的重要人物周約瑟,他不僅起著勾連人物的作用,也起著刻畫、溝通地理空間的作用。車夫周約瑟每天要往返濟南城與濼口鎮,將獨立革命中心的濟南城與濼口鎮這個政治邊緣地帶連接起來。隨著周約瑟所在地理空間的位移,《河圖》的地理空間細節也在不斷地充實豐滿,辛亥革命的進程也在這隱線上不斷地發展著。在反映西方宣教士這一文化現實方面,周約瑟是一個起著吞吐作用的人物,小說人物南明珠也起著這樣的作用,她吞吐出戴維夫婦,而戴維夫婦又吞吐出他們的西方故事,一環扣一環,《河圖》的歷史文化碎片就是在一個個人物各自的故事中串聯成整體的,共同譜寫了山東獨立革命十二天的歷史狀貌。
最后,人物不僅起著鏈接人物與營造空間的作用,還承擔著歷史敘事作用。如南海珠的母親厲月梅與妻子厲米多是太平天國運動時的受害群體,戰亂對普通百姓的創傷延續了幾代人,這樣的歷史敘事在其他人物身上也有體現。所以《河圖》里的歷史敘事不僅僅有山東獨立革命十二天的這一部分,它的歷史敘事是縱深的,籠罩在大的歷史敘事框架之下。
人物鏈接人物、人物鏈接地理空間甚至歷史敘事,這種關聯作用幾乎體現在每一個主要人物身上。在這張關系網中,吞吐式結構使故事的敘事模式和結構蛛網式連接。但是人物形象不同,他們的敘事功能側重也不同,南家花園里的人物有各自的敘事功能。如南家花園主人南海珠是傳統文明的代表,家中長子,肩上擔任著守護家族的任務;而弟弟南懷珠則與之相對抗,作為一名堅定的革命者,為著心中的信仰與欲望,無家也無己;大妹南明珠則向往著西方文明,是幸福、自由的隱喻;南明珠丈夫谷友之是權力異化的隱喻;車夫周約瑟則是底層掙扎的人物代表;醋園工頭伍春水是投機取巧之流;戴維夫婦在故事中既是西方文明沖擊的一種力量,又是一個類似紀錄片鏡頭式的存在,作為置身事外的觀察者,他們似乎知道山東獨立革命的后果,但他們從不置評,以上帝視角存在于濼口鎮歷史的敘事進程里。
長篇小說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與否關系著小說的完成度,《河圖》通過人物鏈接,在一個共同背景下,通過一種共生關系,既借由各色人物描繪出屬于濼口鎮的“黃河百景圖”,揭示出中國人內心的文化密碼,又為敘事提供了一種模式結構。一個人物再生一個人物,然后便有源源不斷的故事內容流淌出來,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既屬于個人也屬于歷史。
意向性立場:人物、故事與思想
常芳身為一名女性寫作者,她既對宏大的革命敘事有著超強的把控能力,也能敏銳地捕捉到流淌在人物心緒間的情感、心理活動,敘事的堅硬與柔軟很好地在作者的敘事中結合起來。如果說人物共生模式是小說敘事的結構模式,那么人物的恐懼、欣喜、悲傷、憤恨、欲求等情緒帶來的回憶、聯想等心理活動和由此產生的行動則是敘事前進的動力。這不同于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動力,例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很多鬼怪小說的敘事結構是以因果邏輯為中心來謀篇布局和安排故事情節的,像“報恩說”“天意說”“緣分說”等,注重故事發生的前后因果,以此作為情節發展的推動力。雖然作者轉化了古典文學資源,但她也融入了現代創作手法,更注重向人物的內心挖掘,尋求人物行為背后的意向性立場。
人性是復雜的,一個人的行為總是蘊含著意向性立場。人物行為最根本的推動力乃是其內心的欲望,這是情節結構的動力,而矛盾、沖突都會由此產生。《河圖》作者關注人物內心世界,在亂世背景下,向人物內心挖掘,探究每個階層人物背后的行為動機,由此產生了一種心理活動經驗的真實。這些心理活動為事件概述了其背后情感,以一種內部視角的方式進行故事敘事。這種敘事方法是《鵝籠書生》等古典小說所隱匿的或者說未被充分探索的敘事領域。
心理活動所帶來的情緒經驗、認知經驗、知識經驗等構成了敘事的內容。在心理活動這樣的內部視角內,一切物象都染上了主體的情緒認知色彩,成了主體自我的確證。如南海珠眼里濼口鎮的黃河或是沉悶的,或是兇狠的,或是輕靈縹緲的,景物的質感無不隨著主體的情緒認知變化而被賦予不同的內容。或如革命者南懷珠胸前口袋里的“玫瑰”,因為關乎著對南懷珠這個革命者的評價,在一些人眼里它是革命的浪漫、希望,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則是革命的軟弱、貪歡甚至虛無。再如谷友之的恐懼與欲望,他將自己妻子的兄弟視為幸福路上的障礙,將兄弟馮一德視為可利用的工具,這種恐懼與欲望,推動了故事走向高潮,也將一個革命者葬送。
作者常芳引用蒲松齡《短禾行》里的詩句“世態漁陽已道盡,人間何事不鵝籠”,并借人物南海珠之口說出,也是在暗示這是一部關于人心相異、為了利益互相殘殺的故事,所以對于人心的刻畫,在作品里也顯得尤為重要。在小說《河圖》中,除了全知敘事者插入的敘事或交代外,很多故事內容都是由心理活動所帶來的內部視角構成的。在小說開頭,無論是周約瑟關于火車的認知還是對濼口鎮風貌、人物的描述,都是通過人物情緒的回憶、聯想、描述、評價等心理活動交代出來的。關于人物的沖突,如南海珠與南懷珠,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情緒欲望的沖突。在這種沖突中,由雙方的情緒帶來的心理回溯性的記憶事件則構成了小說敘事中的張力性力量。在這些情緒事件中讀者可以解讀人物形象原型,例如南海珠長兄式的隱忍源頭,弟弟南懷珠的革命理想的愿望源頭等,甚至也可以解讀自我。
這些包裹在情緒里的心理活動經驗內容,敘述著人物的成長歷史,而人物性格也在這敘述中一點點鮮明起來。在人物現時的活動中,作家以人物的情緒活動作為敘事抓手,將山東歷史、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都融入各種人物的心靈密碼中。敘事看似聚焦日常,其實歷史時刻的點滴都融進了人物的心靈密碼中,揉進了其個人氣質的塑造中。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沖突,中華民族與異邦的沖突,古今的沖突,歷史的創傷,封建帝制的壓迫……都融入了人物的情緒經驗中,在心理活動的敘事中不斷推進敘事,制造沖突與矛盾,豐滿故事細節,于是讀者便能在閱讀中感受到情緒的力量、情感的真實,而后者的真實感是能將人帶往歷史現場的力量,閱讀者的心靈便與這種形象的情感結構相契合。也因此,《河圖》能給人呈現如此豐實的觀感,既充滿著日常世情的瑣碎與真實,又有史實的瑰麗壯闊。
文本很容易被創作野心所壓垮,在歷史故事類型的創作中,想要表現深度和廣度,但如何不被抽象的歷史觀念和既定的史實所桎梏,考驗著作家的才華、知識與耐力。《河圖》雖是個大題材、大故事,但是在作家巧妙的藝術構思下,將所有宏大的歷史事件都化進細節可感的世情敘事中,通過共生人物關系的敘事模式設置,關注人物意向性立場,以人物的心理活動、情緒欲望敘事為動力抓手,在作者想要展現的深度與廣度之間,很好地解決了歷史題材類故事容易敘事生硬、呆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