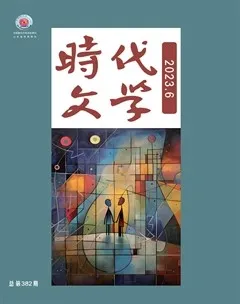一個(gè)人的黃河詞條
米蘭
河水在流淌。
她的皮膚是黃色的。她是一位母親。
客車一路向北。車上全是陌生的面孔。沿途一條一條的河流,在車窗外一閃而過。看不到河水流動(dòng)。河面上的反射光,讓我想起祖母收藏的幾塊銀子。有一次我瘋跑著闖進(jìn)她屋里喝水,把她嚇了一跳,手中一只匣子摔到地上,幾塊沉甸甸的東西在陰暗的屋子里閃著光。我問祖母那是什么,祖母說:“沒什么,別跟你媽說,別讓你媽知道。”我還是忍不住告訴了母親。“那就是些碎銀子,值不了幾個(gè)錢。”母親笑著說。
客車上鼾聲四起。車窗外一只大鳥在秋風(fēng)中盤旋,翅膀劃過的每一條弧線在我看來,都寫滿離愁別緒。我離母親越來越遠(yuǎn)了。那是我第一次離開母親。無所謂傷感,因?yàn)榭荚嚦煽?jī)不好,我被黃河以北一所中等專業(yè)學(xué)校錄取,有些悶悶不樂。
唯一讓我期待的,是這趟旅程必然要經(jīng)過的一條河流——課本上反復(fù)出現(xiàn)的“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
一出戲的高潮往往在最后呈現(xiàn)。抵達(dá)終點(diǎn)之前,那條河自西向東,橫亙?cè)诘缆非胺健!翱矗S河!”客車慢吞吞地爬上一座自錨式懸索橋,前面座位上有人拉開車窗探出頭去。
當(dāng)黃河涌入眼睛,在風(fēng)沙中
長(zhǎng)出蘆葦,夜鶯
鳴聲如滴,渾濁的激流
因此而清澈
那年國慶節(jié),學(xué)校舉辦詩歌大賽,我模仿艾略特寫了一首《黃河之戀》,得了個(gè)二等獎(jiǎng)。事實(shí)上,當(dāng)黃河第一次進(jìn)入眼簾,實(shí)在是一個(gè)令我懷疑的問號(hào)——那種波瀾壯闊,那種勇往直前的力量,我怎么沒有感覺到?
是的,我看到的,是一條沉默而疲憊的河流。它像我母親一樣平凡。在我到來之前,它是否就那樣風(fēng)塵仆仆而不舍晝夜地流淌,我是不知道的;我也從未想過,它帶著怎樣的使命,它的前途是什么樣的。
那個(gè)秋天,黃河在我心里結(jié)下一粒青澀的種子。當(dāng)然,它對(duì)我有沒有影響,生活至今沒有給出明確答案。直到我也做了一個(gè)女孩的母親,成為她眼里黃皮膚的媽媽,我才明白,那粒種子事關(guān)一條河流的源頭和走向,我必須回到河流本身,才能看清它的真實(shí)面貌,繼而找到它所表達(dá)的真意。
黃河灘上,一棵古老的杏樹孑立風(fēng)中,像凡·高的畫。可是,凡·高先生,
春天就要過去了。
河灘上,一棵古老而巨大的杏樹像一幅油畫,吸引了我。它的背景中那渾黃的、深不可測(cè)的河流用的是厚涂法,四周飄飛的柳絮用的是漸淡法——1890年,凡·高在精神病院附近的花園里,畫下了他一生最溫柔的作品《杏花》。畫面上,空間場(chǎng)景被省去了,褐色枝丫托著細(xì)密的淺色花朵,安靜地融化在一片藍(lán)色背景中。
眼前這棵杏樹枝繁葉茂,儀態(tài)悠然。它的花期過了,枝杈上綴滿青果。“凡·高先生,春天就要過去了,每個(gè)人都看到了花,唯有你看到了愛。”我在杏樹下徘徊了很久。
河水在流淌,青杏在生長(zhǎng)。一只喜鵲
在春風(fēng)中飛翔
我平靜地回憶起客車駛過黃河大橋,抵達(dá)那所學(xué)校之后,我在那里遇到的一個(gè)男孩。白天,我們?cè)邳S河灘上行走,朗誦自己寫的詩歌,唱《穿過你的黑發(fā)我的手》和《意大利之夏》;夜晚,我們?cè)诤拥躺夏强眨務(wù)摽档隆⑽鞣矫缹W(xué)和夢(mèng)想。星夜澄明,河水浩蕩。我們不關(guān)心時(shí)間。我們有的是時(shí)間。雨季里豐盈的河水就要溢出大堤,接下來卻是持續(xù)的干旱。裸露的河床上,一些磚頭瓦片半陷在泥沙中。隨風(fēng)而至的,是濃重的魚腥氣。那時(shí)的我們都還沒有見識(shí)過大海,縱使內(nèi)心繁花似錦,想象的翅膀在渦流上方不停飛旋,終難抵擋風(fēng)雨到來之時(shí),被打落在地的命運(yùn)。
渾濁的黃河水裹挾混沌的細(xì)節(jié),一去不返。
那么,河灘上這棵杏樹將結(jié)下怎樣的果實(shí)?
輕飄與白。柳絮讓我想起了什么。
蒲公英和益母草是藥,也是慰藉。
畢業(yè)時(shí),他陰差陽錯(cuò)被分配到地處偏遠(yuǎn)的黃河河務(wù)段工作。命運(yùn)給他帶來一個(gè)猝不及防的急轉(zhuǎn)彎。
河務(wù)段只有兩個(gè)人:他和一位合同工。合同工家里有二十畝責(zé)任田,經(jīng)常請(qǐng)假回去種地。河岸上孤零零的三間辦公室里,常常只有他一個(gè)人。河務(wù)段平時(shí)沒什么工作可做,他白天看書,夜里看書;早晨跑步十公里,傍晚在河灘上散步,不停地往前走,然后再回來。
長(zhǎng)河落日,銀月如鉤,渾黃的河水一瀉千里。仲尼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而他,像一枚落葉,飄蕩在黃河灘上。
班長(zhǎng)從省城趕過來,約我一起去看他。
宿舍里一張舊辦公桌正對(duì)后窗,一抬頭就是那條大河。屋里只有一把椅子。我坐椅子,他倆坐床沿。桌上放著一摞書,我翻了翻,有加繆的《西西弗神話》和帕斯卡的《人是一根會(huì)思考的蘆葦》,有老鬼的《血色黃昏》和程海的《熱愛命運(yùn)》,有《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和一本繁體豎版的《易經(jīng)》。他說,真慚愧啊老同學(xué),沒什么可招待的,待會(huì)兒咱去大壩那邊吃臺(tái)子火燒,先帶你們?nèi)タ袋S河吧。
谷雨節(jié)氣,柳絮如霜。河岸邊柳樹林里傳來鳥鳴聲,清脆的唧啾聲來自柳鶯,咕嘟嚕叫著的是白頭鵯,嘎嘎嘎朝天嘶喊的是老鴰。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
春天是枯水期,寬闊的河灘上落滿柳絮,白花花地伸向遠(yuǎn)方。
“還寫詩嗎?”班長(zhǎng)問他。
“不,我想研究下《易經(jīng)》。要知道,在黃河邊,你會(huì)看到一個(gè)古老國家的遺影,思考人的命運(yùn)……”他雙手背在身后,低垂著頭往前走,像一個(gè)飽經(jīng)風(fēng)霜的老人。
那年春節(jié)后,我們回到學(xué)校,十幾個(gè)老同學(xué)聚在一起指點(diǎn)江山。他喝了酒,激情滿懷,背誦起屈原的《九章》:“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愿徑逝而未得兮,魂識(shí)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然后他就醉了,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河灘與堤壩之間的水洼里,倒映著樹影,一陣風(fēng)吹過來,樹身歪斜得不成樣子。
我想起赫拉克利特對(duì)時(shí)間的理解:人,不能兩次踏進(jìn)同一條河流。
水洼邊生長(zhǎng)著一些野草,艾草、蒲公英、益母草、大青葉,這些治病救人的中藥草都是苦澀的,接受它們需要一個(gè)緩慢的過程,與被時(shí)光寬恕一樣緩慢。
深邃的聲音。唱吧唱吧,不要停止。
蒼茫的河灘上泊著一艘船。船幫上一只大鳥左顧右盼,仿佛在等待什么。
樹林里秋蟬嘶鳴,仿若絕唱。
我對(duì)時(shí)間的困惑來自靜夜發(fā)呆時(shí)的冥想,來自仰望浩瀚星空時(shí)的自慚形穢,來自凝視宇宙無盡黑暗時(shí)的恐懼。空間的終極沉默已令我極度不安,時(shí)間卻是一個(gè)更大的謎團(tuán),它藏在洞中,甚或就是空間的同謀。現(xiàn)代物理學(xué)的最新成果在我的冥想世界中皆不成立,我不認(rèn)同它們。這是我心目中最終極的謎團(tuán):無人給予時(shí)間一個(gè)獨(dú)立的定義,無人提供一個(gè)足以令我信服的詮釋。
一聲犬吠使夜更加寂靜。在黑暗中,我不禁屏住呼吸,透過窗口朝河灘上望去, 那個(gè)手執(zhí)手電筒的巡夜人似有察覺,他將光束精準(zhǔn)地朝著我的窗口射來。
當(dāng)我閱讀的時(shí)候,我的靈魂是在場(chǎng)的。我以我的靈魂與書中的靈魂相呼應(yīng),聆聽、碰撞、交融、吸納、共鳴,書中的營養(yǎng)和智慧滋潤(rùn)了我的靈魂。
月色與鋒刃是兩種不同的詞,即使它們同樣閃光。
……
他的信件我一一讀過,仿佛在讀卡夫卡寫在八個(gè)八開的筆記簿上的真跡。無以名狀的、或許潛意識(shí)里早已存在的某種物質(zhì)被激活,我一度試圖把黃河邊孤寂燈影里那個(gè)靈魂的歌聲記錄下來,以此證明我們的人生歲月里曾經(jīng)發(fā)生過什么;我也曾在日記里百轉(zhuǎn)千回,描述過那個(gè)靈魂的模樣,最終,看著窗外城市里的月光和盞盞燈火,我安靜下來。
當(dāng)有些東西如果只能在月光或燈光下回憶,便意味著它們已經(jīng)消失。
我把沉甸甸的背包從肩上卸下來,擱到船幫上。在我走近之前,那只大鳥飛走了。它是何時(shí)飛走的、去了哪里,我一概不知。
情感的累積和暗示,細(xì)節(jié)的鮮明和凸起,在紙上,在信封里,撐滿背包,沉甸甸地壓在船幫上。黃河水無聲翻滾,像痛苦和愛——當(dāng)痛苦和愛累積到無以復(fù)加的地步,反而會(huì)使人平靜,回歸清醒和清澈。仲尼說,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詩人說,黃河遠(yuǎn)去,我沒有一首歌相送,也沒有一句言辭。事實(shí)上,那個(gè)秋天的上午,我坐在那艘船邊的沙灘上,聽到大河如同一個(gè)人的靈魂,一直在不停地歌唱。
河邊有家火燒鋪。
臺(tái)子火燒是一道美食,與夢(mèng)想無關(guān)。
泥爐內(nèi)火紅似鐵。飄起來的煙霧裹挾著木柴的香氣,在鋪?zhàn)永飶浡R粋€(gè)男人、一個(gè)女人,是一個(gè)整體;一個(gè)男人、一個(gè)女人和一座火燒鋪,也是一個(gè)整體。堤壩旁邊一家名為“臺(tái)子火燒”的鋪?zhàn)永铮腥素?fù)責(zé)揉面做火燒,女人負(fù)責(zé)燒火烤火燒。有客至,男人問一句:“要幾個(gè)?”順手拿過紙袋,為客人裝火燒,女人起身收錢。
從第一次邁進(jìn)這家火燒鋪到今天,二十多年了吧,鋪?zhàn)永镞@對(duì)夫婦仍像當(dāng)年一樣,分工明確,配合默契,生意無所謂興隆,卻細(xì)水長(zhǎng)流一般,令人心安。如果把史蒂文斯的詩句略加修改,以“火燒鋪”替代“烏鶇”,我覺得也不失為一個(gè)完美的意象。
火燒鋪主人姓張,這套制作火燒的手藝是祖上傳下來的。“但我不敢保證能傳下去,我們只有一個(gè)兒子,人家學(xué)的是電子技術(shù),與火燒鋪八竿子打不著。”張氏夫婦原本不善言辭,我作為一個(gè)食客,本也不該像記者似的問七問八,只是因?yàn)橐粋€(gè)人和一段往事,我總想跟他們說點(diǎn)什么。
選了一個(gè)靠近火爐的座位,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跟張師傅聊了起來。對(duì)面墻上掛著一面印有“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臺(tái)子火燒”字樣的牌匾,黃底印花,字跡古雅。我在縣城吃過很多次“臺(tái)子火燒”,韭菜肉餡的、豆腐粉絲素餡的、胡蘿卜雞蛋餡的,它們或許更合我的口味,但我知道,那都不是正宗的臺(tái)子火燒,真正的“臺(tái)子火燒”在黃河邊上,只有麻汁餡的,就是張氏夫婦制作的這種。“都要養(yǎng)家活口,沒必要計(jì)較哪家正宗、哪家不正宗,客人喜歡吃哪種,就選哪種。”張師傅說,“有些人往往更喜歡食物的名氣,而不是食物本身,那是不對(duì)的。”
吃完火燒,我爬上黃河大堤。大堤至河道的灘涂上,種著一排一排的防護(hù)林。靠近大堤的防護(hù)林邊緣,我看到兩座小小的墳塋,靜悄悄地藏在荊棘叢中。過了防護(hù)林再往里,是一片碧綠的麥田。正是小麥抽穗、開花期,空氣中氤氳著馥郁的麥花香。立夏節(jié)氣即將到來的暮春天氣里,楊絮一團(tuán)一團(tuán)在空中紛飛,落到堤壩上,落入河水中,落進(jìn)麥田里,落滿兩座小小的墳頭,落進(jìn)野草叢和荊棘叢中。大風(fēng)吹走了我頸上的一條絲巾,我追著它往河道邊跑去,跑得我氣喘吁吁,忍不住咳嗽起來。
黃河遠(yuǎn)去。它與我的距離是地理
層面的。我們追逐的,都是蔚藍(lán)的自由
河邊的秋風(fēng)還沒有散盡。那些激越而鼓舞人心的秘密誓言一層一層從岸壁上脫落,隨即被河水卷走。我試圖從中拎出屬于他的那一聲回響,突如其來的,一只寒蟬尖叫著從樹上墜落,砸在我頭上,然后滾落于地,讓我一時(shí)不知所措,一如當(dāng)年那個(gè)炎熱的夏日。
是的,那是個(gè)炎熱的夏日,蟬鳴陣陣,我們坐在樹蔭里,中間隔著一個(gè)人的距離。他與往常一樣沉默著。可我隱隱覺得,他不是沉默,而是欲言又止。最后,他說,我要走了……
我原本堅(jiān)信,河流之中,那些隱秘的花朵跳躍著、歡笑著,靈魂各自自由而又彼此相牽,直至一起入海歸于蔚藍(lán)。現(xiàn)在他說,他要走了,去往海的另一邊……可我不敢開口,仿佛一開口,一段往事就會(huì)消失無蹤。
他帶我到臺(tái)子火燒鋪吃午飯。臨別前給了我一本書——像磚頭一樣厚的《尤利西斯》。紙頁在我手中嘩啦啦翻過去,停在夾有書簽的那一頁,我看到中間位置兩行詩句下面,畫著兩道紅色的橫杠——
對(duì)世人我不仇恨,
愛祖國勝過自己。
孤零零站在大堤上的他,并不需要向我解釋什么。我懂得他的內(nèi)心,如同懂得他的孤獨(dú)。
轉(zhuǎn)身而去的那一刻,臉上流淌的是淚水還是汗水,已經(jīng)不再重要,我最先意識(shí)到的,是接下來,我將與他一樣孤獨(dú)。
這些年,我一次又一次走過臺(tái)子街,跨過黃河大壩,下到河灘上,觀望河水東流去的豪邁、激蕩與義無反顧,思索忠誠與痛苦的源頭和盡頭,即使無所收獲,于靈魂的救贖而言,這一過程終是不可或缺,它讓一個(gè)人變得深沉。不如此,河水的流動(dòng)便失去意義——流動(dòng),才是一條河活著的標(biāo)志。
我知道,秋風(fēng)不會(huì)散盡。風(fēng)后面還是風(fēng)。
我知道,來自時(shí)光之初的河流,正如一根從天而降的金色指針,終將指向大海,與世界聯(lián)通。
- 時(shí)代文學(xué)·上半月的其它文章
- 巷子深處
- 從夢(mèng)里取出來的島嶼(組詩)
- 我因滄海而來(組詩)
- 齊長(zhǎng)城活頁(組詩)
- 岔尖的墩子草
- 尋跡安丘齊長(zhǎng)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