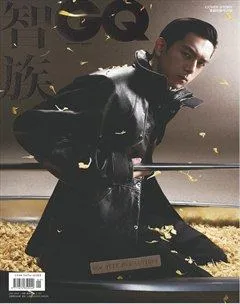形態的自由舞:當我們再次談起現代主義
萬若妍 芽咪


鮮紅的色彩作為底色奪去觀者的注意力,讓畫面氛圍熱烈中帶著喧鬧,畫面中心的女子面目貞靜,沉浸在自己的無垠思考園地,然而劇烈的底色已經泄露她內心的風暴。在畢加索的名作《讀書的女子》中,有別于早期分析立體主義藝術家“色彩不宜凌駕于形象”的觀點,畢加索用大膽的色調襯托出畫中讀書女子的內心,他已不再滿足于復制“雙眼看到的世界”,他要繪制的,是我們人類個體“心之眼”所感知到的內心的風景。
而畢加索在阿維尼翁時期創作的《紙牌、煙草、瓶子與玻璃杯》,帶來的則是獨屬于時代的“視覺插畫”。彼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人們對戰爭的視點互不相同:有頭戴花環受到熱烈歡迎的士兵,也有破損的村莊、荒蕪的田園。在這件作品中,畢加索將日常生活中的靜物以戲劇性的空間和色彩排列,人群的缺失和清冷的色彩,或許隱喻他對戰爭的憤怒回應;而整體詩意的畫風與沉睡的“日常靜物”,透露著他內心深處對過去平靜生活的眷戀,以及對當下戰爭的不解和憤怒。
無獨有偶,用形式的革新來再現個體心靈風暴的做法,還體現在畢加索同時代的藝術家身上。保羅·克利在其作品《節儉男子的只言片語》中,用簡潔的筆觸圈定出畫面中心男子的抽象形象,寥寥幾筆,稚童似原始壁畫;但隨著觀者目光從右至左的逡巡轉換,線條的長短似乎和音律節奏有所耦合,男子的“只言片語”通過構成自身形象的“線條”被吟唱了出來,跨越一百年,依舊能讓觀者(或許也是“聽者”)會心一笑。我們看到藝術家們將或沖突或無關的元素綜合在一起,創造出了全新的視覺概念和觀看路徑。
對心靈風暴的重現,似乎席卷了20世紀幾乎所有藝術家的畫筆。這份形式上的革新與畫面情緒的集體共鳴,一方面來源于藝術家們對時代的通感,一方面或許也是“照相術”發明后,對“繪畫世界”需要有別于“照片世界”的需求。1929年,保羅· 克利完成了作品《墓葬群》,同年亨利· 馬蒂斯也創作了其代表作之一《在尼斯畫室》,二者均將吉薩金字塔進行了抽象化的處理,擯棄了一板一眼的“所看”,重現了不同人眼中對待“所看”的“所思”,力求超越現實——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形式和感知上的“不破不立”呢?

當下AI藝術興起,“創作”和“形式”的概念被重新定義,與遙遠的20世紀相呼應,我們似乎又來到了一個充滿“不解”的復雜時代。當我們在新的世紀里重提起現代主義,或許尋求的不僅是審美意義上的美感,更是希望能通過與過去經典對話,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方向與力量。
在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此次攜手柏林國立博古睿美術館舉辦的大展“現代主義漫步:柏林國立博古睿美術館館藏展”中,匯集了6位現代藝術巨匠的近百件代表性作品,從畢加索、馬蒂斯到喬治·布拉克的大作,這些曾在百年前歐洲引起轟動的藝術家作品,第一次來中國展出,與同樣對現實有所求索的觀眾會面。藝術的普遍性或許就體現在它具有跨越時空的能力。在經歷了世界范圍的生活方式劇變之后,人們可能更能體會到1942年畢加索在巴黎被占領后繪制的《大幅斜倚裸像》中體現的憂郁與不安。
誠如柏林國立博古睿美術館館長加布里埃爾·蒙圖阿所言,現代主義藝術上的“混亂”與戰時社會的混亂狀態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當我們回訪現代主義,目的在于將藝術、文化、歷史與當下聯系起來,提供新的思考維度和思考方式。現代主義不僅僅是一種風格、一場革命,更是一代人的聲音和故事。為了更好地了解現代主義的過去與當下,《智族GQ》本次將對話柏林國立博古睿美術館館長兼本次展覽的策展人之一加布里埃爾·蒙圖阿,一同探討現代主義作品中藝術形式與生命個體的流轉關系。
有別于東京站和大阪站,北京本次展覽采用了編年史結構進行呈現。為什么會選用這樣的展陳形式?
在日本的時候,有一些來自日本本土收藏的作品,所以我們選擇了更加傳統的展陳方式,讓每一個藝術家都擁有自己單獨的板塊。

我們的展覽不僅介紹藝術家本身,還會思考如何在作品之外為觀眾提供更多價值。編年史結構作為一種蘊含歷史維度的展陳手法,使觀眾得以跨越畫作本身,學習到整個20世紀的歷史脈絡。在展覽空間內,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還特別設置了文字介紹,其中一段是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描述,揭示了當時歐洲石油的大規模開采與環境的破壞。這些歷史背景對于深刻理解畫作中的事件至關重要。例如,立體主義的出現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許多評論家簡單地評價立體主義為混亂的體現,但若結合當時社會的歷史背景,便能發現這種藝術上的“混亂”與戰時社會的混亂狀態有著驚人的相似。將文化與歷史聯系起來,提供新的思考維度,也是我們選擇這種方式的理由。
人們會從不同角度來欣賞藝術:或許從宏觀的藝術流派、或許從單件藝術作品的細節來進入。比如本次展覽的作品《海姆· 薩巴特斯肖像》,“藍色”底色之下唯獨嘴唇有一縷“粉色”,這種有趣的細節讓人著迷。您習慣從什么角度去了解一位藝術家,或是一件作品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細節,在畢加索生命的后期,薩巴特斯對他來說十分重要。他就像畢加索的私人保鏢,若想拜訪畢加索,需先通過薩巴特斯的篩選,由他決定當天你是否可以與畢加索會晤還是在門外徒等。這幅畫作屬于畢加索的藍色時期,當時他一貧如洗,剛至巴黎,未決定是留下還是返回西班牙,他的心境沉郁,因而那個時期的作品多表現出壓抑感。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畢加索逐漸找到了自己的風格。而在藍色畫作中的粉色,就像一座通往玫瑰時期的橋梁,在早期的玫瑰時期作品中,藍色的元素仍然頻繁出現,與藍色時期的作品相互映照。
編年史結構的引入,使得觀展體驗更加豐富。初入展廳,觀眾會先看到19世紀塞尚夫人的肖像畫,繼而是畢加索的兩幅肖像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畫作逐漸顯現出更抽象的風格,直至喬治· 布拉克的立體主義肖像畫,這一時間序列有效地展示了藝術的演變過程。
同時,我們得以洞察到線性與非線性發展的概念。現代主義還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觀點,堅信事物發展具有發展性,如同火箭,從一點出發,沿固定方向發射。因此,在20世紀中葉,許多人將抽象主義視為藝術的未來,認為現代藝術的使命便是走向抽象。但在時間的長河中,藝術發展并非一成不變的。馬蒂斯的作品時而變得極具具象性,畢加索的某些畫作也擺脫了抽象的束縛。因此,每個觀賞角度都能成為展示的良好切入點,既可以聚焦單一作品,探究薩巴特斯嘴唇的粉色之謎,也可以隨著時間的脈絡捕捉更多的藝術發展趨勢。
畢加索的《紙牌、煙草、瓶子與玻璃杯》以及保羅· 克利的《藍色風景》都完成于一戰時期,令人驚訝的是,在社會環境比較灰暗的時期,藝術家們卻運用了比過往更濃烈的色彩進行創作。您覺得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什么?

對畢加索而言,在分析立體主義的初期,色彩在其作品中幾乎被忽略,他大量使用布朗色、灰色和赭石色,因為他認為“色彩會干擾觀者對形體的關注”。于是,他與布拉克一道將物體分割為獨立的部分以表現其形態。然而,進入立體主義的第二階段“綜合立體主義”后,他們開始嘗試融合不同且相互沖突的元素,以營造出新的視覺概念,色彩因此重獲其位。這一時期恰逢一戰,而當時人們對戰爭的恐懼并不顯著,反而對其爆發抱有一種期待。在許多當時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頭戴花環的士兵,受到人們的歡呼,直到戰爭后期人們才逐漸認識到戰爭的殘酷本質。這種認識在二戰后的作品中得到了體現,例如展覽中的一幅1942年的作品《大幅斜倚裸像》,畢加索在其中大量使用了灰色元素,一些觀察家和評論家認為,畫中無處不在的灰色使他們聯想到德國軍服的顏色,那是巴黎被納粹德國占領時的情景。盡管畢加索未曾明言,但這幅作品中的戰爭色彩更為明顯。
而對于保羅·克利,在早期創作中,他更像是一位平面設計師,作品多為黑白色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他與朋友們前往北非突尼斯,在刺眼的非洲陽光下,他發現了色彩的魅力。在他的日記里有一段非常好的引文。他說:“色彩已經俘獲了我,我現在成為了一名藝術家。”這一經歷成為他藝術生涯的轉折點。然而,隨后他的朋友馬克在戰場上犧牲,成為戰爭中逝去的藝術家之一。在那一刻,新時代的到來和新突破的誕生,同時也預示著戰爭殘酷現實的降臨。
20世紀的柏林歷史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博古睿先生年輕時也經歷了流亡,后又重返德國。您覺得這段經歷對博古睿先生的收藏偏好有影響嗎,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博古睿先生與這批藏品的有趣故事?
博古睿先生在早年并非一位收藏家,他原本的志向是成為一名記者。他購買的首件藝術品是保羅·克利的《幻影透視》,該作品喚起了他對德國除戰爭外的另一面,即“浪漫”的記憶。正如他所收藏的風景畫所展現的那樣,他偏愛描繪自然木質風景的作品。如果想要領略德國浪漫主義的美好一面,不妨觀賞那些描繪樹木和月亮的畫作。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與自然和諧共處,追求萬物一體的理念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謀而合。
畢加索也有著類似的經歷。他在西班牙輾轉流浪,最終在法國定居。他曾試圖成為法國公民,但因無法返回西班牙而遭拒絕,因此他終其一生都處于流亡狀態。博古睿先生與畢加索的相似經歷,使得他對這位藝術家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親近感。這種共鳴并非僅僅基于對藝術作品的喜愛,而是為他提供了一種理解藝術的全新視角。
與20世紀上半葉類似,如今世界又重回動蕩之中。在這樣的條件下,重新審視20世紀的現代主義藝術,能為我們帶來什么?
這些藝術作品不僅是當時時代的藝術歷史文獻,它們也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例如,我們之前討論的1942年的大型裸體臥畫《大幅斜倚裸像》,是展覽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整幅畫作透露出一種幽閉恐怖的氛圍。1942年,畢加索選擇留在了被占領的巴黎,在那里他被禁止展出或出售作品,這對一個藝術家來說無異于扼殺他的經濟價值。他經歷了食物和資源的短缺,在戒嚴的巴黎,晚上10點后不得外出。在那樣的時代,人們能深刻感受到壓抑和恐怖的氣氛。近幾年,由于各種原因,人們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這使得人們或許能更加深入地感同身受這幅作品所表達的情緒。這就是藝術的普遍性,這正是藝術家所追求的——理解人類的處境以及其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因此,我們希望本次展覽能夠觸及到這一層面的效果。
“線上看展”成為風潮后,實體美術館自身的獨特意義來自什么?
實體美術館的獨特之處在于能夠面對面地欣賞原作。正如沃爾特· 本杰明所說,藝術品的原作擁有一種無法通過復制品,如印刷品所傳達的“靈氣”。若想真心欣賞某件作品,親自去觀賞或許是一項必選,因為網絡上的顏色可能與原作有所不同,線上展覽也難以精確還原作品的比例和畫框。更重要的是,觀賞角度在展覽中至關重要,作品與周圍其他作品的大小、比例和尺寸關系是您只有在現場才能真正感知和體會的。對于雕塑作品尤其如此,它們會隨著觀眾站立的位置和觀賞的角度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視覺效果。因此,身臨其境的體驗至關重要。
本次展覽作品中,您最想向中國的觀眾介紹的是哪一件,為什么?
這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因為在如此多的杰出且有趣的作品中選擇一件是非常困難的,人們的偏好總是在不斷變化。目前,我最喜歡的是畢加索1919年創作的《窗前靜物,圣拉斐爾》,因為它生動地展示了立體派的實驗是如何持續發展并與具象繪畫的表現手法相融合的。今年恰逢畢加索逝世50周年,巴黎正在舉辦一場盛大的畢加索展覽。在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展覽中,展出了1000件紙上作品,這是一場規模巨大的展覽,還為這幅作品撰寫了一篇文章。如果在不同的時間問我,我的答案很可能會有所不同。
和中國的觀眾聊聊博古睿美術館吧。它有什么獨特的地方,以及您是如何被吸引到美術館工作的呢?
對于我來說,它非常獨特,因為我們的藏品雖然只有大約300件,和其他美術館相比可能顯得較少,但我對它們每一件都非常了解和熟悉,如果館內有20000件藏品,你不可能對它們了如指掌。博古睿先生的收藏方式也非常有趣,事實上,在西方的每個美術館中都能看到畢加索的作品。因此,僅擁有畢加索的作品本身并不算特別。但我們擁有畢加索幾十年來的作品,您可以在這里看到畢加索生命中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十年的作品,這在博物館中是非常罕見的。此外,柏林博古睿美術館非常國際化,與巴黎有著密切的聯系,這對我來說也非常合適。
這次展覽也受到了許多觀眾的喜愛,您有什么想向中國的觀眾轉達的話語嗎。
我們非常高興觀眾喜愛這次展覽,因為展出的作品都是第一次來中國,人們有機會以全新的視角欣賞這些作品。同時,我們也希望能與中國觀眾保持聯系,因此我們開設了社交媒體賬號與中國觀眾互動。雖然展覽將于明年二月結束,但我們希望與中國觀眾建立長久的聯系。當我們在柏林重新開放時,如果能迎來更多的中國游客,我們將感到非常欣慰。當人們未來訪問柏林時,或許會有同行的朋友或家人提到曾在國內看過一次精彩的展覽,這將促使他們參觀博古睿美術館。我們希望這次展覽不僅僅是曇花一現,而是能開啟一段美好的文化交流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