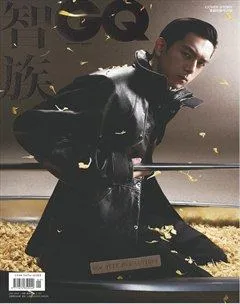一個32歲得了6種癌癥的女人
肖薇薇

“聽醫生的就好”?
一團粉色闖了進來。王夢琳穿了一件粉色卡通衛衣,一雙粉色襪子,走進咖啡館。她高高扎起馬尾,說話時眼睛帶著笑意,總是先講旅途趣事,她與丈夫季理剛從廈門、廣州回到南京,假期和表妹們去上海參加了漫展,Cosplay照片里她頂著一頭炸裂、軟萌的綠色假發。聲音爽朗,聊天時百無禁忌。
只是,許多細節會提醒她作為一位癌癥病人的事實。她隨身拎著一個大大的卡通水壺——一天至少要喝2L水。手指貼了兩個創可貼——她的指甲變得脆弱,不經意就會破開。這都是靶向藥的副作用。還有甲溝炎、潰瘍與臉上大爆發的痘痘,她因此秋日里踩著一雙黑色涼鞋。
王夢琳人生的岔路口出現在2005年,她讀初三,左手肘偶然撞在階梯教室的扶手上,腫了起來,之后在醫院確診了惡性骨肉瘤。惡性腫瘤,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癌”。經過手術、化療,她度過了平靜的10年,病灶沒有復發。這意味著她已經達到一個臨床治愈的標準。
2015年,新的癌癥再次出現,悄無聲息地,有時甚至連腫塊的提醒都沒有,她又被拽進疾病的漩渦。她依次確診了乳腺癌、肺腺癌、腎上腺皮質癌、間葉源性腫瘤、骨母細胞型骨肉瘤。多次手術、化療,在王夢琳身上留下可見的改變,切除腫瘤的同時,也切除了她的一根尺骨、雙側乳房和一片肺葉。
加倍的打擊是,王夢琳的父親也是癌癥患者,幾年前去世。她和父親做過基因檢測,報告顯示,父女倆身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發生了變異。可以簡單理解為,他們抵抗癌細胞的能力極大地弱于常人。

這似乎成了一種宿命,她暫時沒有能夠找到阻斷癌癥發生的辦法,只能在新的腫瘤出現時與之對抗。然而,對于一個已經確診了6種癌癥的人而言,并沒有哪個醫院的科室、醫生能夠完全解決所有的問題,連多學科會診都不能,她每次只能選擇一項癌癥、一處腫瘤去問診。“腹部找腹部的醫生,骨頭找骨頭的醫生,肺找肺的醫生,病理問題找病理科。”她最初的想法很簡單,“聽醫生的就好”。
的確,一些尋常的小病,我們可以遵循“聽醫生的就好”,但當疾病變得復雜,新的問題不斷疊加,這個原則就開始失效了。每個科室的醫生說法可能不一致,甚至互相沖突。
就拿去年發現的一枚腎上腺皮質腫瘤來說,有的醫生認為是此前的癌癥轉移,畢竟她已經有過三種癌癥病史。但是究竟是哪種癌的轉移呢?不同的轉移,意味著完全不同的用藥方向。還有醫生建議,要不干脆切掉這枚腫瘤看看,通過病理檢查確定來源。但醫生同時又提醒,“盲目開刀切除,會不會反而加速體內癌細胞轉移,這都是難以預測的。”
與此同時,術前需要停靶向藥一段時間,而那時王夢琳正在吃一款針對乳腺癌的靶向藥,一旦停藥,病情是否會惡化?她見了許多醫生,但沒人會幫她作決定,每位醫生會給出自己的診療方案,也告訴她其中的風險。決策權在她手里。可是,連這么多權威專家都沒有定論,她作為一個沒有任何醫學背景的年輕女孩兒,又該怎么作決定呢?

她只能是咨詢更多的醫生,然后做出一個不知道到底是對是錯的抉擇。最終,去年年底,在江蘇省腫瘤醫院,王夢琳做手術切除了這枚腎上腺腫瘤,在腹部留下一枚核桃大小的疤。命運和她開了個小玩笑,病理報告顯示,這枚腫瘤并非醫生們此前推測的癌細胞轉移,而又是一個原發癌癥——腎上腺皮質癌。這是她得的第四種癌癥。
再拿肺部的結節來說,去年9月以來,王夢琳的肺部出現了大量微小結節,超過了一百枚,影像報告上是密密麻麻的白色雪花點,看起來令人驚駭,白點仿佛將要把雙肺占滿。可結節都太小了,無法做穿刺活檢。
有醫生說,無法排除是此前的乳腺癌轉移。她去了此前做乳腺癌手術的江蘇省人民醫院,醫生提議,“要不你來住院,做兩個療程的化療試試看。”
王夢琳猶豫,化療的副作用太大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現代醫學的有限性——當各種檢查無法明確,只能通過“排除法”去定位,而這些嘗試的代價是未可知的。
她和丈夫去了趟北京尋求“第二意見”。“無法穿刺,什么都沒能定性,憑什么認為是乳腺轉移呢?”在北京一所知名的腫瘤醫院,乳腺科專家拋出疑問。
好不容易搶到的專家號,就診時間只有幾分鐘,她抱著報告單,急切地想要專家給一個治療方案,和南京的化療方案對比。“如果你一定認為是乳腺癌轉移,我可以給你一個治療方案。”專家語氣有些不耐煩,助理叫了下一位的號。
“我就是無法確定才來的啊!”時隔半年,王夢琳說起依然無奈,她沒去開藥,郁悶地回了南京,決定試試江蘇省人民醫院的化療方案。

化療后,肺部結節卻依然在長。用藥、手術、化療都沒用,治療陷入死胡同。醫生最后說,只能等結節長大,繼續觀察。
今年4月,終于有一顆肺部結節長大到可以勉強做穿刺了。病理結果出來后,確認是此前患過的肺腺癌肺內復發與轉移。經過基因檢測,她的靶點是罕見的“20插入突變”,在所有轉移的患者中只占4% ~ 10%。
這對王夢琳而言,并不完全是個壞結果,至少為期半年多的化療、手術、試藥進程,終于告一段落了。2023年初,針對肺部“20插入突變”的靶向藥在國內上市,從4月22日,她在醫生建議下開始服藥。
新的問題還在源源不斷地出現,8月的一次全身檢查,王夢琳身上新增了三處異常:肝胃間隙腹壁上出現一個腫塊,直徑約3厘米;右腿膝蓋下方脛骨處腫瘤,出現了骨質破壞;腦部也照出一處水腫,直徑0.7厘米……這意味著,未來,王夢琳還要別無選擇地做出更多次選擇。

“到那個時候肯定是保命重要”
從去年切除腎上腺腫瘤手術后,王夢琳就沒法再工作了。這是她畢業后的第三份工作,在親戚的公司里做財務,公司在外省,平時她在家用電腦遠程辦公。
王夢琳兩次重大的人生轉向,都與癌癥有關。2005年因病休學后,她重讀了一年初三,卻沒有報考高中,而是在父母建議下填了家附近的一所五年制專科學校。因為考慮到高考壓力,擔心癌癥會復發。盡管她的中考分數遠超過這所專科學校的錄取線。
“現在讓我想想看,確實也會有點遺憾。”王夢琳回憶說,但當時她沒有提出異議。
與曾差點兒失去左臂,與長達半年的手術與痛苦化療經歷相比,沒有人敢冒一次險。確診惡性骨肉瘤后,王夢琳休了學,住院開始化療。她對化療藥反應強烈,輸液后狂吐,頭發也大把地掉。手術后等了一個多月傷口愈合,固定帶和夾板拆除后,又做了兩個療程的化療。次年5月,治療才結束。
一次化療間隙,王夢琳回了一趟學校,因為太想朋友們了。當時臨近中考,同學們都在緊張復習。她去教室打了個招呼,就在門衛室等他們放學,像往常一樣,一路上嘰嘰喳喳聊天,直到分別的路口。
一旦患了癌癥,身體就成了最重要的人生排序。王夢琳報考了那所大專的財會專業,這是大人眼里最好找工作的專業之一。大專的學業確實輕松多了,和讀初中時一樣,她還住在家里,有了很多空閑時間,她常逛論壇“西祠胡同”,找到了一起玩Cosplay的朋友。2008年南京舉辦第二屆漫展,他們一起排了一臺舞臺劇,還得了獎。她扮演的角色來自游戲《空之軌跡》,一個戴著紫色頭發、很勇敢的女孩。
她做了許多事情去補上學歷差距,盡管并不喜歡財會專業,她還是把每天的時間都排得滿滿當當。“既然學了,還是把該考的考了。”大專進入最后一學年,她“逼”著自己學完所有專業課,考了會計證書、大學英語四級,如愿找到南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實習在那里,她遇到了男友季理,他是隔壁部門的同事。
王夢琳享受那段充實忙碌往前沖的日子。大專畢業后,她去了一家外企工作,做人力資源助理。她還自考了南京大學本科,白天上班,晚上上課。工作第三年,她的職位越來越高,從助理、專員晉升到了主任級別。
她和男友都變得忙碌。她負責做整個江蘇省門店的薪資,每個月發工資前幾天最忙,加班到夜里十一二點是常有的事。不加班的晚上和周末,她回學校上課,季理就帶著工作電腦去學校陪她。
一個勤奮的、事業處于上升期的女孩兒,然而,癌癥再次將一切按下了暫停鍵。
2015年秋天,公司體檢時,王夢琳查出乳腺異常腫塊。復查的結果是壞消息——左側乳腺癌三期,已經出現淋巴結轉移,屬于中晚期。這次南京幾家三甲醫院都給出了確定的診斷。
王夢琳再次被拉回醫院,回到那套早已熟悉的漫長的流程:檢查、化療、等待手術、再繼續化療。兩年病假里,外企的補充醫療保險派上了大用場,讓她不至于有大的經濟壓力,只是再也無暇顧及事業。
“到那個時候肯定會選擇保命重要,”王夢琳嘆了口氣,“一開始肯定難受,那怎么辦呢,必須要接受嘛。”
這次手術后,王夢琳失去了雙側乳腺。手術前后,她一共化療了八個療程,比骨肉瘤治療時間更久。她吃不下東西,頭發掉得很快,于是干脆剃了個光頭。化療結束,她需要終身服用一款內分泌藥他莫昔芬,這引起了強烈的副作用,一開始是拉肚子,最嚴重的時候,她幾乎全天都坐在馬桶上,整個人虛脫。
2017年病假結束前,王夢琳回公司,領導體諒地說,建議她換到更輕松的崗位,管理人事檔案,她的職級依然保留。她心里一時間涌出復雜滋味,那是她剛畢業做人事助理時的工作內容。
不久父親也生病要做手術,她需要經常請假,哪怕調去一個清閑崗位,她也無暇應對了。于是,只好離職。
再次求職時,作為一個有癌癥病史的人,王夢琳的選擇并不多。一位面試官看到她手上的疤,專門問了她,她沒有隱瞞,面試后續不了了之。王夢琳自己做過HR,她當然知道癌癥病人找工作的艱難。
2017年底,王夢琳去了南京一個做國際教育與交流的協會工作,負責與在南京的外國教師溝通。這份工作工資不算高,但勝在輕松,不用加班,還有寒暑假。面試談好后,對方一直沒有要求入職體檢,王夢琳也沒有提起。她忐忑著心情入職,直到拿到第一個月薪水,才放下心來。
后來疫情暴發,協會關了門,王夢琳失業了。她沒再去找工作,而是在親戚開的小公司里遠程工作。2021年初,王夢琳又確診了新的癌癥,情況開始失控,她的身體不斷“冒出”新的腫塊,她經常需要去醫院。
人生完全被打亂了,她再也顧不上其他的事情。
“做自己覺得對的事”
在南京的幾日,多數時間我與王夢琳約在她家附近的公園。工作日的上午與下午,季理需要去處理一些工作,她就一個人提著水壺和零食包出門散步。
去年他們剛搬來這里,在南京的東郊。原本只是偶然陪朋友來看房,他們卻先看中搬了家,這里空氣比市區好,旁邊就是公園和學校。之前他們就在考慮領養的事情,結婚后,醫生曾嚴肅提醒他們生育的風險,因為王夢琳的癌癥病史,“還是領養個孩子,生活更完整一點吧,有點盼頭。”雙方父母也都同意。
他們把領養計劃定在王夢琳乳腺癌手術的五年觀察期后,也就是2021年。2020年,季理去福利院咨詢了領養的條件與流程。
他問過王夢琳,想要男孩還是女孩?王夢琳說:“女孩吧。”不一會兒,她改變了主意,笑起來,“還是看眼緣吧。”后來就是我們知道的事情,新的癌癥出現,領養計劃也擱淺了。
這一年,季理推掉了大部分的工作,有時他們一周五天都要去醫院,時不時離開南京幾天,去一線城市會診。等待檢查結果的日子,他得趕一趕工作進度。季理現在一家公司做資產評估,上下班時間相對自由,薪資構成簡單,多勞多得。領導、同事相識多年,都知曉他的難處,讓他遠程辦公。
錢是必須考慮的問題。盡管王夢琳有醫療保險,但靶向藥需自費,并且終身服用。除了看病支出,他們還有房貸要還,夫妻倆無法承受再失去一份收入。
剛見面聊天時,我不自覺會流露出擔憂,愛情與婚姻的責任,真的能夠抵御漫長的、艱難的抗癌歷程所帶來的消耗與負擔嗎?
畢竟我們看到過太多照顧者“撤退”的故事。
2015年決定結婚時,季理聽過許多顧慮的聲音,“你們現在又沒結婚呢,你沒必要對她負責。”“后面怎么辦,能不能要小孩?”
當時王夢琳剛做完乳腺癌手術,在準備化療。季理這時提出結婚,他的想法簡單,“想讓她安心,安心做放療、化療,怕她胡思亂想。”
季理很坦誠地說,自己當時并未意識到,妻子將終身與癌癥抗爭。他身邊唯一一個癌癥案例,是同事的妻子,曾經得過乳腺癌,手術后健康生活十幾年了。“都說切除以后,就沒事了。”這是他們當時對于癌癥最樸素的認知。
結婚并非倉促起意,兩人當時已經戀愛四年,都見過對方的父母。季理比王夢琳大四歲,兩人感情穩定后,他就把工資交給王夢琳,一起存錢。季理說,以前總想著等攢夠錢,買了房再結婚,不曾想她生病一下打亂了時間表。
決定求婚后,季理先告訴了自己的父母,父母沒有反對,反而告訴他,如果他認定了,他們就支持,“做自己覺得對的事”。父母還打了5萬塊錢過來,王夢琳的父母也支持了5萬,一起幫他們湊齊了首付。
季理則提到了一件對他很重要的小事。他們每個月會開車回老家,在南京周邊縣城農村看望季理的爺爺,老人家身體不太好,藥盒子堆了一抽屜。第二次去,王夢琳特意買了分裝盒,把爺爺未來一個月的藥仔細分好,以免他漏吃。
他們就在這些小事里認定了彼此。一個不化療的日子,王夢琳一早趕回學校做畢業論文答辯,答辯完成,他們順路去民政局領了證,下午去買了鉆戒,一家人吃了火鍋,就這樣結了婚。
與癌癥的戰爭,卻遠比他們想象的都要復雜、漫長。
王夢琳是獨生子女,她既是病人,也是父親的照顧者。那幾年,她和父親住院,夜里都是季理陪護,他不肯假手于人,也無人可替換。白天王夢琳母親過來送飯,他再去上班。父親進了ICU那幾天,王夢琳坐在ICU門口走廊的椅子上守著,直到兩人身上都有味兒了,季理才勸動她去附近賓館洗了個澡。
許多這樣無助的時刻,他們靠彼此支持撐了過來。父親去世后,照顧爺爺的責任也落在夫妻倆身上。爺爺今年89歲了,去年生病后,生活難以自理。當時王夢琳在醫院做腎上腺腫瘤的手術,因為防疫政策病房不能隨意進出,那天夜里,季理打了好多電話,才找到朋友幫忙,艱難地將爺爺送去了最近的醫院。
季理個子高大,長相憨厚,平時跑項目多了,皮膚曬得黝黑。不同于粗獷的外表,王夢琳感受最深的是,他很細心,病歷資料都由他整理,復查從不遺漏提醒。去年手術后,趕上疫情,季理特意買了拆線包,照著網上教程,在家給她的手術傷口消毒、拆線。
10月中旬,我和他們一起去上海,季理掛到一個上海人民醫院骨科專家的號。他帶了一份打印好的表格,詳細列出了妻子的疾病史,細致到哪一年做了什么治療。病歷里缺了一項重要信息,王夢琳骨肉瘤手術后,手臂內被植入了一塊固定的鋼板,病歷單里缺了鋼板的型號與材質,這直接關系到能不能做核磁共振,明確腦部腫瘤。
午飯時,一個手機鬧鈴響了,季理不緊不慢地從褲子兜里掏出一粒藥,遞給王夢琳,晚飯時鬧鈴又響起,他掏出了另一種藥。那兩天,他一直拿著手機咨詢醫生,研究文獻,還給國外醫藥公司發去郵件確認。“好多事情,我自己都記不住,他老記著。”王夢琳說。
季理習慣了對妻子的照顧。他會不經意接過妻子左手的物品,不時拎拎水壺,督促她喝水。雖然她很少主動提及對癌癥的恐懼,但他還是能感受到許多微小的變化,她變得更加黏他,有時他忙事情,不經意說一句心煩,她的情緒會一下崩潰。于是,看病之外的時候,他們盡量做一些輕松的事情,散步,曬太陽,一起玩《原神》,下班后雷打不動看兩集動漫,每天都會有一個動漫更新,一集20分鐘。時間更多一些,就去旅游。
和他們相處愈久,我愈發體會到他們對于彼此的支持是什么。他們在多年陪伴里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相處方式。王夢琳像一個“小太陽”,她會拍早晨季理逗狗狗“年糕”的視頻,和二人的家人、朋友維持著頻繁的聯系,并在吃飯時分享他們的近日趣事。季理的表妹、弟弟遇到問題第一時間總是發信息給她,包括但不限于學習、相親的煩惱。而季理是后盾。不需要說,在面臨如此巨大的殘酷時,這種后盾意味著什么。
“關關難,關關過吧”
前段時間,季理買了一本書—《無國界病人》,作者師永剛也是一位癌癥病人,患癌10年里,他經歷了兩次手術、5次復發、4次急診、6次放療和3次參與臨床試驗,盡管治療過程波折又殘酷,但他也馬上將度過5年觀察期,達到臨床治愈的標準。
王夢琳看完書,鼓起勇氣給作者寫了郵件。師永剛很快打來電話,建議她把患癌的經歷寫出來,“或許能被一些專家團隊看到”。
文章發表后,很多平臺轉載了她的故事。評論區里多是鼓勵的聲音,人們深知生病不易,看病艱難。也有負面的聲音,“這樣活著有什么意義”“何必拖累家人”。幾位親人被這些話激怒,還偷偷集體去回復,讓鍵盤俠們閉嘴。
其實王夢琳早就看過這些評論,后來她不再點開。我們見面時,她說心情已回歸平靜,“這個過程是先被拉到胡同里邊,再慢慢想開,慢慢走出來。”就算命運殘酷到如此地步,“也只能好好活著呀。”
父親癌癥去世前,他們去做了基因檢測,癌癥太過罕見、頻繁地發生在父女倆身上,已經不是一句“壞運氣”能解釋的了。
2021年,王夢琳收到基因報告,87歲的爺爺一切正常,而她與父親都出現異常:TP53基因,一個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發生了變異。報告上的結論只有一句,罹患癌癥的風險高于常人。
抑癌基因和癌基因突變并不會馬上導致腫瘤,但當她的身體內失去了重要的“守門人”,細胞戰役就隨時發生著,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癌細胞可能逃過免疫細胞的追殺,爆發增長,直至難以控制。
她的父親第一次患癌是在44歲。父親性格內斂,平時話不多,喜歡攝影,一生沒什么不良嗜好,生病后只要還能活動,從沒有落下鍛煉。他原來是一位鑄造工人,憑借鑄造技術,到了南京一所大學當了大學老師。這是命運垂青的部分。
“說不難過那是假的,”王夢琳說,“沒想到我和父親就像那個詞,天選之子。”看到檢測報告那一刻的感覺就像是被雷劈中,她感覺全身通電一般,一下被判了刑,拉入深淵。
在《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癌癥患者會經歷五個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可接受一個終身作為“癌癥病人”
的宿命,絕不僅是想通“命運無常”四個字。
社會學家安妮·卡麥茲(Anne Charmaz)將慢性病患者需要面對的兩個交替出現的階段,稱之為“好日子”與“壞日子”,在好日子里,病痛能得到暫時控制,生活回歸日常;而在壞日子里,疾病帶來的痛苦與漫長的治療讓人無暇顧及其他。隨著疾病的變化,那些好日子會縮短,壞日子在延長。
王夢琳頻繁地回到那些“壞日子”里:手術室很涼,濕濕冷冷的氧氣進入鼻腔,時間就停滯了,你不知道手術什么時候會結束,恢復清醒、見到親人;當化療的藥輸進去,很快會感到難受、嘔吐,頭發大把掉落,只能再次剃光頭;然后是手術后漫長的、鈍鈍的痛感,連帶著呼吸也痛,一點點適應傷口,直到它結痂。
而癌癥必然發生,可能在她生命里的任何一天。那種惶惶不安,或許才是最令人恐懼的。許多時候,王夢琳只是這樣平靜地講述著。我們坐在草坪上,靠得很近,除了把手輕輕放在她身上,我無法說出安慰的話。我想,任何語言在此時都顯得過于無力。
她因此把去醫院之外的時間都填滿,安排得豐富。追動漫,玩游戲,帶著妹妹們Cosplay,去旅游。原來她還在學爵士和街舞,只要不住院,她每天都會去跳舞,最近身體不允許了,她就去散步和爬山。未來她還有好多想做的事情,帶爺爺曬太陽、學吉他。
“命運對我不好又好,我身體不好,但身邊的所有人都很好,朋友、家人,還有我老公。”王夢琳說,因為她和丈夫都喜歡小孩子,朋友住在附近,“他的兩個小孩經常陪我們玩,經常會要找我們。”
她努力在無法回避的殘酷事實下活得釋然。回憶起當初做乳腺癌手術,術后她哭了,血壓飆得很高,病房里親人護士亂作一團時,她哈哈大笑。剛見面時,王夢琳每次講起手術的經歷,語氣都很輕松,而我的表情沉重,甚至不知道什么反應才是得體的。當我真實地與王夢琳相處了幾天,我才發現這就是她講述病痛的方式,仿佛只是在說一件尋常趣事。或許只有這樣,過程中的疼痛與殘忍才能被消解。
時至今日,她已經慢慢適應了身體的變化,如同當初適應左手、胸部、難以抬高的腋窩,盡管過程很不容易。她的身上有手術的傷疤,和朋友去澡堂時,朋友會下意識避開目光,擋在她身前,而她則大大咧咧就走了過去。
王夢琳說,她早就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了。2016年冬天,她和姐姐去熱帶的海邊,游泳、學潛水,還穿上了好看的比基尼。我看到照片里,她那時頭發還很短,顯得毛茸茸的,好像頭頂著一只小刺猬,她張揚地笑著,比了個“耶”——一個勝利的手勢。那時所有人都認為癌癥已經治愈,病痛過去了,她可以開始新的生活了。
癌癥從未真正打倒她。盡管接下來的狀況依然很嚴峻,王夢琳身上的第六個原發惡性腫瘤,右腿的骨母細胞型骨肉瘤,已經長大到必須手術切除的地步了,而切除很難繞開膝關節。這意味著,之后她或許再也無法跳舞了,甚至無法如常走路。
可他們兩個普通人,除了停下來,多跑醫院,多問醫生,沒有別的辦法。季理說,他現在唯一想的就是,不要走彎路,不能走彎路,“雖然關關難,關關過吧。”
在南京那幾天,我們的聊天總是在我的語塞中結束。中途我不止一次地想,我是不是要繼續做這個采訪,一方面是感慨于命運的沉重,揭露傷疤的歷程充滿痛苦,更無法輕易談論未來,沒有人知道癌癥下一次滑落是什么時候。
我們就像朋友一樣,天天一起散步、吃飯、聊天,她極少在我面前展露脆弱時刻。夢琳比我年長兩歲,我們聊戀愛、婚姻與30歲的困惑。有一天散步時,她從零食包里掏出了兩只醉蟹,是她媽媽剛鹵好的。每當我變得沮喪,她總能敏感地察覺,說些鼓氣的話,“過好當下”“開心快樂每一天”。聲音顯得中氣十足。
去上海時,我們一起去了一家動漫手辦店,逛了整整五層樓,被動漫全宇宙淹沒,我們沒有再去聊任何癌癥的事情,沉浸地捧著手辦驚呼“可愛”,最后克制地“帶走”了兩小只。這也是王夢琳那段時間最放松的一個晚上。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天,北京人民醫院一位專家打來電話,他說重新審視了王夢琳的特殊病史,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這或許是介于良、惡性交界處的腫瘤,通過合適的手術方案,可能保住膝蓋。”
王夢琳的語氣輕松了許多,這一次,腫瘤至少留給她一些緩沖時間,讓她可以去尋找更好的手術方案。
分別時,我問王夢琳會害怕嗎。
“你看到我的微信簽名了嗎? 4.0T的小馬達。”她朝我擺擺手,說,“我現在雖然只有四片肺葉,但是我的引擎是帶T的,動力還是很足。”我想,這也是她對命運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