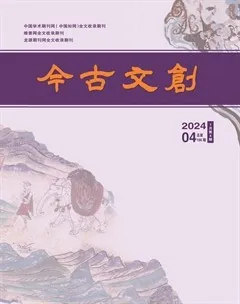以接受美學(xué)及讀者反應(yīng)論角度探索 趙本夫小說(shuō)《天下無(wú)賊》
趙雅寧 衣環(huán)宇
【摘要】《天下無(wú)賊》是趙本夫創(chuàng)造的“理想王國(guó)”中的小說(shuō)之一,該篇小說(shuō)在出版不久就獲得了第八屆小說(shuō)百花獎(jiǎng),本文以接受美學(xué)及讀者反應(yīng)論角度分析趙本夫的小說(shuō)《天下無(wú)賊》,旨在探究作者是如何幫助讀者理解其作品,而讀者又是如何被故事的文本吸引的。
【關(guān)鍵詞】讀者反應(yīng)論;接受美學(xué);《天下無(wú)賊》;小說(shuō)分析
【中圖分類(lèi)號(hào)】I207?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文章編號(hào)】2096-8264(2024)04-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4.004
一、緒論
(一)課題背景
《天下無(wú)賊》是趙本夫創(chuàng)造的“理想王國(guó)”中的小說(shuō)之一,該篇小說(shuō)在出版不久就獲得了第八屆小說(shuō)百花獎(jiǎng),但真正大火卻是在馮小剛拍攝改編自該小說(shuō)的同名電影《天下無(wú)賊》上映廣受好評(píng)后,小說(shuō)再版,并深受讀者喜愛(ài)。該篇小說(shuō)描寫(xiě)了王薄與王麗這兩個(gè)賊在火車(chē)上結(jié)識(shí)了傻根,并“良心發(fā)現(xiàn)”守護(hù)傻根的錢(qián)的故事。
(二)研究目的及價(jià)值
通過(guò)分析原著,加以研究提煉小說(shuō)人物的中心思想,再結(jié)合讀者對(duì)小說(shuō)人物核心思想的理解形成多元文本,以“接受美學(xué)及讀者反應(yīng)論”為理論基礎(chǔ)對(duì)趙本夫的小說(shuō)《天下無(wú)賊》進(jìn)行文本分析。最終實(shí)現(xiàn)以理論切入文章,并對(duì)文章內(nèi)涵進(jìn)行較完備的分析。通過(guò)文獻(xiàn)考察,發(fā)現(xiàn)該理論常用于影視節(jié)目研究,以及翻譯作品研究,對(duì)文本細(xì)讀分析較少。并發(fā)現(xiàn)他人對(duì)趙本夫《天下無(wú)賊》的研究中,主要有敘事學(xué)角度、道德角度等進(jìn)行的研究,目前并無(wú)“接受美學(xué)及讀者反應(yīng)論”研究,故從該角度研究該文章有一定價(jià)值。
(三)文獻(xiàn)回顧
從劉可景《讀者反映論比較賞析〈吳宓先生〉》可探究出基于讀者反應(yīng)論角度的翻譯技巧,并且分析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位置把握對(duì)于文本創(chuàng)作的一個(gè)幫助,是基于原著設(shè)計(jì),來(lái)幫助讀者加以理解,并非是基于讀者的角度改變文本的初衷。①
張伶俐的《讀者反應(yīng)論的意義新究》也提到:“在翻譯過(guò)程中,讀者以一只無(wú)形的手牽引著譯者主體意識(shí)的發(fā)揮,換言之,讀者和譯者共同參與了翻譯的全過(guò)程,成為翻譯的二元主體。” ②
在丁帆的《人的生命意識(shí)窺探和技巧轉(zhuǎn)換——論趙本夫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里提到:“趙本夫小說(shuō)中有對(duì)人性的思考、人性中說(shuō)不清的潛在集體無(wú)意識(shí)予以裸露和思索,同時(shí)也對(duì)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存環(huán)境進(jìn)行解剖、鄙夷人性中的劣根性。” ③作者在小說(shuō)中對(duì)人性善與惡的轉(zhuǎn)換尤其是對(duì)人性中惡的概念進(jìn)行了重塑。
二、基于理論分析文本
(一)“前見(jiàn)”與“偽前見(jiàn)”的梳理與打破
現(xiàn)實(shí)生活當(dāng)中的小偷令人非常無(wú)奈,這就成為很多人厭惡小偷的主要原因。在這個(gè)時(shí)刻這個(gè)小說(shuō)的題目首先對(duì)讀者的“前見(jiàn)”及“偽前見(jiàn)”進(jìn)行了打破,而當(dāng)讀者細(xì)讀之后發(fā)現(xiàn)與現(xiàn)實(shí)產(chǎn)生矛盾反差以及讀者渴望無(wú)賊的融合這一過(guò)程從而激發(fā)讀者閱讀感受。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hù)是人性本善的真實(shí)體現(xiàn),但是理想的創(chuàng)建與現(xiàn)實(shí)之間形成了強(qiáng)烈的反差。對(duì)于這一點(diǎn),在原著中提到眾人勸說(shuō)傻根將錢(qián)通過(guò)郵局匯款回家,但傻根還是固執(zhí)己見(jiàn),堅(jiān)信天下無(wú)賊,執(zhí)意自己把錢(qián)帶回家。在傻根心中天下是沒(méi)有賊的,但是大家認(rèn)為傻根的想法是錯(cuò)誤的,這是原著小說(shuō)中傻根與其他人對(duì)于賊的一種看法。這種看法形成了強(qiáng)烈的反差。那么基于讀者的角度來(lái)看,讀者讀到這里,對(duì)原有概念認(rèn)知與小說(shuō)當(dāng)中的概念理解在尚未讓讀者得到定論之前,讀者會(huì)認(rèn)為天下有賊。
但是伴隨著閱讀的深入,天下到底有沒(méi)有賊?傻根的天下無(wú)賊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理念認(rèn)知呢?當(dāng)讀者處于這種矛盾之中的時(shí)候,“前見(jiàn)”及“偽前見(jiàn)”徹底的被打破 。
(二)竟有這樣的賊?——視域融合的體現(xiàn)
在《天下無(wú)賊》的原著當(dāng)中的王麗與王薄是賊,但他們不以斂財(cái)為目的,甚至?xí)㈠X(qián)捐給希望工程。這顯然不符合人們的常識(shí),從人們平時(shí)對(duì)賊的理解來(lái)看,這個(gè)詞往往是貶義,但是在本文中的“賊”卻成了劫富濟(jì)貧的“俠”,“賊”和“俠”有著截然不同的意思。賊指的是偷東西的人;做大壞事的人;邪的;不正派的;狡猾等等這種貶義,而俠指的是仗義勇為、扶弱抑強(qiáng)、愛(ài)打抱不平的人或行為。這正反的不同使此時(shí)文本中的賊與讀者概念層當(dāng)中的賊發(fā)生沖突,隨著王麗與王薄身份的明確化,讀者無(wú)法將兩人的身份與賊畫(huà)上等號(hào)。當(dāng)讀者曾經(jīng)帶著“賊一定會(huì)偷傻根的錢(qián)”“賊就是壞人”以及“傻根的錢(qián)財(cái)最終一定會(huì)被偷”的觀(guān)點(diǎn)進(jìn)入到小說(shuō)中去時(shí)候,作者通過(guò)讓王薄和王麗人格深處的靈魂救贖的感召與讀者“成見(jiàn)”產(chǎn)生了新的態(tài)度;“盜亦有道”。
“她扯扯王薄的衣袖小聲說(shuō):‘這小子……特像我弟弟,傻里傻氣的。’王麗時(shí)常給弟弟寄錢(qián),可弟弟不知她是賊。” ④
“這個(gè)從沙漠當(dāng)中走出來(lái)的傻小子,居然固執(zhí)地認(rèn)為世界上沒(méi)有賊!就像大沙漠一樣固執(zhí)。這一瞬間,王麗有些感動(dòng)。” ⑤
上述兩個(gè)選段是王麗與傻根情感發(fā)生碰撞的原因,也是能解釋王麗與王薄之后護(hù)送傻根的最好解釋。“王麗在傻根身上看到了弟弟的影子”,從正常視域下來(lái)閱讀,王麗一定會(huì)偷一個(gè)毫不相干且不認(rèn)識(shí)的“傻根”,但通過(guò)作者加入了這兩個(gè)細(xì)節(jié),從王麗的視角下,在遙遠(yuǎn)的火車(chē)上,遠(yuǎn)離家鄉(xiāng)毫無(wú)親人的一個(gè)地方,常年做著違法行為,按理說(shuō)她的內(nèi)心是十分冰冷的。而她經(jīng)常給弟弟寄錢(qián),可見(jiàn)弟弟在她心里很重要。通過(guò)這個(gè)片段體現(xiàn)出這個(gè)冰冷的“賊”是有內(nèi)心軟弱的區(qū)域——弟弟,一個(gè)她愛(ài)的人。而傻根有著王麗弟弟的影子——傻里傻氣的特質(zhì),從而使王麗在傻根身上看到了弟弟影子,這就為傻根與王麗之間形成了一個(gè)聯(lián)系。第二個(gè)選段是一個(gè)客觀(guān)視角,客觀(guān)視角講述了傻根內(nèi)心,奠定了他單純的特質(zhì),在那個(gè)年代,小偷是比較泛濫的,可以說(shuō)從常人視角下,“壞人”的出現(xiàn)是必然,但傻根不是,傻根認(rèn)為“世界上沒(méi)有賊!”這種善良的特質(zhì)此刻與王麗內(nèi)心的純凈柔軟呼應(yīng),也為后文二人的聯(lián)系形成了紐帶。尤其此時(shí)讀者便會(huì)想到傻根的錢(qián)應(yīng)該并不會(huì)被偷走,那么這是理想國(guó)當(dāng)中的人性的真善美的體現(xiàn),這也是原著文本召喚與讀者文本概念得以視域融合的重要性體現(xiàn)。
(三)守護(hù)傻根的期盼——期待視域?qū)ο蠡?/p>
在理想當(dāng)中大家對(duì)于無(wú)賊的認(rèn)知是基于人性的一種善良的美的假設(shè),如何讓讀者對(duì)這種假設(shè)加以認(rèn)可并信任,這便是召喚文本再一次發(fā)生作用的關(guān)鍵。當(dāng)讀者已經(jīng)對(duì)傻根的錢(qián)不會(huì)被王麗王薄偷走有了一定的理解,此時(shí)讀者對(duì)于人性中的善有了一定的信任。原著中的“引導(dǎo)者”引導(dǎo)讀者的視域發(fā)生更為深層次的變化,這時(shí)刀疤男出現(xiàn)了,此時(shí)焦點(diǎn)落在刀疤男身上,連讀者也會(huì)被這一添加的文本所迷惑,刀疤男是誰(shuí)?是賊還是曾經(jīng)被王麗和王薄偷過(guò)的人?而王麗與王薄則是一個(gè)有情意的賊。在這里有了兩種對(duì)于賊的認(rèn)定,讀者的文本概念進(jìn)一步擴(kuò)大,真實(shí)的賊與非真實(shí)的賊有了概念的上明確。當(dāng)之前讀者“盜亦有道”的想法產(chǎn)生以后,讀者會(huì)通過(guò)之前的經(jīng)驗(yàn)論,來(lái)想象,王薄和王麗會(huì)一直守護(hù)住傻根的錢(qián)并且使他順利到達(dá)目的地。而刀疤臉的出現(xiàn)是否會(huì)影響王薄王麗的守護(hù)傻根的愿望?
在原著當(dāng)中有這樣的描寫(xiě):“此時(shí)的王麗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yù)感,心里有些發(fā)抖,悄聲說(shuō):‘這家伙不會(huì)是沖咱們來(lái)的?’王薄沉吟下自言自語(yǔ),心里也咯噔一下,說(shuō):‘你懷疑他是公安?’” ⑥從作者描寫(xiě)“刀疤臉”的寫(xiě)法來(lái)看,這往往不是一個(gè)正面人物形象,但王薄荷王麗竟然懷疑他是公安,這種強(qiáng)烈的沖突形成了可讀性,而這個(gè)刀疤男的確就是警察,且以果敢聞名,但是他被王麗與王薄保護(hù)傻根的這一舉動(dòng)也為之詫異,內(nèi)心對(duì)于是否抓獲這兩個(gè)人開(kāi)始動(dòng)搖起來(lái)。從常理來(lái)看,警察抓賊是天經(jīng)地義的,在前文對(duì)“刀疤臉的警察”已經(jīng)為讀者進(jìn)行了一次理解轉(zhuǎn)換,而一位公安面對(duì)兩個(gè)賊的時(shí)候竟然有所猶豫,對(duì)是否抓獲兩個(gè)賊也有所動(dòng)搖,這種轉(zhuǎn)換是極具戲劇沖突的,于是文本召喚結(jié)構(gòu)從而體現(xiàn)出來(lái)。
從上述來(lái)看,文本的多次轉(zhuǎn)化,形成的這個(gè)召喚文本當(dāng)中的“引導(dǎo)人”不斷地指引讀者對(duì)賊有著更為多元化的理解,賊,不是真正的賊,天下無(wú)賊,這些似是而非的觀(guān)點(diǎn)來(lái)自于小說(shuō)當(dāng)中不同人物的思想觀(guān)念,那么這些觀(guān)點(diǎn)直接作用于讀者身上,這樣讀者原本思想概念層當(dāng)中對(duì)于賊的理解不斷擴(kuò)大,并發(fā)生概念遷移,從而形成新的觀(guān)點(diǎn)。刀疤臉本是一名公安,作為一名正派人物,此刻讀者在某種程度上感受到了刀疤臉可能會(huì)抓王麗和王薄。此時(shí)在雙王的行動(dòng)上成為了敘事者的阻止行為,當(dāng)讀者認(rèn)為整個(gè)事件變成雙王與公安之間的對(duì)立時(shí),突發(fā)事件的發(fā)生“強(qiáng)盜搶劫了傻根”使雙王、公安和強(qiáng)盜之間變成對(duì)立面,微妙地構(gòu)起讀者與敘事者的對(duì)立。
(四)文本召喚的使用引導(dǎo)讀者對(duì)“賊”的全面認(rèn)識(shí)
賊竟然能抓賊?賊的結(jié)局如何?如果說(shuō)前面是對(duì)于文本召喚的使用是一個(gè)層層鋪墊,那么到了這里便是對(duì)之前鋪墊的文本召喚的一個(gè)核心解讀。此時(shí)讀者對(duì)于賊的理解達(dá)到了更為深層次的一步,小說(shuō)文本當(dāng)中對(duì)于賊的迷霧得以層層解開(kāi):
1.當(dāng)把臉是公安——從懷疑變?yōu)楝F(xiàn)實(shí);
2.強(qiáng)盜出現(xiàn),直接搶走傻根的錢(qián)。出現(xiàn)新的賊,這個(gè)賊與讀者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對(duì)于賊的理解是不謀而合的;
3.王麗王薄為了保住傻根的錢(qián),王薄中刀;
4.最后乘警喊著王麗,王麗一臉淚水地說(shuō):“不需要了。” ⑦這是對(duì)王薄的擔(dān)心,也使讀者對(duì)王麗等人身份的一種認(rèn)定,他們是具有俠義之心的賊。
通過(guò)上樹(shù)的轉(zhuǎn)換和文本召喚,賊的定義在不斷變化,讀者對(duì)情節(jié)的預(yù)判在不斷改變。
(五)基于接受美學(xué)與讀者反應(yīng)論談讀者對(duì)于賊的認(rèn)知與理解
讀者的反應(yīng)根據(jù)小說(shuō)文本內(nèi)容不斷變化,成為動(dòng)態(tài)發(fā)展過(guò)程,所形成的美學(xué)結(jié)構(gòu)也發(fā)生變化。但由于小說(shuō)文本內(nèi)容也是既定的,這也使讀者動(dòng)態(tài)概念與文本形成了結(jié)合,在小說(shuō)《天下無(wú)賊》當(dāng)中,讀者對(duì)于賊基于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的概念的理解再到小說(shuō)當(dāng)中對(duì)賊的理解有著更為明確的界定,使得讀者認(rèn)識(shí)到天下無(wú)賊是可以成為現(xiàn)實(shí)的,從而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賊動(dòng)因形成,賊作案的過(guò)程以及賊的行為動(dòng)機(jī)等方面加以理解,有了這樣的理解才能對(duì)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的賊的治理制定切實(shí)可行的方案,最終才能達(dá)到天下無(wú)賊的目的。可見(jiàn)實(shí)現(xiàn)這一目的,是從小說(shuō)文本召喚開(kāi)始再到多元解讀發(fā)生的一幕幕過(guò)程,使得讀者對(duì)于小說(shuō)內(nèi)容的動(dòng)態(tài)式理解逐級(jí)層次的深入,這種引導(dǎo)是小說(shuō)的內(nèi)容召喚所形成的,這就表明接受美學(xué)中的美學(xué)來(lái)自于小說(shuō)當(dāng)中隱含讀者,而這個(gè)讀者是激發(fā)現(xiàn)實(shí)當(dāng)中的讀者獲得美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指引。
其實(shí)至始至終小說(shuō)文本并未發(fā)生變化,但是卻能讓讀者從中獲得一種深層次的理解。基于小說(shuō)的角度來(lái)看,讀者的反應(yīng)也能激發(fā)創(chuàng)作者對(duì)小說(shuō)內(nèi)容進(jìn)行深度性創(chuàng)造,這樣使建立在讀者概念與創(chuàng)作者對(duì)于角色把握的基礎(chǔ)上的人物性格剖析會(huì)更為圓滿(mǎn),這是一種基于讀者反應(yīng)論到引導(dǎo)讀者獲得美感,或者說(shuō)創(chuàng)作者賦予小說(shuō)美學(xué)的一種重要?jiǎng)?chuàng)作辦法。
(六)基于文本創(chuàng)建建立理想讀者與隱含作者之間的關(guān)系
小說(shuō)《天下無(wú)賊》當(dāng)中“好人”“賊”以有形和無(wú)形的方式滲透在小說(shuō)的各個(gè)章節(jié)片段,通過(guò)文本創(chuàng)建建立起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guān)系點(diǎn),這個(gè)關(guān)系點(diǎn)的形成是通過(guò)作者對(duì)“賊”的深度挖掘與矛盾故事設(shè)置以及疑慮的層層解開(kāi)所形成的,那么隨后便有理想讀者根據(jù)這個(gè)點(diǎn)不斷地追擊,層層挖掘小說(shuō)當(dāng)中的中心。尤其是最后該小說(shuō)以開(kāi)放式的結(jié)尾收?qǐng)觯o讀者留下了無(wú)限的想象,到了這里,“賊”到底會(huì)何去何從?但真正是什么樣的結(jié)局卻無(wú)人知曉。此時(shí)雖然作者的文本創(chuàng)建伴隨著小說(shuō)而結(jié)束,但是理想讀者的解讀才剛剛開(kāi)始。讀者對(duì)于作者創(chuàng)建的文本必然會(huì)通過(guò)各種途徑來(lái)發(fā)表自我的觀(guān)點(diǎn)、想法,這些恰恰又是文本再加工的開(kāi)始。這一新文本是基于讀者對(duì)于作者原文本為基礎(chǔ)形成的。在這一觀(guān)點(diǎn)基礎(chǔ)上,作者又會(huì)從中汲取觀(guān)點(diǎn),提煉其中的精髓,再次成為作者下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當(dāng)中的養(yǎng)分。筆者認(rèn)為,對(duì)于這樣的一個(gè)良性互動(dòng)恰恰是一部小說(shuō)當(dāng)中最為成功之處,它以獨(dú)特的社會(huì)背景,深層次的人物靈魂,刻畫(huà)出某一時(shí)代人物的特色的形象。
在《天下無(wú)賊》當(dāng)中,傻根對(duì)于賊的理解,是一種“烏托邦”式的非現(xiàn)實(shí)性主義理念。王麗與王薄恰恰就處于“好人”與“賊”當(dāng)中,他們可以被稱(chēng)之為是俠盜。而對(duì)讀者而言刀疤臉是一個(gè)具有一定正義感的假扮性賊,只有最后那個(gè)為了竊取傻根錢(qián)的人才是名副其實(shí)的賊。這些賊的出場(chǎng)均形成一部分獨(dú)立文本,在多個(gè)文本交織形成的過(guò)程當(dāng)中,給了讀者基于自身認(rèn)知水平基礎(chǔ)上建立美學(xué)的框架,即現(xiàn)實(shí)主義賊與理想社會(huì)的深度交叉。讀者想要構(gòu)建的一個(gè)文本世界,這個(gè)世界的構(gòu)建源來(lái)自于小說(shuō)當(dāng)中的人物、場(chǎng)景、故事脈絡(luò)走向等。此刻,這些概念的集合成為了作者創(chuàng)建《天下無(wú)賊》的根本原因,此時(shí)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guān)系點(diǎn)是積極互動(dòng)的。對(duì)此筆者有一個(gè)大膽地設(shè)想,如果該小說(shuō)的構(gòu)建以讀者反應(yīng)論的角度來(lái)創(chuàng)建,那么讀者便能在對(duì)美學(xué)的接受及對(duì)小說(shuō)的理解會(huì)達(dá)到更高的層次。
三、結(jié)語(yǔ)
通過(guò)理論與文本結(jié)合,運(yùn)用理論對(duì)該文章進(jìn)行了較全面的分析。從“前見(jiàn)”及“偽前見(jiàn)”的梳理打破、以及視域融合的構(gòu)成與使用、以及文本召喚結(jié)構(gòu)的形成都進(jìn)行了較詳細(xì)的說(shuō)明。人們可以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在該篇小說(shuō)中的文中隱含作者通過(guò)對(duì)賊的善與惡的轉(zhuǎn)變的不定向敘事和對(duì)劫匪的突然產(chǎn)生以及王薄中刀的突發(fā)事件使讀者受到作者的引領(lǐng),從而實(shí)現(xiàn)視域融合、發(fā)揮文本召喚結(jié)構(gòu)。其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文章運(yùn)用開(kāi)放式結(jié)局,每個(gè)讀者都能從中找到不同的結(jié)局,這也是理想讀者和現(xiàn)實(shí)讀者的完美呈現(xiàn)。
通過(guò)研究,本文從理論中嘗試分析小說(shuō)并找到形成多元文本的來(lái)源、途徑、方法,構(gòu)建起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度。這對(duì)于今后分析人物故事沖突、事件走向的文本構(gòu)建有一定的幫助。
注釋?zhuān)?/p>
①劉可景:《從讀者反應(yīng)論比較賞析〈吳宓先生〉三譯本》,《海外英語(yǔ)》2017年第4期,第126頁(yè)。
②張伶俐:《“讀者反應(yīng)論”的意義新究》,《科教導(dǎo)刊(中旬刊)》2015年第3期,第148頁(yè)。
③丁帆:《人的生命意識(shí)窺探和技巧轉(zhuǎn)換——論趙本夫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當(dāng)代文壇》1990年第5期,第35頁(yè)。
④⑤⑥⑦趙本夫:《天下無(wú)賊》,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參考文獻(xiàn):
[1]劉可景.從讀者反應(yīng)論比較賞析《吳宓先生》三譯本[J].海外英語(yǔ),2017,(04):125-126.
[2]張伶俐. “讀者反應(yīng)論”的意義新究[J].科教導(dǎo)刊(中旬刊),2015,(03):118+148.
[3]喬改鳳.接受美學(xué)與文學(xué)作品閱讀教學(xué)中的“多元解讀” [D].鄭州大學(xué),2010.
[4]丁帆.人的生命意識(shí)窺探和技巧轉(zhuǎn)換——論趙本夫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J].當(dāng)代文壇,1990,(05):33-36.
[5]趙本夫.天下無(wú)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