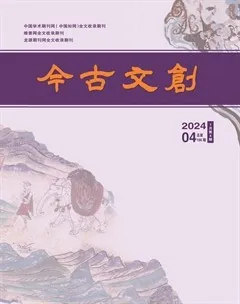超越闡釋對象的執著
洪義為
【摘要】傳統闡釋學的三大文本解讀觀分別是作者中心論、讀者中心論與文本中心論。但隨著目前對文本中心論的反思,人們認為傳統的文本解讀觀是艾布拉姆斯理論在闡釋學領域的延展,也是一種對現實闡釋對象的執著。然而,這一主客二分的文學闡釋理論忽略了文學世界的精神性、非現實性、自在性和唯一性。本文從顯隱說出發,希望推動文本闡釋對象從現實世界的對象轉向文學自在世界本身。在面對兩個世界交流的問題時,我們主張以想象體驗的方式代替邏輯思維的方式。
【關鍵詞】文本中心論;文學世界;顯隱說;超越;闡釋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4-003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4.012
文藝闡釋范式經歷了三次革命性的轉向。第一次是作者中心論的轉向。這次轉向使原先孕育于古希臘模仿說之下的“文學再現現實”的觀點轉為“文學表現作者”的觀點,強調文學作品的呈現具有作者的主觀性。直至1968年羅蘭·巴特在《作者之死》中表達了對作者絕對權威的質疑,文學闡釋轉向讀者中心論。以接受美學為基礎的讀者中心論模糊了解讀與誤讀的界限,“在推翻了作者的權威和否定了文學作品的自主性之后,又樹立了新的權威。”[1]為了調和讀者與作者的關系,20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轉而強調文本,形成了文學闡釋的第三次轉向:文本中心論。
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語言學、符號學、俄國形式主義等流派都以文本中心為基礎。但其局限和不足也很明顯,一部分學者質疑文本中心論切斷了文本與外界的聯系,另一部分學者強調過度拘泥于文本語言形式對文學實踐存在弊害。張江先生率先從“強制闡釋”的角度對文本中心論作出反思。而后韓清玉與蘇昕于《強制闡釋與文本批評范式——對新批評文本中心論的反思》一文中作出了相對系統的總結:“文本中心論所導致的唯文本闡釋傾向,在割裂作者與文本的先在聯系中喪失了意義闡釋維度的豐富性。”[2]在翻譯學領域,《論原文文本中心論在文學翻譯中的局限》一文也認為:拘泥于語言形式對文學性翻譯有所損害。本文認為三大中心兼有利弊,如何實現合理揚棄至關重要。
目前對于文本中心論的反思大多順從了“強制闡釋”的批評路徑,即對象的確定性、闡釋的期望與動機、整體性意義、強制闡釋的一般性推演[3]。直到2022年傅其林先生發表《強制闡釋的新理據及其悖論》一文,認為張江的《再論強制闡釋》也“陷入強制闡釋的困境之中”[4]。本文建立在傅其林的反思之上,試圖探索一種不拘泥文本形式,又能避免讀者主觀主義的文本闡釋方法論。為此,本文會對傳統文本解讀觀點的內在聯系作出解釋,分析其相同的局限。而后回到文學本體論的視角下,思考文學闡釋的對象這一核心問題。最終借由顯隱說的理論對文學闡釋實現文本中心論的超越作出解釋。
一、文學闡釋對于“在場”的執著
傳統的三大文本解讀中心分別是作者中心、讀者中心和文本中心。為了便于討論,不妨把古希臘模仿說納入,就會形成傳統闡釋四大中心:世界、作者、讀者、作品(下文稱為四大中心)。這實際上延續了艾布拉姆斯對文學四要素的總結。而艾布拉姆斯的文學四要素在表征上是一套去中心化的系統,他認為四個要素往往相互影響,而沒有單一要素可以取得絕對優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作為作品的文本再現著世界,表現著作者,呈現給讀者。因此文本這一溝通起讀者、作者、世界的媒介性產物,雖處于文學活動的樞紐,但全然沒有自我控制的權力。所以文本中心論有其進步意義,但其背后仍然是讀者、作者、世界的影子。為解決文本中心論滑向三大中心的問題,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語言學等外部理論專注于文本,這樣雖然避免了滑向三大中心,但是會淪落到“強制闡釋”的處境。因此,我們提倡一條超越艾布拉姆斯文學四要素的闡釋途徑。
艾布拉姆斯最大的局限在于其對世界的解釋。他認為“第三個要素便可以認為是由人物和動作、思想和情感、物質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覺的本質所構成,常常用‘自然這個通用詞來表示’,我們卻不妨換一個含義更廣的中性詞來表示——世界。”[5]不難發現,這里的“世界”并不包括人的精神性活動及其產品,而是可觀測的現實世界,是與人對立著的、外在于人的自然世界。王峰先生曾說:艾布拉姆斯的問題在于將“文學與世界實在化的并列”。真正的“文學與世界同樣是虛構意義上的存在物,而非一般觀念中的實在物”[6]。這一后果便是,文學批評總希望在作品中找到某種現實存在論上的依據,文學闡釋的對象也拘泥于現實中的客觀實在。例如作者的身世經歷,讀者的身世經歷,世界時代的重大事件等。而當這些明顯的客觀實在難以解釋文學批評時,闡釋學的對象落到了文本本身,這仍是一種客觀實在。
艾布拉姆斯理論的本質是以主客二分的在世結構作為哲學本體論依據的文藝學理論,由此產生的是一種認識論式的文藝批評范式。在海德格爾看來,認識論式的文藝批評執著于現實的“在場”,希望將作品背后的文學世界建立在現實世界之上。這種闡釋學“‘執著’于有效用的和可控制的東西”[7],而忽視了讀者與作者作為真實的人而具有的主體精神,忽視了文藝作品作為人的產物而具有的精神性,也忽視了文學世界本身的精神性,這當然有所偏頗。
二、文學本體論:文學世界的自在性
具有精神性的文學世界也稱作“虛構世界”或“想象世界”[8]。這種世界非現實而真實,有精神性但自在,主觀但唯一。文學闡釋應該以文學世界作為研究對象。王峰先生在《文學作為獨立的世界形式》一文中對文學世界作出了概念分析式的考察,認為“文學并不構成一個實際的世界,它不是現實世界的反映形式或改裝形式”[6]。文學有其自在的文本世界邏輯,“如果我們以某種確定的現實世界的事理來解說文本,只能算作過度解釋,而不是發掘出更深的真相。”[6]本文基本贊同王峰先生對于文學世界獨立性的分析。王峰的論述使文學世界獲得獨立于客觀實在(客觀世界與純文本形式)的自在。然而文學世界獲得絕對的自在性仍需要克服讀者與作者的主觀性,成為獨立的主體世界。
主體世界不是客觀外部世界,而是海德格爾認為的“此在世界”。純粹客觀的物質世界沒有意義,只有人生活于其中才被賦予意義。張世英對此總結:“人是世界萬物的靈魂,沒有世界萬物則沒有人,沒有人則世界萬物是沒有意義的。”[7]每個人對自己世界的認識、理解和思考,源自其與世界不斷的互動。每個人眼中的世界都有其主觀性,這使得人們的主體世界都只是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物自體世界的一個側面。
“文學的存在就是一個世界。”[9]與人的世界類似,文學世界是以客觀實在為基礎的精神性世界。其與客觀實在世界最大的差別在于是否被人賦予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文學世界也具有自我存在的主體性。在此基礎上人們可以窺見文學世界對于讀者而言的自在性。在人際交互的過程中,大家不會強行要求“你”進入“我”的世界,按照“我”的主體性意志而行為,這是一種對“互主體性”的承認。而文學世界也是獨立于客觀世界存在的自在實體,同樣具有主體性。讀者不能抹殺其精神性,也不能抹殺文學世界敞開而獨立于讀者的特點,應該在閱讀中與作品保持一種互主體性的關系。而閱讀實踐也確實是這么做的,人們只是順從文學世界,而不會強行要求文學作品貼合“我”的世界展開。
既然文學世界自在獨立,就不應該強行利用人的世界里的“在場”對文學世界加以闡釋。“作品在自身中凸顯著,開啟出一個世界,并且在運作中永遠守持著這個世界。”[13]文學闡釋不能拘泥于四大中心,而應該進入文學世界自身。而人們對于四大中心這些現實的“在場”的態度應該是大家進入文學世界的工具,而非闡釋文學世界的核心。換言之,文學闡釋的對象應當是文學作品自我“綻開”的世界。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提出:“文學是向既定現實決定何謂‘真實’的壟斷權提出了挑戰,它是通過創造一個比現實本身更真實的虛構世界來提出挑戰的。”[10]因此不應該認為文學世界是現實世界的從屬,從而得以避免模仿說和文本中心論的局限;大家也不應該認為文學世界是人的主觀世界的從屬,從而得以避免作者中心論和讀者中心論的局限。
三、顯隱說:文學世界是揭示的而非建構的
如果文學世界是自在的,那么新的問題是文學世界與現實世界是如何互動的?或者說,文學世界如何得以呈現?傳統觀念中,大家把文學世界的產生歸因于建構。“文學世界建構”甚至被赫伯特·格拉貝斯凝練為一個術語,他總結了三類相對主流的文學世界的建構模式:以英伽登為代表的現象學、以古德曼為代表的建構主義、以尚克和阿貝爾森為代表的認知主義心理學。這三種觀點大體上認為文學世界是被建構出來的,他們將文學世界與現實世界對立,并認為現實世界是客觀世界分層的產物。這實際上否認了文學世界的自在,從而滑向四大中心的枷鎖。從建構的立場出發大家傾向于認為作者通過敘事來建構文學世界,讀者對于文本的欣賞和接受成了一種解構過程
“顯隱說”是海德格爾藝術哲學對于審美的看法,張世英先生加以總結改造并于《哲學導論》中作出系統闡釋。文藝在于從“在場”的顯現者中看到“不在場”的隱蔽者,在于從文學形式語言中感受到背后無窮的共時性的世界。原初的文學世界不是自在顯現的,而是處于遮蔽的。而作品使得原本被遮蔽的世界得以“去蔽”,文學世界才得以顯現。在顯隱說的基礎上,人們不認為文學世界是被建構出來的。作品與文學世界的關系,不是前者建構了后者,而是前者揭示了后者。作者通過作品揭示了獨立自在的文學世界,而讀者通過對文本的閱讀也揭示了文學世界,這個揭示的過程就是“去蔽”。因此文學世界不是被文學作品建構的,而是被文學作品揭示而“去蔽”的。作者和讀者都是借由作品文本進入自在的文學世界。
此處對本文的觀點稍作總結:第一,建構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以文本為中心的。“文學建構世界”與其說建構的是文學世界,不如說建構的是文本本身,而文本的“去蔽”才使得文學世界得以敞開。傳統闡釋的對象通常是文本,而非文學世界。第二,每個文本敞開的文學世界應該是唯一的。一個文本照亮的文學世界也是相同的。其原因是作者與讀者都生活于相同的現實,闡釋對象是相同的文本。正所謂伽達默爾所言“理解文本本身”,而非理解讀者自己的世界。
四、想象:進入文學世界的方法論
進入文學世界的問題本質上是一個審美問題,是具有“直覺性、創造性、不計利害和愉悅性”[7]。文學世界具有精神性,這使得進入和闡釋文學世界的經驗必須要在體驗中積累,而并沒有辦法通過邏輯知識進行傳遞。僅通過思維和推理是無法傳遞具有不斷自我展開的“世界”,而體驗才是傳遞和開啟通向文學世界的方法,這與科學主義的認識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具有客觀現實性,能夠通過理論傳授的方式實現經驗流動。而前者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感受,這是一種主觀情感的經驗。張世英將這兩種方式稱作想象與思維。這也是“以文學世界為中心”的闡釋和“以現實世界為中心”的闡釋的最大區別。
以體驗(想象)為中心的闡釋方式,注重的是直覺性的感知,也是對現實出場物的超越。想象的闡釋在本質上是一種審美活動。而以思維為中心的闡釋學,即傳統三大文本批評觀點則相反。三大中心都關注的是通過現實世界的出場對文學世界加以解釋,這是一種邏輯性的解釋,本質是一種認識活動。比如解讀散文《“小趨”記情》,單單從作者身世的考證主義的方式或是從現代讀者的視角出發都失之偏頗。而拘束于文本的結構形式,從理性主義的推論進行文藝批評也有局限。顯隱說是從審美層面,利用想象和體驗進入整體性文本所揭示的文學世界內部加以感知。通過理解“小趨”的人性,從而直覺性地進入那個令作者絕望的時代。在文學作品的翻譯研究過程中,也應該回到文學世界本身,用創造性的方式對文學世界加以呈現,而非落入語言修辭形式的桎梏。
當然,對于邏輯性的文本分析的態度不是排斥或反對,而是超越和包含。必須承認,想象的方式綜合多個在場而共時性融合為一,這是傳統闡釋無法做到的。以思維為中心的闡釋學,無論是對作者、讀者還是文本形式加以割裂的分析都會有所失。因此文學闡釋需要超越思維到達想象。也就是張世英所言的“思致”:“致者,意態或情態也;思而有致,這種思想就不同于一般的概念思維或邏輯推理。審美意識不是通過概念思維或邏輯推理可以得到的。”[7]
五、結語
本文從文本中心論的局限出發,一方面解釋了文本中心論的局限性產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嘗試以文學世界為中心實現對文本中心論的超越。傳統三大文本解讀觀是一種主客二分形式的文學理論,大多會面臨執著于現實的局限。而想象的文學世界恰無法通過現實得以解釋,而是一種自在性的存在。因此,大家應該遵循顯隱說,超越三大傳統文本解讀觀,而在文學世界中找到依據,尊重文學世界自在地位,從其自我展開的自身去闡釋文學。而這種方法的必要途徑是想象和體驗。
當然,本文仍有很多未解決的問題,例如以想象為途徑的闡釋如何具體開展。但是本文希望做出一種范式上的轉化,為超越現實世界的局限性做出一定的嘗試。如果承認文學的本質是審美,就應該承認思維和邏輯的形式在文學研究中的必然局限。正如張世英所言:“新的藝術哲學方向所要求顯示的在場者背后的不在場者,與在場者一樣,仍然是現實、具體的東西,這樣的藝術作品所描寫的人和事和物也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體現實,而非經過抽象化、普遍化的東西。”[7]
參考文獻:
[1]鄧本添.關于西方文學批評史中讀者中心論的興起[J].考試周刊,2009,(07):30-33.
[2]韓清玉,蘇昕.強制闡釋與文本批評范式——對新批評文本中心論的反思[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1):162-129.
[3]張江.再論強制闡釋[J].中國社會科學,2021,(02):4-23.
[4]傅其林.強制闡釋的新理據及其悖論[J].文藝理論研究,2022,42,(05):122-128.
[5]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判傳統[M].酈稚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5.
[6]王峰.文學作為獨立的世界形式[J].文藝研究,2018,(05):5-16.
[7]張世英.哲學導論(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66,3,120,121,147.
[8]約翰·R賽爾.虛構話語的邏輯地位[J].馮慶譯.南京社會科學,2016,(06).
[9]海德格爾.林中路[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32.
[10]馬爾庫塞.審美之維[C].綠原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