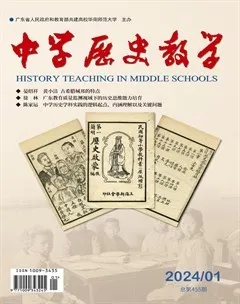古希臘城邦的興起和特點
晏紹祥 黃小潔
《中外歷史綱要(下)》談到,古希臘城邦形成于公元前8—前6世紀,其典型特征是小國寡民,公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隨后介紹了雅典和斯巴達政體以及城邦的社會結(jié)構(gòu),強調(diào)古希臘城邦民主政治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之上,享有民主權(quán)利的僅是成年男性公民,婦女、外邦人和奴隸都被排斥在公民隊伍之外,奴隸缺少最基本的權(quán)利。不過,由于篇幅限制,教材對城邦形成的具體進程、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和城邦政體的多樣性,以及城邦的社會結(jié)構(gòu)缺少具體的說明。本文的意圖,是根據(jù)學術(shù)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對古希臘城邦的基本特點做一些具體說明。
一、古希臘城邦的形成
古希臘城邦的形成源自鐵器時代初期巴爾干半島和東部地中海區(qū)域復雜的歷史形勢。學者們過去一般比較注意巴爾干半島多山少平原、交通不便的地形對城邦形成的影響,但當古希臘人定居于亞平寧半島南部、西西里島沿海以及黑海周邊時,盡管那些地區(qū)的地形與巴爾干半島頗為不同,但古希臘人仍保持了他們城邦的傳統(tǒng),并未因交通便利而建立疆域龐大的帝國。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自公元前2世紀中期起,羅馬共和國將馬其頓和巴爾干半島南部組建為兩個行省,且一直把行省體系維持到拜占庭帝國末年。那時的希臘人服從了羅馬和拜占庭帝國的統(tǒng)治,好像從未想過恢復城邦體系。近代希臘獨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希臘人盡管選擇以雅典為首都,卻從未嘗試要重回城邦時代,而是建立了延續(xù)至今的統(tǒng)一民族國家。不同時代的希臘人做出如此不同選擇的原因,肯定不是地理條件能夠解釋的。只有在公元前8—前6世紀那個特定的時期,古希臘人才發(fā)展起城邦制度,而且將其維持到羅馬征服,因此對古希臘城邦國家興起的原因,我們必須到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而非地理條件中去找。
盡管學術(shù)界關(guān)于古希臘城邦興起的具體年代和進程爭論頗多,但以下基本條件應當有助于它們的形成。
首先,是生產(chǎn)力水平。在古代世界,如列寧已經(jīng)指出的,“當時無論是社會或國家都比現(xiàn)在小得多,交通極不發(fā)達,沒有現(xiàn)代的交通工具。當時山河海洋造成的障礙比現(xiàn)在大得多,所以國家是在比現(xiàn)在狹小得多的疆域內(nèi)形成起來的。技術(shù)薄弱的國家機構(gòu)只能為一個版圖較小、活動范圍較小的國家服務。”[1]列寧這里說的是文明初興時的狀況,基本符合歷史事實,如蘇美爾人國家、埃及的諾姆、印度河流域文明時代的國家、瑪雅人的早期國家,基本都小國寡民,共和國早期的羅馬面積也不到1000平方千米。但這似乎并不適合古代希臘城邦,因為它們興起于鐵器時代初期,那時的希臘已經(jīng)歷過克里特邁錫尼文明的繁榮,而西亞地區(qū)也已興起過阿卡德、巴比倫、亞述、赫梯等大國;古代埃及也已經(jīng)歷過強盛的新王國時代。不過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仍然對城邦的興起具有重要影響。青銅時代發(fā)展起來的克里特邁錫尼文明,國家制度類似于古代兩河流域和埃及,是一種以宮廷為中心、居民社會生產(chǎn)諸多方面都受到宮廷控制的國家體系。那時的希臘不太可能存在公民獨立行使統(tǒng)治權(quán)的城邦制度。然而公元前2千紀末年東地中海文明的崩潰及其引起的動蕩(邁錫尼文明在此過程中也被摧毀),以及鐵器的流行,使生產(chǎn)工具的金屬化和小農(nóng)的獨立成為可能。這一轉(zhuǎn)變最初的表現(xiàn),就出現(xiàn)在荷馬史詩中。奧德修斯的父親拉埃提斯因家中被求婚人占據(jù),出走鄉(xiāng)村,自己帶著幾個奴隸開荒種地。雖然他的生活相當艱苦,但也不受任何外來打擾,尤其是不需要繳納賦稅,是真正獨立的農(nóng)民。而獨立小農(nóng)的出現(xiàn),意味著后世城邦公民隊伍——集土地所有者、公民和士兵三個身份于一體的農(nóng)民——開始出現(xiàn)。古風時代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不同程度地增強了小農(nóng)的地位,確保了公民隊伍的基本穩(wěn)定。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古典希臘全盛時期的社會基礎,是獨立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2]即使到古典時代晚期,公民中失去土地者仍屬少數(shù)。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興起和發(fā)展,使古希臘城邦公民中社會財富的分布相對均衡,內(nèi)部矛盾一般不太劇烈。以雅典為例,公元前6世紀初年梭倫改革前,亞里士多德和普魯塔克都宣稱,當時財富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中,窮人都成了富人的奴隸。然而梭倫改革對公民隊伍的劃分顯示,實際情況遠沒有那么嚴重。如果所謂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記載屬實,則第一等級的公民最低財產(chǎn)標準是土地收入500麥斗,第二等級300麥斗,第三等級200麥斗。學者們公認,第三等級就是一般的自耕農(nóng)。由此看來,最富有者和家道小康者財富的差距,不過兩倍半而已,第二等級——他們也被視為富人——和第三等級之間不過一倍半。在任何一個社會,這樣的財富差距都非常小。即使一般稱為傭工或無產(chǎn)者的第四等級,也并非真正的無產(chǎn)者,只是他們的財產(chǎn)未達到重裝步兵的標準而已。這樣我們不難理解,何以古代希臘城邦那么薄弱的經(jīng)濟基礎,卻從未發(fā)生農(nóng)民起義的原因了。
其次,是軍事制度的變革。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曾言及,古代最初實行貴族政體,因為那時騎馬的貴族構(gòu)成了軍隊主力。但自公元前7世紀中后期起,以自耕農(nóng)為主體的重裝步兵成為軍隊主力。作為重裝步兵,他需要自備武裝和給養(yǎng),在城邦選舉的官員指揮下作戰(zhàn)。因此但凡有資格成為重裝步兵的,一般來說至少家道小康。他們頂盔貫甲,防護嚴密,列成整齊的方陣與敵人交戰(zhàn)。戰(zhàn)斗中決定性的力量不是個人的技藝,而是整個方陣的力量,因此重裝步兵的戰(zhàn)斗特別強調(diào)士兵之間的相互保護和集體力量,將領的作用雖不是可有可無,但不是決定性的,因此古希臘城邦的交戰(zhàn)中,常有將領陣亡而整個戰(zhàn)斗取得勝利的現(xiàn)象。這一方面使普通士兵成為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的主力,增強了他們作為公民的自豪感和政治上的獨立性,創(chuàng)造了城邦的公民集體主義,另一方面使暴力分散于全體公民中,未被國家壟斷,因而古希臘城邦一般無力以武裝鎮(zhèn)壓公民的反抗行動。相反,一旦遭遇重大問題,如抵御外敵入侵,則公民全體做出決定,并承擔主要戰(zhàn)斗任務。
再次,文字的傳入和使用,有助于古希臘人使用成文法。從公元前7世紀開始,許多城邦陸續(xù)公布成文法。目前見到的最早的文字約屬公元前8世紀,刻寫于一個陶瓶上的荷馬《伊利亞特》中的兩句詩歌,表明文字到那時已獲得較廣泛使用。成文法出現(xiàn)稍晚,最早的是公元前7世紀左右克里特城市德萊魯斯頒布的有關(guān)該邦主要職務科斯摩斯任職的規(guī)定。公元前6世紀中期開俄斯的法律,則是目前見到的最早的代表民主政體的法律:那里明確規(guī)定公民如果對判決不服,可以向議事會上訴。在文獻中,據(jù)稱最早的成文法由阿爾戈斯的菲東頒布,加隆達斯、皮達庫斯、德拉古和梭倫等可能也都頒布過成文法。因而公元前7到前6世紀,古希臘城邦有過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頒布成文法的行動。雖然不少法律只是把傳統(tǒng)習慣以成文形式公布出來,但法律的公布,表明民眾公布成文法的要求對貴族產(chǎn)生了巨大壓力,迫使后者把法律公布出來。古希臘城邦法律文本大多刻寫在神廟墻壁或其他公開場合,十分便于人們閱讀。這種情況說明,成文法的公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貴族對法律的任意解釋和執(zhí)行,也表明城邦在向法治化方向邁進。
最后,是在上述變革基礎上,公元前7—前6世紀希臘世界發(fā)生了一系列政治變革。先是貴族政治取代了王政,后來貴族政治被僭主政治或民主政治取代。科林斯、麥加拉、西庫翁和雅典等城邦的僭主都在一定程度上打擊貴族勢力,調(diào)整部落組織和國家機構(gòu),或給貧窮農(nóng)民分配土地,舉辦各類節(jié)日強化城邦認同,不同程度地滿足了農(nóng)民的土地要求。在斯巴達和雅典等更多城邦,則出現(xiàn)了改革。斯巴達給所有公民分配了土地,并規(guī)定公民大會定期集會,公民大會有權(quán)通過立法、做出宣戰(zhàn)和媾和等重大決定,因而斯巴達被許多學者視為第一個重裝步兵國家,部分學者甚至認為它是第一個民主國家。雅典經(jīng)過梭倫和克里斯提尼改革,重組部落制度,組建新的500人議事會,公民大會成為公民參與政治最重要的機關(guān),標志著雅典在公元前6世紀末建立了民主政治。在小亞細亞的米利都、北非的庫萊奈等城邦,也發(fā)生了不同性質(zhì)的改革。這些改革的共同特點,是提高普通公民的地位,界定公民權(quán),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公民集體的形成和城邦制度的發(fā)展。到公元前6世紀末即波斯帝國入侵前夕,古希臘城邦大體形成。
二、城邦的基本特征
首先必須說明,古希臘城邦世界較今天的希臘國家范圍大得多,東起小亞細亞西海岸,西到直布羅陀海峽,北到黑海北部,南到北非,包括整個黑海和地中海周邊地區(qū)以及巴爾干半島和意大利南部。公元前8世紀到前4世紀大約400年中,古希臘人大約先后建立了約1500個城邦。
從領土面積和人口看,這些城邦規(guī)模都不大。斯巴達是面積最大的,領土達到8500平方千米。雅典次之,面積約2600平方千米。其他城邦面積一般要小得多。科林斯約884平方千米;西庫翁約362平方千米;埃吉那僅有85平方千米;提洛島,連同附屬于它的瑞乃亞島(Rhnea)在內(nèi),面積不過22平方千米。殖民地面積相對較大,但最大者如敘拉古,包括后來被它征服的萊翁蒂尼在內(nèi),也只有大約4700平方千米;小亞細亞北部沿海的希臘人城邦平均面積僅有100平方千米左右。與美國比較,它們的面積遠不及馬薩諸塞州(27336平方千米),與最小的州羅德島差可比擬(3140平方千米)。
至于這些城邦的人口,缺乏可靠的統(tǒng)計資料。公元前479年,希臘各邦和波斯在普拉提亞決戰(zhàn),參與抗擊波斯的各個城邦應當是重裝兵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據(jù)希羅多德記載,出兵最多的雅典為8000人,最少的帕萊和列普勒昂只有200人。在這些城邦中,重裝步兵人數(shù)超過3000的僅有5個,占參戰(zhàn)城邦總數(shù)的17%;超過1000的也僅有8個,約占25%;而重裝步兵數(shù)量在1000以下的有12個,約占40%。如果我們把輕裝兵計算進來,據(jù)此估計公民及其家屬的總?cè)丝冢瑒t雅典約90000—120000人;斯巴達約24000—32000人(庇里阿西人也出動了5000名重裝步兵,充當輕裝兵的黑勞士有35000人,但他們都不是公民,這里可以不論);科林斯約40000—50000人;最小的帕列和勒普萊昂只有1800—2400人。中等規(guī)模的城邦,基本在一到兩萬人。所以,希臘的城邦不僅空間狹小,人口也較少。即使以大邦雅典作為標準,大概也不會超過中國一個普通縣的水平。至于小邦,可能和今天的一個村差不多。
希臘城邦的小國寡民使它能夠?qū)嵭兄鳈?quán)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公民既是城邦的主人,更是城邦本身。離開了公民,城邦將無以立足。亞里士多德對城邦的經(jīng)典定義,是“城邦是一個為了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shù)的公民集體”,“若干公民集合在一個政治團體之內(nèi),就成為一個城邦。”[3]對希臘城邦而言,失去公民隊伍,遠比喪失一塊領土嚴重得多。公元前480年,當雅典人為避波斯鋒芒而退出阿提卡、科林斯將領阿德曼托斯宣稱雅典人已經(jīng)喪失祖國時,地米斯托克利義正詞嚴地回答,“但我們還有一個城市,希臘最大的城市:我們的200艘戰(zhàn)船。如果……你們第二次離開,并出賣我們,那么許多希臘人馬上就會知道雅典人已經(jīng)為自己贏得了一個自由的城邦,贏得了一塊領土,比他們拋棄的那塊領土好得多。”[4]地米斯托克利的意思是,只要雅典公民隊伍仍然存在,憑借他們的強大艦隊,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在希臘世界的其他地區(qū)建立城邦。
因為城邦的最高治權(quán)寄托于公民集體,希臘城邦發(fā)展出一套直接民主制度。所謂直接民主,就是公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即直接民主。體現(xiàn)在城邦機構(gòu)上,是幾乎所有城邦的機關(guān)大體都可以劃分為三部分:公民大會、議事會和官員。公民大會最為重要,從原則上說,所有公民,無論貧富都有資格出席,對國家事務發(fā)表意見,在重要問題上投票和表決。由于城邦之間的差異,有些城邦公民大會的權(quán)威相當大,所討論的問題幾乎涵蓋城邦事務的各個方面。有些城邦公民大會的實際權(quán)威較小,甚至若有若無。就整個希臘世界的情況論,第二類城邦是大多數(shù)。在那里,主要由農(nóng)民構(gòu)成的重裝步兵,在精英階級的領導下,在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的公民大會上,就國家的重大問題,主要是戰(zhàn)爭、媾和、政體的組織與構(gòu)造等主動或被動地表達他們的意見。在雅典,公民大會決定雅典的方針和大政,就許多具體問題通過決議。因此,在希臘城邦政治中,一切幾乎都是透明的,政治是徹底公開的活動。為說服公民,演說家是個不可或缺的角色,政治家必然同時是演說家。
議事會是公民參與國家管理的另一重要途徑。在原來的長老會之外,許多城邦組成第二議事會,其成員多數(shù)是普通公民,如開俄斯的議事會由每個部落各選舉50人組成;雅典的議事會梭倫時代為400人,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增加到500人,且一年一任,一生中最多不得超過兩任。斯巴達的議事會不曾經(jīng)過民主改造,由28人與兩名國王組成且終身任職。議事會與公民大會合作,還參與部分司法事務,成為公民參與政治的重要途徑。司法事務在荷馬時代已經(jīng)公開,到古典時代,至少就斯巴達和雅典而論,審判都是多人參與,并且公開進行。官員由選舉產(chǎn)生,但城邦的官員并非職業(yè)官僚,而是普通公民。為保證盡可能多的公民能夠擔任職務,幾乎所有官職都是集體職務。以雅典為例,執(zhí)政官是9人;議事會議員500人;市場監(jiān)督10人;港口監(jiān)督10人;最需要統(tǒng)一指揮的軍隊有10名將軍統(tǒng)帥。至于民眾法庭,全體審判員更達6000之眾,每個法庭的審判員,至少在百人以上。不那么民主的斯巴達,其國王由兩人擔任,而且權(quán)力平等;長老會和監(jiān)察官也都由多人出任。對其他城邦的情況,我們資料有限。但有限的資料顯示,從原則上說,官職都是任期有限制和職務集體制,少有一人專任或獨裁現(xiàn)象發(fā)生。
與集體職務并行的,是官職任期的短暫和輪換制度。亞里士多德認為,作為公民,所有人都有資格參與國家管理,擔任官職,但因官職數(shù)量有限,不可能所有公民同時擔任,于是有輪換制度,即公民輪流成為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于是,官職任期為一年,而且不能連選連任(只有將軍和國庫官等極少數(shù)需要專業(yè)知識的官職例外)基本成為定制。在一些民主政治高度發(fā)展的地方,為防止精英壟斷官職,會采取抽簽選舉。另有部分城邦,對那些影響過大的官員,會采取暫時流放的方式。對社會下層參與政治,一些城邦采取鼓勵措施,有些城邦對擔任官職、出席公民大會的公民給予經(jīng)濟補貼。大約從公元前5世紀中期起,雅典從執(zhí)政官到審判員都有數(shù)量不等的津貼。公元前4世紀初,出席公民大會者也獲得津貼資助。羅德斯、底比斯等為支持公民的政治參與,也不同程度地實行了政治津貼制度。公民如此廣泛參與國家管理的城邦,使它們確有資格被稱為“公民國家”。對古希臘人來說,政府就是公民。
直接民主的另一個基本原則,是公民之間的平等。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都把平等作為城邦施政的基本前提。所不同者,他們更愿意實行所謂的幾何或者說是才能面前的平等,而不是平均主義式的數(shù)量平等。城邦內(nèi)的沖突,很大程度上源自平民和貴族對平等的不同理解。平民要求數(shù)量平等,即身為自由人,應當在所有方面平等。為促進公民間平等的實現(xiàn),于是有一系列在今人看來令人費解的制度,如雅典的抽簽選舉制。抽簽讓那些財大勢雄的公民無所展其長,保證普通公民當選的機會。所有官員任期短暫,或一年或6個月,且不得連任,以保證其他公民的機會。
與抽簽選舉平行的,是對官員資格的嚴厲審查與嚴格監(jiān)督。公元前5世紀,包括將軍在內(nèi)的所有雅典官員都必須定期接受公民大會審查。那些沒有得到公民大會支持的可能被趕下臺、審判、罰款乃至處死。對于那些影響特別大的政治人物,還施行陶片放逐法,將其短期放逐到國外,以保證政治的穩(wěn)定和制度的正常運轉(zhuǎn)。斯巴達的國王世襲繼承,但也要受到監(jiān)察官和長老會的監(jiān)督。國王領兵出征之時,監(jiān)察官會作為監(jiān)軍跟隨。公元前418年以后,為進一步監(jiān)督國王,斯巴達人還給國王指定了顧問委員會,人數(shù)至少10人。如果國王被認為違法,會遭到監(jiān)察官和長老會的調(diào)查與審判,輕者罰款,重者流放。斯巴達歷史上因此失去王位的不在少數(shù),有些國王還不止一次受審。
輪番為治和平等所要求的必然是法治。希臘人對法治和規(guī)則的重視從城邦萌芽時期就開始。公元前7—前6世紀立法運動的基本目標,是就司法和官職的任命做出規(guī)定。希臘立法家,如雅典的梭倫、斯巴達的萊庫古等,立法過程中處理的最重要的方面,也是有關(guān)官職的規(guī)定以及司法程序。到古典時代,無論是以寡頭政治著稱的斯巴達,還是民主政治的典范雅典,無不實行法治。法律成為所有公民處理國家和個人事務的基本準則。伯里克利在為陣亡將士所做的葬禮演說中,首先提到他自己所以做那個演說,是服從雅典的法律。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就雅典公民來說,遵守法律,包括不成文法,是他們的基本準則,一旦違反,是公民的恥辱。斯巴達國王戴馬拉托斯在與波斯大王交談時,宣稱斯巴達人的確自由,但他們有一個至上的主人,那就是法律。斯巴達人對法律的敬畏,要超過波斯臣民對波斯大王的恐懼。用顧準的話說,“城邦公民‘輪番為治’的原則,也使得它必須發(fā)展出一套國家法和私法來。換句話說,城邦必定是‘憲政國家’或‘法治國家’。城邦既然是‘輪番為治’的公民團體,當然高于它的每一個個別公民,也高于它的一切統(tǒng)治者,這就是城邦的‘民主集體主義’——一種以公民最高主權(quán)為基礎的民主集體主義,所以,它必須有規(guī)章,要按規(guī)章治理。”[5]
既然公民是國家的主人,當然享有許多重要的權(quán)利。從經(jīng)濟上看,幾乎所有城邦都不對公民征收直接稅。國家的收入,或來自公共的礦山與財產(chǎn),或來自對商品征收的關(guān)稅。這些收入,有些直接被分發(fā)給公民,有些則通過舉辦公共工程返還給公民。在城邦的經(jīng)濟政策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富人承擔著所謂公益捐獻的義務。而享受這些捐獻的,往往是全體公民。它的根本目的,實際上是國家通過政治手段,調(diào)節(jié)公民之間財富的分布,以保證公民隊伍的穩(wěn)定。與此相適應,只有公民能夠占有土地和不動產(chǎn)。從政治上看,公民享有擔任公職、出席公民大會、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執(zhí)行司法等權(quán)利。
城邦公民性質(zhì)在軍事上的表現(xiàn)是公民兵制度。軍隊的主力是由公民充任的重裝兵。平時他們是生產(chǎn)者,一旦戰(zhàn)爭發(fā)生,則自備武裝和給養(yǎng),在將軍的指揮下參加戰(zhàn)斗。所得的戰(zhàn)利品,除奉獻給神靈的份額外,或分配給參戰(zhàn)士兵,或歸于城邦,城邦再以各種形式返還公民。軍隊和公民的合一,加上警察的缺乏,讓城邦政府除依靠公民的合作外,缺乏強有力的暴力工具,軍隊主要的任務是對外擴張,或者防范其他城邦的擴張。
必須指出的是,城邦的居民不僅僅是公民。擁有公民權(quán)者一般是出身于本邦公民家庭的成年男性,婦女和兒童無政治意義上的公民權(quán)。定居本邦的外僑很難取得公民權(quán)。到希羅多德時代,斯巴達僅有兩個外國人取得了它的公民權(quán)。公元前6世紀雅典一度對公民權(quán)比較寬松,但公元前451年通過伯里克利的公民權(quán)法案后,對公民資格的限制日益嚴格。甚至公元前403年幫助雅典恢復民主政治的外僑,盡管事先已得到過承諾,公民大會也通過了有關(guān)命令,最終仍未能取得公民權(quán)。除非公民自由人外,在許多城邦還存在依附者階層。在斯巴達,有黑勞士以及少量的奴隸;在雅典,則是大量的奴隸;在色薩利、科林斯和阿爾戈斯等地,也有很多依附勞動者為公民勞動。他們的存在,既是城邦經(jīng)濟的要求,也彰顯了公民權(quán)的重要性。公民的特權(quán)地位與外僑、依附者的無權(quán)地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強化了城邦作為公民團體的性質(zhì)。
古希臘城邦形成于青銅時代文明瓦解的廢墟上,鐵器時代獨立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興起,使農(nóng)民成為城邦公民隊伍的基礎。古風時代的變革,促成了城邦最終的形成。作為公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制度,城邦賦予公民一系列特權(quán),包括出席公民大會、輪流擔任國家官職、掌握城邦司法權(quán)力、獲得國家經(jīng)濟資助、得到法律多方保護等。不過我們不應忘記,擁有公民資格的,只是城邦中的一部分人。相對于外僑、奴隸、婦女等,公民權(quán)是地道的特權(quán)。由于資源相對匱乏,古希臘人對公民權(quán)格外珍視,輕易不授予外人。這使希臘城邦基本喪失走向大一統(tǒng)國家的可能,長期保持了小國寡民的狀態(tài)。但正是這些小城邦,創(chuàng)造了古代文明史上非常繁榮的文化。不過關(guān)于城邦制度與文化繁榮的關(guān)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問題,容筆者他日另敘。
【注釋】
[1]中共中央馬列編譯局:《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頁。
[2]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8頁。
[3] 轉(zhuǎn)引自啟良:《中國文明史(上)》,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240頁。
[4] 普魯塔克:《希臘羅馬名人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247~248頁。
[5] 顧準:《顧準文集》,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6年,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