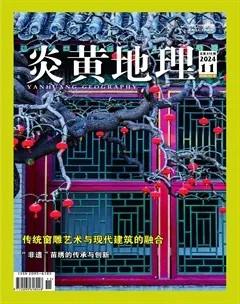藝隨境轉




文章旨在探討中國當代藝術領軍人物谷文達在不同時期的藝術創作特征,分析了他各階段的代表作品,將其藝術生涯分為三個階段:前衛本土藝術、海外華人藝術、中國符號的“擺渡人”。各階段分別以中國元素再認知、生物體實驗及中國符號回歸為特點。本研究試為當代藝術創作者提供參考,使其堅定文化自信并促進藝術創新。
前衛本土藝術家:水墨書法
20世紀60年代初,谷文達出生于上海高知家庭,自小受經典藝術熏陶。他早年學習傳統美術,拜陸儼少為師學國畫,并于浙江美術學院研究生班中國畫系畢業。水墨畫和書法,是谷文達抒發個人情感的首要創作媒介。
20世紀80年代初,“85”新潮來勢洶洶,平面藝術的表達方式已不能夠滿足藝術家們的滿腔激情,他們把目光轉向更多維、可塑性更強的裝置藝術。《靜則生靈》是谷文達的第一件水墨裝置作品,以書法、文字、符號、篆刻等為創作媒介。它以暈染肌理的山水畫為襯,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覆蓋在“靜則生靈”書法字上醒目刺眼的四個紅色墨汁寫就的圈叉,而作品的視覺中心是由紅色的纖維編織而成的類似印章模樣的立體凸面,并與左右兩幅書法由密集的繩索相連接。作品幽深的意境、立體夸張的巨型尺幅、對比強烈的視覺沖擊力,造就了谷文達作品中特有的宗教感。
新格局下,中國水墨畫界的現代化呼聲高漲,是堅守傳統的“筆墨中心”,還是全盤西化?谷文達的實驗水墨《遺失的王朝》系列作品給出了答案。以《暢神》為例,他運用了兩個字共用一個“申”字的“錯字”方式。觀者按照傳統的從右往左的識讀順序可讀為“暢神”,而按現在的方式從左往右讀則又可以理解成“示暢”或者“神易”。在反叛中國傳統水墨畫時期谷文達想要重建中國水墨畫。他搞水墨畫創作借此挑戰正統體制,其具體的實施方案除將異體文字書寫與水墨的抽象表現相結合外,還融入了一些行為與裝置的因素。他的作品熟練地將錯位、肢解的書法文字作為主要媒介,可見其出發點和基礎仍是傳統的,體現了他“前衛的本土藝術家”所具備的極具本民族特征的單一文化身份。
海外游牧者:生物材料
80年代后期,不少藝術家相繼出國,為了迅速在西方當代藝術界找到立足之地,也因急切尋求“自我”廣泛認同的心理作祟,其創作難免會受“他者”意識影響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身,好使作品被馴化為——“東方的”,以符合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獵奇目光和刻板印象。
《三者及其他》:生物活體。在此期間谷文達創作了名為《三者及其他》的作品。這是一項過程藝術,首次以生物活體為媒介進行創作,演示了老鼠受饑餓所迫而啃食毒餌自殺的經過。出人意料的,展覽剛開幕就受到挪威農業部與地方動物保護組織的抗議,表演被迫終止。此事件表面上是動物權益的爭議,實則是中西文化價值觀的本質沖突。東西方文化差異所引發的爭議性話題激起谷文達的濃厚興趣,就此谷文達深入研究普遍物質、探索東西方文化差異的過程中,其研究路徑從語言批判轉變為人體物質研究,從“一頭投入物質世界”轉變為“發現最本質的物質是人本身,人是這個世界上惟一的本體”。同時,他也審慎地選擇創作材料,從生命活體退縮到了人體廢物。
《俄狄浦斯》系列:人體廢物。在探討藝術創新與文化沖突交織的邊界時,不得不提及谷文達極具爭議性的《俄狄浦斯》系列作品。《重新發現俄狄浦斯1號:血迷》以使用過的六百個衛生栓和衛生巾為媒介,玻璃箱內的白綢上置入了從各個不同國家的女性參與者那里得來的現成品,一同寄來的還有衛生用品的包裝材料和她們的信件。作品本意探討生命、死亡和社會禁忌,不想卻觸及女性主義者的敏感點,展覽后迅速引發的大量女性憤怒與抗議差點摧毀他的藝術事業。或許是叛逆的驅使,隨后的《重新發現俄狄浦斯2號:誕生之謎》與《重新發現俄狄浦斯3號:愉悅與罪過之外之謎》以胎盤、胎盤粉、精液等人體廢物作為媒介再次猛烈轟擊公眾。在東方國家,胎盤作為滋補品使用已久且鮮有爭議,而在西方世界該物質卻傳遞出女權運動的味道。這表明即使是同種媒介在不同文化語境下也會激發迥然不同的現象。他原本以為西方言論自由,但沒想到仍避不開政治和社會禁忌。盡管轉型實驗的過程充滿了驚心動魄的兇險,但他沒有放棄對人體廢物的開發。
《聯合國》系列:人發。谷文達以人發為主要媒介創作的《聯合國》系列作品有幾十件,現以初始之時爭議較大的作品波蘭和以色列兩件為例。1993年10月,波蘭羅茲市的歷史博物館展出了谷文達的首個人發裝置藝術——《聯合國—波蘭:住院的歷史博物館》。女性的長發被散亂而齊整地排列在桌椅上和婦產科醫院的白色嬰兒床上,一旁的地板上零散地擺放著一些書籍,強烈的顏色對比同凌亂而有序的人發相交織,令人下意識地聯想到死亡和恐怖。裝置藝術最有趣的點似乎就在于“即時性”,緊扣歷史情境給予觀眾最直觀的感受并激發其無限想象。他顯然忘記了規避歷史遺留問題——展出地所在的博物館曾與世界上最大的猶太人墓地相鄰。這種異常的歷史聯系使得該人發裝置引起了當地猶太人對納粹統治下所經歷的摧殘和屠殺的悲慘回憶。雖然這段慘痛歷史的回憶不是他意有所指,但博物館當天在展出不久后便緊急撤停。
中國符號的“擺渡人”
世紀之交,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增強,中國藝術家被推到時代浪潮前,備受矚目。如谷文達所言,他從未放棄過對水墨領域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探尋。如借助前沿科學技術的力量并結合藝術創新,他在《墨煉金術》里研制了“人發基因墨”,該創作源于對生物材料與水墨融合的構想。他將人發經空氣高壓噴射機設備轉化為能夠制作墨粉的微小顆粒,再制成墨碇,呼應中藥里稱為“血余炭”的古方。《茶煉金術》又用綠茶制成宣紙。從茶到紙的轉換過程象征著從一種媒介到另一種媒介的演變,正如煉金術中礦物轉化為金子般,新作雖脫胎于舊物,卻仍承載著舊物質的文化精髓。值得注意的是,他化用前面兩幅作品的墨與紙繪制出的《基因風景》系列,既是傳統水墨畫材料的突破創新,也是其“涅槃重生之后的水墨筆墨歸零的一個代表作”。該系列作品不光延續了谷文達以往的人發藝術,還重拾了傳統文化符號,這些元素相輔相成,共同治療著中國畫的病弱。
作品《碑林—唐詩后著》同樣應用了傳統文化符號,其靈感源自中國的碑林。它獨辟蹊徑,以石碑為載體,不同于常見的矗立形態,而是設計為平臥地面,形似“墓志”。石碑上鐫刻著著名唐詩、其英文譯文和英文音譯三種不同文本,并記錄了制碑和拓片的完整過程。該作品所具有的紀念碑性,凝聚著谷文達的傳統文化修養和其對中國文化的敬意。這種對傳統紀念碑的物質性和“紀念碑性”的顛覆,實際上是對傳統文化符號的一種重新解讀和重構。
此外,谷文達在21世紀民生美術館舉辦的個展《西游記》上展出的《天堂紅燈》系列作品,從比利時政治重地布魯塞爾“一路西行”抵達中國上海。數千個色彩明麗的燈籠,或黃或紅,密布在當地標志性建筑上,構成了《天堂紅燈》,孫悟空、蒙娜麗莎、弗里達、夢露、埃及艷后等跨越五個大洲的多元文化符號的運用,是其對傳統的再度突破、詮釋與重塑。如他所說“真正的藝術作品,最后一定是走向大眾的、波普的”。
注重作品的公眾參與度,并非他臨時起意。從《我批閱三男三女書寫的靜字》,到《俄狄浦斯》系列和《聯合國》系列,“參與性”一直是谷文達鐘愛的方法論之一。作品《孝道》和《青綠山水畫的故事》,前者彰顯傳統文化,在佛山1060名兒童應邀,于紅綢上書寫《孝經》并剪發祭祖,后者傳揚自然之美,在深圳會展中心,穿著“青山綠水”T恤的1500名學童在宣紙上用藍藻水潑畫。兒童無疑是進入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生活層面的最強力的藥引,其影響輻射整個社會。他們的參與不僅體現了谷文達作為當代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更展露了他長期主義者的野心。
谷文達的藝術生涯所經歷的三段轉變不僅體現在他文化身份的演進上,也體現在他創作媒介的革新轉換中,其態勢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如大樹生長般,越到后面他所能使用的媒介手段就愈復雜,內容也愈充盈豐富。他在前衛的本土藝術家時期,主打水墨與造字等創作形式;在海外華人藝術家時期,從探尋生物活體到將人發作為媒介而使用;在中國符號的“擺渡人”時期,他更加注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求索以及強調社會公益性。這種流動的藝術表現走向是隨著語境變化而變化的。
谷文達的藝術作品也體現了兩大沖突:一方面,他面臨觀眾接受程度的挑戰,即在不同文化環境下創作的底線和限制;另一方面,他遭遇觀眾領悟的困境,即同一媒介在不同語境下理解的歧義,其本質在于藝術家創作意圖與觀眾收受理解的錯位。
然而,谷文達的藝術始終扎根于中國文化這一落腳點。盡管他的創作手法前衛、激進且具有破壞性,但藝術抱負卻是溫順的、傳統的、積極且理想主義的。沒有一直秉持著絕對的冷漠中立的理性態度,也沒有放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探尋,谷文達的文化自覺昭示了偉大的中華文明的優越性是經得住時間檢驗的。“藝術家的責任讓你成為好藝術家”,在“落葉歸根”的后半生,他致力于為中國文化游說世界,肩負起中國文化符號“擺渡人”的身份使命,并樂此不疲。雖然谷文達的藝術世界展現出種種不可捉摸的抽象和未知性,但只要我們用心欣賞他的作品,就能感受到其深埋于母國的根,觸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