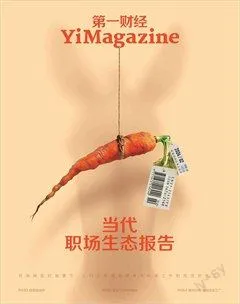鄭雅君:工作的意義需要自己去建構(gòu)
陶紫東
2016年前后,鄭雅君訪談了京滬兩所名校的共62名應屆大學生,盡管他們都通過高考獲得了一紙通往頂尖大學的入場券,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在畢業(yè)后能換來同等豐足的人生。鄭雅君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條件不太好的學生,即便考入名校,可能依然難以平抑自身弱勢背景的巨大落差感和對職業(yè)前景的失望,從而產(chǎn)生強烈的幻滅感和自我懷疑。
鄭雅君以此為課題寫成了碩士畢業(yè)論文,2023年春,這一研究拓展后集結(jié)出版為《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同年,全國普通高校應屆畢業(yè)生規(guī)模達到了史無前例的1158萬人,同比增加82萬人。年輕人面臨的競爭更激烈,出路更窄,評價標準更量化。
在書的第五章《方向》中,鄭雅君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來描述工作之于即將踏入社會的年輕人到底意味著什么:“名校的大學生日常接觸最多的三個話語制造者——家庭、大學和市場——平行地生產(chǎn)出三種不同的意義闡釋邏輯,為名校大學生看待工作的目的和意義提供了競爭性的圖式資源……這些觀念圖式來源各異,對工作意義的定義千差萬別,使大學生仿佛置身于一個多重意義框架的角力場。”
而如何看待工作的目的和意義,不僅關乎剛?cè)肼殘龅哪贻p人,其實也是許多已工作多年的公司人尚未厘清的命題。
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可供他們用來闡釋工作意義的角度是多重的,至少可以有家庭、學校和市場這三種角度。而且這三種角度是并行的、相互競爭的。
“家庭”就是我們在家里經(jīng)常會聽到父母講的那一套,包括父母在替你決策時看重的那一套,比如怎樣才能選到一份收入高的,或者體面、地位高一點、穩(wěn)定的體制內(nèi)工作,然后盡量能把自己賣出更高的“價錢”,諸如此類非常實用的角度。但他們大多不管小孩自己喜歡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怎樣才能把這個“交易”做得有性價比,能讓孩子以一種比較便捷的方式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至于這份工作是不是有意義、是不是好玩,這些都不是他們關心的。

畢業(yè)于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現(xiàn)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在讀博士,著有《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
他的邏輯非常實際,代表著一種頭腦冷靜、深諳游戲規(guī)則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很多父母其實和他想的是一樣的,所以他受到網(wǎng)民歡迎。我認為很大程度上可能家長,還有家長影響下的孩子都會覺得他說得有道理。
從滿足市場需求的角度來說,我覺得他沒什么值得苛責的。真正值得深思的可能是為什么社會上有這么多人信奉他這一套。張雪峰只不過是一個代表人物而已,但社會上相信這一套的大有人在。只要存在傳說中的這樣一套知識,能幫你了解游戲規(guī)則,幫你明智地選擇一個更容易找工作的專業(yè),為什么不聽呢?在他們的觀念當中,工作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東西。而且根據(jù)我的小樣本研究來看,這種工作觀似乎也是大家掌握程度最高也最普遍的一種思路。
“學校”指的就是學生在畢業(yè)典禮上經(jīng)常聽到的——工作怎么能只考慮養(yǎng)家糊口呢?你還得考慮為國家、為社會發(fā)揮價值。特別是當你念了好學校,總不能一天到晚只考慮你自己,等等。這是非常高意義感的一套話語。你可能只是一個拿3000元工資的基層公務員,但你覺得我是在服務國家社會,然后就覺得工作很有意 義。
“市場”這類話語目前好像表現(xiàn)出一點頹勢,但是仍存在。這套話語關心的是自己,以及怎樣可以在這樣一個市場化的世界中過上想過的生活。有的人可能會去市場里找喜歡的工作,有的人則對此不抱希望,認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份好干的或者有趣的工作。如果他是這樣想的,那他的工作目標就變成了如何用最短的時間賺到最多的錢,這樣就可以提前退休,停止工作。這種意義的來源是自己規(guī)定的,來自于個人趣味。我說它有一些頹勢,是因為大家在當前形勢下都有點恐慌,沒有安全感,對市場的信任度也進一步降低。
消費社會締造消費者,也塑造人對市場的依賴,有一天你會自覺地變成一個愿意去工作的人,甚至這個工作你可能覺得并沒有什么意義,但又不得不這樣做,因為你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合格的消費者,你的生活已經(jīng)非常緊密地嵌套在這個消費社會的體系里,就像《工作、消費和新窮人》里講的那樣,你可能有貸款或賬單需要不斷去還,所以你根本停不下來,諸如此類。消費社會創(chuàng)造消費需求,也創(chuàng)造消費者的身份認同。
在當時的社會,選調(diào)生沒有這么熱門,現(xiàn)在肯定變多了。這還是因為大家開始慌了,對民營企業(yè)甚至外企總的來說就是信任度降低了,對體制內(nèi)的信任度增加了。大家的路變窄了,所以就擠到一個賽道上去了。
在這樣一個森嚴的科層制社會里,大家分工極細,導致每一個人都在干自己的那一點點事情,一個環(huán)節(jié)反復做。這樣的工作的確很難產(chǎn)生意義感。
比如同樣都是制造玩具,以前的生產(chǎn)方式可能是作坊式的,一個人要從頭到尾做完,至少會經(jīng)歷比較完整的流程。現(xiàn)在分工越來越精細化,甚至很多工作都由機器做,人只需要照管機器,反復擰那一個螺絲,那他工作時的意義感當然會差很多。以前人們會覺得自己把一個東西從無變有,現(xiàn)在只會覺得自己一天到晚在同一個地方擰螺絲。
所以,因為過于細分,可能導致大量的工作是低技能的,再怎么做技能也不會增長,那么人就會厭倦。
就像剛才說的,我覺得這和工業(yè)社會的生產(chǎn)方式有關。但除了生產(chǎn)方式,現(xiàn)在這種無孔不入的評價體系也會吞噬“意義感”。
舉個非常小的例子,假設你是一名餐廳服務員,會努力地為自己生產(chǎn)“意義感”,比如讓你的服務給人帶來價值和愉悅的就餐體驗。但老板要求你給人帶來的這種愉悅感必須經(jīng)過量化,要落到實處,他會把服務員在大眾點評網(wǎng)獲得的點名好評和獎金掛鉤。這時你就不會像以前一樣,只是單純地想著我怎樣好好服務,而是會滿腦子想著怎樣才能獲得點名好評,會去想一些招數(shù)來實現(xiàn)這個事情,你可能去“操縱”一些客人,讓他們在你的引導下給出好評。做這些事時,你還可能會遇到很多不順,比如說某個客人不愿意給好評,你的行為可能給他帶來了很不愉悅的體驗,甚至可能還會把你罵一頓。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錯愕,我不是應該帶來愉快的就餐體驗嗎?可為了拿到這份帶來了愉快的就餐體驗的證據(jù),我反而給人家?guī)砹瞬挥淇斓木筒腕w驗。那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呢?這時你可能就會感覺,你的工作完全是荒謬的,沒有任何意義。
如今,這個現(xiàn)象在各行各業(yè)普遍存在,不光是服務行業(yè),在很多行業(yè),一個員工的優(yōu)秀程度必須經(jīng)過量化。比如一個剛畢業(yè)的博士要去學界找工作,該怎么證明自己有多優(yōu)秀呢?必須要說自己的論文發(fā)到了什么樣的刊物上、發(fā)了幾篇文章等。至于做的研究課題有多重要、到底在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揮了什么價值,這在當下的評價體系里不重要。當評比無孔不入的時候,很多東西都會被這個評價體系所異化。
對,特別是偏低層或者中低層的員工,完全是被評價的,也沒有任何能力去左右這個評價標準的制定。這些人真的會覺得非常無力。但到底要不要放下很多的自我,去實現(xiàn)一個大家眼中的理想目標,非要獲得一份大家眼中的理想工作,我覺得個人還是可以有選擇的自由,并不是沒得選。
我打個比方,可能父母經(jīng)常會告訴你找對象要找一個有錢的,或者找一個門當戶對的。你按照這個標準選了對象,結(jié)婚了之后可能又抱怨他沒有理想。那你就得問自己在結(jié)婚之前到底是不是根據(jù)有沒有理想來擇偶的,否則這種抱怨沒有任何意義,別人在提建議的時候也不知道你會這樣看重一個人有沒有理想。你既然知道自己非常看重這點,為什么要聽別人的話,以門當戶對為第一準繩?我覺得找工作也是這樣,還是得搞懂自己到底有沒有一個關心的價值主軸,如果有,那跟著這個價值主軸去選就行了。你如果愿意把找工作往大眾眼中的成功標準靠,當然也好。如果實在統(tǒng)一不了,那你還是得有個先后順序,否則就會發(fā)生上述情況:大家都覺得你過上了美好的生活,但你冷暖自知。
我也是花了很多功夫琢磨的,因為這個問題其實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是需要很多功夫的,要和自己探討很多問題,才能澄清很多觀念——你到底關心什么?你可以放下什么?假如真的要取舍的話,哪樣東西是不能取舍的?這些問題是需要經(jīng)過嚴肅論證 的。
我在書里也寫過,現(xiàn)在的年輕人面對的話語體系非常多樣。我把它稱作“文化角力場”,其中包含了非常多的矛盾和張力。所有人跟你說的話都自成一套,你很難說他們沒有道理。對現(xiàn)在的年輕人來說,已經(jīng)不再有一個既定的傳統(tǒng),能把我們固定在某一套思維方式和文化中,我們有點類似于在很多的“文化部落”中流浪,那么你到底要聽誰的?如果不經(jīng)過嚴肅的自我論證,任憑大家怎么說就怎么做,你就會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哪個你都舍不得放手,最后就只能被卡在最中間,這個時候你的自我認同也會出問題,因為你不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
我個人認為工作的意義、人生的意義,都需要自己去建構(gòu)。我們這一代人,包括下一代人,我們對于意義感的選項實在太多了,并且沒有一個現(xiàn)成的答案告訴你什么是正確的,是大家都認可的。更嚴峻的是,現(xiàn)在我們這個社會又沒有留下很多讓你去迷茫、猶豫和尋找的時間窗口。所以我認為,制造一些真正嚴肅的、和自己對話的機會,去建構(gòu)出自己對于工作的意義感,去問問自己工作對你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這件事對于年輕人來說是非常重要且緊迫的。我是一個對意義感有著高需求的工作者。我現(xiàn)在最感興趣的是去解決或者回應一些我能關心的問題,至于到底是通過學術研究還是其他途徑回應,我覺得都可以,總之要服務于這個問題以及它的解決方案。
我現(xiàn)在最關心的問題還是我的老本行,就是研究那些寄希望于教育改變命運的普通家庭出來的學生。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他會遇到很多文化掙扎,對于這些掙扎,我怎樣才能更好地支持他們?nèi)獙ΑN也幌M麅H僅通過發(fā)表學術論文的方式回應這個問題。我覺得這件事非常緊迫,不必非要等到轉(zhuǎn)化成學術成果才做。
我最近籌劃了一個微信公眾號“饅頭故事會”,它已于近期上線,我把它當成我工作的重要部分。它有點像一個非虛構(gòu)的寫作平臺,年輕人可以在這個平臺上分享他的故事,讓更多的同齡人看到,并給他帶來很多情感的支持,也讓他看到自己的處境,見天地,見眾生,見自己。在這些故事的基礎上,我可能還會發(fā)布一些同行的研究,或者一些有助于年輕人理解自身的知識性內(nèi)容,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彌合信息差,啟發(fā)大家更好地思考自己的道路。
所以你問我對工作的態(tài)度,我覺得我是以我要解決的問題為主軸來思考工作的。你有關心的事情,就自然而然想要工作。至于這個工作有沒有人雇我,是一份正式工作還是什么的,這個不要緊。
很多人都沒搞清楚要解決的問題。但這個世界不會給你很多猶豫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人就會感到非常被動。我幸運的一點是有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上了超長時間的大學,所以我可以在充分的時間內(nèi)思考這件事。很多人選擇繼續(xù)深造,可能也是為了讓自己想清楚一點。但這也許也不是最好的辦法,我覺得要想清楚一些事情,光想是沒用的,你得做,而且你得真的有所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