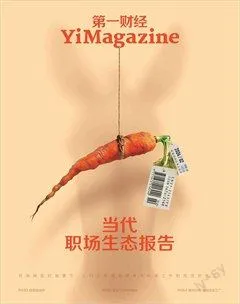為什么都要學下北澤?
趙慧
有太多人關注東京下北澤再開發了。
這有點不正常。我們最初關注到東京下北澤的幾個再開發項目,是因為它們基于下北澤區域的文化屬性,走出了一條展現地區特色的路子。但如果去考察的地產開發商們都想復刻這種“主理人非標商業”路線,這似乎就有些脫離這個項目的初衷了。
東京很多街區的形成和發展都與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密切相關,下北澤也是如此。東京城中心西側近郊的幾條鐵路——JR中央線、JR總武線、小田急線都是橫向延伸,彼此之間大多靠地區公交車連接,京王井之頭線是極少數能把這幾條西向鐵路連接起來的鐵道線路之一,下北澤就是其中一個換乘站點,另兩個分別是澀谷與吉祥寺。
吉祥寺開發是過去的熱點了,畢竟它已經連續多年位居日本不動產信息網站SUUMO評選的“首都圈最想居住街區”前列。它形成以站前商業為圓心,結合公園、商圈的大型綜合開發模式,貢獻了近郊生活圈與文化中心的極佳發展樣本。
澀谷與新宿一樣,是東京都心內公共交通動脈銀座線、半藏門線等地鐵線路的起點,也是東急田園都市線、東急東橫線、京王井之頭線等西向鐵路的始發站。在私鐵早年的圈地開發熱潮中,在澀谷、新宿這種進入東京都心區域的“玄關”站點周邊,東急、京王等私鐵公司早就設置好百貨店這類業態,它們與電車站直接連通,既能拉動客流乘坐私鐵,也能促進公司不斷發展多元業務。
而最近幾年的澀谷再開發,大多建立在鐵道線路高架化這個前提之下,這也是日本“連續立體交叉事業”的一部分。“連續立體交叉事業”是由各地政府與各家鐵道公司共同組成的協議會達成的共識,目標是減少地面上的鐵道閘口(日語中稱為“踏切”)。此前,這些閘口一旦有電車通過,行人和車輛必須讓行,既不安全,又影響通行效率。
東急這類私鐵公司在澀谷區域擁有不少地塊,于是和政府、物業管理公司共同組成了澀谷站前區域管理協議會,重新規劃和使用地皮,這樣一來,不同鐵道公司得以整合站臺位置、優化行人通行路線,進而重塑了公共區域與商圈。
借此重新審視下北澤街區的這輪開發,會發現它融合了吉祥寺與澀谷的再開發經驗。和澀谷一樣,因為小田急和京王這兩家私鐵公司實施了“鐵道線路高架化”,它們原本在下北澤地區設立車站的地面空間空了出來。和車站密切關聯的區域,就發展成吉祥寺站前那種以餐飲與綜合連鎖商業為主、適合大客流快速訪問的傳統招商業態。而在稍遠一些、靠近居民區的地塊,私鐵公司們向小商業主學習,嘗試新的商業形態,也就有了更多試驗空間。
在這樣的前提下,下北澤再開發進程中小田急旗下的代表項目“BONUS TRACK”選擇主理人業態,也和下北澤長期形成的劇場文化與古著文化密切相關。正因為有屬性相同的人聚集在這里,已有的小店也大多與這些文化有關,居民與街區拜訪者都希望保持此地的亞文化屬性,開發團隊才選擇去尋找能夠延續這些業態的運營者——因為這么做的“文化違和”風險最低,也有經過驗證的商業可持續性。
正因為有上述“基礎設施”的鋪墊,這些在長久歷史中形成的樞紐站點,才具備了作為換乘站點的大客流屬性。加上街區原有的亞文化特色,不需要新項目的吸引,年輕人就會源源不斷地主動前往,繼而發現新的值得拜訪之處。
城市給出的有趣答案永遠不止一個。城市開發者們真的把握住自己想要的方向了嗎?
但這也不意味著所有新項目都要遵循這個思路,做成主理人形態。這種形態有幾個前提:首先,主理人的店常常意味著“用愛發電”的試驗性,主理人對某個領域的鉆研程度往往比常規店鋪的經營者更深入,但這樣的店的消費受眾可能也更窄,或者需要接受教育。主理人們的品牌知名度通常也不高,需要先通過社群或者社交網絡傳播品牌,甚至需要借助項目的名氣吸引客流。因此,想要通過主理人來吸引年輕人拜訪,這樣的經營策略有不小的風險。
其次,主理人聚集的項目需要有長期眼光與耐心。項目主體可能需要用更優惠的條件去輔助主理人創業,就像BONUS TRACK那樣——連主理人住哪兒、房子如何以更低成本建造都規劃好了。開發商常常以“需要內容”為前提招募主理人團隊,但如果不能給予長期支持,只希望快速聚集人氣并盈利,反而更容易像網紅項目那樣曇花一現。
而且,主理人項目之所以常常被稱為非標項目,是因為每個“內容”與品牌的建立都需要時間與精力。它們在初期具備高度不可復制性與獨特性,很容易幫助項目塑造獨特的氣質。可一旦這些品牌特性被復制,稀缺性就會降低。開發商也需要厘清自己想要的到底是項目里“內容”的獨特性,還是單純聚集客流。前者需要長時間的積淀與營造;如果是后者,選擇連鎖型的人氣店鋪可能更容易達到目標。
這也是媒體視角中的“內容”與開發商眼中的“內容”不一樣的地方。在開發商看來,內容更多意味著構成空間的要素,它可能是品牌,可能是空間設計營造出的氣氛,以及聚集起來的客群。而在媒體眼中,內容是吸引某個特定族群的文化載體或表現形態。因此,開發者迫切想把他們視角中的“內容”裝進一個個街區盒子打包銷售,進而成長復制,而媒體們更希望看到隸屬于不同街區的人積攢出屬于自己的文化特色。
這兩個路徑的區別,大概是開發商更希望造一個街區,然后把它變成自己希望的樣子;媒體更希望觀察一個街區的形成,然后記錄文化的沉淀。這樣就不難解釋,為什么開發商更容易塑造一個個雷同的街道,而媒體總能捕捉到多元化的世界。
把視角放大到整個東京,新項目遠遠不止下北澤。我們發現,每個街區的再開發都需要研究這個街區留存下了什么文化,以及街區內的人希望延續怎樣的生活方式。平和不動產在重新開發“日本橋兜町”區域時,就基于那里的金融街區屬性,首先重建了新一代的寫字樓用戶畫像——做互聯網金融的創業者們,再基于這個年輕族群的需求配置街區的底層商鋪。此時,主理人業態就是可以關注的招商對象。
最近博得眾多關注,幾乎成了網紅的森大廈的幾個項目也是如此。它的目標族群是國際化的商業人士,它想營造為這些人服務的街區與設施,所以需要重新整合基礎鐵路、公路網,為他們搭好進出東京的移動通道,然后配置學校、醫療設施、酒店,再通過設置藝術機構與博物館、積極參與國際文化活動,提升這個區域在國際上的知名度。這樣的商圈就絕不可能選擇主理人業態。
它們當然有可能被批評為“士紳化”,但城市開發并不是只有士紳化這一條路。想要增加設施的公共屬性,大有將政府力量與民間力量結合的各種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策略,江之島水族館、墨田水族館就是利用這類方式將水族館做成人氣地標的創新案例;也有政府、非營利機構與商業體共同完成的項目,比如日本財團邀請16名建筑師與創意人士完成的那個超酷的“東京廁所”項目,既給澀谷區賺足了國際聲望,也解決了區內公共廁所的改造難題。
城市給出的有趣答案永遠不止一個。城市開發者們真的把握住自己想要的方向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