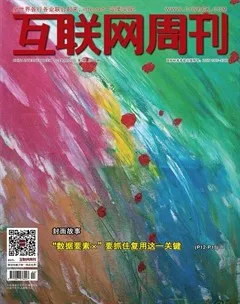大數據時代思政教育的審視與出路
韓曉曉 韓業全
摘要:大數據是時代進步的產物,在教育數字化背景下,探討大數據在思政教育領域的運用,需要對“整合”與“協同”、“優勢”與“劣勢”、“冰冷”與“溫暖”進行理性審視,同時,對于大數據在思政教育數字化發展中“雙向互動”與“及時預警”結合、“群體畫像”與“個體肖像”融合的作用價值進行數據審視。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討大數據相關技術手段與思政教育的融合發展,并從觀念轉變與評價完善、課程整合與協同育人、網絡安全與倫理問題、形式創新與角色轉變等角度提出具體出路。
關鍵詞:大數據;思政教育;網絡安全
引言
加快建設教育強國,推進教育數字化是重要內容。大數據是教育數字化的具體落實,大數據的發展為思政教育提供了新的機遇。大數據背景下的思政教育,可實現個性化教學、智能輔導、數據分析等功能,為思政教育創新提供了有力支持。大數據思維模式驅動下,思政教育模式正向數字化轉變,為思政教育數字化發展提供了契機。
1. 大數據時代思政教育理論的審視
1.1 “整合”與“協同”: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學科趨勢審視
“整合”與“協同”體現為系統性與功能性的統一。大數據思維下,不僅要求學科組成部分高度統一,并且強調各部分相互協調一致。在觀察或探索世界時,大數據可提供特有的思維和視角,促使思政教育呈現“固定轉向個性、糾偏轉向預測、分散轉向系統”的發展趨勢[1]。首先,在大數據審視下,思想政治學科也逐漸突破傳統“口述”育人模式,利用可視化數據平臺,從固有“文字理解”轉向個性的“圖像記憶”。然而,這一轉變不意味著“文字理解”的摒棄,而是二者整合的協同運用。其次,大數據思維下,思政教育主題糾偏趨向客體預測。傳統政治社會化情境下,過分夸大了教育者主導地位和權威性,忽視了教育客體的主觀能動性。大數據思維突出的共享、預測和開放性,為思政教育提供了可參考的思維方式。大數據思維模式認為教育主客體是一個完整的系統,不可割裂對待,系統內教育主客體“協調分工”,解構教育者權威性,賦能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性。最后,思想政治知識點的分散轉向故事線的系統。
1.2 “優勢”與“劣勢”: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網絡倫理審視
諾伯特·維納提出:“技術的未來是不可預測的,這也造就了善惡存在的可能”[2]。大數據為思政教育數字化提供強力支持,優勢顯著。一方面,大數據可對思政教育內容精準把握。“一切皆為數據”的時代,教育主體既能借助數據,對教育受眾精準把控,也能利用數據相關關系對于受眾聚合分類,根據類別進行個性化指導;另一方面,為思政教育決策科學制定提供數據支持。決策的科學與否,將決定思政教育的科學性、針對性及可行性。傳統教育決策為“經驗預判”,不具有針對性、關聯性、動態化的特征。而大數據利用數字化手段,搭建了一個結構性、系統性、非線性信息平臺,構建群體智慧決策模式[3]。
大數據在為思政教育提供便利的同時,也伴隨著不同程度的風險。其一,潛能的壓抑。大數據利用大量歷史數據和動態數據,對未來趨勢做出了數字化預測,易導致思政教育由“被動接受”轉向“主動干預”,限制了受眾主動思考的空間。其二,倫理的危機。大數據基于海量的數據獲取,可能出現受教育者隱私的泄露,產生信息安全問題。這是因為大數據本質就是信息的交換和共享[4],而信息挖掘者為了獲取更多信息資源,會對受眾進行持續的信息監控,使其陷入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繪的“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中。
1.3 “冰冷”與“溫暖”: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評價體系審視
大數據以數據為載體,用數據來解釋事物,數據是“冰冷”無情感的“事實”。而思政教育是以人的教育為主導地位[5],完全信任或依賴數據,便脫離思政教育工作中人文關懷和情感體現的初衷。因此,大數據時代的思政教育工作,不僅要呈現數據的“冷”,還要發揮人的“暖”,注重“客觀數據”與“主觀數據”相融合。主觀數據特指人的意識、感情、性格相關聯的要素,可體現人們內心世界[6]。過分注重數據的“客觀”,忽略內心的“主觀”,難以實現對思政教育動態意識的整體把握。大數據時代的思政教育評價不僅強調“效度”,更要展現人內心的“溫度”或“深度”。“動態數據”和“靜態數據”盡管具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均是圍繞“人的全面發展和提升”這一底層邏輯展開。因此,“動態數據”與“靜態數據”只有相融合、相統一,產生適宜的數據鏈,才是人文關懷的重要體現。
2. 大數據時代思政教育價值的審視
2.1 “雙向互動”與“及時預警”結合:大數據時代思政教育方式審視
思政教育是教育主體和客體互動,增進個體人格、品質、道德的動態過程[7]。思政教育的動態性體現在教學過程的實時把握,對于教學效果及時糾偏的動態性。傳統思政教育模式只是在教育周期內對于產生的錯誤糾偏,然后繼續進行。這一過程被阿吉瑞斯(Chris Argyris)命名為“單回路”(single loop learning)[8]。這種“單向”教學模式盡管針對性強,有助于頂層設計和系統規劃,但也存在問題延時性與錯位性,難以實現教育雙方信息對稱的問題。
思政教育只有實現“雙回路”,利用數據進行糾偏或自糾,借助數據和穩態信息相結合的形式,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大數據不僅能夠呈現狀態、展現變化,更能科學地預測趨勢,從而有助于教育主客體動態化的互動。不同教學情境中教學效果會出現明顯的差異性,大數據的實時交互特性,對于教育對象的學習行為可做到有效把控,形成思想狀態、情感特征、行為趨勢動態監控。教育者可借助動態數據鏈直觀發現教學過程中的熱點和難點,提高效率。另外,動態數據還具有及時預警功能。通過大數據預測教育對象行為趨勢和走向,發現思想、行為、情感的異常或風險,及時疏導給予關懷,避免走進誤區。
2.2 “群體畫像”與“個體肖像”融合:大數據時代思政教育對象審視
大數據可完整提供人群思想動態和行為方式分析材料。為了對教育對象思想軌跡提供參考,大數據可依靠非線性分析手段,對教育對象描繪出“多維度畫像”。盡管傳統思政教育分析多樣,多以定性分析為主、定量分析為輔,但依托數據樣本量有限,都是基于小樣本的“主觀預測”,結果難以信服。當然,這取決于教育對象思想活動的復雜性,以及可用樣本量的局限性,傳統分析難以實現研究結果客觀化、具象化、科學化。大數據秉承“所有皆可量化”的技術特點,可有效解決思想活動難以量化這一難題。大數據時代,個人的言行和思想都會在網絡空間印下“數據痕跡”,而大數據的聚合分析和數據跟蹤會將這些“數據痕跡”整合,描繪出直觀生動的“數據畫像”,從而預測個體的行為方向。
大數據可勾勒出思政教育對象的“個體肖像”,實現數據分析服務于個性化教育內容。思想政治面對的是“現實的人”,只有準確預測教育對象思想動態,匹配對應的教育內容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大數據對此有獨特的便利,表現為不僅可帶來洞察教育對象的“望遠鏡”,還可提供分析的“顯微鏡”,即利用數字化手段,對于教育對象思想行為抓取、聚類、預測,高效精準地進行數據剖析。
3. 大數據時代思政教育出路的探討
3.1 觀念轉變與評價完善:提升思政教育者的政治與數據素養
大數據在思政教育方面具有豐富技術優勢,而思政教育借助大數據的創新發展首先是觀念的轉變,全面提升政治教育者的政治與數據素養。傳統思政教育模式缺乏數據意識,導致政治素養未能達到應有水平,沒能全面達到我國關于思政教育的要求。這要求思政教育工作者不僅要增強對大數據本質屬性的全面認知,將數據意識提升到思政教育工作開展的戰略性資源,還要加強對數據的敏感度和辨識度,并且在大數據思維模式下,提升思政育人的聚類意識,進而實現增強政治意識培育的目的。大數據技術為思政教育評價提供了豐富的數據來源和分析方法。教育者應建立多元化、全過程的評價體系,關注學生的知識、技能、情感、價值觀等全面發展。同時,利用大數據技術對教育效果進行實時監測與反饋,為教育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3.2 課程整合與協同育人:構建完善的思政教育數據庫
在大數據時代,思政教育應與其他學科深度融合,打破傳統的學科壁壘,實現課程資源的共享與優化。此外,學校、家庭、社會等多元教育主體可以通過大數據技術實現信息共享與協同育人,為學生提供全面、立體的教育環境。大數據首要特性是海量數據,思政教育提供大量參考資料,如何甄別繁多的數據資料,將其實際運用于思政教育中,便需要在思政教育領域引入大數據預測分析技術。
一方面,思政教育者專業素養與大數據信息分析的整合協同。大數據時代,在價值網絡中,各個行為發生者趨于某種共同利益或價值認同而展開一系列互動合作,形成共贏的跨域協同價值網,是新生態構建的主要路徑。大數據時代,思政教育不能只單純依靠教育主體的“耳提命面”,還需要對現有大數據信息進行整合,協同大數據分析技術,實現從數據資料中挖掘出深層次的政治要素如情感性、思想性。
另一方面,要突破思政教育者數據分析處理的桎梏。要避免大數據工作者思政局限和思政教育者數據分析空白的弊端,促進大數據和思政教育者相互賦能的格局,消除數據異化引起的道德倫理問題。
3.3 網絡安全與倫理問題:建立安全思政教育數據保護機制
大數據信息開放性及交替使用性是其優勢體現,但也可能成為隱私泄露的根源所在。由于大數據基于海量樣本數據,因此,數據在進行二次利用時,保證所有數據生產者的知情權具有很大難度。首先,完善個人隱私保護制度。大數據輔助開展思政教育過程中,應嚴格遵守個人信息隱私保護制度,確保運用大數據過程合理合法,規避個人信息或數據泄露帶來的負面影響。其次,健全數據收集管理流程。不僅做到對于大數據信息技術人員從業道德、資質、技能的嚴格把控,還要建立大數據使用評價制度,全程以規范化流程進行數據采集,安全發揮大數據在思政教育領域的優勢。最后,構建數據應急處理機制。一旦出現數據泄露現象,立即啟動數據泄露應急處理方案,同時還要開展法律救濟任務以及追責行動。
3.4 形式創新與角色轉變:創新教育形式與教育者的角色轉變
大數據時代為思政教育提供了豐富的數據資源和新的教育方法。思政教育者應借助大數據技術平臺,對學生的個性化需求進行挖掘、分析和預測,設計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的教育內容。借助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先進技術,實現思政教育個性化、智能化、情境化的教學模式,從而提高教育質量。大數據時代要求思政教育教師從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變為教育引導者、組織者和導師,教師需要具備大數據分析與應用能力,利用數據驅動的教學策略,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指導與支持。
結語
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者除了合理運用大數據平臺的大量信息資源,還要保持大數據思維,對于現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和價值進行審視,由此形成一條從思想觀念、評價手段、課程內容、倫理安全到教學形式的創新路徑,真正實現教育數字化。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不僅要牢牢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定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要求,還要具有數據敏感性,根據數據趨勢走向,及時更新教育內容和觀念,以更好地適應思想政治教育科學化發展。
參考文獻:
[1]趙浚.大數據創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探析與應用[J].貴州社會科學,2016(3):120-123.
[2]鄔焜,陳新.信息主義和唯信息主義[J].自然辯證法研究,2023,39(8):3-10.
[3]許燁.大數據時代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策略研究[J].湖南社會科學,2022(3):134-139.
[4]曲一歌.大數據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挑戰與應對之策[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5(4):155-160.
[5]王習勝,朱羅莎.“思想政治教育”界域指認的偏誤與匡正[J].思想教育研究,2023(9):14-21.
[6]崔建西.思想政治教育論域下大數據熱的冷思考[J].思想理論教育,2018(5):95-99.
[7]羅紅杰,平章起.大數據驅動: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引擎[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6(4):257-266.
[8]張娟.基于大數據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研究[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8,36(4):139-142.
作者簡介:韓曉曉,碩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思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