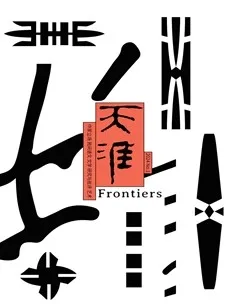記夢(2018—2019)
資料提供者附言
2018年,我在構思并試圖寫作長篇小說《回響》。每天面對電腦,卻寫不出滿意的情節和細節,于是刪刪改改,毫無進度更無驚喜,整天都泡在虛擲光陰的內疚里。為了對得起自己消耗掉的時間,便在寫不下去時記錄夢境,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還在寫作,還能寫作。但夢不是每天都有,而寫卻必須進行。非常神奇,自從我決定記夢后,夢就莫名其妙地多了起來,仿佛自己在討好自己抑或夢在討好手指,以至于我每天都是先記夢再寫小說。夢是現實的投射,沒有無緣無故的夢。夢也是一份心理學樣本,從中是不是可以看出潛意識,而又從潛意識里看到環境?任何時代的浩瀚之夢都由無數個人的夢匯集而成,就像點滴以成江海。這是一次沒有設計的記錄,真實是它的唯一原則。到了2021年9月8日,我的記夢行動中止,原因是《回響》的寫作順暢了,而夢也越來越少了。當我專心于正業時,副業就慢慢淡出。
2018年1月6日,周日
昨晚夢見自己回到家鄉,在我就讀和工作過的天峨中學打籃球(我的腳踝因打籃球受傷,半個多月沒摸籃球了),與楊秀高(當年的體育老師)在中學面向公安局那一方的坡上打球。球場是新開挖的泥地,臨坡一面沒有防護,我擔心籃球會隨時飛下坡去。楊說我們會把球護住。我把正裝脫在地上,換上運動服,在籃下投球。夢中隱約感到腳踝疼痛,匆匆收工。
這兩天往返于深圳,去書城“深圳晚八點”講課,在車站走了太多的路,驚動了腳踝。
2018年1月10日,周四
昨晚夢見自己提著幾個行李箱去飛機場,到了路上,看見一列車,很長,像地鐵的車廂,但是停在馬路上。室內裝修是S型座位。我上車找到一位置,放下手中行李,轉身欲下車再去提放在路邊的行李。車忽然動了起來,我跳下車,原先在路邊等我的一對作家夫婦不見了,我放在他們身邊的行李也不見了。那列車開走了,我顧此失彼,兩頭的行李均失。焦急,尋找,但都沒有結果。最焦急的是丟失了電腦包,里面有重要文件。正在悲催之際,醒了。就想,夢境中的難題可以用醒來解決,但現實中的難題卻不能在夢中解決。
中午,趁坐南航飛機回南寧,在機上睡了一覺。夢見一位著名評論家帶著幾個朋友到我的家鄉谷里。準備吃飯,我進屋找酒。屋內的陳設卻是南寧的次臥室和鉑宮工作室的陳設。翻遍所有紙箱,竟然不見一瓶茅臺。我收藏的所有茅臺都消失了。我非常內疚,先前說好要用茅臺招待他們,現在連一瓶都找不到。只好找了一瓶別的牌子的老酒,結果大家一喝,都搖頭。這是第一次在飛機上做夢。
連續兩夢都是丟失,可見這幾天的焦慮。一是焦慮小說創作的進度緩慢,甚至沒有時間創作(時間被會議和各種活動占用);二是焦慮過幾天又要到北京跟陳建斌導演修改劇本。
2019年1月11日,周五
午睡,夢。作家朱山坡告訴我,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到了廣西,準備去北海。我一路打聽,他到了我家鄉天峨縣。于是,我趕到天峨。他正跟一桌人喝酒。他說這幾天太緊張勞累,今天要喝醉,放松一下。我加入餐桌,一一敬酒,才知道,他是被一位女老板請來的。他喝得高興,竟然跳起了街舞。我跟他商量到學校做講座事宜。他在紙條上寫了三個字,這三個字我忘了。他說是一部電影的名字,我沒看過,叫“肝什么”?這部電影講的是建筑搬遷和平移的故事,他正講著,我醒了。
這是一個與現實對應的夢。早上,學生論文預答辯,楊教授說了一個電影名,我沒有看過,夢里出現了。午飯時,我去電聯系北海文聯主席,打聽近期是不是要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過來?她說是的。不想這事提前出現在我夢里。
2019年1月12日,周日
昨晚有夢,記不住了,感覺是亂。正應和這幾天的心情煩亂。上午去保養車子,午后回,補覺。夢見誰搬家,是個熟人,但忘了是誰。他說家里有50年前的柴火,要不要收藏?我一時沖動,腦海里閃過會不會有珍貴木柴?想去拿,但又想了想,50年的柴火,快變成灰了吧?于是沒有出聲。似乎還有雜亂的內容,但記不得了。記憶力越來越差是個原因,夢痕太淺也是原因之一。
2019年1月14日,周一
記昨晚的夢。夢見谷里村的三嫂遇到冤案,跟著我進城找人主持正義。她像“秋菊”那樣跟著我。具體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委屈,她邊走邊說村里的某某某欺負她,把她的一整箱物品拿走了,讓我想辦法幫她要回來。我忽然想起那個某某某,心有余悸,當年我似乎就生活在這種恐懼之中,隨時受人欺凌。走著講著,好像醒來。
后來,又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在賀先生的二十六樓,他讓我品酒。我把六瓶酒分為三個等級,其中最好的是巴馬瑤鷹拿來的50年(雜牌)老酒。夢跳切到河北作家李浩來廣西,李約熱組織夜宵。我們帶著剛才品過的酒到富安居附近文聯宿舍樓下的小飯店點菜。這期間接到賀先生的電話,他叫大家過去,說已經訂好了航洋大廈通宵營業的某飯店。于是大家又往航洋大廈趕去。
2019年1月26日,周六
開會,宿邕州飯店。醒來記住一個夢。夢見在河池師專,我還年輕,到某副校長家求婚,買的是二手玫瑰,很膽怯。進門發現夫人和岳母在房里。她們穿越了,竟然生活在那個年代的那個副校長家里(這個副校長也穿幫了,他是我畢業以后才提拔的)。我生怕岳母反對,但因為她女兒同意,她也就默許了。
一個穿越的夢境。
2019年1月28日,周一
中午瞇了一會兒,做夢。夢見自己從臥室出來,發現老人躺在鋪在地板的被窩里。正要道歉,發現那人是L。L起床,上旋轉樓梯,到一咖啡館,找了一張長條桌坐上。我一直跟著,坐下后才發現旁邊盡是孩童,Y坐在孩童中間,為他們講故事。我滑到桌上休息。桌下幾個孩子圍觀我。我離開,一痞子裝扮的人追上來,要與我打架。我奇怪,問為什么?他指指我的腳。原來我的腳上纏滿了紗布,我什么時候受的傷?他說從我的受傷情況來判斷,我是好戰之徒,故要找我打架。我趕緊溜走。
2019年1月31日,周四
開會,繼續宿邕州飯店。凌晨做了一個夢。夢見幾個人在我家聊天,其中有G先生,他像《安娜·卡列尼娜》(下卷)里維斯洛夫斯基挑逗吉娣那樣挑逗L,眼睛直勾勾地毫不顧忌地看,讓我像列文那樣難受。這幾天重讀《安娜·卡列尼娜》,夢在模仿小說。之后,在一樓客廳(仿佛聯排別墅的客廳),有一個籃球架,大家在投球(這是不是近幾天和正華先生說回天峨過春節,約好打球的原因)。我發現球是癟的,于是去找另外一個好的籃球,找不到,拿著癟球出門,到右邊汽修廠打氣。打氣過程中,發現球快裂開了(舊球)。于是另外找一個新球。充滿氣,拿回家里客廳發現又癟了,原來那個黑色的球不是球,而是我平時背的雙肩包。L在看電視,“馬大姐”在遠處做著家務什么的。我想那個新球到哪兒去了呢?想了許久才想起在廣西民大的家里。
夢里我已經搬到東邊的新房了。
2019年2月2日,周六
夢里,在某地開會,在山上。餓了,下山去吃飯。一群人。下山路上碰上WHF,她說下面有食堂。到了海灘邊的食堂,有好多人在吃飯。海邊有沙灘,有橫生在沙灘上的椰子樹,還有一些茅棚(無法確認,這些景象是否與上個月下旬去三亞度假有關?)轉過幾個茅棚,看見C羅在沙灘上顛球。有幾個人圍著。怎么會請到C羅?有人說是他來做公益,收入全部捐給窮人的孩子。
上山,記得有作家凡一平和鬼子。鬼子與人撞了一個滿懷,把那人撞倒在路上。那人好像是WHF。
2019年2月6日,周三
4號回天峨過春節,宿天峨五吉大酒店。晚上做夢。夢見我們在廣西新聞中心的樓上找509房間,碰見常哥,說某部門領導召集開會。大家都很忙亂,很緊張(這是否與常哥正在被安排寫一出彩調劇有關?我當然也被牽入其中)。
夢里有夢?在夢之前,我在停車場停車。下雨了,我忘了關車門。于是,走出賓館(不是新聞中心),往停車場走去。賓館門前有立交橋。在立交橋下面遇克參同學。他拉我跟他打牌。我輸了,打開背包,抽錢給他。一小偷湊過來,看見我包里的錢。我很緊張,抽了五十元給他。讓他走。他走了。我們繼續打牌。
因為回鄉過春節,背包里確定放了幾萬元現金。另外,回鄉過春節之前,一位劇院領導一直在跟我商量開某劇的策劃研討會。這個夢是否與這兩件事有關?不知。
2019年2月10日,周日
春節,還在天峨。住五吉酒店,調了鬧鐘,今天要回南寧。鬧鐘還沒到時,被夢攪醒了。夢見自己在一個課堂上,好像是學員,被老師點名對課本提意見。好多同學。我說這個課本沒有創新,沒有感情。正說著,一位本地的聯通老總走進來,夸夸其談,擾亂課堂。我看過去,課堂的一側,坐滿了他們公司的職員,一個個打扮得像空姐。原來,他們公司的職工也來聽課,本來要請一位比我名氣更大的作家來講課,但那位作家沒空,叫我頂上。夢里,我的身份瞬間從學員變成了老師。我對這位老總的表現極為不滿,宣布下課。我們一起走出來,老總走在前面。我跟上,對他說你沒有教養,試想如果是你在講課,我在下面高談闊論,你會怎么想?他做出一副謙虛的樣子,其實骨子里并不謙虛,問我是嗎?我說,是的,你沒有教養。他再也沒說話,朝長長的臺階走上去。我在后面跟著,加快步伐想超越他,想搶在他的前面走到臺階頂部的平臺。因為,在那里停著我的車。我認為我的這輛車能證明我也不是沒有財富。你老總雖然有錢,但我也不缺。但是,我還沒走到臺階頂部就醒了。
晚上8點回到南寧,補記此夢。
2019年2月15日,周五
昨晚夢見父親住院,好像是廣西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現實中,我父親從來沒到過南寧,我工作不久,他就去世了)。我從外地趕回,看見H在醫院里。是個大病房,有十幾張床排著。我沒看見父親,只看見病床上零亂的被窩。也沒看見母親。只看見H。我說了一些感謝H的話。然后,想到一院(夢里在二院的東邊,連在一起,像賓館)還住著一個朋友,就想去看看。但我走出二院往東,怎么也找不到那幢夢里的一院樓房,似乎一院不在這里,是我記錯了。我急赤白臉地轉了幾圈,從東邊樓道走到西邊二院,中途看見林老師和師母。他們住在一間小房里,我和L招呼他們。岳母也好像在場,她做了開胃的菜端上來。林老師說一直吃不下飯,只有喝幾口茅臺才想吃飯。我說馬上回去給您拿茅臺。大家擺菜,聊著,夢里已經忘記了父親,好像來醫院就是來看林老師的。
2019年3月3日,周日
昨夜的夢。夢見自己到了一個極具異域風情的地方,好像是墨西哥。我看見海邊的椰樹或者草棚,看見墨西哥漢學家L在一間房子的后面炒菜,她面前是一個大灶臺,灶臺上是一口大鐵鍋,炒的是雜碎,黑乎乎的一鍋。我不敢吃。然后,跳到文學聚會現場,來了許多文學大咖。我找一個作家照相,以為他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好像他還活著),結果這個人竟然會說漢語。我知道搞錯了,去找那個卷發的略黑的作家(我知道加西亞·馬爾克斯長什么樣)照相。這次找對了。我介紹我的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他一愣,說去年我們在法國見過面。于是,想起一次法國的聚會(夢里的想起,不是現實),一位作家向他介紹我,也講了《沒有語言的生活》給他聽。他說這個小說很棒,構思太絕了,所以當時對我就有印象。
引發這個夢的原因可能是:一、經余華兄推薦,法國文獻出版社正在跟我簽訂法文版《篡改的命》的合同;二、前幾天跟陳建斌導演在北京討論電影劇本《篡改的命》第四稿,他說《沒有語言的生活》構思簡直就是奇絕。
2019年3月4日,周一
午夢。夢見一系列緊張的事情,卻記不得了。只記得我和幾個人在新都賓館打牌(跟誰也是模糊的),一直打到深夜,J先走了。我打到深夜,出來見H與一紅衣女子(相貌猙獰)在大門停車場等我,說是有要事商量。她倆嚇我一跳,我心里一陣害怕。心想,難怪J先走了,是不是她已經看見她們故意先走的?那個紅衣女子,仿佛中午下班時在電梯里看見的那一位?長相確實有點兇。至于緊張心理,一定與春節之后的系列壓力有關。家庭的、單位的、身體的、經濟的……
2019年3月7日,周四
午夢。夢見原也用紙包了捏曲的釘書釘、彎曲的針和一根小小的捏曲了的鐵絲(像牙簽什么的),落在地面,被蘇格(我家養的貓)吃下。我們很緊張,卻沒有辦法讓蘇格吐出來。蘇格蔫頭耷腦地躺在墊子上。我為蘇格打麻藥,動手術,目的是取出它胃里的針。肚皮剖開了,它的胃貼在脊梁骨,沒有針,找不到,我很著急。想縫上,針又沒取出來,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縫。L一時在我身邊,一時又不在。我正在著急、擔心的時候,恐怖的事發生了。一丁(我家的另一只貓)撲過來,竟然咬住蘇格的內臟,扯下來跑開。我制止不住。蘇格一命烏呼。痛醒,嚇醒。
2019年3月11日,周一
昨晚,夢見和一群人在賓館里,遇見領導Q。他休假,正在寫小說(他怎么會寫小說?)。胡紅一說他有一個小孩要進西大附中讀書(他的小孩子都工作了吧)。這個信息被同桌的什么人聽到了。他們利用這個信息,打電話給領導說可以幫他的小孩子辦進西大附中(現實是Q的級別比校領導還高)。他上當了,告訴了對方密碼1024。我擔心詐騙者會用這個密碼攻破他的賬戶、信箱……內心一直緊張。
夢里出現一卡車茅臺酒,似乎只要輸入這個密碼,那一卡車的酒就屬于輸密碼的人了。腦海里出現清晰的畫面,是流動的卡車上一壁的茅臺酒箱。密碼輸入時,那一壁紙箱像電腦的屏幕。紙箱屏(類似電腦屏)有一條橫杠,密碼輸進去了。后來,就斷片了。
2019年3月12日,周二
記住昨夜的一個夢。夢見與陳建斌在山中一賓館討論劇本(現實中正在修改根據《篡改的命》改編的電影劇本),碰見一些熟人,都不明晰,是一些想見的人,也有不想見的人,一絲喜悅依稀記得。然后,我們往東,說是去上海。沒有坐車,而是走路。建斌說一邊走一邊看拍攝外景。到了一臨水的地面,草地上劃著一排排格子,是劃給人起別墅的。位置真好,水非常藍。然后到一菜市,出現田耳和張柱林。田耳被陳導欣賞,說今后的劇本都找他策劃和把關。然后,我們到一鋸木廠,看見一截大木頭放在木馬上。陳導要我和他鋸木頭。我一邊鋸一邊講解,那是童年和少年在鄉村看別人鋸木的記憶。
2019年3月19日,周二
凌晨2點被噩夢驚醒。夢見L端著一盅黃燦燦的紅茶進入臥室,說今晚要修改作品。我入睡,床竟然在路邊,是露天的。我睡左邊。床外的左邊是一排冬青樹,冬青樹外是馬路。景物是白天景物,幾個人影從地鐵口出來,經過冬青樹外。一坨寬大的黑影停在冬青樹前,我伸腳,竟然頂住了她的身體。她一動不動,向我壓來。我只是感覺她要壓下來,而其實這坨影子沒動。一股無形的力量束縛了我的雙手和身體。我喊“殺人啦”“快來人啦”,瞬間驚坐起來,看著左前。臥室的燈還亮著。L還沒睡,她說聽到我喊。
接著,夢見自己與作家L,導演F以及演員F在卡拉OK包廂喝酒。我們都喝醉了。F把我引進洗漱間。我們親熱起來。正在歡悅之時,F忽然停止,說不急,等回賓館休息了再繼續。
接著又做了一個夢。好像是導演催劇本。我說快改好了。
都是令人緊張的夢。
2019年4月4日,周四
上午拜山回來,在飯店與黃家親戚聚后回家,休息,做了一串夢。
之一:夢見在鄉村有幾圈牛,黑壓壓的一片。有人把牛從大牛圈里趕出來,關進四四方方的小牛圈里。牛關進去了,這個四四方方的牛圈就像一輛車似的動起來,沿著黃泥公路往城市的方向行駛。牛就是這樣被運進城市的。但牛不規矩,又鬧又踢。有人說,其實應該叫人趕著牛群進城。
之二:在一幢幾十層高樓的底部,我有一套豪宅。作家H來訪。我們沒有坐電梯,爬了幾十級紅木做的樓梯,到達。我有一套高級音響。H要聽搖滾樂。他找了許多過去的磁帶來播放。
之三:在打籃球。像是露天球場。籃球飛了出去。阿團救球,場地變成清廂快線的路面。球飛下去。在水中漂浮前移。那球是我的。我盯住球。球越漂越遠,漂進前面一座工地。橋面變成了大樓工地,我站著的位置變成了工地的樓層。球在地下層漂,漂到水面架著的木板下。
醒了。
2019年4月7日,周日
昨晚夢見與賀先生在韶山。發現我在多年前用150萬元買了三百多畝地。這塊地有山、有水、有石頭、有樹、有稻田、有人家,我沿邊界周游一圈,保存完好,唯一有個地方被小賣部戶主占去一尺寬,經當地領導協調,戶主答應不再占。領導說這地盤必須馬上動工,否則就要收回了。我著急,找賀先生商量,他說愿意用幾千萬把地買了,交給他的女兒經營農場。他女兒一直想自主經營一個農場。我的心里“啷格里個啷”,可惜醒了。
做這個夢的原因:一是跟賀先生和梅先生到韶山幾次,均是陪他們去談買地;二是梅先生在陳述買地理由時說要做實景演出,即稻田的藝術;三是本人有財富縮水的憂慮。
補記:前幾天有零星的夢,沒有記錄。只記住其中一個,夢見余華來廣西,大家相談正歡,托我打電話給防城港某先生。我翻找電話記錄,明明看見某先生的電話,卻怎么也按不出來。著急,叫別人打,他們也按不出那個電話。拿別人手機打,也調不出。總之,此先生的電話是眼睜睜看著,卻無法撥出去。曾經有過類似的夢,不知道是現實的什么投射?
2019年4月17日,周三
近日胸悶,很擔心。午休時夢見自己到車站為母親送行(母親已去世多年,經常夢見她)。車站在南寧市圓湖路一帶。因上午看了一個關于心梗的搶救短片,午休時似乎還惦記。這么想著,夢就開始了。我剛把母親送進樓去(普通住房,小高層),就發覺她的身份證或什么重要證件忘帶了。于是返身回去拿。母親活著時與我同住在南寧市民主路,離夢中的車站很近。我剛要返身,就見常哥舉著證件趕來。他說是來送證件的。我們走到樓下,正要對著二樓叫母親。忽然,常哥暈倒了,因為心梗。我立即按上午看的短片知識展開營救。先是打他女兒的電話,現實中我手機里明明有,但夢中怎么也找不著他女兒的手機號。看看手機里的人的頭像,估摸著撥一個。接電話的是我家從前的保姆,她說現在在常哥家打工。她說她馬上告訴常哥的女兒。沒想到,常哥這會兒醒了,他從地上爬起來,說沒事,他要回去。我阻止他,他不聽。然后我就醒了。
這是一個胸悶者因受現實短片的刺激而在中午做的夢。
2019年5月5日,周日
早上六點起床,記住一夢。夢見我還在河池工作,住在一個丁字路口的樓上,樓下是各色小賣部。我和原也還在睡覺。他還是小時候的樣子,我們睡在一張床上。我看見H兄和S兄出現在樓下(睡在臥室里怎么會看見樓下)。他們說來看看我。我趕緊下樓迎接。路邊擺了一張小桌,我們坐在桌邊喝茶。H兄提出三人打打牌(他是不打牌的)。他說了一種湖南打法,我基本不會,但S兄很快就會了。我糊里糊涂地打著,想要去給他們買幾條煙。我離開了,在河池的街道轉來轉去,怎么也找不到煙攤。我在河池工作時的工會附近的街道一一出現。但就是沒有煙攤。忽然想起,我的車上還有幾條煙(回到現實,我的車上確定有幾條別人讓我轉交而又一直轉交不出去的煙)。我在二十年前的河池,尋找二十年后我在南寧的轎車。找著找著,一直沒找到,夢就斷了,心里一直覺得對不起遠道而來的朋友。
2019年5月29日,周三
與友人賀先生等,到一個有中國畫風的地方,即有山有水有亭臺樓閣。賀要我說一句他樓盤的廣告。本來,他想要我約幾個作家過來,每人說幾句,但他們都沒有時間來。只好我來說。我說,投資有風險,買房要謹慎,我選某某樓盤。廣告拍得很粗糙。賀說,沒關系,先這么播吧。
畫面跳轉,我在一間房里。L在梳妝。我躺在床上,好像是熬夜打牌累了,需要補覺。另一位牌友,不知道是誰,躺在我身邊一同補覺,兩人躺在一起像同性戀。L梳妝完畢,站起來,畫面立刻變黑。
在一個培訓班,六張床位住了三個演員,我在其中。S兄來看我們,他也是來參加培訓的。大家坐在床上聊天。忽然進來三位非學員,他們訂了另外三張床。他們一邊說話一邊往地上吐痰。
三個夢斷斷續續,就像我現在的工作一樣零亂。第一個夢,是因為我在賀先生處買了房子,有現實的投射。第二個夢,仿佛是我跟L剛結識不久的狀態,那時我單身一人,常跟朋友們熬夜打拖拉機。第三個夢,沒有來由。
2019年6月7日,周五
現實中遇到太多的鬼,夢里昨夜又遇見。一惡鬼在一米遠處糾纏,于是我跟鬼對罵,叫它滾!它越來越兇,雙方對罵升級。L在一旁安慰我,讓我避讓。但我還是對抗到底,直到罵醒。對那些生活中遇見的鬼,我總是站在鬼的立場和角度來勸說自己,原諒它們理解它們,不惹他們。但夢中,我終于跟鬼暴發了沖突。我想從今天開始,對生活中的鬼我也不應該妥協了,必須像魯迅先生那樣,勇敢地面對,哪怕獨自戰斗。
2019年6月13日,周四
午夢,在八臘鄉。與L、原也回到鄉里。好像是去參加勝業父親的喪禮(他父親早幾年就去世了,是我的表姐夫,他不在八臘,而是在天峨縣城),又像是為了回去看我的母親(我母親也在2007年去世了)。仿佛是辦完了該辦的事,我在一條小河邊找到勝業,幾個人年輕人陪著他。我說你們守夜辛苦了。但需要叫他去谷里跟我母親辦一份合同,像是汽車保險。我是為了照顧他的生意才跟他辦的,甚至懷疑他收了我的保險金后會不會真的去保險公司幫我辦理?但為了幫他,我必須這么選擇(這個心情和近期我推薦一位朋友移民美國一樣,我心里怕推薦會帶出什么麻煩,但為了他我又不忍心拒絕,最終寫了推薦信),不知道為什么。我的汽車保險要他去跟我母親訂合同。他說他馬上去辦。我說原也跟他同去,看看奶奶。他們出發了。
回到房間,L在看手機。我把剛才處理的事跟她說了。她翻身繼續看手機。我的思維忽然跳到如何跟單位請假。我想說是回鄉埋葬母親,但母親還活著,將來她生病了我又如何跟單位請假?于是就決定跟單位領導實話實說。醒來,無限傷感。母親已經去世多年,我還吩咐原也和勝業去看她。母親明明已離我而去,在夢里她還活著。而勝業,目前還關在監獄里。他是我的表侄。因昨天晚上聚餐時說到他,今天中午入夢來。
2019年6月15日,周六
午夢。俄國譯者帶了十幾個人來旅游,大家坐在冰雪覆蓋的地面圍桌吃飯。凡先生和毛導演在桌。吃著喝著,凡先生跟一醉了的俄婦開房去了,那個俄婦明顯在挑逗他。我跟毛喝了幾杯,酒席處變成客廳。見那位翻譯,好像是羅季奧羅斯基,他和他的夫人以及孩子坐在一起,我跟他聊了幾句,就出門散步。
散步是正常的南方景色,一位衣冠不整者被兩個戒嚴的人喝斥,說不體面,這幾天有重要人物到來,所有人都必須穿戴整齊。我前面走過去L,她沒有被攔,我被攔住了,因為我穿的變成了運動服,脖子上還搭了一條擦汗的毛巾。戒嚴的說我這種裝束,有損城市形象。我辯解,甚至生氣,硬闖過去。走著走著,L不見了。我來到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有水庫,有大樹,有小島,典型的山區。那里有一群值班的人。他們看著我,似乎很警惕。他們說明天這里有重大活動,不能出入。我說我只是來散散步。中間仿佛有我認識的人,于是我被允許走進山谷。前面走著一對母子,像是俄國羅先生的夫人和小孩。她們走進山谷后,被人跟蹤。我怕他們出事,拼命追趕。但他們似乎是仙,快速登上山頂,不見了。我著急,心想萬一他們不見了,我如何交待。好像他們也是我求情讓他們進來散步的。我又返回了剛才那個有水庫有人戒嚴的地方。遇見一位矮個子熟人,具體是誰不知。他允許我再次進入山谷。他跟著我進山。滿山的樹,很美。突然出現籃球場。他不見了。一群人在球場上打球。他拿著兩個籃球上籃。因為他是隱形的,誰也看不見他,他可以在球場上躲開所有人的防守。而我看見他了。他是慢慢顯現出來的,從球開始。
醒了。跳躍的夢。都是平時的生活場景,接待外賓,喝酒,散步,打球。但一直處在緊張中。這和我近期的內心緊張有關嗎?
2019年6月18日,周二
在羅城參加會議,晚八點與凡先生趕回南寧。路上,H一直在用微信指責我,說我強求YY去參加什么活動。我反擊,并責怪YY處理不當。我心情不好,心想今晚一定會做噩夢。果然,半夜夢見一條蛇咬我的右臉,后來是兩個蛇頭在咬右臉。我嚇得往左邊一翻身,仿佛跌落深淵。當我左邊身子碰到床板時,驚醒了。
2019年6月24日,周一
昨晚夢,自己隨一行人沿紅水河谷往山區走。這一行人中有佩華,有領導張某。我們來到山中,是張的家鄉。他的家鄉正在搞旅游。他親自出馬做創意。我們看村里的第一個節目是燈光秀。一根大柱子,或一面墻壁,上面打燈光,演出一個穿越的故事。第二個節目,村民著少數民族服裝,圍坐唱山歌。張在里面,買力地唱。為村里的旅游業,他也是拼了。現實中,張是副部級干部。夢里他已經退休了。我竟然夢見他退休后的生活。或許,是周圍越來越多的人退休的緣故。
2019年7月2日,周二
夢見幾個熟悉的作家到八臘鄉采風,印象最深的有佩華兄。去了一個老板,是誰不清,反正是附庸風雅的。他帶了一位美人,臉色紅潤,年紀很輕。她趁老板閃開時勾引我。弄得我很緊張也很激動。但周圍都是人,我保持了極度的克制,不至于丟臉。
然后,在八臘鄉的正街中間,擺著地攤,可以喝咖啡(竟然如此洋氣)。一位女作家說她想來想去還是要寫作,是寫作改變了她的命運,給了她最多的好處(現實中這位作家一直在寫)。夢中,她像一位久不寫作的人在自責。
2019年7月5日,周五
晨起,打球,右腳踝扭傷,已經是第四次了。這幾天心情燥熱,前天考核完畢,我在圖書館停車碰飛后視鏡蓋。今早又腳傷。想起昨晚一個夢,也許是不好的征兆。夢見孩子外婆家正在安葬外公(其實他外公已經去世多年了),仿佛是在一片草坡上。外公的尸體停在墓穴里。我們正在忙碌,忽然看見母親拿著刀來幫忙砍草,她帶著深深的內疚。母親去世也多年了,我很高興能在夢中看見她。
2019年7月5日,周六
昨晚夢見在編輯部,有點像我曾經供職的報社副刊部,但不是那棟二十層的高樓,而是三四層高的舊樓。辦公室很寬,推車上擺滿了報紙雜志。蔣作家要查資料,我把自己收藏多年的雜志(主要是發表我作品的)全部拿出來,讓她翻查。仿佛一轉眼,那些雜志全不見了。她說送到二樓當廢紙打包了。我即奔二樓,二樓打包的人說已經讓車拉走了。每天從這個地方要拉走幾十包像單個書柜那么大的廢紙包。我叫蔣趕快去追。但那么多一模一樣的紙包,根本就找不回來了。我說太可惜了,里面有幾位名家的長篇小說首發雜志,語帶怨氣。
夢跳了一下,回到編輯部,看見韓少功兄長和一位陌生人坐在里面。我準備泡廣西茶讓他喝。他說他自帶了湖南茶。
2019年7月8日,周一
夢見桌前有一份合同,旁邊站著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和伊格達拉。我們在逼伊格達拉簽約湖人。只記得這個畫面,沒有結束。這個夢和近日看NBA交易有關。因為是湖人球迷,我為他們補強著急。
2019年7月16日,周二
昨晚在夢里見到了久違的李馮。他是“三劍客”之一,后來辭職去了北京,據說現在住在北京郊區的別墅里,寫作,拍電影。夢里,他住在一棟歷史悠久的別墅里,我們坐在陽臺上聊天。有幾位作家,也有李馮的夫人(都是模糊的)。他辦了一本畫刊,約我給他一個訪談。我發愁,說現在的訪談大同小異,已經談不出什么新內容了。但是,我想起廣西大學有一位做桂學的專家曾經給我做了一個訪談(夢中夢,根本沒有這回事),至今沒有發表。我打聽那個人,找了幾個人,才找到他的電話。然后,叫他把電子版發過來。(為什么會夢到訪談?白天華東師大的肖慶國博士從網上查到了多年前一位記者對我的訪談,用微信發給我。)
作家們都到樓下去吃飯了。我還在樓上找郵箱地址,要把那份訪談發給某個人。明明是李馮約我,夢里變成要發給另一個人。我在臺式電腦上搗鼓了許久,都沒把電子信件發出去。突然手里出現一份打印的訪談稿,訪談者叫蔣什么,我已經不記得了,但夢里曾出現三個字的名字。好像是發出去了,我下樓,在樓梯轉彎處穿皮鞋,穿了很久都沒穿上。我內疚,因為樓下等我吃飯的人已經等了很久,還有余華兄。我趕緊跑進一樓的包間。桌上每人一份越南米粉,就是在法國吃過的那種越南米粉,粉碗的旁邊配了許多張牙舞爪的野菜。大家都說好吃。(為什么余華會出現在夢里?也許是白天我曾給他轉發了一條微信推文的緣故。)
后面的就似乎斷片了,或者夢就在這里結束了。有點想念李馮,記完這個夢,給他發了一條短信。
2019年7月18日,周四
在墻門的前面有一塊平地,兩邊立著幾個講壇。有疑問或需要幫助的人到這里求助。于是,那些有能力的人(竟然有NBA球星)都會走出來,為求助者解決問題。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有能力指數,如果遇到指數高的,你的決議提案或者想要解決的問題就能解決(似乎是這樣,有些模糊了)。最后是我出現在這里,我是來求助的?好像是,也不是,或是來解決問題的?記不清了。只記得我的能力指數是57,不到60,非常沮喪。但有人說,這個指數已經是近期最高的了。
昨晚,一個莫名其妙的夢。
2019年7月23日,周二
夢見一個幾百平方米的牛圈,所有人都出去,讓工人起糞。這所有的人為什么聚集在這里?不知道。忽然這里就變成飯店。中間飯桌,周圍是熱氣騰騰的各種小吃店。
一位縣里的同學請我們吃飯。飯前,在一張長條桌邊,他拿來一摞書,是他為我出版的作品集(為什么要他出版?)。旁邊有谷里屯來的親戚,好像是田興強或秦樹林。他們要把這書帶回谷里。
忽然,同學脖子上掛著兩塊牌,是他父親和母親的靈牌,每塊牌又變成小罐,里面裝著他父母的骨灰。他說明天要回家鄉安葬他父母。他說的葬是葬骨灰。墓地寬,可以合葬他父母兩人的骨灰。
2019年7月24日,周三
昨晚夢到創作。夢見我創作一個男主人公,他一直在跟別人說他的夫人,后來發現夫人是他的虛構,他沒有結婚,卻騙了親人朋友們一輩子。她夫人竟然是幾個字母,在我的小說中。
2019年7月29日,周一
昨晚夢見滿姐夫在一間零亂的辦公室里,他有急事趕飛機,但要坐飛機需寫一幅書法。他怎么也寫不好,時間緊,他直接寫了自己的名字。他拿著兩盒美元,說是要強凍,仿佛是預苗(也許是他長期做防疫醫生的聯想)。有工作人員把那兩盒塞進柜桶,柜桶竟然是冷藏器。坐飛機的條件是必須等這兩盒全部冷凍。柜桶像書柜,外面遮一層紙,四處漏風,無法保住冷氣。我們絕望地等著,似乎永遠沒有機會。
鏡頭轉到草坡河灘。一群黃色的羊在河灘斗角,它們仿佛是監視我們的哨兵,不讓我們離開。我幻想家鄉有一群更威猛的羊,它們會來救我們。果然,沿著河灘走來一群威武的黑毛羊群,它們把看護我們的羊嚇住了。我以為它們會跟這群羊斗角,不料它們左轉彎,上坡,朝家鄉的方向走去了。它們好像是要把這一群羊帶回我的家鄉。
羊群雄赳赳地走上草坡。
2019年8月5日,周一
半夜醒時,提醒要記住夢。但早上打完球,忘了。好像是幾個夢疊加,只記得情緒,是愉快的情緒。仿佛是我和佩華兄等人開車去完成一個什么任務,車行在人流中,生怕碰傷人。而這個任務,是愉快的任務,并且有信心完成。
午睡,夢見歌手X到我家,邀請我為她寫廣播劇。家住一層,有一個拐彎的客廳,有點像我在河池時的房間,但樓層有區別,家具有區別,夢中這個更高檔。母親還活著,在廚房為我們泡茶。她主動擁抱我,還有親昵動作。我讓母親先別泡茶,要找好的茶葉,我翻遍茶柜竟找不出一包好茶來。杯子擺上了,紫沙壺擺上了,卻沒有好茶葉,我非常著急。X似乎困了,到房間休息。我到處找茶葉,仿佛一種困境。忽然母親拿出一小包好茶葉,像大紅袍。我問,在何處找到的?她說,是H給的。H沒有出現,茶葉她如何給?我困惑,開始泡茶。X起床了,來了一群她的熟人。家里很熱鬧。
2019年8月6日,周二
在一間會議室里,學校領導宣傳有幾位公示而不能提拔的干部。原因是他們有“瑕疵”。具體是他們到村里抓扶貧工作,收受了農民送給他們的土地,然后起了四合院。夢里出現一個壩子,中間一條長長的泥路,路旁有一個村莊。校長在晨跑。
然后,我尿急找廁所,有人指二樓。上去,有一個四方形衛生間。然后第二次尿脹,與柱林上去,發現下水道堵塞了,滿滿的一間水。有人在疏通。
再跳一夢,夢見自己收到一禮物(不具體),里面夾一封信。信抬頭有來信者名字,叫WGG。她是一位女性,說想念我。此信正好被夫人看到。她問這人是誰?要我好好交待。她還說去年跟我去意大利旅游(現實是前年去意大利過春節),有一輛車差點把她撞倒,是我設計的,想謀害她。我拿信上樓,這個樓像是別墅的二樓。看著信,我不知道此人是誰?心想寄點禮物給我惹出一堆麻煩。正在憂慮,看見胡紅一上樓,他的腳一瘸一拐,仿佛受傷了。而樓梯變成了毛坯房的樓梯,就是工地上還未建好的別墅樓梯。
醒來,凌晨三點。繼續睡。
2019年8月12日,周一
昨晚夢見自己與家人坐在客廳里,西式的別墅客廳,有幾個客人,氣氛融洽。客廳有一張原木長條桌,岳父和客人坐在對面(岳父其實已去世),夫人和岳母坐在我這邊。我出了一本作品集,很興奮地拿出來遞給岳父。他臉色突變,說這都是舊作品,不值得興奮,應該寫出新的作品來。眾人尷尬(這正是我目前的焦慮,新長篇寫作一直不順暢)。
2019年8月13日,周二
昨晚夢:兩個好朋友,在民國即崩之時,一個到了臺灣,一個留在大陸。他們每隔一段時間交換一箱物品。臺灣的拿來一箱食物,大陸的拿來一箱文件。大陸的拿到食物后,變賣,再買文件給臺灣的。像小說構思。兩人從青年一直交換到白發蒼蒼。
資料寫作者:東西,作家,現居南寧。以上資料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