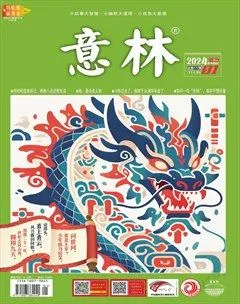有種中國式浪漫叫“讓人吃好”
王左中右

說到“讓人吃好喝好”這件事,好像就刻在了我們每個人的骨子里,很獨有,很中國式浪漫。
當你是個孩子,當你是個少年,當你老了,甚至當你不在了,掛念你的人都會給你帶點吃的。
他們怕你吃不飽,怕你吃不到。
而仔細想想,其實我們現在每一種食物,哪怕是很常見的,背后都有一個浪漫的故事。
很多人最心疼的一幕,是志愿軍戰士在吃凍土豆,甚至還有人發了張“如今土豆管夠”的圖片。
當時的美軍,有面包有午餐肉有火雞,但志愿軍只有土豆,還是凍的。
甚至就連凍土豆,志愿軍也不能頓頓吃上,零下幾十攝氏度的天氣,有些部隊甚至餓了三天三夜。
而且美軍發動了大量空軍,轟炸志愿軍的補給線,二戰時期的德軍就敗在這種名為“絞殺戰”的戰術之下:食物送不到前線,送到了也都壞了。
全世界沒有人相信,志愿軍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吃上飯。
那個時候,有一種叫炒面的食物就出現了。
別誤會,這個炒面不是我們吃的炒面條,而是字面意義上的炒面粉。
把面粉和其他谷物粉混在一起,加鹽炒熟,干燥不易腐壞,有水就能吃。唯一的問題是,沒有儲備,前線要在一個月內湊齊1500萬斤炒面。
當時的東北,家家戶戶都在忙著做炒面,多一點是一點,多一斤就少一頓餓。
那些平日里算計著,要燒多少才能熬過冬天的燃料,被不計成本地扔進了灶臺下。只求在最短的時間做出來炒面,不讓前線的戰士餓著肚子打仗。
炒面也許不好吃,但這些東西,就是當時他們拿得出來的最好的東西了。
有人可能會有印象,東北乃至華北地區還存在著炒面這種食物。只不過在加了糖、油、堅果,努力做成了一道點心,還起了個頗具浪漫色彩的名字,叫作油茶面。
至今我們回憶起這段歷史,回想起那個叫炒面的東西,字里行間我們看到的是勤勞、是汗水、是犧牲、是樸素。
這一切和浪漫沒啥關系,但好像又浪漫至極。
把吃的送出去很難,把吃的帶回來也要冒著生命危險。
很多人都吃過番薯,但可能不知道番薯是明朝才引進中國的,而且能吃到番薯還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
這和一個叫陳益的人有關。
當時,番薯是個很珍貴的東西,當地人并不想讓外人帶走。私帶番薯,是重罪。
機緣巧合下,這個叫陳益的人,得到了幾株番薯苗。可能是心存僥幸,為了讓兒女、讓家里人一輩子都餓不到肚子,他還是選擇把番薯帶回去。
沒想到正準備上船的時候,走漏了消息,安南官兵趕過來。
被抓到是死,臺風天出海也是死。但當時陳益還是連夜往回趕,繞過官兵,躲過流寇,扛過臺風,幾經波折才把番薯帶回來。
關山難越,浪漫不絕,就為了讓在乎的人吃飽飯。
而讓人吃飽這件事,陳益做到了,在番薯苗帶過來后,很快在中國這塊版圖上到處生根發芽。
在番薯全面種植之后的兩百年里,中國的人口,從一億變成了四億。在那些動不動遭遇天災人禍的日子里,番薯讓太多太多人有了一口吃的。
很久以后,陳益墓成了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不斷有人建議為他立像、立廟。
有些宗教總告訴我們,神愛世人。但在這片土地上,我們把神農、把嫘祖、把陳益當成了神。
因為我們知道,誰讓我們吃飽了飯,誰愛世人。
還有一個人,大家可能都知道,袁隆平。
但可能不太清楚研究雜交水稻這件事究竟有多了不起。
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都知道雜交水稻,但在70年前,這個詞是異端中的異端。
因為當時中國的生物學理論,被“蘇聯生物學”統治。這種偽學,是一個“學術神棍”將僅應用于園藝的理論,擴大到了全體生物而得來的。
幸好袁老有一位姓管的老師,幫助他了解孟德爾的遺傳學理論。
蘇聯偽學荒謬,西方權威一樣不靠譜,美國哈佛大學教科書明確寫著:水稻雜交無優勢。
在那個美蘇二分世界的年代,袁老以一己之力,同時對抗東西方兩大遺傳學權威理論,但他從來沒有畏懼過,因為他所心心念念的祖國同胞,還沒有吃飽飯。
更因為那個禾下乘涼夢,實在太美了。
美到即便袁老到了彌留之際,還在對護士說,讓孩子們別為了自己不吃飯。
放在國外,那些吃飽喝足的人可能會想不通,為什么會有人把一生都花在了一塊稻田里還無怨無悔。
因為讓人吃飽這件事,就是我們的歷史,是我們的文化。
“民有恒產”的孟子,想做沒做到,“寧有種乎”的陳勝吳廣,想做沒做到,“均田地”的鐘相楊幺,想做沒做到,“耕者有其田”的孫中山也是想做沒做到。
讓人吃飽飯,這是我們所有人的夢。
最后,想說點別的。
1929年,有一篇名叫《十問未來之中國》的文章刊發在《生活周刊》上。其中有一問,是“吾國何時可稻產自豐、谷產自足,不憂饑饉”。
這個問題讓當時的讀者絕望到,有千余人直接回信表明,自己持悲觀態度。
當時,海地有種食物叫作泥餅,中國也有類似的東西,叫觀音土。
在今天,海地依然在吃泥餅,中國已經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超重了。
從神農嘗百草,到明朝引入番薯,從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到新中國建三峽、小浪底工程,從《齊民要術》,到《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一代一代人為了讓人吃飽,為了編織這個夢,有人家財散盡,有人付出了生命。
但千百年來,一直會有人做著這個夢,這個夢也一直會做下去。
直到夢想照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