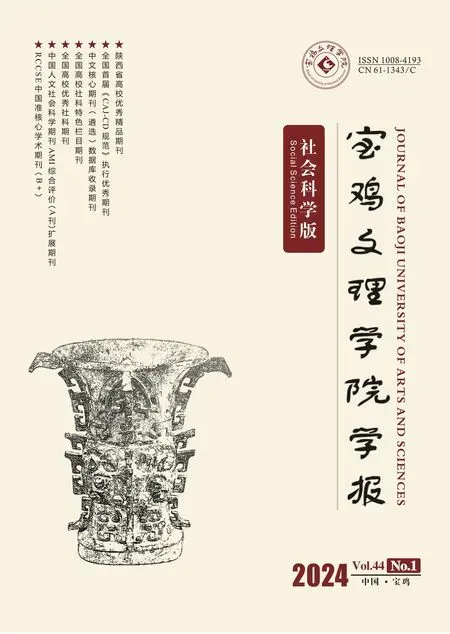明清獸災言說與生態保護意識
王 立
(大連大學 語言文學研究所,遼寧 大連 116622)
野獸作為動物世界的大部分成員,在古代社會,既是人類的近鄰,又是人類危險的對手和捕食者。明清時期,人類與野獸的關系雖然還在基本持續既往的狀態,也有一些新的變化,從民俗敘事中可以約略體察。
一、明清獸災的猖獗與自然生態環境惡化
明清時期,戰亂頻繁與人口無序增長,許多地區的山林被砍伐、墾殖,侵犯了一些猛獸的舊有領地,加劇了獸災的爆發。首先,野狼、老虎等猛獸從山林中跑到人類活動的區域里,猖狂襲擊人類。野獸反常的行為模式,折射出居民的生存危機。清初董含《三岡識略》卷二《狼入境》:“鳳陽潁上縣,群狼入境食人,行旅皆結隊而過。”《申江雜識》的載錄者很有感慨:
云間素無虎……九月初,忽有虎從西來。初十日,伏東郊外華陽橋灌莽中。有顧氏子,年十七,早行被啖。復潛跡至天馬山一帶,居人多有見者,俱閉戶不敢出。總戎遣兵四出搜之,虎往來倏忽,偶一遇,逡巡卻避,經月不獲。詫為神虎。乃于普照寺建道場,命黃冠咒陰兵驅之,后竟逸去。余作新樂府以記其事……嘉靖初年,一虎自北從官路來,入市西空房中蹲坐。市有少年勇力五人,持刀槍攻之。虎躍起,五人皆傷,二人死,虎亦不食。[1](P181-182)
人獸相斗,互有所傷。戰亂饑荒帶來一些特定地區人口銳減,也促發了以虎為中心的獸災猖獗,以至于某些地區人口為避虎而流亡異鄉:“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皆聚于荊、鄂之間。”[2]可以說,如此避災所帶來的一系列民俗心理、生活方式及其價值觀的變化,不可忽視。獸群乘著人間亂世、災荒致人口銳減,迅速繁殖,在春季食物短缺時,偶或出山嚇跑居民,一度占領了縣城,驅趕那里的原駐民不得不奔走異鄉。董含還稱:“蜀保、順二府多山,遭獻賊亂后,煙火蕭條。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約以千計,相率至郭。居人逃避,被噬者甚眾。縣治、學宮,俱為虎窟,數百里無人跡,南充縣尤甚。”[1](P27)
其次,對付獸群泛濫的挑戰,明清多地“有錢出錢,無錢出力”,興起了殺獸自救運動。民家敘事者對捕獲猛獸器械發明和捕獸高超技術,進行著意的標舉。如明人總結捕獵經驗:
帥府茶會,言及殺虎云:虎骨之異,雖咫尺淺草能伏身不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殺虎法,當用三只槍。虎撲人,性勁,必及中槍即殺者上格,退次之,左右槍既接,可殺也。又聞野豕雄甚,牙一觸馬腹即潰。其尤老者,恒身漬松脂,眠以砂石,為自衛之計,槍不能入也。中官海壽,射生有名,無不應弦而倒。一日,得老豕,矢著輒火迸,數矢不入。一老胡教之,云令數卒隨之,作呵喝聲,豕必昂首聽,頷下著矢,彼必倒地,尾后更著矢,斯仆矣。已而果如其言。[3](P278)
在生產力有限的情況下,人們若不講究對付猛獸的方法,可能受到更多更大的傷害,于是不少捕獸發明也相繼出現。據趙翼《檐曝雜記》,他以外來“他者”眼光介紹山西岢嵐州捕虎能人多,以其地多虎:
故居民能以一人殺一虎。其法用槍一枝,高與眉齊,謂之齊眉槍。遇虎則嬲之,使發怒,輒騰起來撲。撲將及,則以槍柄拄于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撲來正中槍尖斃矣。或徒手猝遇虎,則當其撲來,輒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兩手抱虎腰,同滾于地,虎力盡亦斃。
他任官鎮安時當地多虎患,有的虎甚至兼有肉翅,“蓋千年神物”,重金召募能殺虎者,多方不可得;只得一普通的虎,還是靠設下機關以肉為餌鉤獲[4](P46-47)。處于人虎對立的時代,清代人顯然是以土地——萬物主人自居,千方百計獵虎殺虎。而實際上,此舉為的只是人類自身一時的安全,并沒把虎作為生物鏈上的一個環節,沒想到虎的減少會使得食草動物數量驟增,加劇破壞當地的植被,最終造成生態環境的惡化。
多數情況下,毋庸諱言,那些帶有新聞性的野獸食人傳言,立場基本上是站在人類中心的,似乎人類是野獸瘋狂擴展侵略的受害者,控訴中把野獸完全推到災害施加者的被告席上。光緒二十七年(1901)云南鎮康城壩山野間虎食人,先后達四五十人:
紳首馬玉堂命獵戶張地弩,以藥箭射之,殺一虎,而余虎隱遁。……光緒三十年甲辰,鎮康壩灣橋下首有虎與蟒蛇互斗于山坡,數日后,蟒蛇為虎所敗,食其首尾,余其身,長四五丈,大如廈柱。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三月,猛黑有夷人上山打獵,到一巖房下,忽來一熊將伊咬死……六月下旬,大霧露地方忽有一虎,將山上黃牛咬殺二只,十月初四日半夜后,有虎入德黨寨將楊小張家所蓄之騾擒去一匹,至寨外食之,次日,人過其處,見馀騾腿一只。”①
明代詩歌對獸災的控訴,明知事出有因,基本上仍是進行“一面理”的單維推因:
山中猛虎食不飽,群集欲餐狐兔少。號風吼日無奈何,不避人煙來渡河。萬家城郭河邊器,一虎橫行入城里。夜餐犬豕晝食人,只圖飽腹不顧身……一人被噬萬人畏,數月城中無穩睡。繁華市井轉凄涼,陰云慘淡空斷腸。一薪一米貴如玉,忍見兒啼并女哭。[5](P3)
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古人是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上,把猛獸視同仇敵,恐懼而痛恨,更要思考為何猛獸要離開它們舊有的活動區域而進攻人類的疆土。
二、家畜救護人類及官吏德行影響動物
面臨野外猛獸襲擊,人與家畜之間的親密依存關系,得到了實在的驗證,而生死存亡的利害關系呈現,強化了人類與馴養動物彼此的凝聚力。
其一,人們往往依靠有一定抵御能力的大型家畜護衛,并集合群體力量向猛獸斗爭。這些“愛畜”,最有特色的是牛,牛斗虎故事也特別具有動物倫理特色。說詹氏子牧牸(母牛)正躺在牛背上,鄰兒一旁玩耍,有虎從草叢中沖出:
直前搏牸。二兒癡,不識為虎,擲瓦礫,嗾而逐之,虎顧牸不肯去。二兒徙倚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嚙無完革矣。牧子視牸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甦,乃前斗。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牸。牸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虎遂棄而去,牸牧竟全。[6](P371)
故事特別突出兒童天真無知,虎似對其不急于攻擊:“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余愭《書義牛事》也載牧兒方七八歲:“虎至,牛力護之。眾農集,趨殺虎。”牛能如此,既可御虎,又能護兒,不能僅以動物來歧視它,事實上已具有懂人情、明事理,至少道義上與人是站在一個階位上了。這當然不排除載錄者的選擇與偏好,明清倫理文化氛圍,營構出人心目中的理想家畜形象。有時出于自衛,竟還有猛牛斗殺虎奇聞,說陜西漢中的猛虎,獵戶、官兵均無奈,“善搏虎某者”也死于虎口,當群牛遇虎皆退縮時:“惟一牛獨前,與虎熟視者久之,忽奮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賞畜牛之家,并以銀五十兩獎之,一縣稱快。”[7](P384-385)獎額不可謂不大,關鍵是表明官府的重視態度,需要在鼓勵墾殖山林時轟動性的褒揚效應,試圖消減“野外作業”中虎患的阻遏。
其二,面臨野獸威脅,多數情況下作為和平居民的人們,仍依靠地方官德行、能力弭災驅災。明代陳耀文《天中記》卷三十四搜集傳揚此故事類型,如引宋代《九國志》載謝杰為高州刺史,境內多虎,夜入郭中為暴擾民,杰就沐浴謁城隍廟禱告:“愚民何辜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愿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屏左右獨宿殿庭中。三鼓時聞廟東南隅忽有物咆哮如雷,遲明見數虎悉斃。這是典型的“清官廉吏所在地災害不起”的書寫模式,將災害與地方官員個人的倫理品格結合,倡揚愛民恤民[8]。不過,更多的還是積極動員百姓自救,而官府予以政策性鼓勵。清初地方官湯斌(1627-1687)先后在陜、江西、蘇、京四地作官,一直將消除虎災為民除害,成為一項重要政績:
照得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本道暨各州縣刑之頗僻獄之放紛。苛政之害,甚于猛虎,以致惡獸咸召而來,吞噬殘黎,攫嚙牲畜。各官既不能希蹤古循良吏,增修德政,使虎類知感而渡河,自應責彼獸,人驅虎害。乃近見各屬有民間擒得虎豹,強徼其皮獻之官府,是百姓冒死而得者,止供官府饋送之資,何所利而為乎?為此,是仰州縣官吏即傳諭有虎地方人等知悉。如有獵戶善于搏虎者,聽其捕逐擒獲。一切皮肉任彼變賣,不得強行索取。更當洗濯其心,捐除苛政,勿蹈乳虎之誚。[9](P415)
消除虎災,地方官員依靠的是“借虎滅虎”方式,用獵獲者有權處理獵物的“物質刺激”,來充分調動當地民眾捕虎殺虎的積極性。他及時地洞察到下層官吏不去組織救災,而是乘機“發虎災財”,勒索獵戶獻虎皮的弊端。他深知,如聽任繼續侵吞獵戶的戰利品,會降低獵戶們冒險捕虎除害的熱情。如此規定,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既可減少地方財政開支,還能起到全民救災的功效。
虎災盛行,“小獸伏虎”則屬“借獸治獸”,蝗災亦然,被解釋為盛世所感,更因地方官德行而有意助人。據說靈壽山區有虎害,程邑侯為文虔禱山祠,忽睹異獸,文身銳角:
古稱酋耳能食虎,果見搏虎如搏羊。恣噉血肉須臾盡,委骨林麓皚如霜。自茲虎患為衰止,山氓仍得安農桑。前此春寒土出蝻,入夏生羽成飛蝗。竟有細蜂來蔽野,群飛嚙蝗蝗盡僵。出境之蝗渡河虎,大書異績史冊光。中牟傳美或無二,侯與先后相頡頏。邑民感此互傳述,士傳其語作頌章。觀風使者采入告,用備藥什升明堂。[10](P527)
不過,那些戰亂地廣人稀之地,生產力落后,斂財之風難遏,百姓依舊籠罩在虎災盛行的陰影之中。以至于湯斌還要重申此令:
照得虔南兵燹之后,人民凋喪殆盡,荊榛塞路,虎豹晝游,吞噬殘黎,攫嚙牲畜。本道暨府縣各官不能如古循良吏,增修德政,使虎類知感而渡河,自應責令鄉民驅除虎害。乃近見各屬有民間擒得虎豹,強徼其皮獻之官府。是百姓冒死而得者,止供官府饋送之資,何所利而為之乎?合行申飭!為此,仰府縣官吏即便大張告示,曉諭鄉民人等,如有獵戶善于搏虎者,聽其捕逐擒獲。……仍破格賞賚,以示鼓勸。各官更當洗濯其心,慎重刑獄,毋使人謂苛政之害甚于猛虎也。仍將行過緣由,回報查考,毋違。②
兩次三番頒布如此法令,說明地方官吏不顧民眾在虎災肆虐下的死活,而執意搜刮虎皮;對獵虎獲利自得之法也是一再拖延頒布,拒不執行。可見,任憑獸災橫行,還要“大發災難財”的貪官污吏是何等猖狂:
山南白晝猛虎來,柴門竟日常不開。村東少婦血漬草,村西老翁骨成堆。官府明文下獵徒,村舍奔走相號呼。入門不顧索雞酒,由來苛政猛于菟。亦毋張爾弓,亦毋亡爾鏃。明朝群起頌相公,虎畏相公渡河北。[11](P248)
與對付害蟲——蝗災的方式類似,似乎,如同虎這樣的猛獸,也有神靈暗中驅使,而當地官吏的德行、或關愛子民的誠心,則會感動神靈驅使災星轉移。在無助無奈之際,這種迷信的幻想實在也是無法之法,情有可原。
其三,在邊荒地區,也不排除人們往往是是直接求助于當地的神靈。清初時東北地區地廣人稀,生態環境呈現出多虎而人們無力抵御,為免除當地獸災的最大危害——虎患,多以伐木采參等野外活動為生的人們,就建立虎廟求助神靈保佑。但虎患卻并不為之減少。《出關詩》中收有方式濟《虎廟行》:

方式濟(1677-1717),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康熙五十年(1711)因《南山集》案被株連,舉家流放卜魁(齊齊哈爾),作為關內文化中心地區來的漢族文人,荒蠻北地的猛虎成為他最不適應的方面之一。無疑,深在地借虎災橫行的現狀,詩人感慨憤懣找到了一個噴發口。
其四,是如同發生災害要問責地方官員一樣,有的還要甚至將治理獸災無效,來“問責”當地神祗。據說左文襄(左宗棠)駐軍甘肅時,見其地多狼,食人畜,遂命部下出隊圍獵,而終日不獲一狼。某軍官獻計曰:“聞狼之為物,冥冥中有神管轄,故非人力所能驅除。”文襄聽罷大怒,命手下抬來當地城隍神,褫奪其冠冕袍笏,責四十軍棍,用木枷于營門外。[13](P4789)以禱神、責神來治理當地獸災,當來源于陰陽兩界官員“同治一方”的互動配合觀念。如明后期帶有寫實性的公案小說,就昭示出某些地方官員祈神——陳祖拜城隍語曰:
汝為朝廷守土,我為朝廷守官。人害人惟予除之,物害人惟神除之。人害弗除,則為廢官;物害弗除,則為廢祀。凡物之為害,莫過于虎豹、蛇蝎、蛟龍、豺狼……[14](P77)
說明在古代的生態環境和冷兵器時代,野獸對于人類安全的巨大威脅,獸災同樣會危及對當地神靈的供奉。
三、野獸精怪食人的人事兆應與災害預兆
在古代中國,正史的的文化建構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低估的。由于史書之中《五行志》將野獸妖異與人世變故聯系對應的神秘思維定勢,明清人往往還是把無法抵御的精怪,同野獸聯系起來。在清代一些敘事作品中,有的還借助于前代民間野獸精怪食人傳聞,強調“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陳忱的水滸續書描寫老僧真空給聞煥章講述災異之事:
有龍掛在軍器作坊,兵士取來作脯吃了,大雨七日,京城水高十馀丈。禁中出了黑眚,其形丈馀,毒氣噴開,腥血四灑。又有黑漢蹲踞,像犬一般,點燈時候就搶小兒吃。狐貍坐在御榻上。……種種怪異,不可殫述。總之“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眼見得天下大亂了。這是老僧饒舌,先生須要謹言。[15](P121)
這顯然還是基于人獸對立、獸災預示人世的思維路徑。小說這段情節非向壁虛構,而來自明代正德七年(1512)的“黑眚”傳聞:“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貓,若風行有聲,夜出傷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間、順德,漸及京師,人夜持刁斗相警,達旦不敢寢,逾月始息。”此前的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傷人,其色黑,蹤跡之不可得。上乃于……”[16](P270)而宋代佚名《大宋宣和遺事》載宣和三年五月金使來,六月黃河決口,恩州有黑眚出:“洛陽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兒食之,至二秋乃息。二月,童貫進太師,譚稹加節度。”似乎這一具有野獸般外形的精怪,是一種征兆,預示著人間要有相應的別的災難發生。國外學者更多地注意到民眾恐慌心理上,實當為災害心理的濡化所致。
較多載錄野獸侵犯居民的是地方志。根據不同地區的野獸物種的分布,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生態環境惡化,野獸固有的生活領域遭到破壞,是不會有如此之頻繁的野獸與人爭奪資源事件的:
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秋九月,杭州屬縣諸山聚虎成群,白日入民家傷人,道路無獨行者,死者不可勝記,且不可獵,余杭尤甚。”
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秋,(廣東東來)狼虎成群,白晝噬人,成郭之外,行人幾斷。”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八月:“常德熊入城,傷六人。”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皖南)虎成群食人,自后十年中計傷千余人。獵人張網焚山捕之,不獲。”(洪亮吉:嘉慶《涇縣志》卷二七。)
清高宗乾隆十三年(1748)冬,山東膠州:“狼食人,白晝入城。”[17](P485-490,493)
野獸出現了與往日積習異常的行為,對人類造成了嚴重威脅。以當時毫無防備的和平居民看來,真是需要認真對待,因此,記載或詠嘆如何捕捉、擊斃、抵御猛獸,成為富含人本意味的民俗文學題材,如詩詠:
市兒青裙頭布帽,爭言縛虎沙潭側。地平實異溪谷險,公然攫人到昏黑。此物豈因氣數至,居人恒愁爪牙逼。勁弧疾弩誰命中,紛紛貪天謂己力……[18]
王培荀也寫蜀地建昌多虎。雅安令募人以毒駑射死五虎,艾生、習生也打虎,感嘆“我鄉百年無此物”,楊世燾作《打虎行》:
踞牙鉤爪斑斕虎,撲地一吼人皆驚。聚眾追隨遠相逐,虎行緩緩故不速。直上前岡始負嵎,吞身縮爪睅其目。到此相看不敢前,虛呼空喝祇徒然。勇哉艾生無客氣,習生亦豪為之貳……[19](P462)
全不思虎的領地受侵,生態惡化中人類的責任。有的則將別的自然災害同獸災通盤考慮,如地震,有些動物就預感到了,它們襲擊人類其實就是地震前兆之一。康熙《上元縣志》卷十三稱明成化十七年(1481):“江蘇二月,地震,猛虎進城殺人。”光緒《渭南縣志》卷十一也載清光緒五年(1879)陜西“多鼠食牛,噬嬰兒,嚙甕破。五月十三日寅刻,地震。”說明在對獸災恐懼的觀察之中,有時還能關注了其與其他災害的聯系。
四、獸災作為生態環境變化的顯象
首先,對于猛獸帶來的威脅,明清時代人們進行了帶有神幻意味的思考。如所謂義虎仁虎情虎故事,仁狼情熊的傳說甚夥,就是一個重要方面。像義虎能懲惡救善:荊溪二人發小,長大一貧一富。貧子略知書,妻美艷。富子就設謀,邀其夫婦進山去應聘管家,途中富子讓貧子妻守舟,與貧子先行,引行險惡溪林中斫之“隕絕”,認為已死,哭下山告訴艷者其夫君被虎嚙,與婦同往檢覓,宛轉引行險惡處時,忽有虎出將富子咬死。婦返舟與夫相逢,悲喜交加。作者感慨:
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于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20]
如此具有是非善惡觀念的猛虎,豈非現實社會中人將自己的倫理觀念投射所致?由此看來,明清兩代小說中帶有仙幻性質的諸多“虎妻”(如《虎薈》《螢窗異草》)、“熊妻”(如《埋憂集》《道聽途說》)等故事,某種程度上也是當時人們對于獸災受虐的心理補償。事實上,有關人獸和諧的實錄性文本雖然不多,但上述希望自然界猛獸也能具有人的情懷、理想,干預凡俗的善惡恩仇,也當被視為惡人必得“遭克”期許的藝術化體現。[21]
其次,獸災出現,有時還被認為是災害的預兆。作為民俗記憶,1932年太原瘟疫前就傳聞,近日狼入村中,后村西逐出一狼大如驢,無毛:“人多勢眾,狼畏,登山而去。已故里人多以為不祥,慮疾人之不利,恐多喪亡耳。”存續前清觀念的這位作者,還并不止于客觀情狀的描述,進一步倫理推因:“瘟疫之行,人之不善所致也。人情風俗之不善有以致之也。人須為善,以驅逐瘟氣耳。”[22]實際上狼災乃為旱荒之果,又被作為疫災先兆。
最后,地方官員應對獸災的侵襲,還體現在對于勇斗猛獸、協力抗暴的百姓,予以及時表彰資助,減免徭役等方面。如李符清《海門文鈔》載,乾隆己丑(1769)廣西合浦人虎搏斗,吳氏兄弟仲、叔、季三人持農具斗虎自衛,虎傷而曳尾遁,眾抬季歸:“后數日,邑侯汪公龍岡過其地,召視創,且詢人虎相搏狀,感其篤兄弟義,給資療之,復免其徭役焉。”[23](P167)在有些在大力開發墾殖的地區,人獸沖突就更加激烈。[24]的確啟發人們需要“綜合治理”的思考。
野獸表現狂躁異常,往往并非猛獸的一些小型動物,也令人難于應付。這也在獸災與其他災害聯系的民俗言說中屢見。清代后期的同治、光緒年間,社會屢遭兵燹,自然災難頻發,尤以雨雹災和旱災為主要形式。不過兵燹后自然界的生態失衡,又會令人感到恐懼困惑。據說,同治七年(1868)西北某一地區出現的怪異現象:“鼠皆碩大如貓,白晝游散不畏人,且反食貓。粟糧已久無存,不知何以如斯之大,且多狼,成群二三十不等,向堡寨有人處肆行,經多人搶矛追逐,殊不奔避,輒向大眾中,擇人而噬。……其肥腯迥異平時。”[25]又如蜘蛛、蝙蝠等母題,這些“災害”激發、豐富了民國武俠小說中人獸關系描寫的審美想象。③
其實,在冷兵器為主的時代,人們與猛獸的抗爭,往往也是代價沉重的。滿族官員記載了冷兵器對付猛虎的訓練方法:
定制,選各營中將校精銳者,演習虎槍之伎,凡巡狩日相導引。上大獵時,其部長率伎勇者十人,入深林密箐中覓虎蹤跡。凡猛獸出,其部長排槍以伺,虎躍至,猛健先以槍刺其胸仆之,謂之遞頭槍,然后群槍林至。其頭槍者賞賚優渥,故人思效命焉。純皇帝定制,凡殺虎時為虎斃及被創者,照軍營殉難受傷例賜恤焉。[26](P394)
蒲松齡對無辜受害者對猛獸的反暴復仇,有著極高的熱情和激賞態度。他評殺狼報父仇的鄉民于江:“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于血誠,非直勇也,智亦異焉。”[27](P550)對于大蟒口中救兄的胡家弟,則贊揚:“噫!農人中,乃有悌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27](P72)人們與猛獸斗爭,不僅需要勇猛,也離不開智慧,像《聊齋志異》寫對付狡黠狼的篇章即然。而清初徐昆也寫山右多狼,性最狠而狡黠善伺人,某荒村狼夜推碾發聲,引婦出門拖走。說某役乘馬夜行路過辛莊:
見路旁有若人趺坐者,呵之,乃兩狼背負,見人奔逐,馬驚逸,盡力而馳,兩狼固不舍也。黎明,望見郡城門未啟,乃就路旁空灶躍而上,左手牽馬為護,右手以鞭格之,急呼店主人醒,啟戶,狼始去。未幾,閭鄰左有豕疾聲而漸遠,兩人裸逐不能及。蓋狼度不能得人,負豕而去也。后余至山左亦多狼,人或夜行,必挈伴持械,老弱或為所噬,寧海無獵者,遣兵役捕之,兇焰少熄,亦不能盡絕。[28](P120)
而對殺熊報父仇的童元發,俞樾則突出了該青年的正義行為有山神托夢報訊,揄揚孝子緣此善行惠及鄉里:“粵寇之難,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子一村獨無恙。”[29](P123)明清史乘《孝義傳》《列女傳》載這類事幾乎全站在人類中心的立場上,多所采集和彰顯贊揚,而地方官員也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尊重。如斗虎救親的漳浦人藍忠,事后里中父老請旌表:“忠泣辭甚力,僉曰:‘無傷孝子心也。’乃已。”[30](P2488)并不完全聽憑常規和借助輿論為自己的政績造聲勢,歸根結底還決定于孝子自身的愿望和意志,說明在抗擊受災過程中,地方官員相關舉措還是相當人性化的。一定程度上這也稱得上“民本”思想、鄉間輿情對官員決策的制約。
獸災母題的生態美學意義在于,人的生存狀態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地在特定動物的活動(正常的與異常的)中表現出來,人們在與動物的生存對抗中互有輸贏,但具有啟示性:人類不能僅僅從自身為世界主人的立場出發,而不去思考動物活動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尤其是自然環境的變化是否同人類自身行為有關。國外學者即指出,應該把野生動物活動看成是人類入侵和破壞自然環境的晴雨表[31]。獸災的出現,以往常常把野獸群發說成是野獸對人類的侵襲,對于和平居民的威脅騷擾,其實,這是片面和不公平的。如果從當今生態文化與生態倫理角度來全面審視,可以了解,這不能單單來指責野獸,其實,正是人類對于彼時彼地生態幻境開發的過程中,打破原有生態系統的平衡,造成的野獸生存狀態惡化;或導致原本不應有的災害發生時,那些野獸被迫走出固有的生活圈,進入到了人類聚居地尋求食物所致。在華夏災害、御災與生態學融合的文學書寫之中,這可以看作是人與動物關系的一個令人警醒的方面。
注釋
① 《云南·鎮康縣志初稿》卷二十四《軼事》。
② 范志亭等輯校:《湯斌集(上冊)》第一編《湯子遺書》卷八《戢虎暴以除民害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虎渡河”事,典出《后漢書》卷七十九《儒林列傳》載劉昆任江陵令,“虎皆負子渡河”。《宋書》卷四十一本傳載宋均任九江太守,“虎相與東游度江”。
③ 可參閱王立《蝙蝠譜系:還珠樓主小說與明清惡物災難母題》,載于《華夏文化論壇》(總第二十八輯),吉林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劉衛英《還珠樓主蜘蛛母題的道德化書寫》,載于《貴州社會科學》,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