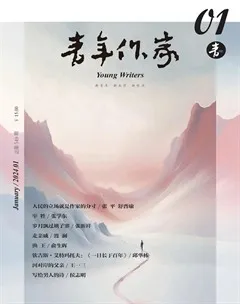桂 圓
俞生輝
一
2010年,在我家還用著大屁股電腦的年代,一位叫“許嵩”的歌手發布了他的第二張專輯。那時候,我哥黃嘉軒整夜霸占著家中唯一的電腦,用“千千靜聽”外放許嵩的歌曲。有時,我和他走在路上,他戴著用壓歲錢買來的MP3,搖頭晃腦的同時口中念念有詞。當他終于注意到我的目光,他會情不自禁地說,太好聽了。在那個周杰倫依然大火的時代,黃嘉軒一度以為他發掘了一位音樂奇才。包括他在內的很多人,其實都沒有想到,這位歌手后來會成為“QQ音樂三大巨頭”之一。
那時候,我剛上四年級,我對周杰倫和許嵩都不感冒。在同齡男生還在看動畫片的時候,我迷上了湖南衛視的快樂女聲節目,并在2009年的夏天喜歡上了一位叫劉惜君的女歌手。從那時起,我便感覺我和身邊的同齡人不太一樣,就像黃嘉軒也會覺得他與其他人不太一樣。
我記得那是個周六,好像還是個節日,奶奶早上特意叮囑我和我哥要多吃點韭菜,出門會有貴人相助,不過我們都沒有吃。我和黃嘉軒剛出門便遇到了李小龍。李小龍是黃嘉軒的發小,與黃嘉軒同年,比我大八歲。他家住在我們家后面,同時也是黃嘉軒中專的同學。李小龍的皮膚黝黑,身材瘦小,打球的時候,我總覺得他像猴子撈月,特別好笑。
一路上,他們在公交車上竊竊私語,似乎在謀劃著什么。我望著窗外的景色,顛簸起伏,那是我第一次來到黃嘉軒上學的中專。周六的街道上滿是穿著校服的學生,黃嘉軒帶我走向一棟建筑,上了三樓,走進一間教室,來到一個女生面前。我后來知道了她的名字叫黃蕓,我哥喜歡她。我抬頭打量著面前這個女孩,個子不高,長發,一雙桃花眼,笑起來的時候略帶嬌羞。黃嘉軒從兜里掏出一盒前幾日我給他的牛奶,塞到女孩的手里,撓著頭發,一臉傻笑。李小龍趁機拉著我走出教室,我轉頭看見黃嘉軒和那個女孩倚在窗邊,有一句沒一句地不知道在聊什么。
沒過多久,黃嘉軒滿臉笑意地走了出來,他一手搭在李小龍的肩膀上,一手摸著我的頭發,說了一聲,走。
我們出了校門,往母親理發店的方向走去,走到一塊巨大的公示牌旁,那面幕布上寫著關于“龍潭鎮黨建優秀企業名單”的內容,隨后便聽到身后傳來一聲吼叫。我們三個人轉過身,愣在原地,迎面過來一群人,足有十幾二十個,他們身穿校服,頭發五顏六色,極其夸張,有些人的劉海遮住了半邊臉。這種頭發我只在母親理發店里外來務工的青年身上見過,他們多數會在星期五的晚上來把頭發做得極其蓬松,越怪越好,隨后成群結隊地消失在馬路盡頭的溜冰場門口,我媽告訴我,他們叫“殺馬特”。
一群穿著校服的“殺馬特”向我們走來。最前面的是個小個子,和李小龍差不多高,我注意到他的手中捏著一塊板磚,黃嘉軒攥緊了我的手。接著是一個很快的鏡頭,領頭的那個小個子高高躍起,板磚順勢砸在黃嘉軒的頭上。我看見黃嘉軒的頭上流出血,我哭了。小個子氣勢囂張地叫了幾句,話語里夾雜著“黃蕓”兩個字,隨后便揚長而去,一旁的李小龍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我們是怎么來到母親的店門口的?或許是攙扶著黃嘉軒,或許是路過的人幫忙。我只知道黃嘉軒的臉上全是血。父親騎上電瓶車載著我與黃嘉軒去醫院。黃嘉軒的頭上縫了七針,整個過程他低著頭,一聲不吭,只是身體在顫抖。有一瞬間,我注意到他的嘴角咧開,似乎在笑。他為什么要笑?
父親也許也注意到了,他開口詢問,是誰干的?起初黃嘉軒沉默不言,后來用“算了”“不要再問了”的話語搪塞。父親把我領到醫院的走廊上,問我實情。我把看見的事實復述了一遍。父親帶我坐上電瓶車,開往事發地點,他撿起那塊遺落在草叢里的板磚,板磚的一角還帶著血跡。父親問我,他們后來去哪了?我用手指指了一個方向。
那天下午,我們尋遍了附近的網吧、游戲廳、桌球室,都沒有找到那個小個子的身影。
最后我們才想到警察局,報了案,至于那群人是否被繩之以法,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段時間里,黃嘉軒的頭上一天到晚包著紗布,母親特意給他買了箱牛奶。我感覺他和以前有些不一樣了。有一天,他回到家,頭上的紗布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和那些“殺馬特”一樣的大紅色頭發,形狀奇特,像一頭非洲雄獅。黃嘉軒告訴我,李小龍也弄了發型,紫色的,不過沒有他的好看。他說話的音量明顯比以前更大了,他問我,還記不記得那個我見過的女孩?我點了點頭。他說,她以后就是你的嫂子了,我們前幾天在一起了,她的名字叫黃蕓。
2011年,一件大新聞席卷了龍潭全鎮,包括整個郊區。黃嘉軒那個中專的一個同學,與人因為感情問題發生了糾紛,對方帶著兩個人,在火車站幾刀便捅死了他。一時之間眾議紛紛,有譴責中專的校風問題的,也有譴責早戀問題的。很快,區教育局頒布了關于“整治校園暴力,打擊校園惡霸”的政策。黃嘉軒和我說,他們學校只要一被發現打架就會直接開除。我不知道這對黃嘉軒有什么影響,他依然和以前一樣會在周末的時候把頭發弄得奇形怪狀,每天起很早去鎮上的車站等黃蕓一起上學。
有一天,黃嘉軒抱著一盒水果回家,他告訴我,他趁黃蕓爸媽不在家,去了黃蕓的家里。他說,黃蕓家就住在鎮政府的后面,家很大,她的房間很干凈,這盒水果就是她送的。黃嘉軒小心翼翼地掀開塑料蓋,遞給我一塊黃色的果肉,問我,好吃嗎?我嘗了一口說,很甜。
他捏著一塊果肉,又問我,你知道這是什么嗎?我看了一眼說,是菠蘿吧。他搖了搖頭說,不是的,黃蕓說這是鳳梨,和菠蘿很像,不過比菠蘿更好吃,也更貴。我好奇地問他,那它和菠蘿的長相有什么不同呢?黃嘉軒摸著下巴想了半分鐘卻沒想出結果。他為了轉移話題,顯得十分激動,他說,你知道嗎?我今天摸了黃蕓的胸。
你伸進去了?我問。
他說,沒有,隔著衣服摸的。
他停頓了幾秒,開口跟我描述那個場景,他說,摸的時候,她家音響里還放著曲子。說完,他連忙蹦到電腦前,打開千千靜聽,沒一會兒,電腦音響里流出音樂。他說,就是這首《夢中的婚禮》,今天去黃蕓家里,她后來還用鋼琴彈給我聽了,她說這是她最喜歡的曲子,以后結婚一定要放這首。
我問他,你聽得懂嗎?
他沒回答我,但不出我所料,半小時后他就把曲子換成了許嵩的新歌。
那年還有一件記憶深刻的事情,國慶期間,聽說海邊有煙花節。黃嘉軒突然問我,想不想去看煙花?我說,想啊,不過聽說門票就要一百多塊錢一張。他拍著胸脯說,沒事,想去,哥就帶你去。
于是在一天夜晚,我見到了把頭發弄成愛心形狀的李小龍,還有穿著一席碎花短裙依舊長發飄逸的黃蕓。
我們繞過海邊景區排隊入場的觀眾,沿著邊緣走上一個斜坡,順著柵欄往前走。黃嘉軒確定四周沒人以后,身先士卒,抓住兩根欄桿,用腳往上蹬,隨后一躍而入。他向我們招了招手,示意讓我們學他的方法進去。黃蕓的力氣不夠,李小龍便在下面托著她,她踩著李小龍的手,往里翻,黃嘉軒在那頭一把抱住她,把她接了下來。我和李小龍緊跟著翻了進去,我們屏住呼吸躲在一棵熱帶棕櫚樹的后面,確保沒人后,翻過景區里的欄桿,下到沙灘,如同劫后余生,四個人興奮地大喊大叫。
很遠的地方,有燈光閃爍,那是購票觀眾的觀賞臺。我們在空寂的沙灘上狂奔,舞蹈,將沙子拋向半空。
夏夜的海風撲面而來,我們坐在一塊巨石上,光著腳丫,黑夜向著我們洶涌。突然一溜火星躥入半空,在外圍防波堤上的夜空中綻放,五彩斑斕的煙花蜂擁而至,巨大的天穹仿佛再次被點亮,夜的面紗被一點點撕開。
二
2012年初,上海的冬天特別寒冷,我一度確信瑪雅人關于末日的預言并非空穴來風。在同一時間,一張關于周克華的通緝令貼滿了大街小巷,鬧得人心惶惶。我和黃嘉軒站在一處電線桿前,看著那張通緝令。我有些吃驚地說,哥,提供線索就可以拿十萬吶。黃嘉軒瞅了我一眼,有些不屑地回答,不就十萬塊錢嗎?這可是殺人犯,手里有槍,讓我們遇到了,我們還不得沒命?
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可轉念一想到巨額的賞金,總還是有些動心。那段時間,母親為了我的升學,貸款六十萬在新城最好的初中旁買了套五十幾平的老學區房。我頭一次開始對錢有了概念,想到父親一個月幾千塊錢的工資,六十萬至少要二十年才能還清,比我如今的一生還要漫長。我經常會在夢中夢到周克華的身影,他步履匆匆,身形佝僂,典型的外八字。我從天而降一把將他降住,拿著十萬塊錢的獎金神采奕奕。直到耳邊傳來雞鳴聲,才發現是大夢一場。
臨近春節的那幾天里,黃嘉軒的眼神越發閃亮,他告訴我,黃蕓邀請他去她家里見父母。一天,黃嘉軒翻出了父親壓在柜底的一身西裝,穿在自己身上,雖然略顯得大,不過他白皙的皮膚,勻稱的身材,看起來倒像那么一回事。他對著鏡子用發膠捋順紅色的頭發,我將李小龍借給他的皮鞋置于他的腳邊。他儼然一個整裝待發的士兵,推開大門,仿佛即將登上開往前線的火車,揮手向我致意,讓我等他的好消息。
那晚我等了很久,在窗邊凝視著星空和一輪蛾眉月,曠野凄寂。一聲很沉重的關門聲打破了眼下的畫面,我知道,黃嘉軒回來了。
他并沒有我想象中的容光煥發,反而一身疲憊,像是遭受了槍擊。他躺回到床上,我沒有問他一句話。他突然開口說,黃蕓的父母都是政府的人。
我問,所以呢?
他說,他們不喜歡我。
我說,你可以慢慢做到讓他們喜歡啊。
他說,他們說了,想要娶黃蕓至少要二十萬的彩禮和龍潭二小旁的學區房。
我環顧我們所住的這棟位于鄉下的兩層樓房,透過黑夜我頭一次看清了墻壁上那塊斑駁的墻體,聯想到父母貸款的六十萬,在那時,我認為我能體會到黃嘉軒的悲傷。
后半夜,黃嘉軒睡不著,打開了電腦,整夜播放著許嵩的歌曲,往往一首才播放一半,他就像趕鴨子下架一樣播放起下一首。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能讓我理解黃嘉軒的悲傷。他實習的電子廠位于工業區,他每天乘坐的公交車都會經過海鷗大廈,那是整個區最高的一棟樓,足有百米高。我每次經過它,都會往上看,總覺得好高。我好奇黃嘉軒會不會也看一眼。他反問我,你難道不覺得它太高了嗎?
在一個雨夜,黃嘉軒接到了一個電話,隨后他問我借走了自行車的鑰匙。我問他,要去哪?他沒回答我,面色凝重,下樓騎上了我的自行車,沒穿雨衣就消失在了大雨瓢潑的夜色里。
我再見到他是兩天以后,我放學回家,發現他已經在被窩里了。通過他后來的回憶,我才知道了那晚所發生的事情。他朋友打電話和他說,看見黃蕓和別的男人在酒吧里。他騎了二十公里,把我自行車的后胎騎爆了,終于見到了黃蕓。(我當時的疑惑點在于他為什么能把我的輪胎騎爆?)
他說,那個男的個子還沒有我高,不過對方身邊都是他的朋友。
我問,那后來是怎么辦的?
他面露驕傲的神色描繪當時的場景。對面的人手中已經抄起了啤酒瓶,劍拔弩張,黃嘉軒則不慌不忙地打了一個電話喊來了一位朋友。他的朋友一到場,對面所有人都認出了他的朋友,個個都坐了下來,像萎了的花。
我問他,那黃蕓呢?
黃嘉軒對此并沒有回答。
那年夏天,還有一件事,龍潭鎮牽頭組織了一場鄉村馬拉松大賽,這和我與黃嘉軒都沒有什么關系。不過從那以后,唯一開在村里的皮包廠突然關了門,龍潭鎮上最大的服裝廠也開始宣布裁員。通過母親對于生意的抱怨,我能觀察出一個肉眼可見的事實,龍潭的外地人比往年少了不少,就連馬路盡頭的溜冰場都關門大吉了。“殺馬特”似乎是在一夜之間消失的,很少再看見年輕人頂著個奇怪的頭發走在路上,不過黃嘉軒依然我行我素,和李小龍兩人沒事就倒騰頭發。
有一天,我發現黃嘉軒滿頭的紅發不見了,他剃了個寸頭,躲在被子里玩手機。他開始不去上班,閉門不出,整天躺在床上,像一個將死之人。他每天早上讓我幫他用一個塑料杯接一杯水,回來的時候再幫他倒掉杯中渾濁的液體與煙蒂。我為此心生怨念,母親也在暗地里跟父親無數次訴苦,說家中養著一個無用之人,她不明白好好的一個人怎么就變成這樣了?
2012年,冬天再次到來,世界末日并沒有來臨,黃嘉軒卻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起初我以為他只是出去散散心,過幾天便會回來,半月以后,我便意識到他是真的消失了。
我再見到黃嘉軒已經是2013年的春節了。我特意觀察到他穿了一身阿迪達斯的衣服以及一雙耐克的跑鞋。那雙鞋一千多塊,我一度以為他發了大財。
那天夜里,他跟我擠在一張床上。他手機里播放的音樂也變了味,他整夜循環著一首歌,吐詞清晰,曲調哀婉,不斷重復著“董小姐”三個字。我是后來在2013年的夏天看“快樂男聲”才知道,原來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董小姐》,那個叫左立的歌手一舉唱火了這首歌,掀起了一股民謠的風潮。
此后的一整年,我只見到了他一次,是我主動找他的。本來是一件小事,那是個周五,我上廁所的時候,尿尿分叉濺到了身旁的人。我連忙向他道歉,抬頭發現對方是學校出了名的公子哥。他怒目圓睜,用力推搡我的肩膀問,幾個意思?我看見他抬起手已經準備打我,好在一位老師走了進來,他立馬縮了回去,湊到我近處跟說我,放學別走。
我害怕極了,回到教室跟同學說了這件事,很快很多人都知道了,放學我要被揍了。我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借來了同學的手機,登了我的QQ,點開與黃嘉軒的對話框,發送了消息:“哥,我放學要被人揍,你過來一下可以嗎?”沒過幾秒,我就收到了回復,“幾點放學?”我回答,“兩點半。”他說,“好。”
那天下午,我早早收拾好了書包,等最后一節班會課的下課鈴一響,我就沖出了教室,來到學校對面的小商店門口。黃嘉軒早就到了,李小龍也在,他身旁還有十幾個抽著煙的社會青年。我信心倍增。黃嘉軒問我,誰要揍你?我說,他們馬上就要出來了。
我看見那個公子哥后面跟著一群人從校門口出來,我向門口指了指,他也注意到了我,我向他招了招手,示意讓他過來,他往我這邊看了一眼,便向我們相反的方向走去,騎上他的電動車,轉眼間便已不知去向。
從那天之后,再沒有人欺負過我。我驕傲極了,風光無限。我穿著一百塊錢買來的假耐克鞋走在校園里,表現得趾高氣揚,都不正眼看其他人。
那一整年我都沒見過黃嘉軒。母親說,他肯定正忙著賺錢。我對此深信不疑。
直到我初三的一個周日,我正在母親的理發店里寫作業,走進來幾個中年男人,腰間夾著皮包,母親問他們,要剪什么發型?他們坐到沙發上,開口說,想聊聊關于黃嘉軒的事。
母親問,嘉軒發生了什么?
其中一個男人從皮包里拿出一張紙放到桌上說,黃嘉軒現在欠了我們十五萬,我們找不到他人。母親停下了手中的活,拿起那張借條,白紙黑字的,的確簽著黃嘉軒的名字。那群男人收回欠條,離開的時候留下了一句話,給你們一個月的時間。
我突然覺得一切都在破碎,生活在破碎,2015年也在破碎。母親翻看了父親的微信聊天記錄,發現他偷偷替黃嘉軒還了兩萬元,那兩萬元是奶奶從養老金中一點點攢下來的。他們大吵了一架。我回到家里,時常會發現窗臺上的花瓶數量在減少,盡管家中依然干凈如新。
有一天深夜,我睡在被窩里,聽到門外有人拿著棍棒敲擊外面的鐵門柵欄,聲音很大,每傳來一聲,我的身體會隨之顫抖。還有一天,我回到家,看見六樓的墻壁上,有人用紅漆水在樓道里寫著:“畜生黃嘉軒,還錢!!”
初三最后的時日里,我每天都生活在擔驚受怕里,我有時覺得自己會遭遇不幸,在緊張的備考生活中,我偷偷寫了一封遺書,塞在書包的底部。我開始有意識地鍛煉身體,在備考體育中考的時候,我拼了命地跑,越跑越快。
暑假的一天,我正在母親的理發店里,四五個染著頭發的青年突然闖了進來,他們話不多說,拿起東西就砸,母親大喊大叫,拿出手機準備報警。我捏緊拳頭,看見一個人端起一張椅子砸向墻上的玻璃,嘩啦啦碎了一地。我一個箭步來到他的面前,對準他的后腦勺便是一拳下去。他的身子往下一沉,又轉身立了起來,注視著我。他拿起手中的椅子往我身上砸了過來,我感到世界瞬間安靜了下來,視線搖晃著,身體倒向地面。我聽見一聲大叫,是母親的尖叫聲,沖破了擁擠的空間。我還聽見門外夏日街道上的車笛、蟬鳴很刺耳,穿過長空直至晴天。
三
2016年在我的記憶里,是兩個拳頭。第一個拳頭是我打在了一個人的臉上,他比我高,一米八幾,身材魁梧。我沒有一點懼色,初中的趾高氣揚被我帶到了高中,帶到了高一軍訓的夜晚。當我一拳頭落到他的臉上,我并沒有想到這會讓他住進醫院,我也沒有想到這會在高中的一開始使我背上處分。
母親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你越來越像趙楊了。她沒有哭泣,沒有責備,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2016年的另一個拳頭是別人打在我臉上的。在那之前,我和很多年前一樣選擇用QQ聯系黃嘉軒,發了十幾條消息,給他彈語音,都沒有回復。我當時以為只是因為很多人選擇開始用微信的原因,他也不例外,沒有收到我的消息。兩年后的一次機會,我特意問他,你現在還用QQ嗎?他回答我說,微信和QQ,我都用啊。這些都是后來我才知道的事情。
2016年,在那個夏天剛剛到來的午后,我被一幫人拖到了學校后面的樹林,一個拳頭打在我的臉上,緊接著便是密集的拳打腳踢。他們離開后,我徹底倒在了地上,四腳朝天,然而我的神經卻沒有感到一點痛感。如果當時有個從上往下俯拍的鏡頭,它將記錄下,我的臉上居然沒有一點傷痕,像死尸一樣躺在那里,一動不動,遠處傳來化工廠鋼筋水泥碰撞的巨大聲響,“當當當”,就像是喪鐘。多年以來,我不可一世的心理在那一刻徹底土崩瓦解。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我背著處分不敢聲張,同樣沒有人會聽我聲張。他們知道的是,那個很爛的學生,更爛了,成績滑到年級末尾,并于學期結束的時候收到一張“退學通知書”。母親哭腫了眼睛,問我也問不出原因。
有時候,我挺心疼母親的,她一個人帶著我從重慶來到上海,十幾年來,只是希望我能出人頭地。兒時開家長會,老師總會因為我上課積極回答問題,活躍參加學校活動而表揚我。我想那時候母親肯定是很驕傲的。但她怎么也想不到我會變成現在這樣。
我后來看到電影《夏洛特煩惱》里的情節:夏洛的母親為了讓兒子留下讀書,在校長辦公室里說了一句,都是為了孩子。隨后便撕開上衣,大喊,來人啊,校長非禮我啊。我是在那時候才明白了母親為什么會對我說,你以為送幾瓶好酒就能這么簡單讓你回去讀書?
在那些刻意沉默寡言的時間里,我沒有見到黃嘉軒,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的生活游離在我的生活之外,我們的生活就像兩條平行的線,似乎有聯系,卻又在物理意義上沒有關聯。
爺爺的死,是我們這兩條線又一次相交的時刻。
爺爺死的時候是2017年的春節,父親與我正在湖北的高速上,大雪紛飛。父親自始至終都很堅強,車子一路飛馳,在第二天夜里終于趕回了家。他往老宅走的時候,健步如飛,一到爺爺的床前,便癱倒在地。
我哭了出來,往后門走去,發現黃嘉軒也早已回家。他拎了一個小板凳坐在后門口,注視著爺爺親手栽下的那棵桃樹。他起身拍了拍我的后背,說,別哭了。
我看了他一眼,他的雙眼早已腫得不像話。就在這時,他的手機鈴聲響了,他接起電話,沒過幾秒,表現得比我還傷心,可他已經流不出眼淚,只能大口地吞咽著面前的空氣。
我后來知道了那通電話的內容,是李小龍死了。
他替人去討債,被債主一鏟子打在后腦勺,當天就去世了。那天,李小龍才剛染的一頭綠毛,沾滿了血。我想起幾年前和他一起打籃球時的場景,想到他那令人捧腹大笑的動作,此刻卻笑不出來。
從那之后,一切都變了。
在少數幾次回老宅看望奶奶的過程里,我發現,樹變矮了,路變短了,河變窄了。只有黃嘉軒和以前一樣,不知所蹤,聽母親說他為了躲債主,出去闖世界了,離開了上海。
上海是一座無數人想留下來的城市,而出生在上海,生活在郊區邊緣地帶的黃嘉軒卻找不到容身之所,這到底是為什么?
也是從2017年開始,我察覺到了龍潭這座小鎮翻天覆地的變化。好幾家工廠關了門,龍潭開始創建上海的郊野公園,打造農家樂型的經濟模式。外地人變少了,市區來的人變多了。
母親對此很開心,她說,終于能掙到真正上海人的錢了。
四
2018年春節,黃嘉軒帶了一個女人回家。若不是他在開門的瞬間便把手伸了進來,恐怕我媽會在看見他的一瞬間把門關上。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并非空手而來。他帶了幾袋禮盒,還拎著水果。
當時我正目不轉睛地看著中央六臺的春節特別節目。他跟我說,弟弟,去把鳳梨切了吃。我起身拿出袋子里的水果,它和菠蘿的外形很像,不同的是,菠蘿會扎手,鳳梨不會。
父親在陽臺上抽著煙,側過身問,什么時候回來的?黃嘉軒沒有坐下,他站在那個女人身邊說,就今天,開車回來的。
我切完水果,放到茶幾上。黃嘉軒趕忙對母親說,阿姨,你嘗嘗,很甜的。說完,他看了眼我,又看向身旁的女人,開口說,佳慧,去帶弟弟買件衣服。
那個女人的聲音很溫柔,看著我說,走吧,跟姐姐走。
我和她下樓,上了一輛白色的轎車。我坐在副駕駛的座位上,打量著這個女人,身子不高,胖胖的,有一張很可愛的蘋果臉。我們開車來到了新營業的萬達商場,她問我,想買什么?我搖了搖頭,有些羞澀。
她領著我走上三樓,進了耐克的專賣店。試了一套衣服后,她看了一眼我的鞋,問我,弟弟,你是不是喜歡打籃球啊?她拿下墻面上一雙新發布的籃球鞋說,這雙,你看怎么樣,喜歡嗎?我回答了一聲,喜歡。我看了一眼價格,1399元。我猶豫了,和她說,這雙鞋好像有點貴。她說,沒事的。
那天,她在臨進門之前還塞給我一個紅包,后來我打開看,有兩千塊。
幾天后的一場家庭聚餐上——當時黃嘉軒和那個女人已經走了——酒過三巡后,母親的話開始變得有點多,她跟我的姑父說,嘉軒要結婚了,就和那個女孩子。那個女孩的名字叫趙佳慧,浙江溫州人,大學生,師范大學畢業的。她爸爸是開廠的,媽媽是公務員,他們家里在浦東買了套房子租給別人的。嘉軒的命就不一樣啦。佳慧她大伯是他們縣里公安局的局長,你懂嗎?
姑父問母親,那嘉軒他們怎么這么快就結婚?
母親說,佳慧她爸爸身體不好,就希望女兒早點嫁出去。
姑父又問,那他們什么時候結婚?
母親說,快了,今年五月一號。
于是那年的夏天,不是自己到來的,是我們一家人驅車五百公里,一路向南到溫州,才遇到了夏天。
母親為了黃嘉軒的婚禮,特意購置了一身禮服。婚禮當天,她盛裝打扮,到了婚禮現場卻傻了眼。女方父母訂的宴會廳連舞臺都沒準備,完全不需要母親上臺做什么致詞。同樣使母親傻眼的是,她特意叮囑黃嘉軒買的龍眼,他卻買成了桂圓。她忍住沒有譴責他,畢竟是婚禮,畢竟那是黃嘉軒。
我特意尋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環顧周遭的一切。宴會廳里循環播放著音樂,恐怕只有我注意到了那首曲子是七年前黃嘉軒在夜里循環過的《夢中的婚禮》,七年后,我知道了彈奏它的外國人叫理查德·克萊德曼。
有人提議拍一張合影,所有人站到新郎新娘的兩側,身后是一面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陰雨的亞熱帶氣候。閃光燈忽然閃爍,所有的笑容都被定格。
人們爭先恐后要和新人合影,我坐回到窗邊,看著黃嘉軒摟著身旁的新娘,露出好些年都沒見過的燦爛笑容。
這時,有人起哄說要聽新人唱歌,有人開始叫好,也有人問唱什么?一個人站出來說,那就唱《因為愛情》吧。兩支話筒遞到新人的手里,趙佳慧的歌聲如同她的聲音一樣柔美,輪到黃嘉軒的時候,他扭扭捏捏,像是做錯了事的孩子,推脫著自己唱歌不好聽。
我不知道黃嘉軒到底經歷了什么,但我知道八年前的他絕對不是如今這個樣子。
我重新注意到了那個堅果盤,一時不相信這個八年前連鳳梨和菠蘿都分不清的少年,到如今也分不清龍眼與桂圓。
或許是我多意,或許是他無心。
我記得曾經的某本教科書上這么解釋桂圓:龍眼經過熬煮,曝曬,風干便會變成桂圓。這一味中藥就與黃嘉軒的現在一模一樣。
那天夜里,半夢半醒之間,我想起了2016年離家出走的我和黃嘉軒一起唱歌的場景:那天的包廂里只剩下我與他兩個人,他紅透了的臉似乎預示著他已經喝多,他的手緊抓著話筒一直不放,他的歌唱似乎用盡了全身氣力,試圖將整個靈魂傾瀉而出。我記得最后的歌曲是一首民謠:《安和橋》,他喉嚨沙啞,聲嘶力竭,咆哮著唱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樣回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