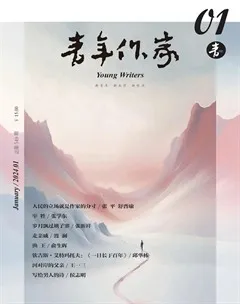“生活”在他的里面生長,正走向郁郁蔥蔥
曾經有一個朋友,給我講了一個夢境,在那個正好不是在夜晚而忽然產生的夢境里,他走在一種戶外開闊的環境中,一切正常而美好,視野的遠處有兩個漂亮的懸浮島嶼,像逆世界一樣的相向而存。走著走著,面前又出現一個巨大的飄蕩著的蓮蓬花束,紫色,香氣彌漫,他只能跟我描述出那是美麗的,可是后來他又回憶起來的時候,提到了恐懼。當時他繼續走著,上空傳出了類似校園廣播一樣的聲音,也許是廣告還是什么,播報出一個女人開設洗浴的同時做了個現實里不讓做的不可描述的描述,他急了,瞬間穿越,沖進好像是曾經學校里的一棟教學樓,瘋狂找尋廣播臺的負責人,還好順利找到了,那個家伙黑黑高高瘦瘦的,下巴上永遠留著一撮小胡子。他質問他,他覺得自己在幫助他,仗義而正直,沒有想到的是,那家伙臉上平靜異常,沒有任何表情,說,不用管,轉身而去。我那個朋友各種呼喊,就像被鬼壓床喊不出聲音只能踹被子也做不出動作一樣,掙扎了許久,放棄了,再次沖到戶外。這次是無垠的草原,海一樣的長草沒過膝蓋,自己一會兒飄在天上,一會兒又沒入草里,草地的盡頭還是草地,看不到海,可是草地上出現一堆一堆的大魚,他開始和忽然出現在身邊或者一直就在的兩個一起生活的伙伴撿魚去了,天氣不冷不熱。剛剛感到富足而幸福,就被樓頂凄厲的鉆頭聲吵醒了,只有自己一個,雙腳冰冷,床頭的窗戶未關,賊風凜凜,頭痛難支。
我沿著鐵軌往日落方向走。我想去看看我和我媽的那個小屋,但到了曾經翻整過菜地的地方,我只看見新修建的賓館。后來聽說在我離開后的第二年里就已經被當成違章建筑給推平了。
我有些難過,但不是想哭出來的那種。十八歲的我看著落日,鐵軌上烙印著我的身影,被無限拉長。我沿著來時的路走,朝太陽升起的方向。那天的凸月已經可以看見,而我身后,是終將落下的夕陽,和蜿蜒通向大海的鐵路。
這是早年間作者發表的作品《鐵路沿線》中的文字,十八歲,一鳴驚人,雖鮮有正式評論,但觀者無不盛贊年輕的作者荷尖初露,文字“老成穩重”,甚至揣測少年生活里的風霜。他慌張過、滿足過、得意過,然后沉默。數年后,我們看到他一如既往的倔強,不過少了抱怨的老成,沒有丟掉少年的風發,而內心愈加有些的穩重也許可以少加個引號了。
《漁王》《桂圓》《秘密》,作者這三篇恰好同時發表的文章等待了數年,齊刷刷地并排站在那里,都是兩個字的題目,極簡而又有嘲諷意味,對著生活,也對著他自己。
我看著主人公的生活,甚至同時看到了作者的生活,就像看著玻璃窗外的雨,他和“他”都在雨里,我和“我”不知道正在哪里,而我眼前的玻璃窗會時不時地被雨水重新淋得模糊不清,時而又顯出一些輪廓。
《漁王》
關于龍潭二中的學生馮明的描述——“幼年的馮明。他有時會躺在野草堆里,一躺就是一下午,有時會拿起一棵狗尾巴草放進嘴里。”“讀初中時,馮明一度迷戀上了弗洛伊德,這位大師讓馮明對分析自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馮明對我說,銳子,其實我有兩個自己,一個是在人群里,一個是在人少或獨處的情況下。”
龍潭為了響應“可持續發展經濟”的政策,決定在八月舉行“龍潭漁王大賽”。之后,馮明忽然有了事情可做,開始釣魚,直到釣上了一條從未有過的大魚,“現在與馮明對峙的這條大鲇魚,目測足有一米多長,它的大嘴絕對可以一口咽下一個小孩。”漁王稱號加冕身上,又瞬間得而復失,“他在所有人的注視下,一個人走向北戴河的西岸,往龍潭二中的方向走去。我后來才得知,那晚他去了月湖,獨自坐了一整夜。”
釣魚大賽之后,“在高三到來的秋天中,馮明總是坐在他那張靠窗的椅子上望著天空發呆。他有時神神叨叨,說著稀奇古怪的話語;有時又像是個詩人,對一切都充滿惆悵。”終于還是在高考前被高中老師勸退了。
再之后,馮明做了月湖的水質監測員,卻面臨建廠占地的困境,抵抗無效,他“專門跑到云節新造的跨江大橋上縱身躍入長江。神奇的是,他的尸體又漂回了北戴河這條幾乎干涸的三級支流。”
馮明和那條躍起的大魚命中相連,生命的執著跨越物種,鎖定在人性可貴的一點殘留中。
馮明和我都是孤獨的,孤獨在人群中,孤獨在伙伴中,孤獨在自己的肉體和心靈中。
《桂圓》
黃蕓和佳慧兩個女孩兒,交代了“我”哥黃嘉軒的成長,紫色或者綠色“李小龍”的死,只是路過的一個年輕悲劇,有些短暫,而黃嘉軒的悲哀卻更長。
關于“李小龍”之死的描述:“他替人去討債,被債主一鏟子打在后腦勺,當天就去世了。那天,李小龍才剛染的一頭綠毛,沾滿了血。”
有關黃嘉軒的描述:“……攥緊了我的手。接著是一個很快的鏡頭,領頭的那個小個子高高躍起,板磚順勢砸在黃嘉軒的頭上。我看見黃嘉軒的頭上流出血,我哭了。”“……他并沒有我想象中的容光煥發,反而一身疲憊,像是遭受了槍擊。”“……他的頭發雜亂,臉上留有淤青。我問他,怎么一回事?他的聲音很輕,像泄了氣的氣球,被他們打了。”“……輪到黃嘉軒的時候,他扭扭捏捏,像是做錯了事的孩子,推脫著自己唱歌不好聽。”
生活中發生的從不中斷的事情給了你一個耳光,你沒有反應,生活于是又打了數不清的耳光。
“我記得曾經的某本教科書上這么解釋桂圓:龍眼經過熬煮,曝曬,風干便會變成桂圓。”就像桂圓的隱喻,在每一個人的身上,且行且在,無常寂靜。
《秘密》
開頭直言“我”與李夢相親,而后講述出了一場深埋在心底的情感,交織而獨立,不同卻相似。
相親,一個饒有歷史時代感的話題,作為了外在形式在作者太極般的文筆中穿梭,你來我往,呼前應后。趣味盎然,又悲傷浸透。
這三篇作品都發生在龍潭,都是以第一人稱“我”的角度來講述的。主人公都是“我”,既是參與者,也是敘事者,作者自我的介入增強了小說的復調性,可以看出作者對自我與主人公關系的恰當處理,建立了合適的距離感,保持經驗和想象的平衡,依然服務于小說的主體表達,在小說的故事表面差異下建立起了底層聲音的一貫性和穩定性,傳達出作者內在的倔強性格底色。
“我”更傾向于一種典型的疏離的內向者(Randall Collins)。作者自我各部分之間對話的隱喻,流淌在文字里,盤根錯節,始終在探尋自己的內心和生存環境的關系。就像來自于米德的符號互動論:思維只是客體的推理,是我所命名的“主我”和“客我”之間進行的一種會話。
龍潭二中舊址的爆破,對于“我”就像自己青春的落幕,繁華落盡,也從無苦盡甘來。眼見出現在作者不同的作品里,穿透作者的生活,挾著年輕人眼里的年代和記憶,時代變遷的代價痛在大地,也痛在“我”的心里。周杰倫、許嵩、快樂女生、MP3……這些時代的符號和碎片,無不卷在時代的車輪里滾滾向前,冷酷而沉默。
在耶路撒冷文學獎答謝詞中昆德拉說道:“十九世紀蒸汽機車問世時,黑格爾堅信他已經掌握了世界歷史的精神。但是福樓拜卻在大談人類的愚昧。我認為那是十九世紀思想界最偉大的創見。”相較于黑格爾所代表的整體主義歷史哲學,昆德拉選擇站在了福樓拜代表的虛無主義個體小說智慧的一邊。
作者始終都在試圖探討人的存在性。
人類的四種基本情感,憤怒、恐懼、喜悅、悲傷,對于人類而言,從生物學來說,這些情感的生理基礎在扁桃腺,是大腦早期進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發現還牽涉到腦皮層和其他未知的部分,這些情感精準卻無法把握,盡數展現在了這些許的文字里,個人化生活的真實赤裸在讀者的面前,無從躲藏,但情感的珍貴和復雜我們其實已經探討了至少幾千年。
捷克詩人揚·斯卡采爾在詩中寫過:詩人沒有創造出詩,詩在那后邊的某個地方,很久以來它就在那里,詩人只是將它發現。
而去年離開我們的米蘭昆德拉認為,在現代世界中,人們變得越來越盲目,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于是會掉進海德格爾所稱的“對存在的遺忘”中。“發現小說所能發現的和對存在的詩意反思。”前輩如此洞見,相信年輕的作者即使筆觸還未渾然,但我們遍覽文字,推敲左右,亦能感受到他定有過從未中斷的深刻思考和內在的認同,這種意識已經潛入了他的字里行間。
當代消費主義主導下的網絡文學、流行文藝鋪天蓋地,現代文學關于“人的文學”根基、精神反抗性和藝術探索性卻言輕式微,可是我依然記得,這位年輕的作者曾在多年前嚴肅地跟我說,他是一個做嚴肅文學的作家,我想時至今日他定然仍舊在堅守這份創作尊嚴。
“這一幕,是那么似曾相識,使我想起了十年前,我和馮明在北戴河東岸留下合影的那個夏日。”
“那天夜里,半夢半醒之間,我想起了2016年離家出走的我和黃嘉軒一起唱歌的場景。”
“她說,我也不該留在這里。我似乎聽見了巨大的潮水聲,其實,在那一年的書店里,金粉般的夕陽灑在記憶里,我也曾聽見過這么一聲,猶如飛機穿過跑道,引擎的巨大轟鳴……”
這些散落的文字恍惚讓我又想起了馬爾克斯,“多年之后,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
孤獨,附著在每一個個體身上,之于人類,亙古未變,于作者,于“我”,不如像布恩蒂亞家族的第一個人被綁在樹上,也或是最后的一個人被螞蟻吃掉。而內心的倔強卻能走向郁郁蔥蔥。
【作者簡介】 王若虛,小說家,出生于1984年11月;著有長篇小說 《馬賊》《尾巴》《狂熱》,短篇小說集《在逃》《守書人》等;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