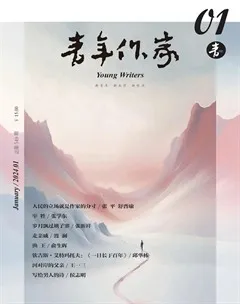窗前
窗子擠在窗子的樓群之中,在樓的樹與白晝、樹與夜的輪廓線里沉靜,枝葉里微風和時間行走的聲音,像在分離一個個最為寬厚的季節,順從著安謐。
云朵充滿天空,朝向我站立的樓后方向飄去,如同增多或減少的數字,從未停止過光陰的漫越。
我宅居的一排三層樓窗戶與對面一排五層高的樓宅之間是一塊長方形的綠地。這還算開闊的間距,自然元素,百步小徑,一端連著小區的長長通道,一端伸向輕顫的蜿蜒小溪。兩邊衰落和蔥郁的樹木,同鳥鳴、狗吠和貓的絮語、每一縷并不艷麗的光線結合一起,消歇得隨心所欲,包容著日常的、每天凝視中的思緒。
窗戶正面一棵高大的櫻樹長了15年。樹干蒼勁,一根根激越的尖梢伸展,柔軟彈跳,像在任意擴大眺望的空間。先于葉子生長的花朵,雪白中透出紅暈,花瓣間鵝黃色的花蕊蘊含著初春的熠熠光線,變得繁茂,越加從容和平靜。仿佛這些花朵都在一夜后的清晨升起,在猝然掀起美麗的幻象,支撐出一切明亮、新鮮的事物。櫻花填滿一個給定的空間,卻又稍縱即逝,像所有清純、浪漫、完美或善良的事物一樣,很快變成紛飛的落英,如撞上一場風雪,飄浮而下,投下暗影,使每一朵花瓣無法脫離現實而保持神奇的絢爛。
緊依櫻樹五米之近的梅樹如同細枝濃密的想象之巢,在隱約閃爍粉紅色光點的花朵之前,還能看清細枝空隙里的一樓北窗及一個小小的院子。院子里養著一條白色小狗。不管是寂靜的上午,還是下午,它像受夠了孤獨,只要路人經過,就會狂吠不已,叫聲如同一種焦躁、一種反應、一種權利,持續一段時間,令人憐憫、心煩和惱火。小狗虛空得一直在爆發抗議之力,追蹤著每一個人影,這使我部分的心靈和感覺如在狹小的生命圈子里,生出第五種第六種第十多種感覺,身上像穿了一件緊身的衣服。
梅樹枝杈的硬脊上,擱著一只5L天然礦泉水塑料空瓶,是被一只手隨意扔在窗子外面的殘物。院子里幾年前還經常看見的一個老嫗,在院子里的自來水池里不是洗菜、洗東西,就是拿著拖把清洗,然后在圍兜上擦干雙手。她像在生活的深處,默默無聞,隨后就漸漸失去了動靜,不見了那個老嫗。而樹杈上的那個空瓶,有時陽光好的時候,我還能看清瓶子上的注冊商標和純水的牌子,里面已沒有任何一滴水珠。白色的、輕飄飄的,視覺或被廢棄的一切,在微風中變成一種知覺,糾結著樹梢、思維。微微向上翹著的瓶口,似在講述一瓶水的過程或家庭故事,靜止在它的存在中。梅花打開一棵梅樹的形態,光速飛逝,蔥綠葉子很快從春天進入夏天,不僅遮蔽住那個窗口和院子,也遮掩了空瓶。更多空間,更少的縫隙,似乎有著針一樣深入的隱語,形成了一種簡化的有用與無用、縱向和橫向的視覺范圍。
我樓層筆直而下的一段臺階連著地面的小路,左側與對面門庭的右側,種著相同的石榴樹。這兩棵樹同時種下,每年的五黃六月天,都會結出淡黃色的果實,如同小燈籠,低垂著照亮空間,也會變成我凝視、比較的全部目光。這兩棵樹品種一樣,土壤一樣,但長著長著樹的形體就一大一小了。對門的那棵石榴樹豐滿,高大,果實如同膨脹和擴大的卵石,充滿張力,而我門邊的石榴樹因為常年被櫻樹的繁茂葉子遮擋陽光,就顯得矮小許多,果實雖也閃亮,但稀少得可憐。即使這樣,果香依然打動了一些老婦,或一些年輕過路人的好奇,他們常常會肆意地拿著竹竿敲打,或索性搬著鉛制的梯子進行摘取。哪怕我在樹枝上掛上“果實已噴農藥,請勿采摘,后果自負”的牌子,卻依然不能阻止他們激蕩的行為。果實總在一夜之后隱秘消失。
桂花飄香的芬芳點綴起粒粒金黃的星星,似乎我的窗戶是忍不住吸了又吸的鼻子,想把這獨特的幽香藏入肺腑。這棵桂花樹就長在我樓下一層的院子里。在我剛搬入這座居所時,它還是一棵幼樹,光陰荏苒,十幾年過去長得枝繁葉茂,高貴而優雅,顯得愈加強壯,愈加寬大。這棵樹的梢尖已達三層樓板之上,葉子貼著封閉陽臺的玻璃像在探望我日常的寫作姿勢和思考句子的模樣,或以滑動的輕泛香味緩解我繃緊的神經,紛紛揚揚,把空氣鍍得金光閃閃,那么柔軟和明亮。
長在我樓下院子里的桂花樹,是我的一種心情,使我安靜。一樓和二樓是另一戶人家,是房主購買后用來出租的房子。第一家租戶用尖銳的裝修聲音,持續了四個月的噪音,安定了大半年就搬了出去。第二撥租戶一進場,便立即將第一個租戶分隔的、裝修的墻體全部拆除,化成破碎和蓬起的粉塵。然后稍稍小住了兩年,又舉家遷徙了。現在第三撥租戶又開始裝修了,且有一輩子居住下來不走的架勢,除了改變原來一層二層樓梯的位置,還把原來所有過時的門窗、內部結構全都按照最時髦的樣子進行改造。于是,整幢樓的墻體和地面激烈震顫,電錐的嗥叫如同瘋狂的吠尨,像在鉆透我腳心底下隔空的地球。浮起的塵土,斜過窗戶玻璃,出現濃厚的蒼白和一片混沌的沙塵暴,像在瀕臨十級震源、毀滅性的崩潰中心,使倒塌的寧靜,我的心葉一瓣一瓣凋落,陷入十分戰栗的廢墟之中,變成一個心智十分正常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這種擾亂,命中注定的鄰居,無法阻止,無法選擇,只能咬著唇齒忍受。似乎城市里最有財富的一面,就是這些租戶背后的房主和為急劇上漲的房價而不斷改建的人。而我只能忍耐一次又一次劇烈的轟鳴,只能撕扯自己的胸腔或默默尖叫,永遠忘記屬于自己的一半獨立的樓板和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一天傍晚,一切嘈雜停息了下來。我坐在封閉的陽臺上凝望一片被噪音蹂躪過的空間,突然發現窗玻璃外的桂花樹葉子在這盛夏全部掉光了。這很不正常的現象,讓我反復比較其它樹木,發現櫻樹、梅樹、石榴樹、李樹、檵樹、枇杷樹十分蔥蘢,葉簇生機勃勃,唯獨這棵桂花樹孱弱、萎靡,樹枝灰白、枝叉空散、枝條斑駁,與衰敗不堪的凋零有了一致的命數。我百思不得其解,只看到一片片枯死的葉子。
隨后幾天,我不止幾次探出頭往窗底下看個究竟,從樹梢、枝干到樹根的底部,想尋找它枯萎的緣由。然而除了一點,我似乎只有唯一的理由。那就是這棵樹遮擋住了樓下一層或二層的光線。而誰都知道,每棵樹在這片國土上,誰都沒有隨便遷移的權力。只有讓它死去,才有一切可能。
這種精神與自私上產生的墜落,是萬物的一次戰栗。因為影響窗戶的采光,而以赤裸的手段,強迫一棵樹卷起所有焦枯葉子。這過程中我的疑惑,或我最終似是而非的結論,讓我如在一個懸浮的空穴。
我不知樓下的鄰居用了哪一種辦法。被戕害的它,枝杈閃著白光,恰似陰燃的火焰,在不可容忍的煎熬中逐漸熄滅,無法言說一種秘密的惡,但它依然活著,居然在綠葉凋零幾天后,在光禿禿的枝頭重新爆出了春天的嫩芽。
嫩芽幾瓣如同祈禱的言辭,被我當成一種再生的希望。它在風兒吹拂的枝上喘息,藏匿起恐怖的大限,喚出生命的倔強。以神奇的活力再次閃露出復活的綠葉。
綠葉經歷死亡和幻夢。我略有興奮的目光沒有幾天,便很快又進入陰郁和憂傷之中。發現那幾枝冒出的嫩芽沒有釉光,只有憂愁似的黯淡,彌漫出一股戰栗的氣息。那淺綠的色調中更多充盈著泛黃的磨難光澤,它很快又開始凋落。我的內心不寒而栗。當我又一次探頭觀察這棵樹的任何細節,從樹枝到收攏視線的樹干,從根部到土壤,依然沒有發現任何做過手腳的痕跡。那時,我只覺得這棵曾經給我歡愉空氣的桂花樹,它真的死了。
我呆立發愣。枯死的枝條凝然不動,沉默不語,蒼白或趨暗的樣子,飛速流過生命之影,在我面前卷縮的葉子,一片一片落向堆滿建筑垃圾的地上。
橫貫綠地的平坦小徑,干凈得沒有一點皺紋。我似乎已看慣它的安定。喜歡靜靜的光和樹影。可光和樹影每日總在很快移動,突然消失,如同一種存在過的夢境。而鶇鳥和斑鳩像是短途的旅客,常常會在地面陪伴在灌木叢中出沒的貓,散會兒步,相互傾聽悄聲、細語和致意,交流生活的心得。貓有時則會頓生悠閑的興致,會在一塊石頭旁停下腳步,似乎總想在朋友面前露一手捕獲獵物的絕技本領。
小徑已然適應寂靜。鳥畢竟還是空中的驕子。偶爾在窗前右邊的紫葉李樹棲一棲,連翹的樹梢就連接起一片聯想的天空。看到那些攀登到高處的紫紅色的成熟李子如同一粒粒糖制的小腦袋,加調著甜的順境味道,并在舒展一番的感覺里,想起許多有了更大空間和位置,以及一些事物、人的形態和稱呼。
我生活的這個住宅小區所見和所想的那么多瞬間,難以被言語傳述。有時我看到我的窗沿上,兩只麻雀,先親密地在一起,然后一只緊收身子,另一只抖動蓬松的羽毛,嘰嘰喳喳,欲近還遠,遠又趨近。不知經歷多少這種過程,最后兩只鳥互相配合地懸飛在空間,完成親密而不可言說的事情,那時,我特別地認為我這個小區雖是一個很小的小區,但還是一個繁花似錦的自然界。推而擴之,眼里除了近在咫尺之內的桂花樹以外,還是滿目蔥綠。不僅充溢著溫和或灼人的陽光,也拂動愜意的月光。窗口是我站著或坐著的一方世界,或有著我太多的俯瞰、仰視,或本然的怡情和詫異。晴空經常萬里,經常薄霧籠罩,默默無言的安逸,雖被此事那事沖擊,但看到狹小而空曠的白晝光亮、夜晚的黯淡,我依然覺得小空間是明亮和寬廣的空間,讓我在視覺的氣流里,隱身于綠葉滿眼的一片樹叢、一朵花瓣、一滴露珠;或同樣在塵世之中,隱于無奈的抑郁和孱弱的閑逸之中。
我窗前臨近小溪的岸邊還有一棵檵樹。這種樹似乎永遠在莊重的寧靜中,在我所提到的我的小天地的各種樹木里,以全部玲瓏的枝干,緩慢生長的軀體,默默以風雨催生的葉子和淺紅色的花朵,濾盡喧鬧,注入淡定的思考,使滄桑變得如同奇花異木……
我有一次去溧陽看一個朋友的臨湖別墅,一走進庭院,看到那里的檵樹正開得紅紅火火。我朋友跟我介紹說這是梅樹中的一種金縷梅。我告訴他,這種樹是特別耐旱、耐寒冷、耐瘠薄的一種樹,但不是梅樹,而這棵樹的樹名,字很難寫。
【作者簡介】 王學芯,詩人,生在北京;著有《雙唇》《文字的舞蹈》《飛塵》《遷變》《老人院》《藍光》等13部。曾參加第十屆青春詩會。獲郭沫若詩歌獎、紫金山文學獎、中國第五屆長詩獎、劉伯溫詩歌獎等;現居江蘇無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