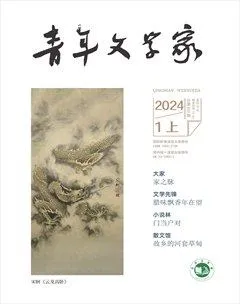春燕
李歌
八十歲的春燕坐在炕上,透過窗子看向門口。家里很安靜,只有她手里的木棍敲打在身上,悶悶的聲音,偶爾還夾雜著一聲嘆息,現(xiàn)在回想起來是期盼,是失望……
太爺李明哲,是一位教書先生,他的為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明智、睿哲。他一定是這樣的人,不然也不會成為教書先生,也不會成為抗美援朝志愿軍中的一員,成為一名指導(dǎo)員。明哲二十四歲的一天,春燕挺著大肚子,手里牽著大兒子,淚眼婆娑,看著他遠去的背影,望了很久很久。她那身影,那被風吹起的衣襟,那身邊的一棵小柳樹,在藍色透著蒼茫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紅的晚霞下,猶如一幅紙剪的畫影……
明哲毅然踏上北上的列車。隨著轟炸機越來越近的轟鳴,明哲奮力抬起頭,看向家的方向,硝煙已在天空上凝結(jié)成云霧,他好像看到了春燕,他睜大雙眼想再看清楚些,可是視線漸漸模糊,光熄滅了。一年后,春燕披著月光趕去打探消息,得知全軍覆沒……那黑夜茫茫,夜路如蛇,不知道哭了多久,走了多久才回到家。坐在門檻上餓得嗷嗷大哭的兩個孩子讓她如夢初醒,孩子涕淚橫流,嗓子都哭啞了,她的公婆就住在隔壁,大門緊閉。他們說,自己還有一堆孩子,哪兒還顧得上孫子。她把明哲留下來唯一的黑白照片,放進最貼近心臟的口袋,仿佛他從未離開。后來,村主任親自送來烈士證明,她不相信,她說,她知道明哲肯定在某個地方活著,那個地方很遠,很偏。在那個年代,一個年輕女人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在田間地頭,面朝黃土背朝天。她說,她一定要撐住,不然等明哲回來就找不到家了。
她的嫁妝,一個木色櫥柜擺放在炕邊。每年中秋她都會用一層層小布帕包裹幾塊月餅,放在里面,說明哲愛吃。過了一陣子再打開,已經(jīng)生出了長長的毛,她換上幾塊新的,如此反復(fù)。只要我來,她就從柜櫥里掏出一個小袋,給我一塊薄荷糖。我吃著,她就開始說:“你一定要好好念書,除了念書以外什么也別干,只有當了大學生才有出路……”那時,我正在讀小學,只覺得她嘮叨,比起遙遠的大學,我更喜歡去村外樹林里捉知了,去街上小賣鋪買辣條。后來,我考上大學,考上研究生,都去墳前告訴她了,她應(yīng)該會驕傲吧!
直到查出癌癥前一天,春燕一直都很健康。每次吃飯,我的奶奶都幫她端到炕上,她咕嚕咕嚕地能吃一大碗,我跟她吃一樣的飯,總覺得她碗里的更香,我就懷疑奶奶是不是在她的碗里藏著肉呢?食管癌病情發(fā)展得很迅速,七月份檢查什么問題也沒有,九月份再去就是晚期了,醫(yī)生說最多還有三個月時間,回家吧。天氣越來越?jīng)觯榭s在炕上,蓋著厚厚的被,像一棵枯萎的樹。我用小勺輕輕刮下蘋果泥,送進她的嘴里,她的唇舌蠕動片刻,但終究沒有咽下。我沖出家門大哭一場,等我雙目通紅再回去,她從枕頭下摸出一枚五角硬幣,遞給我,讓我去買點兒辣條。有一天,躺了很久的她突然坐起來了,看著屋外,手指著門口,她說:“明哲來接我了,你看他去廚房了。”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頭皮發(fā)麻,嚇得我此后很久不敢去廚房。第二天,春燕就在睡夢中去了。那一天,家里來了很多人,她躺在那兒,表情和姿勢都很平和。我想,心愛的人來接她,她一定是幸福的吧!我握著她冰冷的手,心里默默地想著,太奶你記得給我托夢啊。不過,十六年了,春燕一次也沒來過我的夢里。
人群散去,凌晨天還沒亮,一陣啜泣聲將我吵醒,爺爺坐在炕上雙手掩面,抽抽搭搭地嗚咽,說:“我沒有娘了……”奶奶在旁邊輕撫爺爺?shù)谋常聊苍S從小失去母親的她,更懂得如何安慰從小失去父親,現(xiàn)在又失去了母親的他。生活的苦被他們嘗盡了,溢于言表,到最后只有默默陪伴。我不禁鼻頭一酸,眼中涌出了淚。
也許是某種緣分使然,我找了一位丹東的小伙子作為人生伴侶。我站在斷橋上,看著對岸,這里的每一步都是明哲走過的路,是春燕終其一生,魂牽夢縈,心之所向的地方。小雨蒙蒙,我來到紀念館,做了一件不太道德的事—我從花園里挖了一捧土,拿了一塊石頭,帶回了家,放在了春燕的墳前。這是七十年來,春燕距離明哲最近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