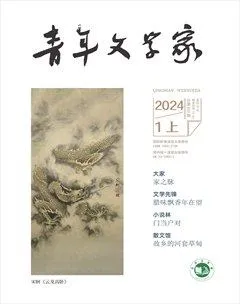那年·那月
成峰

午后的陽光暖暖的,門前的麥子已經泛黃,空氣里飽含著麥穗成熟的芬芳。我雙目微閉,在窗外的柳蔭下假寐。一曲《父親寫的散文詩》悠悠飄來。
1984年,莊稼還沒有收割完,兒子躺在我的懷里,睡得那么香甜。女兒說,她很喜歡這支歌,她聽得好感動,好心酸。而我卻不以為然。在現代人的眼里,這些經歷應該屬于童話故事,但在我們生活的那個年代,這就是日常瑣事。從那個年代走出來的人,哪一個沒有一本辛酸賬!想當初,我初為人父那會兒,除了一身力氣,滿屋子裝的,就只有貧窮。
記得有一年,哥哥出門去做手藝了,嫂子一個人在家,又帶孩子,又下地,還要養豬喂牛。偏偏這個時候,侄子病了,感冒發燒,因為沒有及時看醫生,竟然燒成了小兒肺炎。嫂子這才慌了,可送孩子進醫院,要錢啊!而她的身上,除了一身債,兜兒比臉還要干凈。那一夜,為了把孩子送進醫院,嫂子生生跑了大半夜,好不容易才借到了二十元錢。
二十元錢,對現在的人來說,一頓飯,一包煙都不夠。可在那個年代,它可是救命錢!
我結婚第三天,父親買來一口鍋,就跟我分家了。說是分家,其實他只分給了我一口鍋、一斤油、幾斤米,再就是幾畝責任田。
那時候,我們村還沒打圍護堤,經常淹水,一年的收入養活不了全家。至于蓋房買車,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兒。窮則思變,當可以出外謀生的信息在村里悄悄擴散的時候,我第一時間踏出了家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城里和鄉下似乎沒有太多區別,幾乎都是一大家子擠在幾間小屋。不過,他們都有工作,工資雖然不高,但生活有保障。
我的第一站是咸陽,路費是結婚時妻子的茶錢。那是一個早春的晚上,天很冷,路面結著白花花的冰,跟我同行的是和我一般大的同村小伙兒。我們下了車,找到一家旅館,一問價錢覺得太貴,沒住,就走了。然而這一走,就再沒看到旅館的影子,我們兩人只能在冷清的大街上來回溜達。
隨著氣溫降低,腹中饑餓,我們把帶來的衣服全部套在身上,依然止不住地瑟瑟發抖。那時,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徹骨的寒涼一個勁兒地往骨頭縫兒里鉆。
幸好遇到一個雨棚,棚子底下還有兩個飄著藍色火苗的爐子,我們迫不及待地騎了上去。好不容易熬過了兩個小時,又被人攆出了雨棚。最后,我們跑進了一個按時間收費的茶棚,在一張躺椅上蜷曲了一晚。
在咸陽轉了一個星期,我們決定回家。因為距離上車還有些時間,所以臨時改道,跑到西安逛了一圈動物園。然而,就在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們被騙了,手上僅有的百十塊錢被騙了個精光。
那可是在人地兩生、舉目無親的千里之外啊!喊天不應,叫地不靈!
那一次,我們餓了三天三夜,一路靠著乞討,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家。也就是那次之后,我吸取了教訓,不義之財堅決不取,哪怕是送到我腳下的錢,我也會選擇無視。我在外漂泊了近二十年之久,其中所歷經的艱辛和磨難,不是親身經歷的人,很難想象的,其中的苦楚和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我已從一個二十幾歲的毛頭小伙兒變成了一個年過半百的中年人,雖然我沒有取得什么成功,但跌跌撞撞,也過了半輩子。也許正是這二十年的磨礪、沉淀、積攢,才有了我今天的堅韌和灑脫,懂得了什么該拿起,什么該放下。
就像這麥熟的田野,恬靜、自然,在成熟的芬芳中,看時光的腳步悄然蕩平一波又一波俗世的浪花。
時光一去不復返了,我們的境遇也許不會在歷史的長河中重現,但那段痛且快樂的青春時光,會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深處,相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