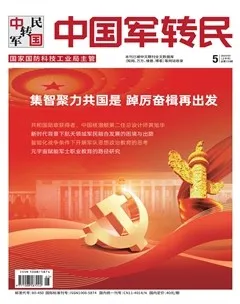構建具有社會主義本質特色的使命價值觀
王浩然
自2016 年國家領導人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 周年大會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這一詞起,習近平總書記就高度重視關于“初心”和“使命”所蘊含的深厚價值內涵。在2017 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上更是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1]為報告主題。再到2022 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開篇就提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并且放在“三個務必”之首,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的堅守,彰顯了黨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初心和恒心。在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和反復提及下,“初心”和“使命”這一詞很快便在全黨,全社會掀起一波討論的熱潮,其深厚內涵被不斷發掘,然而我認為“初心”和“使命”除了在現實社會層面具有深刻含義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層面同樣意義非凡,它直接了當地點明了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價值觀。

一、初心,使命的詞義以及蘊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
初心一詞在漢語詞典中意指做某件事的最初的初衷、最初的原因。根據現有資料最早處于東晉《搜神記》卷十五:“既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訣。”聯系原文,初心在這句話中的意思可理解為,如果初心不能保全,對一個人來說相比于死亡。所以說這初心一詞在最初應用之時就代表了極高的價值水準,也說明了早在晉朝時期的中國人就已經在形成一種超越個人生死這種基礎價值判斷之外的價值體系。
使命一詞在漢語詞典中意指出使的人所領受的任務;應負的責任。根據現有資料最早處于春秋《左傳· 昭公十六年》:“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在這句話當中使命表命令,指一個國家命令執行不暢,就會導致禍事。而今多從使命被授予者的角度去理解,指承擔使命者的應盡職責。
使命一詞不是孤立、靜止的一個詞,它的詞義本身就蘊含這一種聯系的邏輯,代表一種過去與現在相連的橫向認知。當我們把這個含義在時間的范圍上拉長,拉到整人類歷史的長度,我們從中就會看到一種觀點,一種歷史的觀點,一種自1845 年提出就震撼哲學界,影響人類至今的歷史觀點——唯物史觀。所以,使命二字的內涵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具有深厚的哲學聯系,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語言生活上的完美體現。
二、中西方傳統的價值觀內涵
每一個社會都有它所匹配的價值與道德體系,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 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價值觀在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領域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它是重要的精神推動力,也是一個國家政治體制的擬人化反映。所以一個成熟的的社會必須構建起屬于它自己的價值體系。《中國文化要義》指出“在西洋人的意識中生活中,最占位置者為個人與團體兩級;而在中國人則為家庭與天下兩級。此其大較也。”[2]西方古代社會的價值體系是依據于宗教神權為基礎的,人與人之間是單個豎狀獨立出來的,個人與個人之間互不干涉,人的價值第一要求是對垂直上方的“神”負責,只要他們相信的是同一位“神”那么二者就有了認同的基礎,就可以進行現實的交流。這種只對上帝負責,精神層面中人與人彼此獨立的現象,給西方古代價值觀帶來一種超脫的情愫在其中。中國古代的價值體系在《中國文化要義》書中表達,和西方豎狀獨立正好相反,是一種扁平化的以個人家庭為核心再擴大到整個國家社會的價值體系,人與人之間不是彼此獨立,相反把彼此之間視為自己價值的一部分,形成一種“天下”觀念,這也給中國古代價值觀帶來一種世俗的情愫在其中。然而,當理論落入人的現實之中,往往會表現出事與愿違,本該是表現超越的東西,實質卻被蠱惑淪為世俗,那些看似是世俗的外表,內核卻總是表現出超越。
三、在現代化要求下,面臨的西方現代價值觀沖擊
歷史的浪潮奮勇向前,在生產力提高,交通運輸擴大,文明的聯系不斷加強的絕對發展狀況下,新的經濟基礎必然會要求產生新的上層建筑,西方現代社會順勢產生出了適合時代要求的價值觀念,例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極具侵略性的金錢主義,這些價值觀無一例外帶著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尤其是金錢主義價值觀,在資本主義全球金融貿易體系的掩護下,以及西方價值觀對價值概念的刻意掩蓋,使得它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可以找到他的信徒。
消費主義,金錢主義在現社會能夠大行其道自然尤其理論合理性,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的價值衡量,表現一定程度是以商品來體現的,商品本身被賦予了價值屬性,所以當一個能代表“價值”的物品出現時,不管它是什么,追求“價值”的這個過程天然就具有合理性。
正如馬克思指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之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理解這句話首先就要找出它的隱藏前提是指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表現為價值,但馬克思之所以能成為馬克思,這句話的精髓還在于后面部分,即商品為何能在資本主義階段下成為價值是因為商品其中包含的人類勞動,價值的本質上是人類勞動,不過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人類勞動以商品表現出來,所以商品才有價值。對于消費為什么能滲透到社會價值之中,具體理論為商品具有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兩個屬性,其社會屬性,人支配人的權利,使得人對商品的追求,就可以實現“人支配人的權利”價值,歸根到底,是關于“人”的價值問題。問題的根本永遠在于人,金錢只不過是“人”主動找到使這一過程進行更流暢的最佳替代物,可悲的是,從表象結果來看,這些在這一信條中處于弱勢,被支配一方的人同樣受它驅使。弱者本性也像強者那樣,希望能彰顯自己的意志,駕馭弱者;彰顯是所有人的本性。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利用了這一人性之惡,人總是想要影響,支配他人,把價值與金錢等同,掩蓋價值實體,來對人進行歇斯底里,永無止境支配。
四、人的本質彰顯與歷史繼承
然而關于人的彰顯本性這一點這是有問題的,問題出現在哪了呢?出現在把人的定義與人類混淆了。個體人類所展現的特質無法擴大概括到整個人類層面。舉個很簡單但一直被忽略的事實,相比于其他生物生理結構和外界磨合穩定后,其習性可以保持千萬年的不變,然而縱觀智人這個物種,在晚期智人5 萬年的階段,其生理結構變化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現實的社會行為表象上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樣的人種族,沒有生物機理的變化,在一萬年以前他可能是部落氏族的首領,過著采集打獵的生活,在6000年以前他可能是一名奴隸,每天受到奴隸主的驅使,在3000 年以前,他可能是一個小地主,每日和土地做伴,從事著日復一日的農業勞動,在300 年前他可能是一名工人,在一個巨大的工廠里沒日沒夜的在流水線上從事工作,到如今,他可能是一個坐在100 米高的鋼筋水泥土建筑物里對著閃閃發光屏幕打字的無名小卒。那以后呢,在未來的300 年,人將會成為什么樣的表現?我們不知道,但有一點,我們是無比確定,就是不可能是如今這樣。對的,我相信如今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會對這一點表示確定,好像這是一件再稀松平常不過的事了,然而這并不普通,甚至應該說是非常耀眼!千年一直以來的改變,使我們默認改變是一種常態,對此我們不會感到質疑,但同時好像也忽略了原因。我想這其中蘊含的原因是我們理解人類本質價值的關鍵。過去對于這個現象的解釋比較淺顯,大多是從生理的角度,指出人類因為自身大腦發達,使人產生了智慧,所以才會使得我們不同于其他生物,成為萬物靈長。但這其實解釋不了上面舉例的現象,部落首領,奴隸,小地主,工人,以及正在看這段文字的你,相互之間在大腦方面有不同嗎?答案是肯定的,顯而易見的。
在過去,我們總以為哲學家,科學家,甚至是企業家,其所達成的一切都是憑借其自生的行為,歷史的篇章是由那些具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拍一拍自己腦袋書寫的,然而,馬克思戳破了這個美麗的童話故事,毅然指出,“人類史是我們自己創造的。”[3]這一點在標準教科書又詳細展開為物質財富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精神財富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同時人民群眾還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然而這也是表象,實際內涵藏著的是人的本質定義問題,與歷史的繼承。在唯物史觀看來人的精神不是自我憑空的產生,同樣也不是來自神秘的虛空,而是來自過去。從當下的時空來看,人與人之間的彰顯是相互的,一個正在彰顯他人的人其構成前提就是先接收他人的彰顯。所謂人就是在無數他人彰顯下形成了“自己”,然后以這個“自己”去彰顯他人。同時!人的彰顯并不局限于他自己所出的歷史時空中。從整個的歷史視角來看,這個彰顯的發生過程并不處于某個假定的靜止時空下,所有人接受的彰顯還包含來自過去所有時間段彰顯的積累,因為時間是連續的,歷史也是連續的,人的彰顯內容也是連續的。人類文明的形成,歷史的形成就是在一代一代的繼承。如果沒有對歷史的繼承基礎,所形成的“人”必定是一個空虛的概念。
所以說個人的概念只在現實生活中,在人與人之間,在社會運轉之間用于評價判斷善惡是非時才是成立的!在哲學層次來講的話,只討論單個人的價值是不成立的,因為“人”不可能單個存在,或者是說“人”的表現一定是在人們中體現的,同時也和歷史深深地綁定著。所以馬克思講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的就是從最根本,整體的視角來看人的定義。人的本質組成就是,來自他人和來自歷史的繼承,同時自己又構成他人的一部分,構成以后的人所承接的歷史一部分。大腦不過是這一過程的物質基礎和前提要求,把建立在物質生理大腦DNA 上的差別加上,這三個就是全部的社會關系。
五、構建具有社會主義本質特色的使命價值觀
根據人的本質,歷史的繼承,宇宙的價值這些原理,我們就對當下要構建的使命價值觀的內涵有了把握。使命價值觀是什么?是一個嶄新的,在理論上具有深刻內涵的,符合歷史時代發展規律的,在實踐方面具有強大感召力的價值觀。具體落實到我們當下,就是構建具有中華優秀傳統價值取向,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思想,符合人類文明價值走向,包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應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當中的使命價值觀。內容包含,從人的根本價值上,人與人之間如何認知彼此,從歷史和文明的角度認識自我。價值不是一時一刻的體現,是在整體中的。從不能忘記自己的來處,自己承擔的使命,于個人是這樣,于國家,于社會也是如此。歷史人物,由于其自身的集合代表,在體現上確實會照耀很多人,但不論多耀眼的火焰,都是由其中的火苗組成,越耀眼的火焰蘊含越多的小火苗。單獨看這些火苗的一生,可能體現出來的只是螢火蟲般弱不禁風隨時可能會熄滅的光亮,但最令人欣慰和感到希望的是這渺小的光會一直傳遞下去,哪怕最后已經微乎其微,哪怕火焰也不曾意識到,但這不代表他會消失,歷史知道,他曾經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