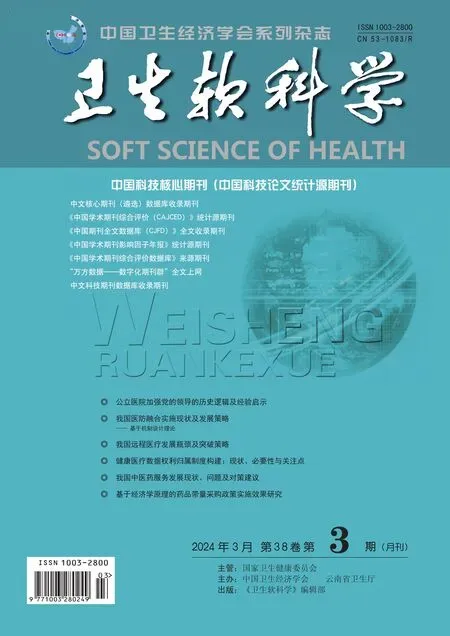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水平耦合協調及關聯性分析
王 瑩,方文箐,秦才欣,陳一丁,徐 穎
(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江蘇 蘇州 215006)
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已達63.89%,以經濟發展為導向的傳統城鎮化,產生了公共服務資源尤其是醫療衛生資源空間布局不均衡、分配不合理等問題。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城鎮發展質量的提升,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城鎮化是保障醫療服務體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1],合理配置衛生資源是衛生事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解決健康服務供給總體不足與需求不斷增長之間的矛盾。2021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21〕18號)中再次強調要提高醫療資源的區域均衡性,提供優質高效的醫療衛生服務。
近年來,針對衛生資源配置和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問題,有少數學者探究了經濟發展與衛生資源配置的關聯性[2],城鎮化對公共衛生資源的影響[3],以及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機制[4],但是有關新型城鎮化與衛生資源配置的關聯尚未有學者探究。本文以江蘇省為研究對象,構建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基于耦合理論探究兩者間的協調態勢,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對各個指標間的關聯程度進行微觀分析,從而綜合探究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水平的影響程度,為江蘇省衛生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于2013-2022年《江蘇省統計年鑒》。為全面客觀地反映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之間的關聯性,基于數據的準確性和可獲得性,衛生資源配置方面選擇醫療機構數、衛生技術人員、醫療機構床位數、年度診療人次、入院人數、病床使用率和衛生總費用7個指標作為衡量指標。借鑒黃敦平[5]等人新型城鎮化質量綜合評價指標,從宏觀質量、產業結構質量、人口質量、生態環境質量、公共服務質量和城鄉統籌維度進行評估,選取人均GDP、單位GDP能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商投資總額、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口城鎮化率、城鎮人口就業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環保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濕地面積占轄區面積比重、醫療保險社會綜合覆蓋率、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和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之比作共14個指標為評價指標。其中,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和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之比為負向指標,其余均為正向指標。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權法
熵權法是指根據數據的離散程度來確定指標的權重,可以很好地克服主觀因素對結果賦值造成的偏差[6]。對于某個指標,可以用熵值對其離散程度進行判斷,信息熵值越小,離散程度越大,即該指標對綜合評價的權重越大。計算公式如下:
首先,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假設有a個評價對象,b個評價指標,設Xij(i=1,2,…,a;j=1,2,…,b)為第i個對象第j個評價指標的原值,Yij為無量綱化后的數值,則:
(a)
(b)
其中,(a)為正向指標的標準化處理公式,(b)為負向指標公式。
其次,計算第j個指標下第i個評價單元的占比Wij;以及第j個指標的熵值ej;
(c)
(d)
最后,計算第j個指標的熵權Sj:
(e)
各指標權重計算結果見表1。

表1 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水平評價指標權重
1.2.2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度是用來度量系統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程度的大小,可以很好地對多個系統間的協調發展情況進行評價和分析。協調度模型一共涉及3個指標的計算:耦合度C,協調指數T和耦合協調度D,計算公式如下:
T=αU+βQ
其中,U為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水平系統,Q為新型城鎮化水平系統,C為系統間的耦合度,取值范圍為[0,1],取值越大,說明系統間耦合性越高;D為系統間的耦合協調度,取值范圍為[0,1],取值越大,說明系統間耦合協調作用越緊密;T為系統間的綜合協調指數。α和β為待定系數,在本文中,筆者認為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和新型城鎮化水平同等重要,故令α=β=0.5。耦合協調度發展階段與等級劃分見表2。

表2 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
1.2.3 灰色關聯分析
灰色關聯分析通過影響因素時間序列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比較關聯度,幾何形狀越相似,曲線越接近,表明相應的序列間關聯度越高[7],反之則越低。本文采用灰色關聯理論,分別測算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水平和新型城鎮化綜合水平各指標的灰色關聯度。灰色關聯度數值大于0.7為重要因素,0.5~0.7間為相對重要因素,低于0.5為不重要因素。
2 結果
2.1 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水平分析
2012-2021年,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綜合水平均值為0.506,新型城鎮化水平均值為0.517,耦合協調度均值為0.681,上述指標均在2012年值最低,2021年值最高。見表3。

表3 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指標描述性分析
2012-2019年,衛生資源配置水平持續增高,2013年增速最快,達到76.47%,之后增速逐漸放緩,在2020年出現下降,較2019年下降了0.077,在2021年又增高至0.837。江蘇省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結果在2012-2021年呈現持續上漲趨勢,2012-2013年增速最快,達72.66%;在2016-2017年實現新一輪增長,增速為37.19%;2020年增長趨勢為10年間最慢,增速僅為5.28%。見表4和圖1。

圖1 2012-2021年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和新型城鎮化發展耦合協調度動態變化

表4 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水平耦合協調度分析
2.2 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水平耦合協調度分析
近10年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和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結果及兩者耦合協調度總體呈現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趨勢,耦合協調階段經歷了嚴重失調、輕度失調、勉強協調、初級協調、中級協調、良好協調和優質協調階段,耦合協調等級持續提升。2012-2013年,耦合協調度由0.1增長至0.367,增長率267%,呈現快速增長趨勢;2014-2017年,增長速度大幅下降,增長率由2015年的19.2%降低至2016年的8.29%,又增長至2017年的16.94%,呈現波動增長趨勢。然而,2020年兩系統雖然處于極度耦合協調階段,但是耦合協調度較2019年下降了0.014,表明兩者間耦合協調態勢不夠穩定,需要進一步磨合與鞏固。對比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和新型城鎮化水平后,發現2012-2016年兩者綜合評價值基本相等,2016年之后新型城鎮化水平略優于衛生資源配置水平。見表4和圖1。
2.3 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水平關聯度分析
計算得出2012-2021年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水平各指標同新型城鎮化水平總體指標的灰色關聯度,以及江蘇省型城鎮化水平各指標同衛生資源配置綜合水平的灰色關聯度。各指標關聯程度及影響程度排序結果見表5。

表5 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灰色關聯度分析
結果顯示,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7個指標與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指標的關聯度都在0.5以上,其中,衛生總費用的關聯度最高(0.82),為新型城鎮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其次是衛生技術人員(0.708)、醫療機構床位數(0.689)、入院人數(0.679)、年度診療人次(0.633)、醫療機構數(0.617)以及病床使用率(0.573),醫療機構數和病床使用率與新型城鎮化水平的關聯度相對較低。
結果顯示,新型城鎮化14個指標與衛生資源配置綜合指標的關聯度都在0.5以上,其中,關聯度高于0.7的重要影響因素共有4個,分別是外商投資總額(0.804)、醫療保險社會綜合覆蓋率(0.786)、人均GDP(0.753)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748)。環保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0.566)和單位GDP能耗(0.537)與衛生資源配置綜合水平的關聯度相對較低。
3 討論
3.1 衛生資源配置和新型城鎮化水平耦合協調增長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總體來看,10年間江蘇省新型城鎮化水平呈現持續上升趨勢,但衛生資源配置水平在2020年有一定下降。在耦合協調度方面,兩系統間同樣顯示持續上漲的趨勢,耦合協調態勢較好。具體來看,兩系統耦合協調度大致可以分為快速增長(2012-2013年)、波動增長(2013-2017年)和基本穩定增長(2017-2020年)階段,但是在2020年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說明耦合協調態勢不夠穩定,仍然需要進一步磨合與提升。
2008年,我國開始實行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了江蘇省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規模擴大。2009年《關于深化醫藥醫療體制改革的意見》頒布后,分級診療、三醫聯動的系統化改革成為重點。在此階段,城鎮化的發展縮小了城鄉間的差距,能促進分級診療的有效落實,相應地,醫改對優化衛生資源配置提出新要求,對農村和城市基層地區進行重點傾斜,有利于加快城鎮化進程。衛生資源配置與城鎮化協調發展,相互促進,從而表現出整體耦合協調度快速增長。
2013-2017年,衛生資源配置與新型城鎮化耦合協調度增長速度大幅下降。在此時期,國家進一步優化醫療資源配置,出臺《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分級診療制度的指導意見》,推動分級診療的落實。同時,江蘇省內多數城市進入到城鎮化成熟階段,城鎮化進程放慢[8],與衛生資源配置趨向失調,導致耦合協調度增長速度的大幅下降。
2016年,《“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健康中國建設;黨的二十大將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戰略位置,作出促進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布局等重大部署。“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 “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在該階段,江蘇省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工業化水平良好,產業體系完善,資源要素加速流通,城鄉衛生資源配置水平改善,促使整體協調度穩定增長,但資源配置水平略低于城鎮化發展水平。這可能是因為衛生資源供給的限制因素較多,缺乏動態調整機制,導致配置水平的提升速度緩慢[2]。
3.2 新型城鎮化水平與衛生費用及人員投入密切相關
灰色關聯分析結果顯示,江蘇省新型城鎮化水平與衛生總費用關聯度最高。近30年,城鎮化的發展是衛生費用占比提高影響最大的因素[9],但是在城鎮化較低的地區,城鎮化水平對衛生總費用的影響不顯著[10]。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重要地區,江蘇省經濟發展水平高,城鎮化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11],人口向城鎮轉移,農村居民被抑制的衛生服務需求一定程度上得以滿足,促使衛生支出增加,衛生總費用也隨之增長。同時,研究還發現新型城鎮化水平與衛生技術人員數和床位數的高度相關,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城鎮人口增多,對醫療衛生服務需求也隨之增加,城鎮衛生資源供給壓力加劇[12],醫療機構需不斷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增加床位數量,引進高質量衛生人才,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就醫需求。王巍[13]等人發現,城鎮化的發展擴大了城市醫療衛生服務規模,增加了床位和醫護人員的數量,與本研究結果一致。此外,有學者證實[14],城鎮化發展與醫療衛生資源配置間的雙向正相關關系,即城鎮化水平有利于提高衛生總費用、擴大衛生人員數量和床位規模,相應地,衛生資源配置水平的改善能促進城鎮化發展,兩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3.3 衛生資源配置合理性離不開經濟發展
衛生資源配置灰色關聯分析的一個結果是其與外商投資總額、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宏觀經濟質量指標有較高關聯。經濟發展是衛生事業發展的基礎和保障,為醫療資源供給提升承載空間,對醫療資源配置的促進與完善起積極作用[15]。一方面,經濟發展為醫療衛生體系的建立健全提供資金保證,通過加大衛生投入來保障醫療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利用率;另一方面,人均GDP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能有效促進衛生服務利用效率的提升,提高衛生資源可及性,刺激衛生服務需求的增長,從而對衛生資源配置的結構產生影響。另一個結果是醫療保障水平與衛生資源配置的高度關聯。作為新型城鎮化的公共服務質量指標,醫療保障是減輕群眾就醫經濟負擔,增進民生福祉,維護社會和諧的重要制度。衛生資源的均衡配置,有利于提升衛生服務可及性,能充分發揮醫療保障制度的優勢,縮小城鄉居民間的健康不平等[16]。以往研究發現[15],醫療保險覆蓋率與醫療機構數和衛生人員數存在正相關關系,說明合理設置衛生機構數和衛生人才隊伍對保障居民醫療需求至關重要。
4 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及新型城鎮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基于耦合協調度模型及灰色關聯分析,對兩者間的協調發展和關聯度進行探究。研究發現:①兩者耦合協調度呈現快速增長、波動增長和基本穩定增長的階段性特征;②新型城鎮化水平與衛生總費用及衛生人員、床位數密切相關;③衛生資源配置水平與外商投資總額、人均GDP等宏觀經濟質量指標,以及醫療保障水平高度關聯。未來城鎮化與衛生資源配置協調發展的趨勢是調整衛生支出及資源投入結構,促進城鎮化高質量發展。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議:
4.1 推動“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持續推動,如何提高居民的服務可及性、提升其健康素質成為當前健康中國發展的重要難題。城鎮化的核心是人口市民化,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是當前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一方面,推動戶籍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保障城鄉二元結構下流動人口能平等地享受醫療服務等社會保障,真正落實“以人為本”。另一方面,要關注地區間人口的流動情況,依據人口變化來合理地配置醫療資源,提高公共衛生服務供給能力。
4.2 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提高衛生資源利用效率
此次研究發現,江蘇省衛生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綜合水平落后于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速度,因此,提高衛生資源配置效率,促進配置合理化是當前的重要任務。第一,要加強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十四五”規劃提出,要提升醫護人員培養質量與規模,擴大兒科、全科等短缺醫師規模。衛生人才在衛生事業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城鎮化進程下日益增長的高質量的衛生保健服務需求,離不開衛生技術人員的科學配置,而合理的衛生技術人員配置有利于緩解看病難問題,能有效促進人口健康素質的提升。因此,可以建設衛生人才培養基地,強化基層人才隊伍基礎,同時落實薪酬保障機制,在工資待遇、職稱晉升等方面為醫療人才創造優質環境[17]。第二,提高衛生資源利用效率,提升醫療服務質量,應綜合考慮江蘇省各市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增加或減少資源投入,縮小不同城市間的衛生資源差距。此外,技術進步有利于衛生保健服務的發展和衛生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18],江蘇省需要重視技術發展,同時提升基層醫療機構服務能力,強化分級診療制度,促進衛生資源配置的合理化。
4.3 衛生資源配置應考慮經濟發展狀況
此次研究發現,衛生資源的配置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江蘇省經濟在國內處于較高水平。通常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醫療保障水平的提升,居民在醫療衛生服務方面花費的費用會逐漸降低,在精神層面的投入便會增加,此外,隨著財政分權制度的落實,不同地區的醫療服務水平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直接影響。因此,政府需要提高衛生支出比例,以保障居民的生活質量;同時,要充分發揮經濟對衛生資源配置的輻射作用[19],依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按需調整優化衛生資源配置結構和布局,促進衛生人、財、物的合理分配,促使衛生資源配置要素與經濟發展狀況相協調,從而提高衛生資源配置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