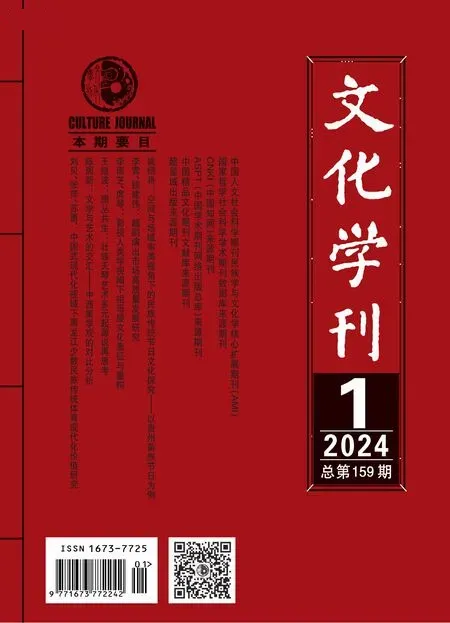大運河流經下的蘇州城市空間發展變遷
袁瓊嵐
一、漕運的歷史痕跡
江南運河段河道寬闊,周邊物產豐富,沿運河城市借運河航運之勢形成了一些中心城市,蘇州便是當時江南運河沿線著名的中心城市。大運河在明清時期,漕運作為國之大事,是大運河航運的優先事項。漕運興盛時期,南北經濟文化交流通過運河流淌不息,蘇州作為運河沿線城市亦得益于這種頻繁的商貿往來。
蘇州在明清漕運興盛時期商貿頻繁,手工業發展迅速。隨著漕運的深入,大量外地人口遷入,區域內文化融合加速。所有種種,在蘇州一段時間內的城市發展上有所映射,考察今天蘇州運河沿線建筑樣式、功用、分布情況,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現漕運時期這股時代洪流對沿線城市的裹挾。
漕運依托河道進行,在明清漕運興盛時期,漕運經過蘇州的河道主要有城內的環城河及城外山塘河、上塘河,外加南郊南下吳江的運河河道。貨物整頓集中在城市內進行,故考察漕運興盛時期對蘇州城市發展影響宜集中在古城內及山塘河、上塘河周邊進行。與城市發展同時進行的是周邊鄉鎮的繁盛發展,由于大運河對蘇州沿運河市鎮發展的影響較大,受篇幅所限,城郊鄉鎮將不作重點關照。
蘇州漕運興盛時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主持的水政措施,主要包括對河道的疏浚維護等,吳江塘路是江南低濕地帶的杰出水利工程體系,包含的寶帶橋、吳江古纖道作為水工設施均得到多次修筑,使用狀況良好,運河沿途的溇港圩田在漕運時期得到定期的疏浚治理。明清時期,蘇州將城內河道疏浚作為治水重點,據載,明代中后期至清中期,蘇州城內河道疏浚沒有間斷,甚至康乾年間平均七年左右便會有政府組織的疏浚行為(1)王衛平.《明清時期江南城市史研究》.。蘇州古城河道儼然,三橫四直結構的干河系統至今仍在發揮著重要的調節水位等作用,以永豐倉船埠等現存的文保單位,代表了漕運功能完備時期的城內河道形態建制。
倉儲設施是蘇州城內遺留下來直接關乎漕運的構筑物,在漕運運行時期,各地興建糧倉儲存糧食,大多官倉都建在河道周邊,方便運輸。蘇州當時的官倉主要分布在平江路及城南府衙周邊,兩地靠近環城河。平江路官倉集聚地靠近婁門,當時婁門外大運河水面寬闊,城東一片淺塘,明代楊循古《吳邑志》載,“今觀水之流派,常自閶盤二門入,即西南、西北水也,由葑婁齊三門出”。婁門為水流東流之口,水流可達東海,經蘇郡之婁門,至太倉之劉河,出天妃閘以入海,是為婁江。大批量的漕糧可由婁門進行河運或海運分發。平江歷史文化街區現存豐備義倉舊址是保存較好的清代官倉建筑,是舊時蘇州倉儲設施的代表。
二、商業與市民生活
蘇州城市建設在明清時期得到了迅速發展,其原因之一便是作為中心城市獲益于漕運的興盛,漕運產生了運輸中各階層夾帶私貨現象、漕糧部分貨幣化、人口遷徙、商貿往來等直接或間接現象,猶如幾股合力指向城市的發展布局。
明代漕運時期的蘇州商業發展尤以閶門為盛,明人在各類筆記中有很多記載。“嘗出閶市,見錯繡連云,肩摩轂擊,楓江之舳艫銜尾,南濠之貨物如山,則謂此亦江南一都會也。”(2)[明]王心一.崇禎《吳縣志》序.清代畫家徐揚以寫實的筆法在《姑蘇繁華圖》中展現了這個地區的商業活力。當時大運河河道上塘河、山塘河與環城河在閶門匯聚,這一帶商貿形態多樣,南北貨物齊聚,經濟富庶,成為江南最繁華的商業中心。伴隨大運河而來的不僅有漕運的船只,南北民間商貿也依賴這條大動脈進行運輸,且蘇州本身物產豐厚,手工業發達,成為大運河上沿線商貿中心之一。明代開始,蘇州成為各地商業聚集之所,商品種類多,輻射地域廣。“閶門為蘇孔道,上津橋去城一里許,閩粵徽商雜處,戶口繁庶,市廛櫛比,尺寸之地值幾十金。”(3)李果.《讓道記》.
明清時期蘇州工商業發展迅速,并推動了城市化進程的發展,導致行業聚集與手工業細化,諸如以蘇州絲綢、棉布行業,形成印染、生絲加工、成布等產業鏈細分行業,且生產地域開始向某一地聚集。“織作在東城,比戶習織,專其業者不啻萬家”(4)乾隆.《長洲縣志》.,“蘇布名稱四方,習是業者,閶門外上下塘居多”(5)乾隆.《元和縣志》.。清代乾隆年間,絲綢業主要集中在城東,而棉布印染業則集中到了閶門外的上、下塘一帶,形成了完整的絲織布匹加工產業區。而另外一些地區,則憑借著運河地理優勢,成為某一貨物的大型集散地,如楓橋米市:“為水陸孔道,販貿所集,有豆米市,設有千總駐防。”“為儲積販貿之所會歸”(6)康熙.《長洲縣志》.,行業公會在這些生產聚集區域大量產生。各地商人在蘇州的商貿活動除了將蘇州物產販賣至全國市場外,也將各地的特產在蘇州這個市場進行銷售,故紛紛在蘇州新建會館商會,交流信息,互通有無,“閶門一帶,堪稱客幫林立”,蘇州最早的會館嶺南會館就位于閶門外山塘街。目前蘇州的會館建筑遺存大體沿運河河道分布,是明清時期商業經濟發展的見證。
大運河在明清時期留在蘇州的印跡還在于疏通便利的河道交通后,憑借經濟的繁榮改變了市民的生活方式,這其中以現山塘歷史文化街區最為典型,它是清代完整商業居住社區的范例[1]。山塘街區依傍山塘河而形成,從閶門直至虎丘,兩岸房屋緊湊,商業形態完整,清代中期已經成為蘇州府城外著名商業街區。《嶺南會館廣業堂碑記》記載:“姑蘇江左名區也,聲名文物,為國朝所推,而閶門外商賈鱗集,貨貝輻輳,襟帶于山塘間,久成都會。”繁華的盛景包含完整的商業設施:會館、店鋪、公會,修筑了普濟橋等道路交通公用設施,富裕的家族在此地定居,并修建義莊、祠堂等宗族社會活動場所,而山塘等地的道觀廟宇群與虎丘山一起構成了蘇州城外的社會休閑場所。
從宋元至明清,蘇州的宗教建筑分布北半城一直多于南半城,且受經濟政治影響,多分布于市井生活氣息濃厚之地,城區及周邊宗教建筑在明清時期主要以佛道及民間祭祀三種為主[2]。宗教生活中的集會活動隨著世俗生活的影響,在宗教儀式、集會之余產生了士女游園性質的活動,吳地民眾經常在宗教活動中由娛神旁斜橫逸出娛人、甚至自娛精神來,豐富市民生活。《清嘉錄》嘗載吳地有很多道教、佛教節日盛典,士女出游者眾,“十九日,為觀音誕辰,士女駢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長明燈油,以保安康”。而這些廟宇宮觀所在地,每逢宗教節日儼然成為當下熱門出游場所,“觀音誕日,有至支硎山朝拜者,望前后已聊綴于途,馬鋪橋迤西,乃到山路也”。謹以山塘地區為例,山塘地區本身在吸納五湖四海的外來民眾后,習俗紛雜,有眾多民間活動,燈會,花市,廟會不斷。“吳郡無祀厲壇在虎丘山前,附郭三邑統祭于此。清明賽會最盛,十鄉城內外土谷神咸集,游人群聚山塘,名三節會,謂清明、中元、十月朔三節也。”(7)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山塘有寬闊的河道水域,交通便利,商業氛圍濃厚,地處城外郭野,野趣盎然,且靠近虎丘這個明清時期著名的士女郊游場所,成為獨特的市民游樂文化高地。明代虎丘游觀已成規模,是士大夫階層與普通民眾同樂場所:“至今吳中士夫畫舡游泛,攜妓登山。而虎丘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臺閣數重,增益勝眺。自是四時游客無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8)張紫琳.《紅蘭逸乘》卷 2《古跡》.虎丘山自宋后景點沒有大變,既是宗教文化場地又人文遺跡眾多,明清時期在這里舉行的文化雅集不勝枚舉,與周邊的宗教建筑一起形成山塘宗教游樂場所中心。山塘歷史文化街區周邊現存的宗教建筑以沿河寺廟、宮觀及虎丘山宗教建筑群共同構筑而成,在探究其宗教本源之外,明清時期蘇州地區市民階層的興起,由此帶來的游樂文化對宗教集會的影響不應忽視[3]。
三、西風東來的大運河軌跡
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西方的人、事、物涌入蘇州,蘇州出現一批迥異于中國傳統建筑的西方樣式建筑。這類西方建筑在《南京條約》后,在蘇州城內大量建成,它們中既有租界區域的住宅建筑,也有西式教會,學校、醫院、工廠等公共活動場所,這些平常生活場景中的建筑代表了一個時代的來臨。大運河作為一條貫通南北的主航道,在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前期在江南段仍發揮著重要的航運作用[4]。在西方觀念及事物的涌入途徑中,仍在通航的大運河是不可忽視的交通通道。
蘇州靠近上海這個早期通商口岸,《馬關條約》后成為幾個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事物進入蘇州時部分直接循運河而來,留雪泥鴻爪在運河兩岸。日本租界及關稅務司等代表外國侵略勢力的建筑遺存就在大運河兩岸,它們的選址體現了帝國主義對蘇州經濟社會文化企圖控制之心,日本租界選址的最初設想如下:“先索城內元妙觀、城外閶門南濠繁盛之處,繼索胥門外壇廟最多地方,后始議定盤門外相王廟迤東空曠地畝作為通商場。”(9)《咨送蘇州日本租界章程》,1897年4月23日.除玄妙觀為蘇州城內繁華地外,其余幾處均為大運河交通便利之地,且有賴運河的航運作用,這幾處經濟也較為繁華。大運河的便利,一直就是日本設立租界的首選,日本曾為是否將蘇州沿運河十丈地納入租界范圍和清政府僵持不下,曾在內部文件有此記錄:“該地區對我租界占據最樞要之處,碼頭建立、船舶停泊、貨物上下等都須仰賴這個地區,能否管轄,對于將來租界各方面經營有最關痛癢得失之感。”(10)《外務大臣大隈重信致駐上海總領事珍田舍已》,1896年11月16日.同一時期,英國殖民者興建的蘇州關署也是出于類似的考量,把控制蘇州進出口的關稅務司公署設立在大運河環城河南,是為了擁有更好的交通區位優勢,以便更好地控制蘇州,攝取中國國民經濟成果。蘇州洋關對進出蘇州口岸的輪船貨運及應稅貨物辦理報關、查驗、征稅、放行、查私等海關業務,在1909年滬寧線鐵路全線通車之前,火車貨運還沒有普及的年代里,大運河仍是蘇州關的主要來往通道,蘇州關與上海、寧波、杭州、鎮江等其他進出口關的聯系通道也依托大運河為通道。現在蘇州大運河兩岸分布的這類在西方政府主導下建設的公用建筑保存良好,他們見證了大運河在漕運之后被帝國主義攝取用來侵略中國的屈辱歷史[5]。
進入20世紀后,蘇州的近現代建筑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帶有西方特色的普通民居與工業廠房是這個時期新增的特色,是先賢們接受西方文化后主動擁抱世界探索民族未來的體現。帶有西方近現代特色的民居主要由當時社會上層達官貴人、富商及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興建,他們較早接觸了西方便捷的生活設施,在房屋營造方面趨向選擇適合這種生活方式的西方樣式,這類近現代民居大批分散在蘇州城內外。工業廠房的選址較之民居有更多考量,大運河承擔大宗貨物運輸的功能,是近代很多民族企業家選擇在通航河道旁興建工廠的原因之一,蘇州的大運河河道旁留下了一批近現代民族工業的遺存。
從19世紀中期開始,閶門淤積嚴重,大型船只進城困難,因此,商船選擇從寒山寺附近南下,于橫塘驛站附近用原胥溪河道作為大運河蘇州段主航道,直至20世紀80年代,這條胥江一直是大運河進入蘇州的主要航道,見證了大運河作為傳播現代思想、實現實業自救渠道的時代通道。政府主辦的蘇經絲廠、蘇綸紗廠,兩廠同時在1895年籌建,選址在盤門外青旸地附近吳門橋東首,當時尚為荒地,地價合理,貨運成本較低。蘇州胥門附近至覓渡橋這段河道周邊在20世紀上半葉工廠分布密集,主要原因包含了:大運河沿岸地勢平緩開闊可作碼頭使用,蘇州大運河河道聯通各鄉村,通過船運可深入村鎮腹地獲取生產原料,水路運輸連接的上海、寧波等都市則提供了廣闊的銷售市場,且離海關較近報關方便[6]。太和面粉廠、鴻生火柴廠等民營企業在這里生產產品并銷往全國,如鴻生火柴廠創始人劉鴻生對于在這片區域內建造廠房很是滿意,在1920年致蘇州總商會的函件中,曾有“該地四面空曠,距離胥門和盤門市厘各在數里之外,水陸交通便利,絕無障礙之慮”等語。蘇州民族工業在大運河沿岸蹣跚起步。
四、結語
綜上所述,大運河流經下的蘇州城市空間變遷,主要涉及漕運的歷史痕跡,同時涉及商業和市民生活,展現出蘇州城市建設在清明時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原因,并且提及19世紀中后期西方的人、事、物等涌入蘇州,蘇州出現了西方樣式的建筑,最后分析蘇州民族工業在大運河沿岸起步的情況,為蘇州大運河的歷史分析和未來發展等夯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