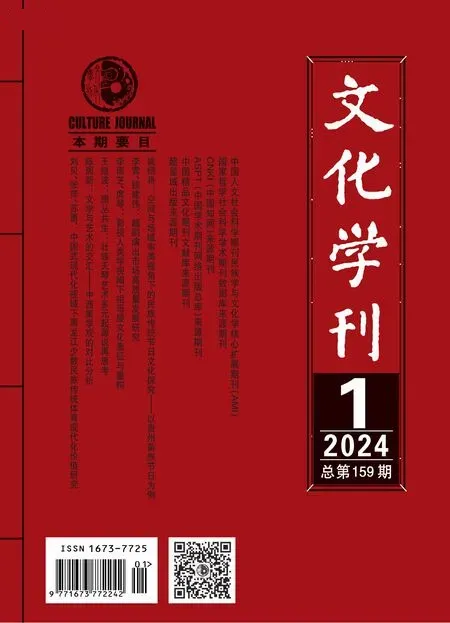生態人類學視角下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創作研究
周 芫 陳振桂
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創作通過描述人與自然的關系,深刻揭示當前存在的生態問題,反對人類對自然的肆意掠奪和干涉,提出用生態學視野變革人類文化,致力于建構生態與文化的關系。在廣西兒童文學的語境下,突出利用童真、童趣和童味來表達生態人類學的人文價值論,強調呼喚人性美好、終極關懷以及人與自然的共生共榮,為深入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提供廣西生態智慧、生態方案和生態力量。
一、生態人類學視角下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創作現狀
在生態人類學的觀照下,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創作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矚目景象,集中表現在神話傳說、英雄史詩、歌謠、民間故事、寓言、童話、小說等方面,為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創作注入鮮活的血液。一批批“兒童文學桂軍”筆耕不輟,辛勤耕耘,其中有韋其麟的詩歌《尋找太陽的母親》,通過在民族文化的發掘中尋回人類失落的世界,構筑奇特的民族生態意境;有黃鉦的小說《猴師》,通過描述祖孫倆公萌和阿萌費勁心思地捕猴到心甘情愿地放猴經歷,展示人類與環境共存的智慧和經驗;有陳麗虹的童話《花瓣上的海》,通過插上想象的翅膀,張揚生態環保的理念,激發兒童的環境保護意識;有朱德華的童話《一年四季花》,通過創造一個叫花兒村的童話世界,從花花草草著眼,體現生物物種多樣并存的生態價值,引導兒童理解自然、感悟自然和崇尚自然……秉承著廣西生態優勢金不換的理念,廣西兒童文學作家深深眷念著家鄉的山山水水,自覺地投身于生態創作的熱潮中,他們用心靈與自然萬物對話,為廣西生態文明的文化自覺樹立旗幟,為生態人類學的發展引領綠色生活方式,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提供一種新的美學追求。
二、生態人類學視角下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創作特點
(一)以鄉土經驗為主的生態創作
王勇英以自己的家鄉——廣西玉林市博白縣東平鎮大車村為背景,創作了“弄泥童年”系列叢書,通過講述一件件帶有鄉土氣息的生活故事,向兒童展示一幅呈現廣西生態和諧發展的鄉村畫卷。她的文字令人陶醉在一種溫暖又質樸的感覺,字里行間流露出廣西鄉村特有的大自然味道,打破過去流行的熱鬧型兒童文學框架,為都市化、世俗化的現代世界帶來一種樸素、深厚、令人神往的鄉土元素,通過傳遞生態道德和人文關懷的力量,體現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意識和家園意識。
就像王勇英所說:“鄉村是給予我豐富創作靈感和蓬勃生命力的自然天地。寫與鄉村山野有關的故事,心情愉悅,舒展,是一種享受。我出生在廣西博白縣一個叫大車的山村,客家人。童年生活中所有經歷過的,對我的創作影響都很大[1]。”“弄泥的童年風景”系列小說就是通過以鄉村兒童的口吻來敘述,挖掘帶有地方性審美經驗的特征,講述土味又充滿童稚的個體經驗世界,重構作為心靈棲息的鄉土家園。透過生態人類學的審視,王勇英致力于廣西兒童文學鄉土經驗的尋根創作,獨樹一幟地為本土兒童開辟一條還鄉之路,給予鄉村生態創作活力,實現鄉村生態追尋價值。
(二)以動物題材為主的生態創作
楊映川的兒童文學作品《千山鳥飛》呈現出山中居民的生命體驗,再現桂北地區人民的生活情態,為主人公包森林提供自我成長的生態環境。通過展示他與大風洞、天堂灘的生態對話,描述他能模仿50多種鳥叫的聲音,吹出動人的口哨曲《百鳥鳴》,塑造出一個具有當地生態智慧和技能的少年形象。面對工業化、商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包森林能夠不盲目遵從成人與自然世界的從屬規則,不遭受物質主義對于家鄉的傷害和侵蝕,堅持用赤子之心去關注當下生活,主動維持銀蘭村自然生態系統的穩定發展,進而還原兒童生命的本真,激發兒童生存的動力,實現兒童與自然的良性互動。
隨著現代生態災變的問題激化,人們的生態意識逐漸覺醒,正如《千山鳥飛》中所呼吁:“這里的山是我們的,鳥是我們的,你們來這里打鳥,打爛你們的燈活該!如果再敢傷人,你們怎么對付鳥,我們就怎么對付你們[2]!”顯然,過去以“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已被淘汰,生態人類學認為采用不適當的方法去利用自然生態系統,必然造成生態系統的改性,主張以資源利用和管理模式的多樣化去緩解人為生態災變,引導人類學會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促使人類能夠不斷反思人性,叩問人性,善待自然和他人。
(三)以民族文化為主的生態創作
廣西兒童文學圍繞少數民族價值觀的生態創作不勝枚舉,這些作品引發出有關非遺文化的傳承、生態環境的惡化以及民族矛盾的沖突等問題,令廣西兒童文學在民族文化和生命經驗的先在性交織下,獲得文化間性的雙向認可。
王勇英的兒童文學作品《花石木鳥》《木鼓花瑤》《青碟》《少年陀螺王》《半河小魚》《烏衣》等,以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域的視角來體察廣西少數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其中有圍繞苗族百羽千花衣的制作;有瑤族的踩高蹺和吹蘆笙等民間趣味游戲;有磨刀匠、桶箍匠、補碗匠等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有南丹白褲瑤人與陀螺的多維文化互動;有侗族的油茶和南瓜節風俗;有壯族的黑麻布衣盛行等,其作品集繼承性、民族性、多元性于一體,流露出明顯的文化間性意識,旨在引領讀者走進廣西少數民族的生活情境,在各民族的互動交流中達成認同,形成互補,實現文化的互為主體性。
楊映川的兒童文學作品《少年師傅》突出描寫侗族風雨橋的構建和修補過程,風雨橋是侗族文化的象征符號之一,寄托著侗族人“天人合一”的生態文明思想,這一鮮明的建筑意象包含侗族傳統文化、族群生活場域、民族歸屬認同等多種元素,作品善于構建廣西侗鄉木匠的生態圈,很好地開拓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點,在群體中實現生態人類學的主體訴求,在時空上完成生態體驗的審美擴張。由此可見,生態價值已經成為民族文化與自然傳統的交融產物,成為廣西兒童文學創作的初心與使命。
三、生態人類學視角下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創作意義
(一)構筑生態話語體系
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話語呈現出濃厚的生態民族味、鄉土味和童趣味,通過兒童文學的文本挖掘出代表廣西地域文化的特殊符號和元素,以獨特的俗語和俚語呈現生態人類學的內涵,從而構筑具有廣西兒童文學風味的生態話語體系。
在王勇英的生態創作筆下,《花石木鳥》勾勒出一個具有苗寨風土人情的世界,文本善用短小的方言語句描繪人名,如,嘎咕、嘎鬧、阿烏、衣花、花娘等。同時,她還將苗族歌謠嫻熟運用到語言敘述中,如,“黑麻線,粗麻線,你像你生長的泥土,你是風干后的枯草,阿努喲,阿努喲,你別沉睡,要快醒來,過不了多久,你就會發現,你是多么漂亮的衣裳[3]……”。《半河小魚》詳細描述體現侗族特色的語言系統,如,“三江縣是侗鄉,白草山中的居民全是侗族,我們住在青禾村,以后也要學侗話。糧食“百萬”,那是早先古越語中早期粳米稻其中一個品種的名稱,后來侗語對糧食通稱就叫百萬。侗話中的稻谷叫“華”,田野叫“版那”,說起來也有點兒像漢話中的‘飯’[4]。”《巴澎的城》將客家方言演繹得惟妙惟肖,如,“落水拐是一種米粑的名字,客家話,本義是跳水的青蛙。于是,弄泥的腦海里立即聯想到一大堆青蛙紛紛跳入塘水的景象[5]。”又如,“大車話用‘蛇’來做尾音是對自己家里最小的孩子的昵稱。這一聲尾音如果是一種愉悅向上挑起的聲調,那么傳達出的是一種愛;如果是一種重重下沉的短促的聲調,那么傳達出來的就是一種責備[5]。”
王勇英將帶有本土特色的童年經驗融入到生態話語中,展現出語言美學維度中的民族特色、鄉土氣息和兒童情趣。在語言和構詞的組織上以歷史地域為背景,將廣西少數民族的生存境遇和傳統文化聯系起來,并以生態人類學的角度進行深層性、遺留性、邊緣性的雙向對話,為兒童留下巨大的語言想象空間,引導他們體會生態創作的人文感召力。王勇英的語言敘述形式與兒童的審美接受能力高度契合,能夠創造出屬于兒童本真的自然、自在和自由的生態話語體系,她還將抽象化的意象以形象化的語言呈現出來,讓兒童獲得一種帶有真實性、具象性和視聽性的地方話語體驗,極度渲染出一種帶有人看自然,人看人特征的廣西生態話語色彩。
(二)助力生態文學發展
生態文學是描述人與自然的關系文學,是揭示生態問題的文學,也是面對問題試圖擺脫危機、探尋生態之路的文學形態。在廣西兒童文學的哺育下,自然成為真正的他者,映射出生態人類學的生態良心和生態正義,體現生態文學的生態責任、文化批判、生態理想、生態預警和生態審美內涵。
王勇英的《霧里青花泥》是中國原創兒童生態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生態文學的主旨在作品中得到沉淀和舒張。作品通過現代文明與神話傳說的有機融合、生態審美的詩性表達、文化觀念的童話演繹,真摯地講述霧里村關于青巾老媽、青麥子和青花泥的感人故事,展示出一個愛與被愛、守護與被守護的生態鏈,體現萬物平等、生命神圣、生態和諧的完美境界。王勇英能夠縱情謳歌生態文學之美,以生態審美為廣西兒童文學的創作主旋律,形成獨具一格的生態文學創作特色。同時,通過對生態危機及其社會根源的觀察與研究,用文學的形式表達對人類命運深刻的憂患意識,從而引領兒童走進自然、熱愛自然,激發兒童的生態感知力和想象力,具有現實的生態創作意義。
廣西兒童文學是生態敘事的重要途徑,是生態文學的創作源泉,是生態人類學的知識載體。在本土作家的關注下,兒童文學通過滲透對生態的獨特思考與理解,主張將人性、生命哲理、藝術創造力融于作品之中,進一步強化兒童的生態主體意識形成,引發兒童對野生動物的生存和自然界生態平衡的深刻關注,凸顯廣西生態兒童文學的地域性、審美性、開放性和批判性。
(三)打造生態文化圈
隨著人類社會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廣西兒童文學作家以自己特有的生活經歷,以廣西少數民族文化為生態創作背景,充分展現了廣西少數民族的民情風俗,講述具有獨特民族氣息的兒童成長故事,彰顯出廣西生態文化的美學意蘊,力圖打造代表廣西兒童文學特點的生態文化圈。
在王勇英的生態創作中,《花石木鳥》通過敘述瑤族傳統服飾制作的過程,刻畫苗家的織、繡、挑、染的傳統技藝,表達苗族女性對于自然的認知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體現廣西生態文化中的苗繡文化。《少年陀螺王》通過生動描述白褲瑤人熱愛打陀螺的民俗習慣,傳達南丹人要像陀螺一樣具有自由、陽光、快樂、勇敢的人生態度,展現廣西生態文化中的陀螺文化。《半河小魚》通過細致描寫侗族的三江大糯“清香、油亮、軟、可口”的特色,呈現侗族種植水稻的過程,抒發侗族人民熱愛勞作和農耕的感情,表現廣西生態文化中的稻作文化。同時,通過說明三江侗族風雨橋的特點,發掘侗族傳統文化的地標價值,突顯廣西生態文化中的建筑文化。《巴澎的城》通過介紹艾藥治病的經驗,具體描述客家人如何用艾草燒炙穴位來治病,顯示廣西生態文化中的醫藥文化。《烏衣》通過全面展示壯族“三月三”的唱歌、對歌、賞歌風俗,記錄壯族人民擅長打扁擔、吹芒筒、唱山歌的精彩畫面,顯現廣西生態文化中的歌圩文化……無論是在民族服飾、民族體育、民族飲食,還是在民族建筑、民族醫藥、民族音樂等方面,王勇英致力于研究廣西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不斷關注族群之間建立的情感和心理聯系,專注于尋找地區與民族文化的認同模式,引導人們重視多物種的生態倫理與關聯價值,賦予廣西兒童文學在生態文化演進中的善待和關懷意義。
從“非我中心”的相對文化觀出發,人類應該樹立正確的自我角色意識,走出狹隘的人類中心地位,深化“周審天地、關懷萬物”的思想觀念,處理好人類與自然的內在統一關系,進一步強化生態人類學的“多物種民族志”理念,致力于營造廣西生態文化共同體,實現生態與文化的共興共通。
四、結語
廣西兒童文學以強烈的族群意識和歷史責任感,自覺肩負起發展生態創作的重任,通過對八桂大地的山水風光和人文歷史進行考察和體驗,對其自然生態及精神生態進行真實性寫照,從而在自然保護和社會發展的道路上尋找生態人類學的平衡點和契合點,在生態和人類出現的危機中追求詩意的、無遮蔽的生存和棲息,在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生態文化碰撞下獲得主體表達的自由。
面對新時期的廣西兒童文學巨變,眾多作家都不約而同地盡情抒寫和歌頌廣西兒童文學的生態之美、語言之美、民族之美和文化之美,令本土兒童文學的生態創作散發出一種獨具南國風情的迷人姿態。以生態人類學的視角來超越主體與客體、自然與文化,主張建立基于和諧共處的生態倫理關系,并用生態中心主義實現人類的文學觀和價值觀,這是廣西兒童文學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生態創作的永恒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