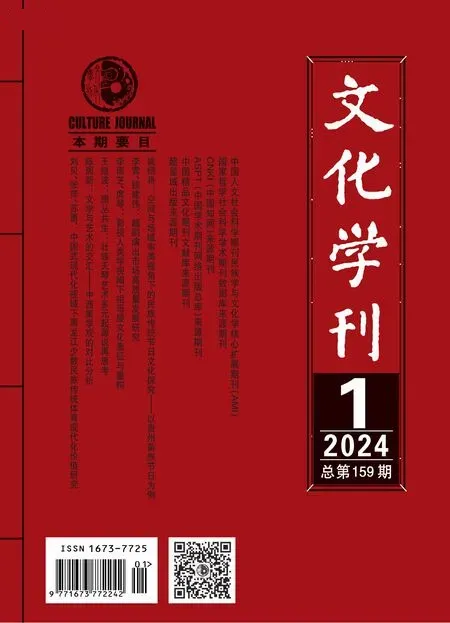論遺傳資源數據的法律保護
黎 梓
引言
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1],在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關于遺傳資源數據的利用和保護等相關研究與應用也愈發得到重視。在科技創新越來越依賴于科學數據綜合分析的情況下[2],醫療系統的專家、學者可以通過由遺傳資源數據組成的各類數據庫進行生物基因、病理等分析,使得相關疾病可以通過數據的形式實現可視化,這在藥物研究、疾病防控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但遺傳資源數據較一般的數據信息更具有主權性、隱私性和倫理性。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以下簡稱《生物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以下簡稱《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相繼出臺實施,為遺傳資源數據安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護,但整體上仍比較乏力。因此,對遺傳資源數據的采集、保藏、利用、對外提供等進行法律規制,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善的遺傳資源數據法律保護制度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
一、遺傳資源數據的基本法律問題分析
(一)遺傳資源數據的界定
關于遺傳資源的法律界定,《生物多樣性公約》認為是指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遺傳材料,而遺傳材料是來源于動植物等任何含有遺傳功能單位的材料。我國早在1998年《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中就對人類遺傳資源概念進行了界定,將人類遺傳資源分為了遺傳材料和遺傳信息資料兩大部分。2006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以下簡稱《畜牧法》)對畜禽遺傳資源進行了界定,著重點仍是胚胎等遺傳材料。2010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專利法實施細則》)對遺傳資源的界定跨越了人體、動植物等類別,強調是含有遺傳功能并且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材料。2017年,生態環境部起草了《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管理條例(草案)》,認為遺傳資源是具有遺傳功能的材料、衍生物及其產生的信息資料。而《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生物安全法》在人類遺傳資源的界定上沿用了同一定義,人類遺傳資源的法律概念達成了一致,仍分為遺傳資源材料和遺傳資源信息兩大類。
數據的本質是信息的載體[3],遺傳資源數據承載著遺傳資源信息。《生物安全法》《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突破了《生物多樣性公約》對遺傳資源的界定,將非實體形式的遺傳資源數據等信息材料認定為了遺傳資源,實際上也是確立了遺傳資源數據的法律地位。人類遺傳資源數據就是利用人類遺傳資源材料產生的數據,但對于人類遺傳資源材料的衍生物所產生的數據是否屬于人類遺傳資源數據等問題存在留白,而《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管理條例(草案)》則將衍生物所產生的數據歸入遺傳資源信息材料當中。為了更加全面地界定遺傳資源數據,筆者認為遺傳資源數據同樣有三個方面的內涵:一是直接來源于遺傳資源材料,二是來源于遺傳資源材料衍生物,三是來源于遺傳資源及其衍生物產生的遺傳資源數據。綜上,筆者認為遺傳資源數據應界定為:利用來自人體、微生物或其他具備遺傳功能的遺傳資源材料及其衍生物所產生的數據以及利用該數據所產生的二次遺傳資源數據。
(二)遺傳資源數據的特征
遺傳資源數據的來源具有多樣性,在原始遺傳資源數據產生方式上既可以來自于人體,也可以來自其他動植物與微生物,以及在遺傳資源材料基礎上產生的衍生物遺傳資源數據和依據二者所產生的二次遺傳資源數據,這也造就了遺傳資源數據規模的龐大性。但遺傳資源數據本質上仍是一種擬制數據,其來源于實體的遺傳資源材料,通過采集、獲取遺傳資源材料中具有遺傳功能的物質成分進行分析記錄而擬制產生,因而具有無形性特征。
遺傳資源數據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具有雙重性,即具有私權性質與公權性質。當涉及人類遺傳資源數據時,其中必然包括了人體基因組等個人生物識別數據信息,其是個人隱私權、人格權的重要保護客體。雖然該類遺傳資源材料屬于私權所有,但因遺傳資源數據本身的重要性與特殊性,其關系著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全,遺傳資源數據勢必納入國家公權力的管轄范圍之內,遺傳資源數據也就具有了公權性質。
二、遺傳資源數據法律保護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一)遺傳資源數據保護受到新興技術的沖擊加劇
一方面,遺傳資源數據實質上是研究者通過技術手段將遺傳資源材料及其衍生物所包含的信息數據化、可視化。在大數據、人工智能時代,遺傳資源數據的實驗研究器材、技術手段等不斷地得到強化進步,使得遺傳資源數據的采集、利用工作更加高效,研究者從中獲取的遺傳資源數據也更為準確翔實,并依靠數據庫等技術組建起了我國各類遺傳資源數據庫,為遺傳資源數據的保藏和研究利用提供了技術支撐。同時,遺傳資源數據的法律保護不僅面臨著基因編輯等技術倫理風險,還面臨著日益頻繁猖獗的黑客等網絡攻擊,特別是在遺傳資源數據的主要存儲方式由原始的書面存儲演變為計算機存儲、云存儲等形式,對遺傳資源數據的法律保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遺傳資源數據的國家主權性與財產價值性特征加劇了目標的可攻擊性。某些國家企圖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他國遺傳資源數據進行研究分析,進而開展基因戰、生物入侵等新型戰爭;在利益的驅使下,商業公司也可能會雇傭黑客等通過非法技術手段獲取遺傳資源數據。這些主體為了達到最后的目的往往為技術入侵提供強大的物質保障,對遺傳資源數據的存儲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嚴重危及國家安全。
(二)遺傳資源數據權屬不明
遺傳資源數據的權屬問題是遺傳資源數據進行法律保護所不得不解決的首要問題,唯有明確遺傳資源數據的權屬,才能更好地貫徹落實權利義務相統一的基本法律原則,清晰定位數據管理的責任邊界[4]。享有遺傳資源數據權利主張的主體,主要為遺傳資源數據提供者、采集利用者和國家。遺傳資源數據提供者可以根據來源分類劃分為人體提供和其他生物提供,其他生物,例如植物、微生物等不可能對從其本體采集的遺傳資源數據進行權屬主張,而是由該生物的所有者主張,可能是個人、國家或其他組織。我國《生物安全法》規定國家對人類遺傳資源和生物資源享有主權,實際上明確了國家對我國的人類遺傳資源數據和生物遺傳資源數據擁有主權,但需要注意的是主權不等同于所有權,享有主權并不意味著對所有權的擁有。《專利法》對于利用遺傳資源進行發明創造的發明人授予專利權,專利權人對授權發明享有所有權。這說明了利用遺傳資源數據產生的產品,利用者可以對該遺傳資源數據產品享有所有權,但對于遺傳資源數據的權屬至今仍爭論不休。此外,遺傳資源涉及的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國家秘密等情況,在對遺傳資源數據的權屬進行探討時,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對這些因素進行考究,合理平衡各方權益。
(三)遺傳資源數據保護方式待完善
《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將遺傳資源數據納入了遺傳資源信息資料予以保護,自此認定了遺傳資源數據屬于遺傳資源信息材料的一種法律保護方式。但遺傳資源信息材料的法律保護研究尚處初級階段,針對遺傳資源數據的法律保護機制并未建立。欲要依托現有的個人信息、商業秘密、重要數據、國家秘密等法律保護方式,則需要進一步厘清遺傳資源數據與個人信息、商業秘密、重要數據、國家秘密等之間的關系。刑法上雖然設立了非法采集人類遺傳資源、走私人類遺傳資源材料罪,但根據對遺傳資源的法律概念闡釋,遺傳資源包括了遺傳資源材料和遺傳資源信息材料,片面理解刑法上的遺傳資源材料將導致該條文對遺傳資源數據走私行為無法追究。2018年,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以及科技部對遺傳資源出境的6起行政處罰的出現,也暴露出目前政府規制立法層級低等問題[5]。
三、遺傳資源數據法律保護制度的構建
(一)明確遺傳資源數據法律保護的權利義務主體
遺傳資源數據法律保護需要明確遺傳資源數據的權屬,這樣才能更好地劃分各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權屬不明極易發生“公地悲劇”與權力濫用等現象。在國家主權領域上,遺傳資源數據的權屬需要衡量好提供者、采集利用者、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當個人權益與國家權益發生沖突時,個人權益應當讓渡于國家權益,國家再通過其他途徑對個人權益進行適當合理的補償等考量。筆者認為,在我國的遺傳資源數據權屬問題上,雖然遺傳資源數據的提供者對于遺傳資源材料享有所有權,但該所有權是一種物權所有權,物權所有權的享有并不能延伸至遺傳資源材料上無形性的遺傳資源數據。遺傳資源數據雖然是附著在遺傳資源材料上的,但遺傳資源數據的采集、利用等需要極其專業的設備與知識,一般的個人難以從遺傳資源材料中提取出遺傳資源數據,遺傳資源數據的所有權應當歸屬于采集利用者,這樣才能激發科研人員從事遺傳資源數據的研究工作的積極性。但對于遺傳資源數據的提供者,即遺傳資源材料的所有者而言,理應尊重和保障其知情同意權、基因權[6]。依據遺傳資源數據來源的主體,遺傳資源材料所有權的主體大致可以分為國家、集體和個人。法律規定由國家、集體或個人享有所有權的遺傳資源材料,其遺傳資源數據的延伸權利則由相應的國家、集體或個人享有。且由于遺傳資源數據的特殊性,關系著國家安全,遺傳資源數據權利人在行使所有權時應當以符合國家利益為前提,合法行使所有權。依托一次遺傳資源數據產生的二次遺傳資源數據的所有權則歸屬于二次遺傳資源數據采集利用者所有,但一次遺傳資源數據提供者同時享有收益權等權利。在國家主權管轄范圍外的遺傳資源數據,任何國家和個人都沒有合法的理由主張該遺傳資源材料所有權,但為了保障非國家主權領域的遺傳資源數據的保護和合理利用,應當就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的目標達成共識制定軟法[7],由相關國際組織統一規劃。
(二)優化遺傳資源數據惠益分享機制
在遺傳資源數據的收益分享上,我們需要處理好遺傳資源數據提供者、采集利用者的關系,合理反饋各方的權益訴求,建立良性的收益分享機制。對他人所有的遺傳資源材料采集遺傳資源數據,要充分保障提供者的知情權和收益權等合法權益,屬于國家所有的還應當經過主管部門的同意批準,合乎法律規定的法定程序才能更加有效地激發所有權人對遺傳資源材料的保護。采集者一般情況下與利用者是統一主體,采集工作是遺傳資源數據得以利用的前提條件,是遺傳資源數據能夠脫離遺傳資源材料附著狀態的必經流程,采集者將采集到的遺傳資源數據移交數據利用者,對于通過數據利用而產生的收益,理應得到分享。遺傳資源數據利用是數據實現價值的重要一環,利用者是遺傳資源數據的直接利益獲得者,但該利益不能由利用者獨自占有,應當合理分配給遺傳資源數據的提供者和采集者。同時,對于非營利性的遺傳資源數據采集、利用,可以借鑒我國已經較為成熟的義務獻血、器官遺體自愿捐贈等公益模式,注重構建非貨幣利益形式的分享模式,淡化貨幣利益的直接反饋形式,推動遺傳資源數據利用更多地轉向公益。
(三)完善遺傳資源數據跨境流動監管機制
數據流動不可避免,我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規定了人類遺傳資源未經允許不得向境外提供,境外組織不得在我國境內進行遺傳資源的采集。我國對人類遺傳資源單行加以法律保護,主要是相較于其他生物,人類遺傳資源更加具有特殊性,關系著我國人民的生存安全,其流失更具危害性。但其他生物遺傳資源也同樣重要,特別是反擊生物入侵已成為我國常態化的國家安全工作。遺傳資源材料一般是有體物,跨境流動必須將該有體物在我國進出境,相較于遺傳資源數據,其更加容易被發現和截留。但遺傳資源數據可以存儲在各種具有存儲功能的工具之中,在攜帶進出境時難以檢查和發現。并且隨著現代網絡技術的發展,遺傳資源數據完全可以通過網絡向境外流動,更加難以發現。因而,遺傳資源數據跨境流動監管制度的完善顯得更加重要和急迫。
四、結語
遺傳資源數據涉及個人信息、重要數據、生物安全等領域,保護和利用遺傳資源數據是遺傳資源價值開發和保障國家生物安全的重要舉措。準確界定遺傳資源數據的概念是對其進行法律保護的前提,針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對遺傳資源數據法律保護帶來的機遇與風險挑戰,應當順應技術發展進行法律規制,厘清遺傳資源數據提供者、采集者、利用者和國家之間在遺傳資源數據權屬和利益分享的關系,制定合乎法理的遺傳資源數據法律監管和保護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