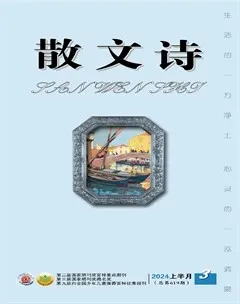小 區
◎吳曉錦
小區里的老人們
老人們南腔北調, 卻總是主動問候別人, 恨不得將小區里的陌生同齡人, 都變成牌友、 步友或舞友。
有的老人消失一段時間后, 再次出現。 有的老人卻再也沒有見到。 他們會在牌桌上像孩子般爭執, 會和二三新友躲在角落里, 小聲數落兒女。
他們送孫輩去學校, 買菜做家務, 午后的時光里才出來閑聊一下, 而后分別去菜市場, 到學校門口等著孫輩們放學。
華燈初上, 阿姨們準時加入各自的廣場舞陣營, 跳到汗濕衣衫, 才結伴而回。 有人余興未盡地停留在路邊, 交流某個舞姿的最佳跳法, 偶爾還起爭論。
有的阿姨還要到蔬菜店里排隊, 耐心等待晚間的大折價。
老頭們邀約著, 在小區綠道上一圈又一圈地邊走邊侃, 或者坐在花壇邊沿上, 看著阿姨們翩翩起舞。
于是, 我也珍惜起了自己的身體, 不再冷落書桌上的毛筆,我不想只做觀眾, 更想滿頭白發時, 像鄰居老人們一樣步履從容, 心境平和。
小區里的孩子們
小區里的孩子們, 雀躍于下午放學后的時段里。 他們你追我趕, 騎行在小區大小路上。 或盤腿坐在地上, 大聲地揮甩紙牌,或鉆進角落里捉迷藏。 也不時傳出爭吵聲和哭聲, 有的稚氣揩著淚花, 沖著某個小友, 模仿大人嚷“絕交”, 隔天卻又重歸于好。
他們的父母有的素不相識, 有的只是點頭之交, 因為孩子,他們成了朋友。
陽臺上, 作為觀眾的我, 常常回想起當年的陀螺、 雞公車和那修了又修的破舊自行車, 想起結伴去上學去趕集去放牛去砍柴去割草去喝酒去結識異性的兒時弟兄。
我原以為, 異鄉的孩子們只能孤獨地伴著父母、 老師和作業成長, 沒想到, 他們還能找到同伴來綻放童心。 我默默祝福他們。
獨木難成良材, 獨木難成森林, 珍惜有玩伴和能玩樂的時光,這才是人生最珍貴的板塊。
小區門口
只有三十來平方的小區門口, 每天的放學之際, 才是最熱鬧的時光。
帶娃的大人們坐在水泥凳上認識陌生的同樓業主, 熟悉昨天剛剛認識的鄰居, 深交來往了半年的牌友、 步友和舞友。
孩子們在水泥地上學習交際, 認識新朋友, 娛樂老朋友, 或暫時斷絕情誼, 明天以后再做好朋友。
保安一時間少了許多寂寞, 豐巢柜旁邊的快遞員, 情不自禁地放慢了分發速度。 也許, 她也想起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我偶爾也去旁觀他們的交流, 油然想起子產不毀的鄉校, 想起老家村口的平地, 平地旁有一條小溪, 一棵垂著胡須的老榕樹, 幾排光滑的石凳, 有閑聊的老人團, 有嬉戲的孩子幫, 深更半夜時, 還有戀戀不舍的小情侶。 平地還是村里聚餐的餐廳, 是由老人們主持的會議室。
因此, 遠行的年輕人, 一到年節關頭, 總會按時回歸, 而且是堂堂正正地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