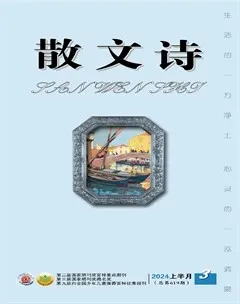我內心低矮的島嶼
◎席南凇
除了抵達
為了抵達, 你掏出湖心的一點白。
像往事浮在水面上, 有船經過時, 水就碎了。 那不滿足于成為一滴水的水, 還在夜晚繼續叫囂。
我問你: “過了這么多年, 你的疆土是否還能種出海棠花?”眼看著, 疆土越分裂越小, 壓在你名字上的眼淚, 已是禁忌。
總有人等待著被原諒。
脫下厚重的皮囊, 露出骨骼, 并無差異的, 在深秋, 凝視著一只麻雀。 你說: “看, 那只麻雀要降落了, 與海棠花的種子一起降落在腐朽里。 萬物的憂傷沉積在這兒, 內心干涸, 無論怎樣催促, 都發不出聲響。”
你說: “為了抵達結果, 我重新編排了開始, 但依然無法跨越黑與白的鴻溝。 是的, 我該堅貞地走上這條路, 使用自己的軀體、 承諾、 本我的定義, 來重新衡量生的價值。”
為了抵達真實, 你開始虛構。
“至今, 我沒有見過那扇只進不出的門。”
暴露在高原與高原的交匯地帶
靜靜地, 回望遙遠的光, 日復一日地照在故鄉的房檐上。
不斷重復的, 所謂的命運, 就這樣呈現了。
當我同朋友談起一種懷舊感, 仿佛是在高原與高原的交匯地帶灌滿回憶。 我突然記起, 火車站旁的一家面館被聒噪的喊叫聲籠罩著, 一如送別時內心的咆哮。
我牽過許多人的手, 也牽過河流的手, 往事零碎, 堆在廢舊的草場上。 微風吹過, 記憶里搖曳的身姿再次搖曳起來。
我暴露了。
我的故鄉被三大高原兜著, 搖晃, 我身處其間, 說不出來它具體的模樣。 一張看慣了的面孔, 如今是夏天的顏色, 也遠遠地望著千里之外的我。
而關于一個村莊的詩句, 一個女人注定要在村頭和村尾徘徊很久、 很久……
黑瑪麗魚
你不再是那條黑瑪麗魚。 那方寸之地, 數得盡的水草, 看得盡的陸地。
你不再用魚鱗來遮擋昆侖山北坡的雨。
一次次, 它們落在湖泊的眼睛——湖泊中的湖泊, 柔和而浩渺, 仿佛世界的終點就是這里。 悠揚的琴聲落在水中央, 將寂寥推得更遠……
之后, 水, 打開了你的鰓。
之后, 沒有誰可以阻止你長出腿來, 在水的利刃上直立行走。疲乏的時候, 你就坐在桑樹的果實上, 跟著一起紅, 或者白。
僅僅是一條黑瑪麗魚, 卻擁有了比夢還要寥廓的內心。
此時此刻, 另一條黑瑪麗魚從你身旁游過, 高喊, “褪去一身鱗片, 從繁瑣的秩序中跳脫出來的, 終將自由。”
你說, “在繁瑣的秩序中得以寧靜的, 終將自由。”
一只鳥的自白書
你叼著玉佛寺門前的枝條, 一路飛向深邃的黎明。 同時, 也將你狹隘的欲念隱藏在佛的慈悲里。
“佛說眾生, 我便是眾生。”
萬千生命濃縮在你的雙翼上, 振翅, 飛翔, 于油菜花地里誕下孩子。
死生之間, 這個巨大的黑洞常常槍聲四起。 子彈掠過你的羽毛, 擦出明亮的火焰, 最終把巢穴燒毀。 不僅僅你一個人的巢穴, 等到大海水漲時, 潮汐也睡在這里。
從豐盈到嶙峋, 漫長的流年間, 儲藏在你子宮里的風, 越來越小。 在人間這個沒有邊界的鳥籠里, 你持續地飛。 那些躲在紅色磚瓦背后的人們也持續地飛。
但是, 只要一想到在田地里耕種的婦人, 你的鳴叫突然有了意義。
年輕的槐樹
活著的年歲不足十年。
在門前站立的年歲同樣不足十年。 如今, 已經將大半的枝條搭在屋檐上了。
一棵槐樹, 也只有在冬天的時候才肯坦誠。 裸露, 無需緣由,在母親那間房子進進出出時, 它毫不猶豫地攔下呼嘯的北風。
母親挺直腰, 又彎下去, 把生命之水引到槐樹的表皮。
這就足夠了, 善與惡、 奉獻與索取, 在同一個女人的命運里不停地流轉, 為遠方的我埋下淺顯的伏筆。
雨來, 就長在喧鬧里;
雪來, 就長在沉默里。
而無論怎樣, 都用自己挺拔的身軀擋住了災禍。 正值夏季,我年輕的槐樹已然繁茂成陰, 與微風有了另一種神秘的誓約。
——“無法倒回去的, 我的體魄, 還未萎靡。”
——“我長居于人們的悲歡里, 即便常淋雨, 對生活, 還是一無所知。”
黑 犬
甚至沒有一個像樣的窩。
唯一一件墊在身體下的衣服, 還是去年冬天我從衣柜里翻出來的。
雪未消融的時候, 就堆在鎖住它的鐵鏈上。 鐵鏈橫躺在雪中,異常醒目, 而最醒目的, 還是它輕微的叫聲, 落在結冰的玉米稈上, 擲地有聲。
白的雪, 白的天空, 白的來路, 白的歸處。
黑的犬, 黑的枷鎖, 黑的瓷碗, 黑的洞口。
只是用手撫摸著它的背, 它便把前半生的秘密說了出來。 關于貞潔, 它說它夢見一只蝴蝶在稻田里留下印跡, 隨后就跟隨喜鵲奔向黃昏。
廣袤的紅色壓在蝴蝶和喜鵲的額頭上, 沉重, 卻堅毅, 于熾熱中獲得安寧。
我們的靈魂在相互觸碰的過程中有了停靠的位置, 或是墻壁的陽面, 抑或是羊群的玄關處。
從無到有, 水聲潺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