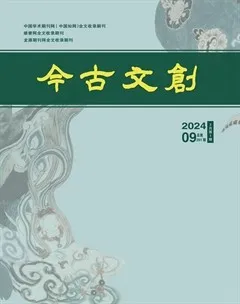框架理論視角下《詩經(jīng)·桃夭》的翻譯認知闡釋
崔連連


【摘要】自中西文化交流伊始,《詩經(jīng)》便是中外學者翻譯的焦點。先前研究多從翻譯理論、文學價值以及文化傳播角度分析《詩經(jīng)》不同譯文中的翻譯策略、意象傳遞等現(xiàn)象。認知語言學在翻譯研究中雖得到了廣泛應用,但與《詩經(jīng)》翻譯的結(jié)合還值得進一步探索。基于此,本研究從框架理論出發(fā),選取龐德和許淵沖《詩經(jīng)·桃夭》英譯版本為研究對象,闡釋譯文中存在的框架認知操作,涉及框架成分增添、刪減和更換。
【關鍵詞】框架理論;《詩經(jīng)·桃夭》;框架操作;翻譯
【中圖分類號】H315?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9-011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9.034
基金項目:認知語法視角下中外新冠疫情話語的神秘化機制對比研究(立項號:2021SS030)。
一、引言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文化“走出去”的底氣所在。《詩經(jīng)》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記錄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優(yōu)秀詩篇。孔子對于《詩經(jīng)》的思想內(nèi)容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的高度評價。故中西方文化交流伊始,《詩經(jīng)》一直就是各國翻譯學家關注的焦點。《詩經(jīng)》翻譯已經(jīng)有了三百多年的豐富實踐基礎,僅英語翻譯也有超過百年的歷史[6]。《詩經(jīng)》的第一個英譯選本始于18世紀,由Sir W. Jones完成,隨后即是James Legge、Ezra Pound等學者的英譯本,其中Pound的創(chuàng)意翻譯法為《詩經(jīng)》翻譯開創(chuàng)了新風格,對翻譯理論和文化傳播方面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9]。國內(nèi)學者許淵沖、汪榕培等也致力于《詩經(jīng)》英譯研究,傳播中華優(yōu)秀詩歌文化。先前學者往往傾向于從翻譯策略,如翻譯的原則、標準等層面探析《詩經(jīng)》的不同英譯本[12],雖得出許多意義非凡的研究成果,但未能回答為什么要使用那樣的翻譯方法、語言表達式等問題。隨著語言學理論被應用于《詩經(jīng)》翻譯研究,讀者經(jīng)歷了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過程[5][7]。認知翻譯學是翻譯學的一種新范式,重在回答“為什么要那樣翻譯”,探索譯者的認知過程,但鮮有研究將其與《詩經(jīng)》英譯聯(lián)系在一起,研究成果還未充分體現(xiàn),值得進一步探索。基于此,本文從框架理論出發(fā),對《詩經(jīng)·桃夭》翻譯的基本認知過程做出更加符合其內(nèi)在規(guī)律的闡釋,并對翻譯中一些在語言轉(zhuǎn)換層面上無法清晰解釋的現(xiàn)象做出更為合理的解釋,以龐德和許淵沖英譯版本為例。
二、框架理論
最初,F(xiàn)illmore[2]認為“框架”指與場景中各種典型實例相關聯(lián)的任何語言選擇系統(tǒng);后來,他多次對框架概念進行了修正完善,認為認知語言學中其他描述知識表征的術(shù)語,如圖式、腳本、場景、認知模式、民俗理論、觀念架構(gòu)等,都可統(tǒng)稱為框架,是“人類經(jīng)驗概念化的結(jié)果”[3]。總而言之,框架是具體統(tǒng)一的知識系統(tǒng)或連貫的經(jīng)驗在大腦中的圖示化表征,是譯者和讀者理解文本意義的背景參照[11]。
框架的構(gòu)成包括三部分,分別是特征—值、結(jié)構(gòu)常量和限制條件。框架的特征指框架范疇成員共有的某個要素[10],而值是特征類型的次概念。例如,在“學校”框架中,特征包括“教室”“老師”和“學生”等,其中“老師”的值有“英語老師”“語文老師”等。因此,只要激活了框架中的某個值或特征,則整個認知框架都會被從大腦中激活。框架的結(jié)構(gòu)常量指的是框架內(nèi)的特征在關系和概念上彼此高度相關,通常描述的是規(guī)定性的關系;而限制條件指的是在具體情境下,不同特征—值又相互制約[1]。根據(jù)上述定義,文旭和肖開容提出框架具有四大基本屬性[11]。層次性指框架系統(tǒng)由框架、子框架和成分組成,彼此相互依賴,協(xié)同工作;典型效應意味著特征位于框架網(wǎng)絡中的不同位置,有的處于中心位置,稱為原型特征,有的則位于邊緣位置;動態(tài)性指框架的修改和創(chuàng)建隨著語言的發(fā)展以及人類的經(jīng)驗而發(fā)展;文化差異則主要體現(xiàn)在不同文化和經(jīng)歷的人會激活不同的框架,也是翻譯存在框架成分操作的根本所在。由此可得,譯者理解原文和目標讀者理解譯文所激活的框架有所差異。所以,譯者翻譯時,通常會在概念層面上對原框架進行認知操作,以使目標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相同或類似的理解效果。其理論框架視角的翻譯認知過程基本模式如圖1所示:
在這一框架認知操作過程中,譯者首先進行第一階段:閱讀原文,通過原文語言結(jié)構(gòu)中的值或特征激活大腦中的知識系統(tǒng)和經(jīng)驗,產(chǎn)生原文框架1;其次進行第二階段:譯者根據(jù)目的語文化以及對目標讀者知識系統(tǒng)的預設,對激活的框架1進行框架成分操作,獲得譯文框架2;第三階段:譯者對概念層面上操作完畢的框架進行語言表達,產(chǎn)生譯文。由于中西文化的差異,所以翻譯中涉及的框架操作主要為非理想化的框架操作,包括框架內(nèi)部操作、框架層次調(diào)整、框架視角更換和框架移植。
三、《詩經(jīng)·桃夭》翻譯中的框架操作
賦比興,是《詩經(jīng)》中運用的三種主要表現(xiàn)手法,《桃夭》一詩運用比興的手法,通篇以桃花起興,以桃花喻美人。詩中既寫景又寫人,情景交融,是中外學者翻譯的焦點。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翻譯策略呈現(xiàn)的譯文也百花齊放。因此,了解不同譯者的翻譯認知過程,有助于讀者和譯者避免對文化經(jīng)典翻譯中的誤讀誤譯現(xiàn)象。因此,這一部分將基于圖1解釋龐德和許淵沖《桃夭》英譯本中存在的框架操作(見表1和表2)。
原文: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龐德譯本:O omen tree,that art so frail and young,so glossy fair to shine with flaming flower/that goest to wed,and make fair house and bower/O omen peach,that art so frail and young,giving us promise of such solid fruit/going to man and house,to be true root/O peach-tree thou art fair,as leaf amid new boughs/going to bride, to build thy man his house[4].
許淵沖譯本:The peach tree beams so red,How brilliant are its flowers/The maidens getting wed,Good for the nuptial bowers/The peach tree beams so red,How abundant its fruit/The maidens getting wed,Good as familys root/The peach tree beams so red,Its leaves are manifold/The maidens getting wed,Good for the whole household[8].
通過表1和表2可得,龐德和許淵沖《桃夭》譯本涉及的主要框架操作類型為框架內(nèi)部操作,涉及框架成分更換、增添和刪減。這體現(xiàn)在原文和譯文框架特征—值的數(shù)量的差異上,即讀者所能激活的知識系統(tǒng)的詳細程度與譯者不同,因而目標讀者或許無法獲得相同或類似于原文作者的理解和閱讀效果。因此,譯者翻譯時,需要對激活的原文框架1進行以下具體的框架操作。
(一)框架成分刪減
《桃夭》全詩分為三章,每章都以“桃之夭夭”開篇,以桃花紛紛怒放,色彩嬌艷比喻新娘的年輕嬌媚。故“夭夭”一詞喚起的原文框架1包含兩個,分別是色彩框架和植物的生長框架。色彩框架里指的是桃花的顏色特征——鮮艷,紅似火;植物的生長框架里指桃花已經(jīng)到了開花期,特點是紛紛綻放,茂盛美麗。龐德和許淵沖的版本在翻譯“夭夭”一詞時都進行了框架成分刪減操作,各有側(cè)重。龐德保留了通過原文激活的植物生長框架,將其譯為“so frail and young”,即綻放的桃花嬌嫩無比,但是刪減了色彩框架的特征。相反,許淵沖版本將其譯為“beams so red”,閃耀紅光,刪減了桃花綻放初期茂盛、生機勃勃的特點。此外,許譯本中還存在一處刪減處理,“有蕡其實”大意是桃樹果實累累,又肥又大,許將其英譯為“Abundant its fruits”,用形容詞“abundant”修飾果實特征,只實現(xiàn)了果實框架里“結(jié)實很多”這一特征,沒有表征“蕡”激活的“果實碩大”框架成分。原文是想通過桃樹果實累累,結(jié)的又肥又大象征新娘早生貴子后嗣旺,許譯本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表達效果。這一操作與許淵沖先生1979年提出的“三美論”有關,指意美、音美和形美。許譯本的兩處刪減處理是為了與前后章節(jié)詩句形成押韻,實現(xiàn)音美,但意美有所欠缺。龐德翻譯時還省略了詩句“之子于歸”中的“之子”,指這位姑娘,《桃夭》中指出嫁的女子,他用代詞“that”代替。這可能是譯者故意而為之,目的是與“that art so frail and young”中的“that”相呼應,由于目標讀者的認知框架里并沒有植物意象“桃花喻美人”的存在。所以,譯者是為了讓目標讀者意識到桃樹的形象代表即將結(jié)婚的美麗女子,這一譯法非常巧妙,符合龐德的創(chuàng)意性翻譯策略,把詩歌翻譯視為重創(chuàng)作,竭力表現(xiàn)詩歌在認知框架層面想要傳遞的內(nèi)容。
(二)框架成分增添
框架成分的增添是指為原文框架增添原先沒有的成分,對激發(fā)的框架進行補充,本詩指實現(xiàn)意象從靜態(tài)到動態(tài)的轉(zhuǎn)換,主要以龐德譯文版本為例。“灼灼其華”大意為花朵色彩鮮艷如火,描述的是一個靜態(tài)的意象。但龐德在翻譯時,將其譯為“glossy fair to shine with flaming”(閃耀著光芒),這顯然是對原詩歌“灼灼”框架進行增添,添加了“閃耀”成分,以至于讓目標讀者感受到桃花綻放,散發(fā)著光芒的美麗景象,這也有利于古詩意象英譯的傳遞。前文提到的“有蕡”,龐德將其譯為“Giving us promise of such solid fruit”,譯者通過增添“give”這一動作,旨在將桃樹擬人化,賦予人的動作特點。從而使目標讀者進一步將桃花與年輕嬌艷的女子聯(lián)系在一起,實現(xiàn)意象的傳遞。通過桃樹給人們帶來肥碩的果實比擬新娘為夫家添丁,后嗣旺。除此之外,龐德翻譯桃葉時也進行了框架成分增添處理,將“其葉蓁蓁”(原文大意為桃葉茂盛)譯為“Leaf amid new boughs”,增添“包圍著枝條”成分,側(cè)面襯托桃葉的茂盛,有利于讀者展開豐富的想象力。龐德通過巧妙地增添框架成分,不但減輕了目標語讀者的認知負擔,還促進了植物意象的跨文化傳遞。
(三)框架成分更換
框架成分更換指由于中西文化差異,譯者需要采用不同的框架成分來激活類似的語義框架,從而實現(xiàn)翻譯目的。譯者通常根據(jù)自己的背景知識、情感經(jīng)驗以及先前預設進行成分更換。因此,譯文讀者所激活的語義框架基本上是在原文基礎加上主觀解釋后的結(jié)果。龐德翻譯“桃樹”時,用“omen tree”更換“peach tree”。中國讀者閱讀原詩時,通過“桃樹”這一詞匯可以激活“美麗的姑娘”框架,因為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桃樹的寓意意象眾所周知,但是譯文讀者并不具備這樣的聯(lián)想。所以,龐德用“omen tree”,意思為“有預兆的樹”,目標讀者通過后文提到的“peach”就可以產(chǎn)生“桃樹象征某種預兆”的框架,從而獲得和原文讀者類似的意義理解。“宜其室家”,喜氣洋洋歸夫家,意思是為夫家?guī)砻篮蜌g樂。龐德將其譯為“make fair house and bower”,直接將原文框架成分更換為“夫婦美麗,房子漂亮”,這是因為原文和譯文讀者知識系統(tǒng)中存在不同的家庭框架成分,中國人的家庭結(jié)構(gòu)特點是大家庭,重視家族意識,但是西方家庭的家族意識比較淡薄,核心家庭占絕對的主導地位。基于此,龐德對此詩句進行框架成分更換是為了符合目標讀者的認知理解。許淵沖先生同樣如此,將原詩句譯為“Good for the nuptial bowers”,大意為祝福婚禮中的夫妻雙方,聚焦家庭框架中的小家庭。詩歌第二章節(jié)尾句“宜其家室”通過以桃樹的果實做比喻,意為子嗣興旺,激活生育框架。龐德和許淵沖在翻譯時,采用意譯的方法,將其更換為“To be true root”和“Familys root”,激活“家族根基”框架,含義由新娘婚后延綿子嗣轉(zhuǎn)向成為小家庭的根基,從側(cè)面表現(xiàn)女子婚后生兒育女,家庭得以穩(wěn)定的重要性。兩位譯者完美抓住了詩句的準確含義,并在此基礎上通過框架成分更換,使譯文讀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四、結(jié)語
《詩經(jīng)·桃夭》全詩以“桃花喻美人”意象為主線,從桃花到桃實,再到桃葉,三次變換比興,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興旺的景象。龐德和許淵沖的兩個譯本為了向目標讀者生動且有效地傳遞意象,都對譯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框架成分增添、刪減以及更換。研究發(fā)現(xiàn),根據(jù)翻譯策略和文化差異,譯者解碼原文后,翻譯時會對激活的原文框架進行認知操作;其次,框架操作是一種減少目標讀者因文化背景和知識系統(tǒng)差異造成理解障礙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框架操作有助于將譯者翻譯時大腦中的認知操作可視化,能夠解釋翻譯時為什么選擇不同的結(jié)構(gòu)、單詞等。總而言之,翻譯的框架操作是譯者在概念層面上的抽象表征,也是譯者進行具體翻譯實踐的語言轉(zhuǎn)換策略。
參考文獻:
[1]Barsalou,L.Frames,concepts and conceptual fields.In E.Kittay&A.Lehrer(Eds.),F(xiàn)rames,fields,and contrasts:New essays in semantic andlexicalorganization[M].
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Fillmore,C.J.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J].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1975:123-131.
[3]Fillmore,C.J.Frames and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J].Quaderni di Semantics,1985,(06):222-254.
[4]Pound,E.Shih-Ching: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M].New 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5]高燦.基于認知框架理論的《詩經(jīng)·國風》文化意象英譯對比研究[D].鄭州大學,2019.
[6]李玉良,王宏印.《詩經(jīng)》英譯研究的歷史、現(xiàn)狀與反思[J].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6,(04):36-39.
[7]梅龍.生態(tài)翻譯學三維轉(zhuǎn)換視界下《詩經(jīng)》英譯轉(zhuǎn)換效度分析[D].江南大學,2022.
[8]孫美琳,胡燕娜.從三美論視角淺析中國古代詩歌英譯——以《桃夭》的英譯本為例[J].海外英語,2022,(03):
33-35.
[9]王貴明.論龐德的翻譯觀及其中國古典詩歌的創(chuàng)意英譯[J].中國翻譯,2005,(06):20-26.
[10]文旭.框架與話語理解[J].外文研究,2013,(01):
27-33.
[11]文旭,肖開容.《認知翻譯學》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12]周一然.《詩經(jīng)》龐德英譯本的字符并置研究——以意合闡釋學為視角[D].南京大學,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