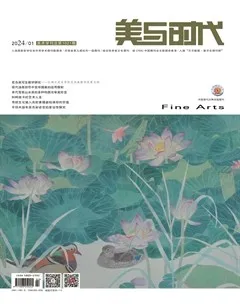探析虞世南的書法修為
摘 要:虞世南是“初唐四大家”之一,其書風溫潤如君子,端莊素雅,是初唐學習、繼承和發展“二王”筆法的著名書法家之一。他的《孔子廟堂碑》是對后世影響較大的書法作品,其書法著作《筆髓論》比較全面地反映出他對于書法藝術的理解。就其書法理論和書法實踐所表達的主要思想進行探究,同時對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行論證。
關鍵詞:虞世南;《筆髓論》;《孔子廟堂碑》;書論思想
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鼎盛時期在唐代,這個時期,書法受到極大重視,各具特色的書法名家輩出,理論研究也十分興盛,出現了許多具有針對性的、系統性的書法理論著作。在唐朝書論中,對于書法技法的總結和創作規律的把握成為主流內容,出現了明顯的“尚法”風氣。虞世南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并稱“初唐四大家”,他的書法作品溫潤秀美,學承魏晉筆法,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對后世的影響較為深遠。同時,其在書法理論上的成就也很顯著,為書學者較為熟悉的《筆髓論》是其代表作,較為全面地反映了虞世南對于書法的理解和感悟。
一、虞世南生平簡介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人稱虞永興,越州余姚(今浙江慈溪)人,是歷經南北朝與隋唐時期的文學家、政治家、書法家、詩人。虞世南從小就志向高遠,學業精進,與其兄長在吳郡顧野王(南朝文字訓詁學家,其編撰的《玉篇》為現存最早的楷書字典)門下學有十余年,后跟從智永學書,繼承王右軍筆法,又受王獻之書法的影響,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宣和書譜》稱其書法“內涵剛柔”。張懷瓘在《書斷》中將虞世南的隸書和行書列為妙品,評價“其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容秀出,智勇在焉”“君子藏器,以虞為優”。
虞世南曾在弘文館任教,所以他對后代書法的影響首先體現在教育事業上。作為書法家,他的《孔子廟堂碑》《破邪論序》《汝南公主墓志》都是極其優秀的作品;作為政治家,他不僅德才兼備,而且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唐太宗十分賞識他的才華,常邀他共同探討和學習書法,曾言其學識、文詞、書法均是當朝一絕。
二、虞世南《筆髓論》主要思想
虞世南在書法理論方面之所以能夠做出遠超于同時代其他書家的貢獻,是因為他是一位有著獨特思辯能力的書法理論家。其傳世的書法理論著作有《筆髓論》與《書旨述》兩篇,特別是《筆髓論》,對后世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這篇文章系統地將書體的結構特征、書寫法則,以及運筆方法歸納為敘體、辨應、指意、釋真、釋行、釋草、契妙等七則,詳細論述了書法功能、創作狀態等,其中獨特的比喻、書法的發展及對當朝流行技法的分析都十分精妙。以下是對《筆髓論》中三個重要思想的探析:
(一)“得之于心,應之于手”,講求心悟
虞世南在文章開頭“辨應”一則中,將心比作君主,手比作宰相,宰相應該輔助君主治國理政,同樣手也應該順從于心,這樣便清晰地闡述了虞世南對于心手關系的理解。可以說,書法創作在根本上是書寫者心理變化的過程,一件書法作品中,重要的不僅是內容和技法,能夠寄托、體現書者的情感和審美觀點也是一件好作品的重要條件,“輕重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就是強調了“心”的本源作用。
對于“心”在藝術中的主導地位,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認為藝術是人心靈的物化,從這里也能看出藝術創作是心靈的反映,作品是書法家對于書寫的理解和審美情感的展現。鄭板橋曾強調“成竹在胸”,也就是要展現“胸中之竹”,所謂的“胸中之竹”實際上就是創作者將自己的心中所想物化之后,再用藝術的手法創作出來,以繪畫作品的形式展現在世人面前,以此也說明了“心”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性。因此,在書法創作上,“故知書道玄妙,必資于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以心悟,不可以目取也”。虞世南認為,創作一件好的書法作品需要“心”有感覺,不能強求,技巧也需要在“心”里感悟,只是看是得不到的[1]。
在“敘體”一則中,虞世南提到王羲之、鐘繇、張芝等著名書法家,并對他們高度贊賞,評價他們“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虞世南認為,體悟書法之“妙”應該是在一種“神遇”之后的“玄妙”,不是“目取”“力求”所能夠得到的,而是要進行“心悟”。悟出來的也并不只是書法的某一技法,而是運用書法藝術來表現自然界萬事萬物之美的藝術本質。同時,在書法創作中要做到心正,“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對于此觀點,宋黃庭堅十分認同,他提出“心正則筆正”的說法,他們都強調“心”在書法創作中的主體地位,“心”的狀態影響著手、筆的狀態。因此,在虞世南看來,要想創作一幅優秀的書法作品,既要有得到“神遇”之后的“心悟”,又要排除雜念,使自己達到心平氣和的狀態。
(二)精準總結真、行、草三體書寫特點
在《筆髓論》中間部分,虞世南針對真、行、草三種不同書體在創作上提出不同的理解和要求,分別從“釋真”“釋行”“釋草”三則來論述其特點和規律。虞世南認為,一支筆不能超過六寸,寫字時拿筆不能超過三寸,其中真書一寸、行書兩寸、草書三寸,做到“指實掌虛”,以便靈活運轉。此外,還談及他寫真書的經驗,寫正楷的時候要“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問巨細,皆有虛散”,即字的體態要像八分書,筆勢應如同章草,但是各有妙趣,不管大小,都應該有空靈虛散之氣。他對點畫的要求十分嚴格、講究,強調行書與真書的區別,行書“至于頓挫磅礴,若猿獸之搏噬,進退鉤鉅,若秋鷹迅擊……旋毫不絕,內轉鋒也”,點畫間的連帶關系較多,行筆速度也比真書快。他借用王羲之的話,“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于輪扁”“自然勁健”,強調筆畫連帶猶如游絲一般似斷非斷、似連非連,自然有力。從虞世南對行書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其對古法的看重和繼承,同時,再次論證了心手“輕重出于心,而妙用應乎手”的關系。
對于草書,他主張:“懸管叢釓,柔毛外拓,右為外,左為內,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即筆管要懸起來,筆鋒合攏,用柔軟的長毫展現筆毛開展的效果,運筆時筆鋒藏在點畫中不外露。自古以來,草書用筆講究節奏,輕重緩急,有快有慢,起伏頓挫,方能反映書家對書寫的控制和技法的精妙,并且體現自然之美[2]。草書相比于真書和行書,更能體現“氣雄不可抑”“勢逸不可止”的奔放特點,更利于釋放書家個人情感,也更能達到“縱狂逸放,不違筆意”自由揮灑和酣暢淋漓的感覺。
筆者認為,虞世南對于書法創作時“心”的狀態要求是非常高的,動筆之前不僅要先調整狀態,“不疾不徐”“平心靜氣”,還要心有所悟,達至高深意境,從而進入自由創作的境界。
(三)沖和之美的中庸思想與道家無為思想
《筆髓論》這篇文章根植于儒家思想,兼含道家的無為思想。虞世南在“契妙”一則中提出,“正者,沖和之氣也”,反映出唐朝初期的中庸思想。他不僅強調以儒為規,學習修身,還強調文字為政治服務的重要作用。
在唐朝極其重視儒家思想的背景下,書法藝術在表現形式上追求中庸思想,不偏不倚,恰如其分。虞世南崇尚孔子“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思想,認為書法也要崇尚簡約之風,不能太過張揚,也不可太過內斂,講究恰到好處的美。要在書法的矛盾之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使之得到緩和,整體呈現和諧共生的狀態。同時,虞世南認為“契妙”一則中的“妙”,是書法在以特殊的方式來展現自然之美和客觀世界的魅力。因此,他所言的沖合之美,從根本上看,是儒家思想對書法藝術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建立在儒家中庸思想基礎上的。
此外,“契妙”中還體現了虞世南“無為于書”,以求“神遇”的創作觀念。強調在書寫時,要保持心態的平和,追求自然無為的心理狀態,這樣才能寫出“神遇”之下的精妙作品。這與宋蘇軾強調的“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的論調相一致,這種無意間的、不帶有目的性的書寫是虞世南所崇尚的,這種思想與道教“道法自然”的思想一致。虞世南提到“心悟非心,合于妙也”的觀點,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莊子“耳止于聽,心止于符”的思想[3]。也就是說,“心悟”不僅是心智,還要通過感悟去深刻理解,達到妙境,此為中國書法所具有的獨特的美學思想。
三、從《孔子廟堂碑》看虞世南的書法實踐
虞世南的《筆髓論》闡述了他對于書法藝術的理解,《孔子廟堂碑》則是他具體的書法實踐。《孔子廟堂碑》雖然整體很茂密,但不會使人感到局促,反倒呈現出淡雅、靜穆之氣。此碑楷書結字瘦長,上緊下松,形體外鼓,字間疏朗;用筆圓勁含蓄、溫潤雅致,轉折以圓為主,線條變化簡潔,對比微妙,起落輕巧,以任自然,內含筋骨,筆勢舒展,有道逸之姿。虞世南的楷書有一股“正氣”,看上去中正平和,筆畫之間舒展自然,每一筆既有力量感又不會讓人覺得死板呆滯。并且讀這本帖時還會有一種恬淡的感覺,像是嘈雜世界的一片凈土。整體來看,該帖以含蓄取勝,沒有任何的刻意造作和濃妝艷抹,完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講究的是水到渠成,給人一種柔和雅致、舒朗從容的感覺。從其中和緩而從容的筆調我們可以看出,一筆一畫都是在平靜中徐徐展開,流露出一種純粹的寧靜。這種深沉自然的寧靜,并不是死水一潭,其點畫的組合安排就像一位位君子,謙和而高雅。這就是虞世南書法的獨特之處,這種不愿與世俗同流的隱士之感,是不染世俗的道家無為思想的表達,與《筆髓論》中所體現的道家思想一致。并且在這本帖上我們能感受到的自然萬物的大氣之美,也深受道家的影響,是“取法自然”“師法自然”的表現,和他在“契妙”中“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的說法相符。《孔子廟堂碑》起筆露鋒,行筆中鋒,最后收筆又回鋒一轉,加重突出主筆。虞世南對于楷書的寫法,多運用轉筆,讓字看起來堅實有力,更有氣勢,并且虞世南的書法妙處在于他將楷書與行草的特點相結合,在布局上一反以往十分整齊的格局,而是稍加錯落,以呈現一種透氣的效果,這一變化在當時書法界是具有開拓精神的創新。
仔細閱讀《孔子廟堂碑》,會產生很多感悟。筆者讀后有一種如同春風拂面般的舒適、從容和自在,不緊不慢,隨遇而安。這就如同老莊思想的平靜恬淡,為人處事波瀾不驚;也如同武俠小說中的高人,表面看上去招式普通,若將一刀一劍分解來看,卻是化繁為簡后的高度提煉,能以不變應萬變。虞世南在楷書中結合了草書的用筆節奏,即將“起伏連轉,收攬吐納”的節奏融入楷書中[4],使得《孔子廟堂碑》的字與字之間給人一種絲絲連連、似斷不斷的感覺。并且我們在此碑上感受到的平淡不是一成不變的單一,而是一種整體的協調感,這與他在《筆髓論》中提到的沖和之美的中庸思想是一致的。在局部方面,他將字體大小處理得符合自然規律,從中可以看出虞世南對于書法的深刻理解和細節的精準把握。
在此碑中,我們之所以能體會到恬淡靜謐感,是因為虞世南做到了心手統一,字里行間透露出他的所思所想,達到了“得之于心,應之于手”的境界。當然,這與他的取法有很大的關系。虞世南用筆取法“二王”和魏晉時期的莊嚴,我們可以明顯地體會到虞世南筆下“內斂”的特點。此碑與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相比,褚遂良的字跳宕明顯,對比強烈,有一種年輕的朝氣和活力。而虞世南的字不同,他的字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君子之氣,柔而不弱,剛卻不鋒,外柔內剛,剛柔并濟,就像他本人一樣“君子藏于器”的大氣智慧[5]。他能達到這種境界,必然是明了了自然界萬事萬物的規律,又得到了“神遇”,在優秀書法作品創作中做到了他所說的以“心”為主導。筆者認為,虞世南在創作《孔子廟堂碑》時,應該是心如止水、波瀾不驚的狀態,因為從他這幅作品中看到了這種看似平淡但堅韌無比的豐富內涵,一筆一畫都淋漓盡致地透露出他獨有的書風。可以說,虞世南真正做到了人品、書品的高度統一,同時他在書法理論上的成就也實實在在地得到了后人的認可和傳承。
四、結語
虞世南的書法理論與其書法實踐基本是一致的,他的書法作品對后世書家書風形成有很大的啟迪作用。其《筆髓論》中對書法藝術的理解和創作的感悟,為我們當下書法學習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研究方向。《孔子廟堂碑》中所體現的書法技法和創新思想,值得我們仔細品鑒。筆者認為,以“絢爛之極復歸平淡”來評價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最為合適,這種看似沒有任何奪目技巧的表達方式,才是真正至高的技巧。作為當代的書法傳承者和學習者,我們應該在復雜多變的現代社會中靜下心來,細細品讀虞世南的作品,品味這種樸素淡雅的魅力,從中得到一些力量和思考。
參考文獻:
[1]王敬姍.虞世南《筆髓論》中的書學思想探究[J].美與時代(下),2017(5):69-70.
[2]李雪莉.論虞世南書法的美學思想[J].語文學刊,2011(15):107-108.
[3]鐘月亮.道家思想影響下的初唐書論研究:以《筆髓論》和《書后品》為例[J].書法,2022(8):77-79.
[4]孫南南.淺談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書法研究[J].現代婦女(下旬),2013(2):162-163.
[5]章莉.溫文爾雅 渾然天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賞析[J].七彩語文(寫字),2013(5):12-14.
作者簡介:
王宣懿,暨南大學藝術學院學生。研究方向:古代書畫鑒賞、書法理論與實踐研究。